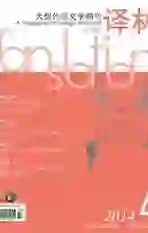温室
2015-01-13

逃跑一周。
开始,一切还顺利。第一天傍晚,有些冷。只见匕首寒光一闪,一个倒霉鬼慌忙双手奉上钱包,一边哭喊一边求饶:“求你别杀我。”还使劲摘下婚戒奉上;凯利正是因为这个才揍他,打断了他的鼻梁。但是凯利没有拿刀捅,他可不需要一具尸体。凯利是在法院外趁乱跳下囚车逃脱的。一英里开外一个浑身刀伤的人或许会告发他,说他还藏在布朗克斯。
他的通缉令遍布全区大大小小的警局,想必每个警察都知道。他原本打算,就算有天大的危险,也要回到南方,回到自己的家。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因为发现了那片小树林。
他用那倒霉鬼的钱从破旧的慈善超市买了身连体衣裤和宽松夹克,换下那倒霉鬼的大衣,现在不需要用它来遮挡身上的绿色囚服了。吃的东西,不论咖啡还是巨无霸汉堡,都是那个笨蛋“请客”。在这个冬夜,凯利走出慈善超市,像一具行尸走肉漫无目的、步履蹒跚地走着。别看我,你不看我的话我就不会看你。最后他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铁栅栏前。身后是韦伯斯特大街,砖砌的围墙高高的,连墙内的树似乎都在盯着行人。就你和我,伙计。好在冬天天黑得早,夜色给凯利翻墙提供了保护,不绝于耳的汽车声也恰好掩盖住他翻墙落地时踩压枯枝败叶的声音。
五天来,每晚他都露宿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洞里,盖着树叶,一动不动地窝在从慈善超市买来的睡袋和油布里。每天一大早他都首先藏好睡袋和油布,然后等到植物园门开以后出去。为避人耳目,他会故意选择从不同的门出去。不过有一次经过门口,一个门卫眯着眼瞟了他一下;从那以后他都有意避开那道门。好在其他门的门卫从没有抬眼看过他,对他们而言,他只不过是喜欢在冬日早晨来植物园散步的某个人。
布朗克斯街上很脏,1月的天气也阴沉,不过对他的藏身和行动倒很有利。在风头过去之前,他只能暂时尽量用这些旧衣服保暖。这里太冷了,真见鬼,刺骨严寒,甚至冷到让人眼泪不断。今冬是历年来最寒冷的,连报纸头版头条都这么说。派派斯、肯德基或其他快餐店的炸鸡和牛奶咖啡,让他勉强维持着生存。在快餐店,他只能无所事事地坐在冷冷的日光灯下瞪着周围的人,他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他感到耳朵滚烫,而脚趾麻木的感觉事实上他已经习惯了。
第一天临近傍晚,他来到一个图书馆门口,鬼使神差地溜了进去。这儿很破旧,但是除他以外还有人在里面溜达。图书管理员都是热心助人的,但是他们通常不问世事,从不去看通缉令什么的,对他这样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向他推荐一本介绍佛罗里达景物的书,来愉悦放松心情,但是这本书让他心里很难过。他哪里需要看家乡的介绍,那些鹈鹕、棕榈树、寄生藤、长叶松,他简直如数家珍,还能列举出更多呢。但是现在他不能回去,太危险了,要回去也得等到风声过了以后,等到人们淡忘了他,或者相信他已经远走他乡的时候。
昨天晚上,天气干冷,风渐起,凯利从空气中嗅出一种新的气味。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塞在睡袋、油布和树叶中。周围一片寂静,但所有东西都好像带有一丝恐惧在等待着什么。他睡得并不踏实,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醒来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睡袋上,有些沉,又听到远处类似于海浪的咆哮声。他缓慢地从树根下面的洞里爬出来,被眼前从未见过的白色世界惊呆了。象牙色的“山丘”,蛋壳色的“波浪”,还有粉灰色的“土丘”压着树枝。银色的鹅毛大雪从低沉的天空中纷纷扬扬飘落而下,海涛般咆哮的风肆虐无阻,冰冻像刺一般扎着他的脸。他现在有麻烦了。
睡袋上是树叶,树叶上面是油布,油布上有厚厚的积雪。即便你可以当雪不存在,窝在睡袋里,但是从睡袋出来了就不能再爬回去,因为如果回去就会把雪带进去。雪融化后结成冰,到那时你就像躺在冻透了的土坑上。一旦出去,回来就不可能了。
突然,一阵狂风吹过,雪从树顶上咔嚓坠落。他把帽子压低,胳膊抱在胸前。冷风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的衣服可不是因为迎接这场暴风雪而穿的——盖住绿色囚服的连衣裤,宽松的夹克,靴子。他没有洗漱整理一番,但谁会在这种条件下拾掇自己呢?这个地方每年都不断有冻伤、冻死的事情发生,以前怎么还会有人决定住在这里?所有的绿叶,所有的花——红的,黄的,紫的,纯色的或者杂色的,小的或者大的,娇嫩的或者粗壮的,都已经凋零。鸟儿也基本绝迹了,留下来的也避免不了饿死、冻死的命运。这种环境下,即便没有祈祷的习惯,你也不得不在每年的等待中,虔诚祈祷生命重新回来。
但如果在家乡,空气则是温暖柔和的,所有东西都生长旺盛。你还得尽力不让它们生长,才能在那片过分繁盛的长势中给自己留下一个角落。你要小心提防着,否则你一转身离开,杂乱的东西就会生长出来湮没了属于你的寂静角落。
而这里呢,所有一切都已经终结。你也会发抖,就像他现在这样。因为寒冷,因为饥饿,因为恐惧。八年来,包括在监狱的最后四年里,他一直在发抖。这样的寒冷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让人感觉很沉重也很寂静——正如他杀她的时候。回家,他还能拥有那个角落吗?
不能。为什么不能?如果一切都处于温暖祥和、宽容开明的氛围中,那么她当初无论是挖苦他还是背叛他,他本可以都当作是开玩笑。回到家,他就会大笑,然后走出去,留下她一个人在那里发怒,尖叫,扔东西。他则会找到另外一个海滩,丛林,总之只要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就好。
这里,除了寒冷,什么东西也没有,白色天地间看不到任何东西,他脑子里只有她。
他闭上眼睛,沉浸在回忆中。他面部僵硬,手指发烫,他必须要离开。
雪,令人惊奇的东西,这么厚实,这么沉重。脚陷进雪里还会打滑。光线摇曳,给人厚重感,虽然是白天,但你却无从知晓。经过和这些齐膝的积雪艰难的抗争,他终于挪到了门边。门锁着。门外没有车辆,轨道上也没有火车,暴风雪太大了,植物园没有开门。凯利知道他不能在刺骨寒风中爬围墙,无论戴不戴手套都爬不了。而且,他都找不到任何理由翻墙出去,外面既没有人做巨无霸汉堡或者炸肉丁,阅览室也没有美貌的姑娘。
现在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躺在这里等死,老实说这主意不错。他们说这很舒服,最后满心温暖地被冻死。也许这只是个选择。要么找一幢楼避寒,他以前一直远离高楼大厦,怕被发现,怕被认出,但是现在冰天雪地的,谁会去管他呢?endprint
远处有一个大温室,像个圆形土丘。迎着刺骨寒风,他深一脚浅一脚费力地往那儿走去。这条路很漫长,可隐隐约约中他还能看到盘旋于白色雪花之中的温室中心圆顶。他不知道那儿的门窗是铁的还是玻璃的,但他知道肯定锁好了,所以温室未必能进去,然而那样的场所一般来说都会有车库、垃圾场、维修房和仓库之类的地方。只要一个带着屋顶的地方就很好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会碰到带暖气的呢。
温室在坡上,走了一会儿似乎看不到头,他几乎放弃了。但突然他开始非常生气。就是她的主意要到北方来;就是她想要来他才会在这;也正是因为杀了她,他才会在这儿这么受罪,在寒冷的山坡上走得肌肉酸痛,两脚冰冷。也许回家后他会考虑自杀,这样他就再不用担心遇到这么艰难的处境。得诅咒她,诅咒她下地狱,以前他没有如此痛恨她。
雪从拱形玻璃屋顶滑落。他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向前走,路上不断摔倒在雪地里,又不断爬起来,继续艰难行进,一直走到温室附近。他冻得直流眼泪。就在此时,一道夺目的光束刺穿茫茫白雪。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看,居然看到了汽车灯光。他以为自己发疯了,严寒和冷风已经把他逼疯了吧,所以他才会产生这样的幻觉。真的是汽车?它靠近了,并没有消失,那可不是海市蜃楼,而真的是车子。他看见一辆履带式全地形车在这片冻土上轰隆隆前进,路过他附近也没有停下来。开车的人也许没看见他,或是看到了没在意。车缓慢前进到了温室门口,发出轰的一声后停在一边。一个身穿深色派克外衣、脚蹬深色靴子的女人从车上跳了下来,金色头发如雪花般随风舞动着。她拨开头发,走到了门口。她是要开门吗?
她打开门进去了。他悄悄尾随其后,走到车旁。这车不是他的幻觉。他慢慢绕着车边走边观察着,不知不觉走到温室门口——也就是在这儿,那个长发女人消失不见了。他停下脚步,透过飞雪突然看见温室玻璃亮了起来,这亮光着实吓了他一大跳。一定是她,是她把灯逐一打开的。开始是温室两边的灯先亮起来,接着最高圆顶也亮起来了。她打开灯后就转身向温室中心走去。
他的手冻麻了,只能吃力地去握住门把,然后一把将门拉开溜了进去。进去之后,他随手关上门,这样一切声响都被关在了门外。

开始他感觉到周围一片寂静:没有狂风的咆哮声,没有暴雪发出的布匹撕扯声。他感觉到的是安宁:没有暴风,连地面也显得很安静。慢慢地,意识到不需要再和任何东西作斗争,他感到全身都轻松了。手套湿透了,帽子也冻得硬邦邦的,他脱下了手套和帽子。一会儿工夫,耳朵和手指暖和起来,也恢复了知觉,他才开始感觉到疼痛。眼睛不舒服,直流泪,他又从口袋里翻出一张旧餐巾纸擤鼻涕。低头一看,从衣服上滴下的水越积越多,已然形成水坑。
这时不知道从哪里飘过来一阵沁人心脾的香味。哦,天啊,这气味甜甜的、辣辣的、润润的,充满着生命活力。这里连泥土都是温暖而又潮湿的。橘黄色的花朵努力向空气中散发着各种香气,仿佛在期待人们能培育出更多美丽的花来。我发誓,如果有可能我会这么去做的,这些花多美好啊。凯利想。就应该都种上这些花,让它们遍地开放,甚至应该一路向北开放。用它们温暖的色彩、怡人的芳香和无限的慷慨去驱逐这死亡的苍白。
他满心欢喜地站在这些兰花、栀子花,还有大堆不知名的花中间,贪婪地吞咽着潮湿的香草气息。他不是园丁。当然,回家以后也没必要成为园丁,再说了,回家以后这些植物也不需要他这样的穷人照料。这里的花儿必须得有花盆、滴水器、灯光和高玻璃墙,好让它们避开恶劣的天气,远离过早的黑夜,躲过寒冷的狂风。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慷慨的气度如果过于柔软,则不得不需要人们加倍去呵护。
他开始往里走,想走到这个地方的中心。他想走回家。
每迈进一步他都越发感觉温暖,感觉开心,也更加像是在做梦。但当来到中心的空旷地带时,他意识到自己开始想得太美好了。
这里的植物树叶硕大,呈扇形,栖息在巨大棕榈树下那些高低不等的小土丘上,颜色碧绿,和家乡的植物一样,迎风摆动着。但这绝对不是微风。凛冽刺骨的寒风钻进了玻璃房,夹杂着半融化的雪花飞舞着,最后落在这些高高的棕榈树叶上,就像下雨一样,但又不是完全像雨。凯利缩着脖子,退了回去。他憎恨这些东西破坏了他原本美好的想象,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走到温室圆顶附近,他感觉到温室也似乎在阵阵疾风中甘愿俯首称臣,东摇西摆。
他听到了声响。那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高处温室顶部豁口的狭长走道上走着。他看到她伸手去碰了一下什么,马上又跳了回去,接着锯齿般的玻璃掉了下来,落在离他不远的地面上,碎玻璃的回声不绝于耳。
她在小走道上忙碌着,又爬到高处。机器轰鸣,升降机降低了。一个四角的宇宙飞船似的东西,从枝枝丫丫和摇曳的树叶里直接降下来。凯利急忙躲进棕榈树粗壮树干的影子里。
女人从升降机的吊篮里跳出来,拨开脸上乱蓬蓬的头发,随手丢下手套,然后掏出手机,“莱昂?”
“是的,”电话那头很嘈杂,噼里啪啦的,“情况严重吗?”
“两块玻璃掉了。还有一些碎了,至少需要四块。橡树的一根树枝也断了。”
“完全坏了?天哪,一定是这风造成的。”
“不是暴风雪,简直是飓风。”她气喘吁吁地说,好像自己正身处风暴中心。
“如果是飓风,”电话里声音很小,“那不会有问题。”
“是的。莱昂,雪太重了,碎玻璃随时会掉下来。”
“雪没有融化?”
“太冷了,雪下得太快。”
“糟糕。你得弄点什么上去盖住。通知保卫室的人了吗?”
一阵刺骨冷风裹挟着雪花毫无理由地翻滚而进,满含敌意。凯利都能感觉得到气温骤降。
“只有一个人能够过来,”她说,“那就是威尔逊。”endprint
“哦,他娘的,那个纳粹?”
“他已经在路上了。但是他不能爬高,按照劳动合同规定,我不能强迫他去爬高。”
电话那头一阵模糊的噼里啪啦的咒骂声。
“我打了电话给苏珊,”她说,“她在到处打电话问附近有没有义工来帮忙。”
“那你自己一个人不行?”
“不行。”她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呆呆地看着上方。凯利看到棕榈树都冷得簇拥在一起。它们困在这里,一个不属于它们的监狱,扎下根无法逃脱了。它们本不该生长在此。如果上方的破洞一直敞开它们就会死掉。
“我要再打几个电话,莱昂,看看是否有人能帮上忙。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好。天啊,祝我们好运吧。如果他们能清理路面……”
“对,一会儿再说。”她打断了他的话,开始摁按键。猛烈的旋风摇晃着温室四周的墙壁,要把雪从洞里铲进来。她抬头看着棕榈树,凯利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恐惧,同时也看到了关爱之情。
他上前一步,“约翰·凯利。”
她转过身。
“义工,”他说,“接到电话后过来的。”
她脸上满是疑惑,“你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我就在韦伯斯特住。”
“你怎么……”
“门没锁。”他用大拇指朝身后比画了一下。她没说话,看了看他不合身的夹克,破旧的靴子,还有几天没刮的胡须。“你遇到困难了,”他指着上方,“最好把它堵住。”接着又说,“苏珊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这是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她能相信他吗?也许她无所谓是谁,只要能帮上忙就行。
她上下打量着对方,“你爬高没问题吧?”
他们从工具房里拿来了油布、绳子和木板,一股脑放进升降机的吊篮,然后爬了进去。
“我们必须灵活应变。”她拨动开关,吊篮开始缓缓上升,“这些木板上有螺栓和钩子,以备不时之需。这么多年来,还从没有出现过如此紧急的状况。”雪从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洞口大量落下。“我们把油布连起来,然后用木板撑住。我开了暖气,只要风雪不是持续时间太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她担忧地看着周围不断经过吊篮的树,然后对他挥了下手,突然笑起来,“简·莫尔斯,园艺师。”她主动伸出手。
“约翰·凯利。”他不得不这么说,因为他之前已经自报家门了。现在他很懊恼自己那么诚实,他觉得不应该说实话的。但是在这种氛围里,在她真诚的眼神面前,他已经毫无防备了。“你一定也住得很近。”
“恰恰相反。风暴来的时候,太远了赶不回家。当时在办公室。”
“那你当时很担心。”他说,因为他知道一定如此。
“嗯,我那时是担心,也确实应该担心。”
“那你应该不会听到——断裂声。”他不得不提高音量,他们离洞口和风暴越来越近了。
“没听到,是温度警报器,在我办公室响了。”她面向肆虐的风雪,眨眨眼睛,让雪从睫毛上落下。升降机颤动着,缓缓升高,最后停了下来。“等一等。”她对他说,从吊篮里跳出,小心翼翼地走在小道上,检查着洞口,风呼呼地灌进来,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回头朝他大喊:“要不从这儿开始……”
他从来没有这么卖力工作过。她和他一样强壮。他的强壮是因为监狱的经历,而她的强壮来自于内心的压力或者决心。雪在脖子上融化开来,冰刺痛着他的眼睛。风猛刮进来,打着旋,时而托着时而摇晃着圆屋顶。小道上因为融化的雪变得很滑。他们用折叠刀在油布上挖出几个洞以便让绳子穿过,举起油布仿佛在大风中航行。他使出浑身力气搬起木板放在油布和绳子中间。他们靠呼喊、手势来交流,像海员在大风中那样。突然,在接过木板的时候,他脚底打滑,整个人撞在吊篮扶手上。他感觉到她马上死死地抓住他的夹克。如果不是因为她,他就会翻落下去。“谢谢。”他说,声音随即消逝在风中,但是她心领神会。他们继续工作,弯曲着一条腿去拉绳子一端,掖好飘动的油布,用冻得发紫的手指把绳子打结。她前额破了,在流血,但是她没有注意到。
他大汗淋漓,浑身酸痛,感觉温室里的混乱减退了。他们又推了几次木板,拉了一次绳子,然后肩并肩坐在临时修建的“防护坝”旁边。头顶上,油布层层覆盖着,并且用板条固定好了,虽然在风中不时发出声响,但是洞的位置和窗玻璃坏的地方都被堵住了,没有问题。凯利感觉温度上升了。
一个美妙的声音:“真丑。”她摇晃着脑袋,指着他们的“杰作”笑道。他抬头看了看。
“你的意思是我们本应该做个艺术品?”他抱着胳膊,“真见鬼。”
她笑了,看着他的眼睛。“真的,”她说,“谢谢你。”
“嘿,真有趣。”
“有趣?”
“好吧,很糟糕,但是——”他耸了下肩,环顾四周,“我是南方来的。”
她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我在这里一直照料它们已经八年了。有些树很稀有,也很昂贵。”
“但这不是重点,不是吗?”
她再一次直视着他,“是的。”她的眼睛竟然那么蓝,像风平浪静的海面那样闲适。
他也笑了起来,举起手,在她额头的伤口处停住了,“最好处理一下。”
“什么?”
“你受伤了。”
“我?”她很惊讶地去摸额头,发现有血迹,不禁大笑起来,“好,”她说,又最后检查了一下他们的成果,“我们可以下去了。”
他们爬进吊篮,把材料都扔在了小道上。
升降机缓缓下降的时候,她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
她微笑着听着。义工,他说过他是义工。他接到了个电话才来的。他该怎么回答呢?在这样的地方,义工都是什么职业呢?
“很多事,”他最后说,“乱七八糟的,你也知道。”她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他不希望她怀疑什么,于是又说:“我做些瓦工活,比如临时的护栏之类。”endprint
她点点头,似乎刚要说些什么,这时候下面有人大喊:“莫尔斯博士,是你在上面吗?”
他们从吊篮扶手边望过去,一个身穿制服的人在下面伸长脖子,枝叶遮住了他,看不清楚。“当然是我!”她大声回答,很厌恶的语气。“威尔逊,”她平静地对凯利说道,“一个混蛋。”
得小心威尔逊。当他们到达地面时,他发现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和你在一起的是谁?莫尔斯博士,你知道你和我有协议在先,你不能请其他人,你……”
“别说了,威尔逊。这是约翰·凯利。”千万别告诉他我的名字!“一个义工。他在帮我堵住洞口的时候差点丢了性命。这种事你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请你闭嘴。”她从升降机的吊篮里跳出来,狠狠瞪了门卫一眼。他脸红了。她马上转过身,艰难地爬上落满枝叶的小土丘,检查受伤的棕榈树。
门卫红着脸有些尴尬地整理了下衣服。他愤怒的目光越过她的背影和她狂乱的头发,投向了凯利。“约翰·凯利?”他轻轻地念叨着这个名字,眯着眼。见鬼,他就是那个门卫。
凯利也从吊篮里爬出来,对一心挂念着植物的园艺师说:“我有事要离开,去看看……”
“凯利!我就知道!”威尔逊的狂叫声中充满着喜悦,让人作呕,“警察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他们要抓你回去,小子,赏金很多。前几天我在门口就看到你了,不是吗?”他一边走近一边说,“这家伙是危险人物,博士。”他说“博士”的语气恶狠狠的。
“不是,”凯利边说边后退,“走开。”
“你被捕了。”
“不。”
“发生什么事了?”她跳下来,站在他们中间。
“他是杀人犯,是逃犯。”
“我觉得不是。”
“那你可就错了,”威尔逊冷笑着,“警察散发过他的照片。他杀了他老婆。”
她转向凯利。
“是别人干的,”他说,又加了句,“我要走了。”
“不能走。”门卫大喊,掏出手枪。
“威尔逊,你疯了吗?”她愤怒地喊道。
“博士,闭嘴的应该是你。凯利,蹲在地上!”
“不。”凯利走过他身边,到了门口。他没有开枪。
“蹲在地上!”威尔逊用手枪指着凯利喊道,并打开对讲机,“紧急情况,请求增援。在温室——”
没有人过来。凯利弓着腿冲过去,不是抢门卫的手枪,而是对讲机。他夺过对讲机,一拳打在门卫脸上,随后撒腿就跑。
几乎就要跑到门口了。
两声枪响,炽热的子弹划过柔和、芬芳的空气。第一枪打在凯利的肩胛骨之间,偏右了,没击中心脏,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他还会活着并且清醒地看到第二枪。子弹打碎了拱顶的玻璃。碎片闪着光,和雪混在一起,纷纷坠落。冷风像逮到了时机,变着风向肆虐,最后冲了进来,把美好的氛围变得一团糟,也把他们刚补上去的油布的边缘吹得起伏不定。积雪从油布上滑下来落在阔叶棕榈树上。凯利看到了这一切,也听到一个声音不停地哭喊:“不要!不要!不要!”他想站起来,但已经艰于呼吸了。
他到处看了看,都是血,血流了一地。她跪在他旁边,蓬松的金色头发落在他脸上。他听到她结结巴巴的声音,悲伤地哽咽着,“坚持住,坚持住,救护车快来了。”
在这样的暴风雪天气中吗?而且他也不想救护车来,他只想回家。这些树,他注视着畏缩在冷风中的棕榈树,想对她说,但是他说不出话,她又能为它们做些什么呢?对不起,他对树说,对不起,我们都没有能够回家。凯利身上沾满了玻璃碎屑和雪,血仍在不断地汩汩流出,他开始感觉寒冷,身体也哆嗦起来。黑暗终于带走了他眼里最后一丝光亮,他的目光呆滞地定格在那畏缩成一团的树叶上。至少,它们的结局不像他这么糟。严寒,它们说,未必不是一种温暖的死亡方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