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油风土记
2015-01-13陈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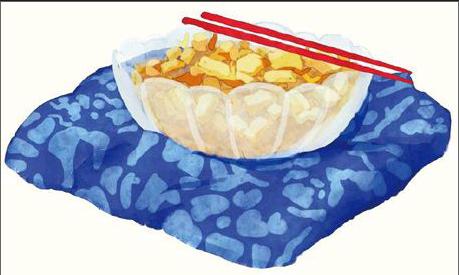
中秋节以来,台湾笼罩在一股“香猪油” 的馊油风暴里,从应景的绿豆饼、肉饼、酥饼等糕饼开始,炒米粉、碗粿、肉圆、米糕等各种的台式小吃也纷纷染了馊油,无法幸免的还有泡面以及快餐食品的酱料包,从油葱,到咖哩酱,甚至充满西式风格的牛肉汉堡淋酱,最后连西红柿浓汤都逃不过此劫。
在谴责诅咒黑心商人的不是之时,一张由猪油支撑的无国界美食地图却也随之不知不觉地浮现。在我从小的认知里,猪油是本土味的象征,没想到它可以如此的跨界。
小时候家里的猪油都是自榨的,即使到今天亦然,取自腹部的猪板油切小块放入锅中,随着温度的升高,油脂慢慢融出来,最后留下一块一块的渣,猪油渣,即所谓的油粕仔。每次母亲榨猪油时,童年的我,总喜欢守在一旁,等着吃油粕仔,满满的一盘油粕仔,一小块偷拿来,热热的入口,油脂从酥皮中喷出还挺吓人,虽然我挑啊挑的,希望挑到点猪肉摊老板不小心切到的瘦肉,但往往就如不了愿。不过,尽管如此,母亲一转身,那一大盘的油粕仔还是消减了大半,甚至没了踪影,让原本想用它来炒豆豉或卤白菜等为餐桌再添一道菜的妈妈也莫可奈何。
油粕仔于台湾,于许许多多像我这般1960年代或前后出生的人的记忆里,就是一种难得的零嘴,曾经也有人拿它来拌糖成了特别可口的点心。而穿透油粕仔的零嘴记忆,在我的心中还有一碗猪油拌饭,热腾腾的白饭上,一颗浓郁的蛋黄,以及香稠的酱油膏,虽然常抢去了它的大半光彩,但细细地咀嚼,一股甜甜的滋味流淌着,啊!那是无可取代的猪油香。
回想我的成长过程,我确实是让这种带着甜味的猪油气息给喂养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的餐桌虽不时也会飘出花生油的味道,但那又大又便宜的肥猪肉榨出来的猪油香才是主流。虽然后来随着美国大豆(黄豆)大量进入台湾,以其制成的大豆色拉油以健康的理由,抢进了台湾的餐桌,取代了花生油,更让猪油在台湾找不到立足之地,几乎一度绝迹于我家的餐桌,不过,那种猪油的气味对妈妈这代老一辈的家庭主妇来说总是放不下,于是经过猪肉摊时,有时不免会被那一大块肥猪肉给拉住,最后只好将它拎了回家。餐桌上的炒青菜,不知不觉中就又泛起猪油的光泽,一种泛着甜味的光芒。
翻开七十年前,甚至百年前,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相关文化学者对台湾社会生活的记录。“台湾人似乎比较喜欢猪油” ,“不管如何贫穷,厨房的碗柜都会摆上一小罐的食用油,或至少半碗的猪油”,“对农民来说,油是最重要的料理品,如果去掉了油,农民的饮食生活将不能成立”,而“最主要的食用油为猪油,接下来才是花生油” 。猪油一度主宰台湾餐桌,自有其历史渊源。
根据194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头猪在台湾依部位的差异,有六种不同的油脂可供利用。1.板蚋油(板油):腹部的油,凝固就像蚋仔(即蚬仔,台语发音laa)一样纯白,天热也不容易溶化,是猪油中最佳者。2.网西油:同样位腹部如网状,常用于鸡卷或虾卷的制作。3.鸡冠油:包围肺脏的油脂,状似鸡冠,据说和麦芽糖或冰糖一起蒸煮,可用于治咳嗽。4.后座油:腿部的油,富弹性,是办桌菜金钱虾饼少不了的材料。5.腻樃油:皮和红肉中间白肉的油,虾料理也常用之。6.杂油和总油:较不易凝固,茶褐色略带臭味,价格最廉。
就像平常家庭主妇抱持着不浪费的心情,将猪肉的肥肉部分取下,细切后榨油,供炒菜用,或者肥肉榨油后剩下的油粕仔再进一步变化出各种料理,这套依部位不同而有不一样用途的油脂使用法,也是一种台湾社会长久以来传承的节约简朴精神的体现,不过从中也显露了台湾人对猪油气味的掌握自有其独到的一面,那是一种深入滋味精髓的掌握,随着舌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不知不觉汇入人们的血脉中,一种难于割舍的依赖也滋生,让猪油几乎成了台湾餐桌的灵魂。
于是尽管大豆色拉油从台湾餐桌崛起,而后台湾油品也来到一个百花争鸣的时代,猪油的滋味仍在台湾餐桌的角落伺机渗透着,一块标榜出自传统糕饼业者之手的糕饼得由它支撑味道,而它与油葱酥结合更是无往不利的打进各种台式料理的王国,那是一种无法抵挡的香甜力道。只是没有想到,最后连汉堡酱汁与西红柿浓汤等西式的料理都得派它上场。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也不足为怪,英国饮食作家伊莉萨白·戴维(Elizabeth David)半世纪前写下的食谱不也常常飘着猪油的香气。在她的笔下,橄榄油、九层塔、茄子和大蒜构成的地中海风味,以及普罗旺斯一派欧洲田园想象里,猪油的光芒总藏不住。
一道用肉类(牛、猪或兔不拘)以及大量红萝卜共熬,于法国乡间被称为“梅铎红酒酱(sauce au vin du medoc)”的炖菜,伊莉萨白·戴维说:在有锅盖的厚重炖锅中热油,若用烤箱肉滴出来的猪油更好。提到意大利菜佛罗伦萨的烤肉时,她也一再强调,最后肉烤好了,肉汁千万别倒掉,因为冷却以后它的“上面有相当好的猪油” !
介绍法国西南部一道以镶黑松露而闻名的猪肉料理“佩里戈尔式猪腰肉(Enchaud de Porc a la Perigourdine)”时,伊莉萨白·戴维同样不惜笔墨写着烹调过程中流出来的猪油。“倒出来充满香味的油脂可以涂在烤过的法国面包切片上,在休息时间给小朋友吃,就像我们用吐司沾牛肉汁吃一样。”而即使在葡萄盛产期没有松露,当地人还是会做没有松露的佩里戈尔式猪腰肉,然后将滴下来的油脂涂在面包上,加上一片冷猪肉与腌黄瓜,做为采收葡萄时休息的点心。
透过伊莉萨白·戴维这一笔又一笔的猪油风土记,在某个时空的交会里,不管是欧洲葡萄园里的农民,还是嬉戏中的欧洲儿童,他们口中散发出猪油香气的面包,似乎与我童年里的那一碗猪油拌饭或油粕仔点心交迭在一起。
这一回台湾馊油风暴中,固然有令人可憎可恨之处,但藉此我却看到了这张跨界而坚不可摧的猪油美食地图,而从中浮出的是更多为了维持猪油质量与风味而自榨猪油的商家。谢谢那些尊重猪油食品而坚持自榨的商家。当然也谢谢长年来自榨猪油的妈妈,从她的手中,我也学会了榨猪油。待会儿,我就先来回味猪油拌饭。至于油粕仔,也少不了趁热越酥,来几块,解一下嘴馋,再来就是煮成我最爱的油粕仔白菜卤。
下次有机会,我应该再跟妈妈学一手猪油炸油葱酥,那是我家煮汤面、肉豉仔的味道支柱,更是端午节绑肉粽炒馅料时无法缺少的一味。
陈淑华,台湾彰化出生。曾供职台湾的《经典杂志》与《大地地理杂志》,近年喜欢透过一些日常被忽略的事物,特别是食物,重新发现生活的可能性。著有《掌中天地宽》、《台湾原住民知识库》、《岛屿的餐桌—36种台湾滋味的追寻》、《彰化小食记》。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