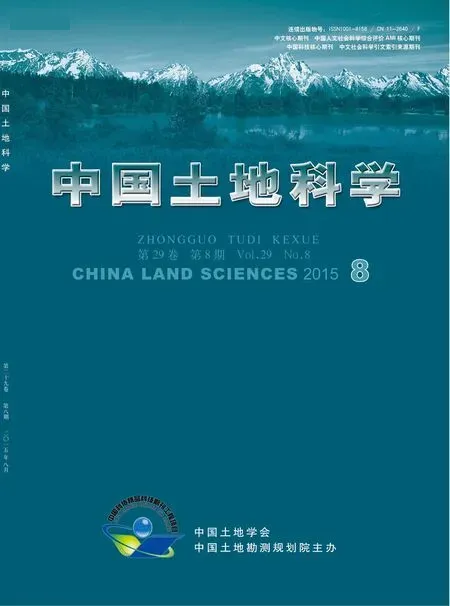中国园区建设中的工业地价、产业升级及其地区差异:城市层面的产业发展雁行模型
2015-01-12藏波,吕萍,赵松
藏 波,吕 萍,赵 松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住房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3.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100035)
中国园区建设中的工业地价、产业升级及其地区差异:城市层面的产业发展雁行模型
藏 波1,2,吕 萍1,2,赵 松3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住房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3.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100035)
研究目的:在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背景下,观察中国不同等级城市工业地价和产业升级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从城市维度将工业地价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分解为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并运用三产品、多要素产业发展雁行模型,对35个已经大规模开展新城和园区建设的大中城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多数城市处于劳动密集型向中等资本密集型过度,且暂无资本密集型形成的阶段,即地价上涨带来了部分促进效应和完全抑制效应。只有深圳、南京、上海和北京4个城市已经出现由中等资本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态势,但这几个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仍表现为增长趋势,即地价上涨同时带来了完全的促进效应和完全的抑制效应。研究结论:依据城市产业升级难易程度推进差别化的工业用地市场化供地机制,这其中基础性工作是根据城市主体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形态和土地使用权价值来综合评定基准地价。对于以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企业为主的部分二三线城市,还应允许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用途转变,激励企业前期固定资本积累以促进其产业升级。
土地管理;工业地价;产业升级;产业发展雁行模型;地区差异
1 引言
随着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逐步收缩,各国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虚拟经济重新回归为实体经济,中国也不例外[1-2]。怎样找到一种既能增加产品市场的需求,又能夯实要素市场的支撑作用的途径,是中国在不断借鉴市场化改革经验,以及完善市场主体行为规则等制度建设中长期寻觅的目标。以地区间产业承接和地区内转型升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3-5]①原因是地区间产业承接有利于有效发挥地区禀赋优势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进而以成本优势拉动产品市场需求;地区内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有效配置,进而提升中国整体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园区建设是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组成部分[6],可以预见其将成为疏解人口压力和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战场”,但要实现预期目标,还需认真研究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园区的建设这一国家意志是否可以减少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周其仁[7]认为公共权力界定不清将导致个人均有攫取公共“租金”的 冲动。这种攫取行为在人口拥挤的地方更演化为一种公开的竞争行为“,不用白不用”的心智构念导致个人在公共资源面前均表现出“日终效应”②“日终效应”是行为经济学中对于传统期望效用理论中一种异象的解释,即赌马的参与者在终局时改投高风险大赌注的一种行为,详见尼克·威尔金森的《行为经济学》。。园区的建设一方面可以疏解人口压力,缓解公共资源攫取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是全新的基础设施和相对老城较低的产权界定费用有利于确定对公共产权的标识性边界。Demsetz[8]认为企业面临着员工在剩余索取权行为上的不确定性,即信息搜寻成本构成企业外部和内部主要的交易成本。工业园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搜寻的成本,众多的企业聚集会带来规模优势下的信息集中,如向求职者传递更多就业机会的信号。同时,从产业转移来看,中国西部对东部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不仅压缩了前期固定的沉淀成本,而且充分利用了要素的比较优势[9]。
第二个问题是园区建设是否会带来产业转型升级?既然园区的建设可以为当地居民带来产权更加明晰的公共服务,为企业带来生产的规模效应,为当地政府带来税收增加等诸多好处,那么各地都应该大规模建设园区,这明显是不可能的。若建设工业园区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首选,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和众多类似地区展开招商引资的“锦标赛”[10],而通过协议或定向招标等方式降低工业地价已成为各方的主要“武器”。这势必带来再一次的产能过剩,以及为争夺大型产业项目入驻而导致产业结构同质化等问题[4],且这一问题在没有优势产业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严重[11]。所以,在没有优势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园区建设基本违背了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通过扩大“招拍挂”范围来提升工业地价的政策措施能否带来产业升级。针对地方政府有意压低价格吸引特定企业进驻的“寻租”做法,2009年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知》正式提出了“严格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这一正式规则将带来工业地价的上涨,进而增加新工业企业前期沉淀资本的投入,这种成本累加效应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向作用表现为内生的“优胜劣汰”机制,即高地价促使高附加值企业的增加,进而带动整体产业的升级;反向作用表现为高地价形成的“挡板”效应,即预期高成本对外来工业企业进驻的阻隔,这可能导致部分地方工业长期深陷于低附加值的泥沼中。暂且将地价对产业升级的正向作用称为“促进效应”,反向作用称为“抑制效应”。在不同地区,两个作用孰高孰低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这就需要从理论模型和现实数据两方面予以考量。
综上,国内学者对于土地价格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均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产业发展雁行模型,创建土地价格与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原始模型自变量为单位劳动资本投入,因变量为单位劳动产出,由于土地、劳动力均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本文将模型中的劳动要素替换为土地要素,并基于最优化产出框架,从生产者的收入函数、资本投入价值的决定因素、最优的名义产出3方面得出地价与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同时,将地价上涨对产业升级的作用界定为促进和抑制这一对双向效应,并通过经验检验来量化两种效应,同时体现出其地区差异。
2 理论模型
2.1 理论分析
产业发展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可以描述产出带来的资本密集度和产业升级的相互关系,即不同产业的生产模式,随着时间的推进,不同产业出现的不同状况的繁荣上升,然后下降,最后逐渐消失的轨迹。该模型最早由Kaname Akamatsu[12-13]提出,但Akamatsu的模型还仅仅是单中心要素,显然与现实不符。Schott[14]拓展出了一种多要素产业发展雁行模式(Multiple-Cone Model, MCM),即“三种产品、两中心”模型。其中“三种产品”分别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且相互独立;“两中心”分别为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①限于篇幅,对多要素产业发展雁行模式的内涵和基本设定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由于该模型认为三种产品彼此独立,且分别与土地和资本要素相互关联,所以,Schott模型对于分析产出与产业升级的相互关系更为可信。

图1 土地资本要素与产业升级的Schott 模型:三产品、两中心Fig.1 Schott model of land capital an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ee-goods, two-cones
Schott模型的基本思路可以表示为图1②Schott原始模型是围绕劳动要素来构建的,即原图1中的横坐标为单位劳动资本投入,纵坐标为单位劳动产出,这里将劳动力替换为土地。。单位土地资本k 形成了三种产品间的边界点,表示为τ(jj = 0,1,2),其中τ0= 0。n 为生产不同产品的产业,其单位土地产出和单位土地资本分别表示为yn≡ Yn/ Tn和 kn≡ Kn/ T(nY1+ Y2+ Y3= Y,K1+ K2+ K3= K),其 中Y 为产出量,K 为投资量,T 为土地面积。产业n 的产品价格为pn,假设每个经济体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即pn为确定且固定的。Zn是产业n 的产出价值,zn是每单位土地的产出价值,其中Zn= pnYn,zn= pnYn/ T。
曲线w'AB 为每单位土地产出价值(z = z1+ z2+ z3),其随着单位面积土地资本的累积而增加。当单位土地资本位于0和τ1之间,产出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不会产生资本密集型产品。同理,当单位土地资本位于τ1和τ2之间,产出为中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但不会产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单位土地产出和单位土地资本的关系被称为产业发展路径[14-16]。其中,劳动密集型、中等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展路径分别为w'τ1τ2、0Aτ2和0τ1B。
2.2 模型设定
为从理论上定量判别地价与产业升级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趋势,引用Schott发展的“HO集聚”(Heckscher-Ohlinaggregation)概念。生产过程集合以产业行业年度资本强度为基础,而不是标准的产业分类为基础,即类似的资本密集度来表征生产过程是否集聚。用h 表示“集聚”的界限,hi和hi-1分别是第i 个“集聚”的资本密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k(nt≡ Knt/ Tnt) 表示第n 个产业在t 年的资本密集度。“集聚”的3种情况可以表示为:

式1—式2中,Zit表示“集聚”i 在t 年的增加值,即资本密集度位于hi-1和hi之间的所有产业增加值的总额。
为求出真实的资本密集度,构建一个已基于最优化产出的框架,从生产者的收入函数、资本投入价值的决定因素、最优的名义产出的决定因素3方面得出地价和资本密集度理论模型,化简后的最终表达式为:

式3中,Pk为资本价格,K 为资本数量,PT为工业用地交易价格,ST为工业用地供应面积,r 为利率,L 为劳动力数量,π为贴现率,α为劳动力边际贡献度,N 为勒纳指数。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
为了定量判别产业的发展路径,这里针对不同产业的“集聚”进行时序数据的回归,其回归形式分别为:
(1)劳动密集型的“集聚”:

式4中,kt为t年的单位土地资本。dj为虚拟变量,其赋值准则为:若kt位于τj-1与τj之间,dj赋予1;τj-1与τj之外的赋予0。τ为各产品单位土地资本边界值。β为待估系数,ε为残差(下同)。
(2)中等资本密集型的“集聚”:

(3)资本密集型的“集聚”:

式5—式6中,“集聚”的边界值为:h1= 600,h2= 1000;产品的单位土地资本边界值为:τ1= 3.00,τ2= 6.00。若待估系数满足β3>0或β2>0, 表示地价上涨带来“完全促进效应”和“部分促进效应”,说明地区整体的工业地价较为合理,产业发展正在由劳动力密集型向中等资本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即正在进行产业升级,且系数越大,转型的速度越快。若β1<0, “完全抑制效应”逐渐减小,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萎缩;若β1>0, “完全抑制效应”增加,说明该产业仍在不断增长。由于式4、式5和式6具有相同的要素投入,所以可能具有共线性问题,所以使用不相关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3 实证检验
3.1 数据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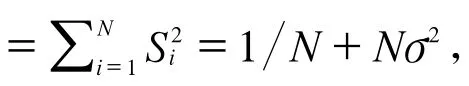
3.2 描述性统计
3.2.1 工业地价的区域差异与变动情况 为了便于从城市层面和时序层面横向、纵向比较工业地价,对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工业地价进行了简单的算术平均。通过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相较其他城市,一线城市的平均地价和年均增幅均较高,东部沿海城市的这两项指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②一、二、三线的划分标准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划分等级划分》。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来源于2000年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的“三大经济带”。。其中,2003 —2012年,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地价均值均在1000元/m2以上(表1),高于天津、沈阳等二线城市300.78元/m2,高于石家庄、呼和浩特、合肥等三线城市512.13元/m2。一线城市地价年均增速为9.83%,分别高于二线、三线城市2.16和4.79个百分点。若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三个地区城市的平均地价分别为886.27元/m2、532.87元/m2和475.24元/m2,在空间上呈现沿海至内陆阶梯式递减的特征。
2003 —2012年,工业用地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为了便于观察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地价的变动情况,从中选取三个代表性的年份来表征③将2003—2004年最为市场化初年,是因为2003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策略,明确提出了工业用地要实行“招拍挂”方式出让。2007年,国土资源部在全国部分城市试点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这标志着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所以称之为市场化改革中间年。2011年全国所有省市基本均已出台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细则,且“招拍挂”出让比重几乎占到了出让总量的90%以上,所以称之为市场化改革的末年。,分别为市场化初年(2003 —2004年),市场化中间年(2007 —2008年)以及市场化末年(2011—2012年)。从平均增速来看,全国的工业地价在第二时期出现了大幅下降,其原因可能是金融危机来临前资金流动性已趋于放缓,社会投资减少带动地价下跌。其中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地价下降的幅度最大,哈尔滨下降了2.29%,宁波下降了5.23%,厦门下降了10.43%,深圳下降了41.36%。但随着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2011—2012年,地价开始逐渐上升,增幅最大的也是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图2)。
3.2.2 地区产业升级:投资—收益分析 产业升级的衡量可以简化为从投资和收益两方面来综合考虑,即以较低的投资获得较高的收益,其中投资水平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来表征,收益则以地均产值和人均产值来表征。从不同等级的城市,地均固定资产水平的空间特征表现为:二线>一线>三线,均值分别为3.84亿元/hm2、2.65亿元/hm2和2.11亿元/hm2;地均产值表现为:一线>二线>三线,均值分别为22.04亿元/hm2、3.88亿元/hm2和3.35亿元/hm2,这与地价的空间分布特征相一致。人均产值则与地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一致,即二线>一线>三线,均值分别为39.66亿元/万人、34.26亿元/万人和18.79亿元/万人。所以单纯从产出与产业升级相关指标的均值来看,一线城市以较小的投资换取了较大的产出,二线城市次之,三线城市长期维持在低投入、低产出的发展状态。

表1 2003 —2012 年35 个大中城市工业用地价格的基本统计Tab.1 Statistics of industrial land prices in 35 big cities, 2003-2012

图2 3 个时期35 个大中城市工业用地价格的年均增长率Fig.2 Annual growth rate of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 35 big cities, during the 3 periods
产出与产业升级相关指标的增速得出的判断也与基于上述均值得出的判断相同。综合上述地价与产出、产出与产业升级的空间趋势判断,基本可以得出初判:一线城市的工业地价较高且增速较快,二线次之,三线城市地价平均水平较低且上涨较慢。产业升级的优先次序也呈现相同的特点,即一线城市将优先出现产业升级,二线城市次之,三线城市能否出现产业升级则要看能否打破现有低投入—低收益的增长怪圈。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经验判断对于以东部、中部和西部来进行城市划分同样适用。
3.3 计量结果
通过回归结果可知(表2),35个大中城市多数处于劳动密集型向中等资本密集型过度的阶段,其中劳动力密集型逐渐萎缩的城市有19个,占到了总数的54.29%,中等资本密集型增长的城市有31个,占到了总数的88.57%,而 资本密集型增长的城市只有4个,分别为北京、上海、南京和深圳,仅占总数的11.43%。从产业升级的速度来看,兰州、厦门、西安和天津的中等资本密集型增长速度最快,但同时这4个城市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处于增加的趋势,地价平均水平在2013年基本均达到了800元/m2左右,这也从侧面说明地价的增长在长期将不利于这4个城市完成完全的产业升级,即不利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这样的短期升级“乐观”但长期升级“悲观”同样出现在石家庄、宁波和济南等9个二、三线城市(其中东部4个,中部2个,西部3个),2003 —2012年这些城市的土地价格基本平稳增长,年均增幅为3.97%,2013年都超过了800元/m2,未来如果工业地价再继续以相同稳定的增速增长,这类城市的产业升级将更加困难。
相反,广州、杭州和海口等18个城市却在较低的地价平均水平(2013年的地价基本位于550元/m2左右)上实现了部分产业升级,这里的部分主要指劳动力密集型向中等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具体表现为β1<0和β2>0同时出现。18个城市中,东部城市5个,中部城市7个,西部城市6个,其中升级速度最快的是广州、杭州和沈阳等东部城市,长春和哈尔滨等中部城市次之,西部偏慢。这类型城市由于具有较低的工业地价这一成本比较优势,所以可以通过较快的资本原始积累来实现部分产业升级。但随着工业地价不断上涨,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缩小。
在35个大中城市当中,只有深圳、南京、上海和北京的资本密集型系数β3>0且β2<0,表 明这4个城市已经出现由中等资本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态势。其中转变速度最快的是深圳,南京次之,上海和北京转型相对较慢,而这一规律与平均地价的高低次序基本一致。同时,这4个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表现为增长趋势,其中深圳增长最快,上海次之,北京和南京相对较慢。这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头增”的发展态势说明了现有地价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带来了一种双边“锁定效应”(lock in effect),即现有的地价水平还不足以打破低附加值企业固化的行为路径,地价增加虽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这部分企业的经营利润,但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企业试图继续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或压低劳动力成本来维持过去的平均利润。与此同时,高附加值企业可以在现有的地价水平上通过纵向或横向一体化等举措来获取更大的可占用性“准租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现两种产业同时扩张的问题。对于深圳等已跨越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资本积累阶段的城市,应更好地发挥地价上涨对于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并压低其带来的抑制效应,这其中工业用地使用权的完全市场化定价是一条可行路径。市场化定价以一种信息较充分利用的方式为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了组织激励,这种激励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促进更多的高附加值企业(或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集中,引致区域投资力度增加;另一方面以高地价引致的进入性壁垒将低附加值工业企业(或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逐渐边缘化,甚至退出至劳动力禀赋较强的城市,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这在高波等[19]的研究结论中已经得到证实。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35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工业地价较高且增速较快,二线次之,三线城市地价平均水平较低且上涨较慢;产业升级的速度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这一规律性特征对于以东部、中部和西部来进行城市划分同样适用。35个大中城市多数处于劳动密集型向中等资本密集型过度的阶段,即地价上涨仅部分发挥促进效应。从产业升级的速度来看,兰州、厦门、西安和天津的中等资本密集型增长速度最快,但这4个城市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处于增加趋势,即地价上涨带来部分促进效应和完全抑制效应。这样的特征同样出现在石家庄、宁波和济南等9个二、三线城市。广州等18个城市以较低的平均地价实现了劳动力密集型向中等资本密集型转变的不完全产业升级,即地价上涨带来的是部分促进效应。只有深圳、南京、上海和北京4个城市已经出现由中等资本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态势,但这4个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表现为增长趋势,即地价上涨同时带来了完全促进效应和完全抑制效应。
4.2 政策建议
(1)依据各城市产业升级难易程度和带动效应,推进差异化的工业用地市场化供地机制。如对于北京和深圳等已经出现由中等资本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即较易实现产业升级的城市,现有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应向更完全的市场化出让方式转变,如不区分国有、民营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环节应统一施行挂牌和拍卖等完全市场化机制,可以强化地价上涨对产业升级带来的“促进效应”,并放大高附加值工业企业的带动效应和提高低附加值企业的进入性门槛,进而实现区域整体的产业升级。对于兰州和厦门等中等资本密集型增长速度较快但资本密集型企业仍逐渐萎缩的城市,未来的供地政策应允许招标、拍卖和挂牌共同存在,虽然招标略带不完全的市场属性,但目的是保留中等资本密集型企业上升的势头,以引导其逐步实现全域范围的产业升级。
(2)依据城市主体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形态和土地使用权价值来综合评定基准地价。对于在国家主体功能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密集的地区或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应周期性调整工业用地基准地价,显化土地使用权增值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溢价,以期将产业升级演进轨迹与工业地价调整频度相匹配。对于以传统加工制造业等低附加值为主导产业的地区或城市,如青岛、福州和厦门等,用地基准地价调整周期可适度延长,且不宜采取大幅度调高的策略,目的是保护工业企业正常的经营收益和其对劳动力的吸纳力。
(3)以允许适度土地用途转变形式,激励部分二、三线城市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企业前期固定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增幅较快,但中等资本密集型增长较慢及还没有形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地区或城市,未来如果工业地价再继续以现有的增速增长,地价对产业升级的“抑制效应”将更大,这类型城市的产业升级将更加困难。所以,建议允许部分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企业可在一定量或一定比例的工业用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并给予增值税和土地变性费用的适度优惠,以增加其固定资本积累速度从而进行产业升级。
(
):
[1] Bischoff O. Explaining Regional Variation in Equilibrium Real Estate Prices and Income[J].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2012, 21(1):1 - 15.
[2] Langenfeld J, Li W.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ruise Line Industry:Implications for Market Definiti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Welfa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8(,2):1 - 25.
[3] Miller N H, Osborne M.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the Cement Industry: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Mode[l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45(2):221 - 247.
[4] Xiao X, Peng Y, Li S. China’s Optimal Industrial Structure:Theoretical Model and Econometric Estimation[J]. China Economist, 2014(1):32 - 52.
[5] 蔡昉,王德文,曲玥. 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J]. 经济研究,2009(,9):4 - 14.
[6] 柳泽,周文生,姚涵. 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1):161 - 168.
[7] 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6 - 178.
[8] Demsetz H, Alchian A.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5):777 -795.
[9] 周伟林. 企业选址、集 聚经济与城市竞争力[ J]. 复 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 008(, 6):94 - 100.
[10] Du J, Peiser R B. Land supply, pricing and local governments’land hoarding in China[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4, 4(87):180 - 189.
[11] 林毅夫. 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J]. 经济研究,2007,(1):126 - 131.
[12] Akamatsu K. Trend of Japan’s Wooden Product Industry[J]. Shogyo Keizai Ronso, 1935, 13:129 - 212.
[13] Akamatsu K. Dialectic Process of Japan’s Economic Developmen[tJ]. Shogyo Keizai Ronso, 1937, 13:179 - 210.
[14] Schott P K. One Size Fits All? Heckscher-Ohlin Specializ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686 -708.
[15] Leamer E E.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factor, n-goo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961 - 999.
[16] Leamer E E, Hugo M, Sergio R, et al. Doe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Increase Latin American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59:3 - 42.
[17] Elzinga K G, Mills D E. The Lerner Index of Monopoly Power:Origins and U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3):558 -564.
[18] Giocoli N. Who Invented the Lerner Index? Luigi Amoroso, the Dominant Firm Model,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arket Powe[r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2, 41:181 - 191.
[19] 高波,陈健,邹琳华. 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J]. 经济研究,2012(,1):66 - 79.
(本文责编:郎海鸥)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ir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Industrial Parks: A City-Level Flying Geese Mod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ANG Bo1,2, LV Ping1,2, ZHAO Song3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Hous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China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Institue, Beijing 100035,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land pric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t city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in recent decad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e., industrial land price affects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two aspects(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the inhibition effect), the methodused in the paper mainly includ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lying geese model of three-goods and two-cones. The paper aims to do the empirical test to identify which effect is stronger in the 35 big and medium-sized cities with large-scale industrial parks a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cities are in the transition phase where the leading industries ar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labor-intensive to middle capital-intensive, and none is in the form of capital-intensive.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iddle capital-intensive change to capital-intensive has only emerged in Shenzhen, Nanjing, Shanghai and Beijing, however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belonging to labor-intensive are still show growth trend. It shows that the growth of land price not only brought complete promotion effect, but also resulted in the complete inhibition effect.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different industrial land supply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of urban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key point for such task is to develop the benchmark land price system based on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industrial land assignment, and the price of land use right. Furthermo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ermit the less-developed cities where the industries are mostly labor-intensive ones to change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to other uses in more flexible way in the purpose of encourag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land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dustrial upgrading; flying geese mod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gional differences
F301.2
A
1001-8158(2015)08-0024-09
10.13708/j.cnki.cn11-2640.2015.08.004
2015-04-28
2015-06-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22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藏波(1987-),男,山西大同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与管理、土地经济与政策。E-mail: zb2416650@163.com
吕萍(1962-),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住房政策、土地经济与管理。E-mail: lvping@mparuc.edu.cn
猜你喜欢
——以杭州为例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