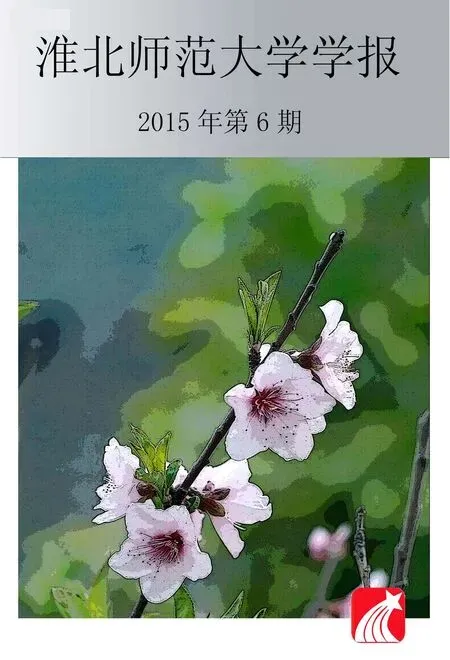张孝祥书法风格成因管窥
2015-01-07高玥孟宝跃
高玥,孟宝跃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张孝祥书法风格成因管窥
高玥,孟宝跃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张孝祥作为南宋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为人所熟知,同时其书法在南宋时期同样形成了劲健洒脱、纵横恣肆的艺术面貌,在南宋时期取得了较为独特的艺术面貌,受到时人及后世的广泛认可。在对其书法艺术风格进行简要概括的前提下,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着重对张孝祥书法风格的形成因素进行了探析,以期能够更为真实、客观的展现张孝祥书法艺术的风格特征。
张孝祥;书法风格;成因探析
一、张孝祥生平及其书法风格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原籍和州乌江县(今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张孝祥出生于明州鄞县桃源乡。后随父张祁迁居安徽芜湖。孝祥自幼天资过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孝祥被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从绍兴二十四年(1154)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孝祥官于临安。绍兴二十九年八月遭御史中丞汪徹弹劾而落职。绍兴三十二年(1162)复官,并一直在地方为官,先后知抚州、领建康、知静江军府事,乾道三年(1167)三月,改知潭州。乾道五年(1169)三月,因病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旋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六月病卒,终年三十八岁。
张孝祥早年便已享有书名,高宗时期,孝祥书法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据《宋史·本传》记载: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劄。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1]407张孝祥书法早年取法颜真卿。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了高宗见到孝祥书法的情景:“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戳首选。”

从现存张孝祥书迹及碑刻拓本亦可清晰感知其师法颜鲁公的迹象。《疏广传语》(图一)为孝祥楷书风格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此作点画沉实,结构较为宽博,保留了清晰的颜书痕迹。楷书方面除了“法颜字”,其更是广设博取,上追唐楷诸家,如欧阳询、褚遂良、李邕等人。其后期楷书作品如《朝阳岩记》(图二),风格恣肆雄劲,奇伟豪放,气格逼人,与前期作品形成了较为显著地风格转变。

图三 《适闻帖》
孝祥行草书主要师法米芾,然笔力劲挺,奔放洒脱。宋人陈槱云:“于湖、石湖悉习宝晋,而各自变体。”[2]240张孝祥行草书传世书迹有《临存帖》《休祥帖》《适闻帖》(图三)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米芾书法的特征。《适闻帖》为孝祥后期行草作品,书风在米字基础上更为奔放奇倔,不拘一格。杨万里曾如此描写张孝祥:“于湖张公下笔言语妙天下,当其得意,诗酒淋浪,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兴逸天半。”[2]243元人吴师道曾赞赏其书法“笔势奇伟可爱”[2]244。与其同时代的理学大家朱熹对张孝祥书法的奔放恣肆并不以为然,评之曰“不把持,爱放纵”。[3]44由此也反映出孝祥书法奔放洒脱、奇伟劲健的特征。
二、张孝祥书法风格成因
(一)儒家思想渊源的影响
宋代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理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然而文化的繁荣昌盛并未给国家带来足以镇守四方的军事实力。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国势最为薄弱,民族忧患尤为显著的一个朝代。南宋叶适曾感叹道:“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4]张孝祥正是出生于这种民族忧患尤为显著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六年即公元1126年金人铁骑南征,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灭亡。这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建炎三年(1127)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建立南宋,国破城亡这样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创伤是难以估量与想象的,动荡的社会环境给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儒学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显得更为宝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文人士大夫更加需要得以安身立命的心灵支点。正如《宋史》所载:“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2]1亡国之耻、丧家之恨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潮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高点。
张孝祥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并逐渐成长,自然深受社会时风的浸润和熏染。孝祥参加殿试之时高宗“策问师学渊源,秦熺之子埙与曹冠皆力攻程氏之学,孝祥独不攻”[1]405从中可知孝祥早年应对二程之学多有接受。宋人叶绍翁曾言:“与南轩、考亭先生未辈行友,而不能与之相琢磨,以上继伊、洛之统,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为紫府仙,惜夫!”[5]71张孝祥一生与儒学大家张栻和朱熹来往密切。张孝祥虽未“能与之相琢磨,以上继伊、洛之统”,但从中亦可知其儒学渊源之深厚。我们从张孝祥的行迹及诗词中亦可对此得到印证。
绍兴三十年(1160),其父张祁得知金主亮有叛盟之迹象,数次上书,而朝廷大小官员皆反对与金动武,军政不修。此时张孝祥以罢职闲居之身代父上书,最终“言者以张皇生事论罢之”,其父张祁被罢官。而第二年金兵果然举兵南侵,张孝祥分别致书边防将领王权、李显忠,呼吁他们团结抗战。张孝祥为国难奔走天下的壮志豪情可见一斑。当其得知虞允文大败金军于东采石后,兴奋至极,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张孝祥终于将其从戎卫国的一腔热血与豪情壮志淋漓尽致的挥洒于笔端。如此激越昂扬的爱国热情不正是儒家思想文化深处传续千年并一再被发扬光大的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之所在吗!
由此我们将视角再次转回张孝祥的书法。“法颜字”确是张孝祥书法的主要特征之一。从张孝祥早年楷书传世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捕捉其中颜书意味。以张孝祥隆兴元年(1163)知平江府任上时所书《疏广传语》(图一)为例,此碑书法点画沉厚,结体宽博确实保留浓厚的颜书意味。张孝祥早年除了“法颜字”之外,还对欧阳询、褚遂良用功颇深,从其早年楷书作品《宏智禅师碑》可以明显发觉此二家迹象,然而,笔者以为,张孝祥自入世以来特别提出“法颜字”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含义所在。
纵观千年书法史,能够留名书史的书家不计其数,而能常为人所称道的大书家寥寥几人。无论是羲献父子,还是颠张醉素,亦或是诗酒澎湃的文坛豪杰苏东坡,这些千百年一遇的书坛翘楚都没有比颜鲁公更能呼唤起在千年儒家文化熏染下的文人士大夫那颗赤子之心。颜真卿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达到了士人理想与书风面貌的高度统一,是传统儒学倡导下的人格精神在书法领域的鲜活写照,是中国传统士人心目中的典范。这一方面归因于颜真卿用生命诠释的卫道精神,另一方面颜真卿用书法展现了一位卫道者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
正如傅山所描述的其本人在临写颜真卿书法时的感受:“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犹读《三国志》,于关、张事,便不知不觉偏向在者里也……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6]123
在《跋山谷帖》中,张孝祥更是明确指出鲁公精神的伟大:“字学至唐最胜,虽经生亦可观,其传者以人不以书也。褚、雪、欧、虞,皆唐之名臣。鲁公之忠义,试悬之笔谏,虽不能书,若人何如哉”[1]278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张孝祥书法不仅在风格特征甚至是书法取法及师承方面都是在儒学思想所倡导的传统文人士大夫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儒学思想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波澜不惊的人生际遇对其书法风格的嬗变所产生的激发作用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创作者的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往往通过其个人的诗词文赋得以表达和抒发,人生际遇的改变往往影响着作者作品风格趋向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书法与诗词、文赋具有相似的反映创作者的真实心理感受和生活情态的作用。扬雄的“心画说”正是对这种关系的最好概括。
张孝祥一生可谓波澜不惊。从少年被高宗亲擢力第一力压秦桧之孙秦埙而“取高第”,并用短短五年时间便已擢居五品要职,掌起草朝廷诏令,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此一时期张孝祥的仕途生活可谓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然而,刚刚达到人生至高点,仕途无可限量之时遭人弹劾落职归乡,此种跌落起伏常人很难有机会直面以对,对其心理产生的冲击更是常人难以体验和想象的。之后赋闲乡居几年,再次被任以官职不久又遭到弹劾。官场的起伏对人生抱负的打击、外敌的入侵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朝廷内部相互的倾轧无不对张孝祥的思想时刻产生着冲击,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其个人心理的变化。
诗言志。诗词是表达作者内心情感最为直接的方式,因此,诗词风格的转变也最直接的反映出作者内心情感状态和生活状态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张孝祥词风的变化清楚地把握到人生际遇对其个人创作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张孝祥早年词作大多创作于春风得意的临安五年期间,加之当时处于宋金议和之后的安定时期,朝廷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此时其词作大多以才子佳人、诗酒风流为主题,词风香软绵丽。之后伴随着仕途的急转直下以及国家安危的日益紧迫,张孝祥的视野不断得以扩展,胸襟日渐拓宽,词风转而豪放深沉。(关于孝祥词风的嬗变多有论述,此处不展开讨论。)在这种人生历练之下,张孝祥书法也经历了两次风格的嬗变,其书风由最初的俊逸秀美转入中期的厚重雄强进而发展成后期的豪放劲健,这种显著地风格转换表面看起来与其不同时期师法的书家不同有直接关联,但从本质上说,书风的转换甚至不同时期选取不同书家作为师法对象都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感触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强烈的人生际遇的改变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变化对张孝祥的文学创作以及书法风格所带来的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三)南宋孱弱的时代风气的局限
张孝祥书法虽然在南宋时期享誉书坛,但终究未能度越前贤,成为书坛一代大家。其中除了因其个人过早离世的原因之外,笔者以为这与南宋王朝整体孱弱的国势及依此而形成的先天文化缺陷有关。
文化与政治历来是被人们经常讨论的一对范畴。宽松的政治环境可以使文学艺术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经济状况。在两宋时期,虽然赵宋统治者一直高度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为文艺的繁荣提供了最为宽松的环境。文学、书法、绘画均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但南宋与北宋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北宋时期,书法方面出现了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书家群体,引领了行草书风的一世辉煌。但南宋的书风局促于北宋苏黄米辕下,大善乏陈。张孝祥虽然有着过人的才思以及试图度越前贤的豪情壮志,但最终还是无法回避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先天不足。
同样的现象在南宋画坛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北宋时期画坛以李成、范宽为主将,擅长描绘雄浑壮阔的北方山水,画面气象宏大。相比之下,南宋时期以擅长画边角山水的马远、夏珪却极富盛名。我们并非因崇尚高大壮阔而小觑精工典雅小巧可人的艺术风格。相反,我们应当赞叹南宋画家能够在历代前贤铸造的一座座艺术高峰外另辟奇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艺术风格的转变所蕴含的深层的文化动因,那正是文学艺术的发展阶段及形态面貌从根本上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南宋书风为何大多局促于北宋苏黄米辕下,而未能出现与之相匹敌的千古大家。
结语
张孝祥作为南宋书坛著名的书法家,虽因过世太早,未能形成极近成熟的艺术风格以及未能对后世产生深远而长久的历史影响,而往往被后世研究者所忽略。然而,对这样一位未能全面施展个人才华的艺术家的深入而全面的发掘与研究恰恰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知,张孝祥书法风格的形成是其个人思想、人生际遇、社会文化及历史环境等各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其中所反映出的史学意蕴和文化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1]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M].徐鹏,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黄珮玉.张孝祥研究[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3]宛新彬.张孝祥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宋]叶适.水心集·纪纲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2年,卷4.
[5]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张于湖》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责任编校谢贤德
J292.1
A
2095-0683(2015)06-0117-04
2015-10-15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研究项目“张孝祥书法研究”(2014SK37)
高玥(1987-),男,山东临清人,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孟宝跃(1966-),男,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