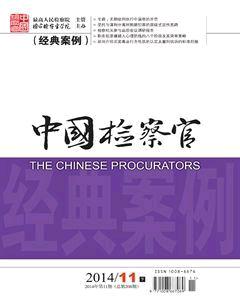环境污染职务犯罪查处困境及其可能出路
2014-12-30吴美满
文◎吴美满
环境污染职务犯罪查处困境及其可能出路
文◎吴美满*
当前,环境污染致使地球从外层空间、大气、土壤到饮用水等每层空间均无一可以幸免,并且呈日益严重的发展态势,其危害已经由传统的对人身和财产的单维度损害向引发公共安全危机方向转化。从法律制度的构建来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阻却污染的两道规制手段,但刑法谦抑性决定了刑事司法的最后手段作用,因此首善之选是发挥行政执法环境保护的第一道防御关口作用,但从现状看这一关口已经全面失守。因此,充分发挥刑事司法在查办环境污染职务犯罪中的作用,督促行政执法人员切实履行保护环境职责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环境污染职务犯罪的立法困境
一般而言,环境污染职务犯罪是指环境监管失职罪,但从全国查处的部分案例可以发现,行政执法人员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必然伴生受贿行为,因此,本文所称环境污染职务犯罪是指环境监管人员受贿而实施的渎职犯罪。从实践来看,这类犯罪的查处面临困境。
(一)入罪依赖实害结果
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案件若干解释》)着重突出了从严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精神,进一步降低了污染环境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第1条第1至5项新增了按排放量或行为入罪的新标准,即不再要求以造成实害结果为前提,这对今后惩治污染犯罪将产生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上游犯罪立法的改变,并未带来下游犯罪立法的同步修改。根据该解释第2条的规定,环境监管失职罪只适用于第1条第6至13项,仍未脱离对实害结果的要求。
(二)结果论导致入罪门槛过高
如前所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该解释第1条第1至5项的规定可使污染环境犯罪查处不力的局面得到改善,但由于污染环境犯罪所存在的“三难问题”由环境监管失职罪直接继受,直接导致环境污染渎职犯罪难以入罪。第一,实害结果鉴定难,即对实害结果的鉴定存在机构少、费用高的问题,而且污染单位案发时往往已停止排污致取证难。第二,危害后果量化难。由于污染后果具有潜伏性、持续性、难以预测性和多样性等特点,“重大损失”和“人身伤亡”难以量化。第三,因果关系界定难。环境污染的特殊性渎职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这直接导致无法追究渎职人员的责任。
(三)低法定刑导致起诉难
环境监管失职罪法定刑最高是三年有期徒刑,对行政监管人员的威摄力不足。从近年查处情况看,几乎每起重大责任事故背后都存在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问题。但是,由于渎职犯罪本身就存在查处难的问题,如果无法确定行为人的渎职责任,即使其被查处存在受贿行为,也往往因为受贿金额不高而难以成案,实践中往往被撤销案件或被决定不起诉。
二、环境污染职务犯罪的司法困境
两高上述司法解释的出台将极大改善今后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境地,但环境渎职犯罪的查处困境可能并不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同步改善。
(一)结果犯或危险犯的问题
不放弃环境污染事故结果犯的立场,三难问题将始终如影随行,制约我们及时处理环境污染犯罪。事实上,规定这类犯罪为结果犯已不符合惩治环境犯罪的发展趋势,也不符合国际立法例。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我国香港以及美、德等国均将环境危害行为设定为危险犯。这是承担自身对世界的环境责任在刑事立法领域的体现,有利于所在国融入国际刑法,也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果我国将该犯罪由结果犯转化为危险犯,则司法认定上,可直接将《环境污染案件若干解释》第1条第1至5项加诸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认定,规定出现该条第6至13项情况的,以结果加重犯论处,直接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鉴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建议因果关系理论随之变迁,应借鉴民法上对证明责任实行的推定原则,兼采一定情况下的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只要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被查明具有受贿犯罪事实,被监管企业在其监管期间又存在污染环境事实,两个事实具备足可推定环境监管失职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同时,要赋予行为人以申辩权,明确由行为人负责证明自己没有失职;如果证明不了,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三)刑法谦抑原则的适用
与其他规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刑法罪名不同,污染环境罪是规制人与自然关系的罪名。人类之间的关系可以选择,但人类深深嵌入并依附于自然,无法选择无处逃遁。面对这一特殊关系,刑法谦抑性理论理应区别适用,即对于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及相关的职务犯罪行为,应该实行零容忍并排除刑法谦抑原则适用,以此唤醒公众对环境的责任。其实保护环境只是手段目标,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能够在合适的环境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排除适用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一原则本身,当前期的排除适用促使保护环境成为人类的内心自觉和生活方式时,刑法就自然而然被谦抑了。
(四)司法能动补足立法不足的问题
司法不应静待立法改变而无所作为,理应自觉担负起保护环境的不二使命。针对立法不足的问题,司法机关应当主动作为,强化对环境污染渎职犯罪的打击。首先,对于因为法律障碍所导致的证据不足的问题,只要行为人放任违规排污的事实明确,虽无法就此对其独立定罪,仍应作为受贿行为的一个从重情节予以综合评价,这既是对其渎职行为的批判性否定,也是司法对环境、对公众的应负责任。其次,对于存在环境监管渎职行为又收受贿赂的,建议实行零容忍并不考虑受贿数额,直接认定其属情节恶劣,即使有自首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但从政治、社会、法律效果最大化的角度看,应一律选择起诉。再次,如果由于证据不足难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督促有关机关对环境污染提起公益诉讼时将放任排污的行政监管人员一并起诉,使其承担一定民事责任。
(五)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问题
《环境污染案件若干解释》加强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并强化了可操作性,但是,如何分配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方面的责任以避免推诿扯皮、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等问题如何解决等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于证据收集责任的分配问题,建议由检察机关牵头,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分别订立各自的证据收集分配标准,以解决推诿扯皮的问题。对于以罚代刑问题,可由检察机关介入,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并引入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来解决。这其实是将环境污染职务犯罪查处关口前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职务犯罪预防手段。
三、环境污染职务犯罪立法司法困境的可能出路
环境污染职务犯罪立法和司法困境并非孤立存在的,其背后体现的是各地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问题上的艰难选择。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要求我们在立法司法上提供技术之外,还应当重视两个问题。
(一)从人与人关系法转向人与自然关系法
当前法律界始终未能将眼光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法的关注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法的关注。环境污染是人对自然的犯罪,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关系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环境污染职务犯罪则触犯了三重客体,行为人不仅违背了职务要求,而且还是对自然、对人类的犯罪,使得在地球上呼吸的每个人都不能自外其中,都会成为受害的一份子。因此,从人与人之间关系法转向人与自然关系法(至少二者并重),理应成为法学界、立法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高度关注并共同推进的刑法的未来发展脉络。
(二)“此在”对“彼在”心存敬畏
首先,有必要重温江山教授在《法的自然精神导论》中的一段话:“动物的生存本能、欲求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内涵。我们刚刚发展出了人在法,可它还相当原始、嫩稚,还难以规约我们的真实价值和行为…人的性智觉悟和理智能力都没有达到完全承担自身行为之责任的水准,而作恶又是极易为之事。谁来帮助我们收拾残局呢?一种可能性就是未来的我们(彼在),但它要求我们(此在)所作之恶必足以容许未来的我们(彼在)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否则,自在法恐怕只有行使它的最高裁判权,将我们罚下场去。”如果这种提醒不能够让我们觉悟而心生敬畏,很难保证人对自然所作之恶会让“未来的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难保证我们不会被提前罚下场去。阻止自在法行使它的最高裁判权,需要包括立法和司法人员在内的所有人类有足够的觉悟和行动。这,才是突破环境污染职务犯罪查处困境的根本出路。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3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