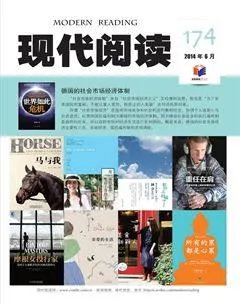书信传情:罗家伦与张维桢的恋爱
2014-12-29罗久芳
罗家伦(1897~1969年),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民国年间担任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长之职。1949年到台湾,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本书作者罗久芳为其女儿。
我的父亲、母亲,1919年底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集会中结识。不久父亲先出国留学,回国时母亲已获得美国大学奖学金即将启程出国,其间经过6年多的越洋通信,短短相聚而定情。一年后母亲完成了硕士学位,在双方将近30岁时才结成了夫妻。
他们的故事,日后在中国大学生中产生了一些传说,数十年来曾出现过不同的版本。
进入21世纪,我发现网上竟然还载有这类的传说,其中一篇的题目开头是,“罗家伦百封情书追到校花”。这句话的前一半离事实倒是不远,因为现存父亲在6年多中从海外写给母亲的书信有61封(15封寄自美国,46qou4IDVLU5/5xZc0VwpdMg==封寄自欧洲),另外有写上一两句话的风景片和艺术明信片,共约40张,还不算途中可能失落的少许,和回到上海后的一些,加起来足够有100封。这种“长途式”的通信交友与追求,维持了这样长的时日,竟然达到圆满的结局,大概算是比较稀有的事。
1920年初,父亲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寄了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给母亲,她也回赠了一张个人小照,可称是个好的开端。同年8月父亲再度南下,经上海赴美留学,匆忙中却失去了与母亲会面话别的机会,船未离港立即给她写了一张明信片投邮。
1921年春,父亲在普林斯顿大学才半年,便在信中鼓励母亲多读外国书,并告诉她清华大学招考女生赴美的消息,劝她积极准备。此后他常在信中谈到求学的方法和计划,也开始寄书送给她。1922年2月19日的信中,他提出次年学业告一段落时,想回国两三月,可以和她见面,不然二人另设法在欧洲相见;并且问起她家庭对她出国和资助的问题。因母亲把他的信给同学看的事,传到他耳中,为此表示不满。足见此时一切还嫌太早,这些问题大概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
1922年母亲考进了沪江大学,1923年父亲去了德国。1924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8月30日父亲借机给母亲写了一封问候信,这才恢复了冷却已久的通信关系。从那年年底起,父亲差不多每月一封信,谈阅读、求学的心得外,还鼓励母亲翻译书,也托她买书和笔墨。这时彼此在性格与志趣方面的了解渐渐加深,父亲的情感也在字里行间自然地流露出来。他在1925年5月20日的信中附了一副颈珠(珠子项链),是他参观英帝国展览会时为母亲选购的。这是他除了书籍外,第一次送母亲穿戴用的饰物,并说“我选的一种颜色,自己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我游展览会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分别了5年,他这份千里外的心意,一定使母亲感动,1926年新年,她寄了蜜枣和松子糖回赠。
这时,父亲的经济来源已经中断,1925年通过蔡元培校长向张元济先生借得巨款,计划在法国再维持一年。他虽热衷看书、买书、收集史料,却不得不做回国的打算,但国内政情仍然混乱,他内心矛盾。1926年1月至4月之间,父亲寄了好几次书,写了16封信给她,3月19日信里对她的称呼,从“薇贞吾友”换成了“薇贞”。
1926年4月,父亲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就在此时,母亲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计划秋季进入研究院。时间如此迫切,双方必然意会到如果再一次阴错阳差,后果可能不堪设想。5月底父亲突然接到母亲汇去的500法郎,可见她已能体谅他的困难、支持他的计划、愿意与他共处患难了。6月18日父亲在马赛登船,7月23日到达上海。他们结束了6年多的离别,但仅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相处。没有谈心的地方,他们有时在“法国公园”的一隅见面,两三周以后,似乎已经互许了终身。第二年母亲获得学位回国,1927年11月13日他们终于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结成了夫妻。
(摘自商务印书馆《我的父亲罗家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