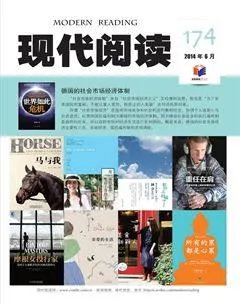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忧思录
2014-12-29艾青椒
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突然病故,这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和《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思这位杰出青年学者。
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无疑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是,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指出:“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都要面临的处境,但是,对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而言,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人)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的个性,这群人很容易感受到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
廉思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写到,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在5138位受访的高校青年教师中,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这些数字让我们震惊,一个精神贵族的群体,本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为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这群人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盛行的今日中国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的知识群体,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
精神劫难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的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
“50后”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10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10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1949~1966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何其困难。
教师分化
高校青年教师于是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并适应体制的弊端,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然对学术抱有敬意,他们倡导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鼓励。另外一群人则彻底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所谓变味的“应用性研究”靠拢,成为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部分学人则对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套体制,也不是完全退出体制,而是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他们或者通过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毫无疑问,这部分教师和前述青年教师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他们逐渐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愤愤不平之感。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他们完全沉浸在学术所构建的人文世界之中,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他们是一群“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读书人,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如今的大学校园正在形成一种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极其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或者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倡导去政治化的学术研究(比如史学倾斜于文献整理的学术计划)的课题、项目、计划大量出现,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成为学院主流价值,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
现在,“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怀旧热潮,民国优秀大学的风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向往。不管这种风潮如何被质疑为一种浪漫化的历史记忆或历史想象,我们都可以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发现,在大部分时段内,民国大学的教师收入确实足以让这群知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仍然可以维持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根据湘潭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陈育红的《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状况考察》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30元左右。即便是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生活费80元也已经相当宽裕。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30~1936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北京大学教师在1931~1934年的月薪收入统计显示其平均月薪在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达500元(外教更高达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当时的大学教授则普遍在校外还有数份兼课收入,光兼课收入几乎就能满足全家较为宽裕的生活。历史学家郭廷以曾经说,“1937年前5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除了学术自由且有充分保证之外,也跟物质生活、业余生活的丰富有关。
松绑
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高校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尤其是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最可贵的就是内心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地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弊端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既不做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也不做连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在完成学院体制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超越了幻觉,我们才能回到蓝天下的真实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内心和真实世界的学问之门才会真正地在我们面前打开。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重拾学术传统,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中国2014:改革升档》 主编:胡舒立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