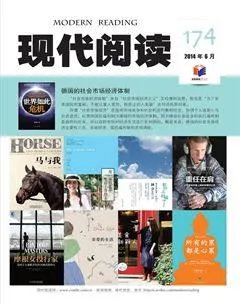史上著名的禁书机构和禁书时代
2014-12-29朱子仪
罗马教廷颁布的书目、英国的戏剧检查官职和美国的文化机构,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都曾被视为对文学艺术实施禁锢的象征。至于“禁书时代”,则指欧洲一些国家禁书最严最烈的时期。
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
教会禁毁书籍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基督教的草创时期。圣保罗的门徒曾大量焚毁所谓“迷信”书籍:公元2世纪后期的《穆拉托里经目》中既有权威性的《新约》篇目,也有须排除的篇目。教会首次给书定罪,是在公元325年的尼西公会议上。神学家阿坦乌的诗集《塔利亚》遭禁,作者本人也被判定异端而处以绝罚(受此惩罚者不得与别人来往)。教廷的第一个《禁书目录》发布于5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一世给图卢兹主教开列遭禁的伪经书目。早期教会禁毁书籍,其目的是维护教义的统一性,清除异端邪说。
有人认为公元495年由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发布的法令,是第一份《罗马教廷禁书目录》。但《基拉西乌斯教令》是一份推荐书目,与《禁书目录》出发点不同。不过,《教令》跟《禁书目录》一样关注公众读物,它明确指出:不得阅读已被查禁的书籍,即便是私下里进行研究。《教令》分三部分:《圣经》的权威书目;推荐阅读书目,包括神甫们的著述和殉道者事迹;被公会和教皇禁止的异端著述和伪经目录。14世纪的教会命令欧洲各大学教师不准发表未经教会检查的著作,世俗书商也须发誓只出售教会批准的书:1467年,英诺森八世下令书籍在印行前须交当地教会当局审批。这一教令旨在防范任何歪曲天主教教义的出版物。当时每本书都必须在题页上刊印教会当局准许出版的执照。一个类似的教令于1515年5月4日由列奥十世发布,并在各地宣读。该教令指示各地主教专门指定书籍检查员,对逃避检查者处以绝罚。教皇一再签发内容相似的教令,也表明教会控制印刷物不甚得力。1545至1563年间的特伦托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教会更有效地控制印刷物。这个教皇授权的立法机构,制订了《特伦托会议信纲》,其中包括在此后300年间一直沿用的书籍出版“10原则”。“10原则”的最后一条重申书籍正式出版前由地方宗教当局审批和地方宗教当局拥有查禁权力的原有规定。
1557年,教皇保罗四世正式发布了第一版《罗马教廷禁书目录》。仅过了7年,庇护四世通过特伦托会议,又发布再版的《禁书目录》。1571年教廷设立禁书目录部,由教皇亲自主持,委任枢机一人负责。该部直至1917年才被撤销,其职能归教廷圣职部。《禁书目录》共发布了12版。最后一版的发布时间是1948年。这部书目经不断增补,禁书总数达4126种,其中大量书籍是17世纪下半期查禁的,有862种。1900年以后,教廷查禁书籍的数量大幅度下降。20世纪上半期列入的禁书仅有255种。《禁书目录》发布以后,随着教廷权威的日趋削弱,教会也逐步失去了决定书籍出版和阻止书籍流通的权力,对禁书作者、出版商和销售人的处罚也从审讯、拷打、火刑逐渐变得无所作为,充其量也只是开除教籍而已。
宫廷大臣:英国的戏剧检察官
查阅美国学者安妮·莱昂·海特的《古今禁书》,英国宫廷大臣直接下令禁演的戏剧有:菲尔丁的讽刺剧(1737)、易卜生的《群鬼》(1892)、王尔德的《莎乐美》(1892)、梅特林克的《莫娜,瓦娜》(1909)和阿瑟·米勒的《桥上所见》(1956)。实际上挨宫廷大臣棍子的戏剧名作还远不止这些。
英国首相沃波尔于1737年6月6日使《戏剧审查法》得以在议会中通过:按照这项法令,一切剧本在上演之前14天必须先送当局审查,否则将吊销剧院执照并罚款50英镑。宫廷大臣在以后两个多世纪中,成了英国首席戏剧检察官。这个官职也因此臭名昭著。到了20世纪居然出了这样的怪事:一部美国戏剧的单行本畅销一时,全是因为在护封上极鲜明地印了声明,称英国宫廷大臣禁止该剧的演出。
萧伯纳写于1894年的《华伦夫人的职业》,也成了宫廷大臣禁演大权的牺牲品。直到1924年,宫廷大臣才取消禁令,允许该剧在伦敦公演。
易卜生《群鬼》的遭禁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出戏在作者的故乡挪威已遭敌视。在宫廷大臣下令禁演之前,伦敦评论界对《群鬼》也是一片谩骂声,说它是“实在讨厌的戏剧”、“直言不讳的下流货色”、“一部腐朽透顶的戏剧”、“百分之九十七的《群鬼》观众都是些淫荡之辈”。
禁演王尔德的《莎乐美》,宫廷大臣动用的是不准许任何戏剧涉及《圣经》里人物的古老法规。
欧洲各国的“禁书时代”
纳粹上台使德国进入了空前的“禁书时代”。1933年5月10日是个黑暗的日子。那天夜里在柏林大学前面的广场上,2.5万册犹太裔作家的著作被付之一炬。大批所谓“非德国”书籍在全国各地被焚烧。1935年2月,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犹太人中心开设了“纳粹禁书图书馆”,陈列各种在德国被希特勒禁止的书籍。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残暴举世闻名。1483年至1820年间,仅火刑处死者就达10多万人。西班牙教会在禁书方面与罗马教廷比起来毫不逊色。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禁书目录》要早于《罗马教廷禁书目录》。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使用除希腊文和拉丁文版以外的《圣经》版本,西班牙的《禁书目录》于1551年禁止西班牙文或其他文字的《圣经》。一年以前,该禁书目录还将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的全部著作列入。1640年,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又查禁了培根的全部著作。相比之下,罗马教廷对这位英国哲学家则要宽容得多。西班牙的《禁书目录》甚至列入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查禁原因仅仅是为了书中的一句话:“不是用心做的慈善事业是没有用处的。”名列该禁书目录的文学名著还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至于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直至1790年,西班牙的《禁书目录》才取消对它的禁令。
西班牙的另一个“禁书时代”是在佛朗哥1936年10月任西班牙元首以后。1939年,佛朗哥禁止各图书馆收藏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不体面的作家”的作品。佛朗哥政府还禁演易卜生的戏剧名作《群鬼》。1943年,西班牙作家塞拉(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遭当局查禁。他的另一部小说《蜂房》被迫在国外出版,11年后才获准在西班牙国内出版。
在欧洲现代禁书史上,爱尔兰一度臭名远扬。1929年,爱尔兰成立了书刊检察委员会,归司法部领导,查禁色情和涉及避孕、流产的书籍,被禁者无上诉权。于是,大批文学名著以这样或那样的罪名在爱尔兰遭禁。像左拉的全部作品、纪德的小说《如果它死了》、德莱塞的《黎明》、辛克莱的《大门洞开》、辛克莱·刘易斯的《埃尔默·甘屈莱》。直到1970年仍有4000种书被禁。
1853年,小说家龚古尔兄弟前一年12月发表在《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遭起诉。文章被指控为“有伤风化”,原因是文章引用了16世纪的一首诗。当政的拿破仑三世怕显得像个傻瓜,便亲自干预了这个案件。1856年,因写《巴黎的秘密》成名的小说家欧仁·苏,在流亡中完成了另一部小说《人民的秘密或一个家庭的数百年经历》,作为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直接反映。该小说在法国国内遭禁,作家本人也受迫害,死于流亡中。1880年初,莫泊桑的一首爱情诗因被一家小报馆照原文刊出,被检察官以“不道德”的罪名起诉。这首诗描写一对夫妻在夜花园里相亲相爱的情景。出诗集时已删去的两句是:“在一片白的墙上,显出两个并在一块的爱情的影子。”时隔不久,年轻作家路易斯·德普雷茨的一部小说以“淫猥罪”被起诉。陪审团判决他有罪,处以一个月的监禁和1000法郎的罚款。此时德普雷茨重病在身,在刑满获释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左拉就此事气愤地表示:“那些谋害这孩子的人是群恶棍。”
在19世纪中期,许多18世纪法国作家的作品被当局以“不道德”的罪名禁止再版。像伏尔泰、卢梭、阿贝·普雷沃、肖德罗·德·拉克洛、皮隆、克雷比永、米拉波,都有作品名列“黑名单”。被禁的还有16世纪法国诗人龙萨的作品及外国文学作品,如薄伽丘的《十日谈》等。
(摘自金城出版社《禁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