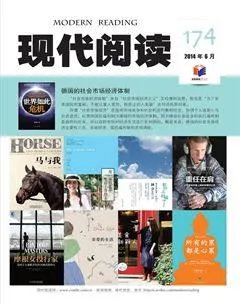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2014-12-29高连奎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将市场竞争和社会利益均衡相结合,协调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以贯彻国民福利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德国是在世界上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的国家,德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其“社会国”宪法原则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德国制胜的法宝。
政治领域是“社会国原则”,经济领域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德国进行福利保障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是中立的力量,由于市场经济对个人存在着一些威胁和挑战,而国家的任务,就是帮助个人应付这种困难和挑战。在德国,“福利国原则”也是被纳入宪法的,这也是德国在上个世纪50年里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来自“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的设想,他也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这句话的原创者。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将市场竞争和社会利益均衡相结合,协调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以贯彻国民福利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执行福利制是政府的任务,所以政府有权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概括来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主要有三点:市场经济、国民福利制和宏观调控。
“二战”后在德国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便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其执政纲领,后来社会民主党也抛弃陈旧的计划经济主张而皈依社会市场经济。
其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比如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
与美国相比,德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19世纪全世界都在处于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但进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都认识到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实行自由放任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提出的“保护幼稚工业论”,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20世纪20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时,德国弗莱堡的经济学家却提出了不同东西。他们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因为莱茵河一般被看做是德国的象征。
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用通俗的公式表示,就是“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政策应该实现的国民经济总目标: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这四大目标由于其实现的难度而被经济学家称为“魔鬼四角”。
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包括“二战”后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等莱茵河谷两岸的国家。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今日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国家。联邦德国创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莱茵资本主义的基础。
德国虽然信奉市场机制,但原则上,只要国家能够比市场提供更好服务的地方,都应该让国家积极活动。国家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建立和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应当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包括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通讯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生产,这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
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与信贷政策建立金融秩序,维护国家的货币稳定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还负担维护秩序的责任,负责确定市场参加者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条件,并且负责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德国把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比作足球赛中的裁判员的角色。
除此之外,国家还要通过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维持经济繁荣,阻止或者延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这也叫做“反经济周期的景气政策”,德国反对把一切都交给市场。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国家,英国学者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强调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与结构的同时,具体又将他们划分为4种类型。
英国的制度,强调社会与医疗保健服务,但是规定了与收入挂钩的福利金。
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高额征税,十分出色的国办的服务事业,包括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
中欧制度,没有十分庞大的社会服务福利,但是具有数量可观的福利金,主要通过就业关系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
南欧制度,与中欧制度比较类似,但是不那么广泛,国家提供救济水平较低。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贡献。甚至说,英国人贡献了自由,法国人贡献了民主,德国人贡献了社会市场经济,其实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实行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都相对比较平等,收入差距明显比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要小。中产阶级在美国占50%,在德国占75%,在瑞士或瑞典占80%。
德国模式抛弃了传统的放任,而是驯化了资本主义,给野蛮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通过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建设抑制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抑制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自由一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在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自由也像法律一样神圣,然而中国人对消极自由强调过多,对积极自由强调的少,这是最大的问题。自由,最通俗的讲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不包含违法的事情,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钱的话,很多事情都干不了,因此要保障民众的自由,首先就要保障民众先有钱。德国不仅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而且建立了从哲学到法律,再到社会管理模式一整套的东西。
在西方世界中,德国的所得税率几乎最高,包括社会保险金在内的税率超过了50%,而美国不到30%。这样的高税率,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免费教育造就了高水平的劳动力,在这一点上,德国与美国的反差特别强烈。美国新一代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于婴儿潮一代,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教育退化现象。这使得风雨飘摇的美国制造业更加难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也是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的主要动因。
经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而不放任,德国模式就非常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中,连美国媒体近来也纷纷承认,西方世界如果要维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和社会稳定发展,就必须效法德国模式,特别是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保障社会公平和限制两极分化。这都是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秘密。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德国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摘自上海三联书店《世界如此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