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表述方式的写生
2014-12-25吴灿
吴灿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为发掘新人,让艺术的火种越燃越旺。 本期本栏目特推出七位即将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莫高翔工作室毕业的女研究生,展示她们几年来师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工笔花鸟画家莫高翔研究中国画的成果,展示她们对工笔花鸟画的认识和理解,展示她们创造性的艺术才华。
她们七位,有的已为人妻,为人母,但多数尚为妙龄。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视野和情怀,以细腻工致的笔触,抒写生活的酸甜苦辣,或以锅碗瓢盆表达相夫教子之妻情母爱,或以超现实的手法阐述对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忧虑,更多的是以花香鸟语叙述对自然世界的欣赏和敬重。 总之,她们以一颗颗素朴的心灵,抵挡住各种压力和诱惑,虔心创作,描绘出一幅幅娟秀的画面。 透过她们的作品,我们仿佛触摸到了中国美术的美好明天。

东君拂开素心花 莫高翔 纸本墨彩 68cm×68cm
进入传统中国画家眼中的大自然,以绘画的物质载体纸或者绢为参照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大观小,以一种吞吐与俯瞰的气势,将自然山川浓缩简化,进入一纸图画,这是山水画;其二是以小见大,以微观视角看待世界,着眼的对象是一花一鸟,这是花鸟画。
庄子那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直觉性智慧,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的无限性。《梵网经》也形象地展示了一个层级累进的无限世界:卢舍那大佛坐于千叶大莲花中幻化出一千尊释迦佛;这一千尊释迦佛,分别居于千叶世界之中;而其中的每一叶世界中的释迦佛,又在更小的空间里幻化出一百亿位释迦佛,他们各自坐在属于自己的菩提树底下。这种超越经验世界的描述,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在自然界中,一朵花,一片叶,即便是它们的存在如此微不足道,仍然包含了无限丰富的内容。英国诗人布莱克以一首富有禅意的诗歌,描述了这一可能:“在一颗沙粒中见一个世界,在一朵鲜花中见一片天空。”汉语中更为普遍的说法则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我们不能将这种描述仅仅当成是宗教呓语或者文学想象,因为现代的粒子物理学从一个更为逻辑的角度证实了它的合理性。

境系列-琴棋书画 朱爱珍 纸本 95cm×95cm

境系列-锅碗瓢盆 朱爱珍 纸本 95cm×95cm朱爱珍当代女性承受的远比传统女性所承受的更多。 一方面,传统的家庭职业身份并未减退,承担照顾孩子、从事家务等活动仍被认为是她们分内的事情;另一方面,社会又要求她们进入公共社会空间,与男性一起参与工作,--一个没有正当工作收入的女性,也很难被周围的人所认同。 朱爱珍很好地处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中付出了多少艰辛,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投身绘画,但绝没有舍弃自己作为家庭女性的身份,所以在她的画面中,锅碗瓢盆整洁有序地排列着,呈现出别样的美感。 同时,属于文人雅趣传统的琴棋书画,依旧在她的笔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因为情绪已经传递表现到位,所以这种表现方式是否受到过清代"八破画"的影响,也不需要去作深入探讨。
但是,人类的日常世界里,在视觉上既不可能达到无限大,也无法达到无限小。我们所能把握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有限的、狭隘的中间部分。对于花鸟画家而言,他们仅仅是希望能够通过对一个微观物象的表述,来反映出自己对于世界的感受。
因此,不管采取何种描述方式,对于了解这一切的观者而言,他都能够清楚地察觉到,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相对于山水画的物象而言,花鸟画家笔下的物象皆为微观化的存在;对于这种微观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普通人通常无暇顾及,而花鸟画家却注意到了。这些平时微不足道的小趣味和小事物,经过细致地处理以及带有情绪化地呈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这扇大门以内的世界,既合符我们的日常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种日常感知。换而言之,它不荒诞,但绝对是我们所忽视的。
记录这一世界的方式,通常以“写生”的手段来完成。写生于绘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今天的学院教学中,它已经被泛滥使用。当今绝大多数艺术家对于写生的依赖,足以让古代的画家感到惊奇,因为离开写生,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就无法进行。对于后者而言,写生意味着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并以艺术语言将它的外在 形态和内部结构描述出来,——很少有人去思考它最初的意义。

双生花 朱 娟 绢本 68cm×68cm朱 娟文献记载中,唐代的边鸾最先创造了折枝花卉的构图样式。尔后,宋代将这一样式推向了顶峰。 取象不在多,一朵花也足够体现春天的气象,所以折枝花卉一直是花鸟画中重要的表现方式。它能更好地反映出一个画家对于构图的处理、物象的取舍等。 朱娟继承了这一传统, 同时也将蝴蝶的意象加入其中。 它们或者来自庄周,或者来自梁祝。 在蝶恋花这个古老的主题中,朱娟显示出了女性的温婉细腻,既有花褪残红式的伤感,也有小雨初晴后的清新。

四季·春 朱 娟 绢本 93cm×88cm
在《说文解字》中,“生”字指的是草木从泥土中冒出来这一状态。它的针对对象是植物。它描述的是一个自黑暗的地底进入阳光世界的过程。并且,它预示着这一过程结束之后,植物本身会产生的各种无限可能,包括吸风饮露,开花结果,等等。此后,这个简单的汉字衍生出将近二十种意义。《辞源》中的对于“生”字的两个解释,大约可以完整地表述绘画中“写生”一词的含义。其一是,活,与死相对;其二是,本性和天性。画出来的东西徒有其形,或者仅仅是一个准确的标本,都不能算是写生。
因为“生”的原初意义在于描述草木,所以“写生”这一汉语词汇,在传统艺术范畴中,也主要是指对于植物的描绘。传统的山水画训练,几乎不采取今天的直接对景写生的模式,因为山水画中的对景写生,会无形地给这一图式原本具有的包容性、游观式的表述加上一个限定性的框架。过去人物画创作中,有关写生(即直接面对对象描绘)的记载并非没有,但是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素材的收集,而非创作本身。画家更习惯于称之为“写真”。严格意义上的人物画创作,即使是肖像画,也都需要对人物的言行举止加以仔细体察。否则,人物会沦为一个模特,成为展示动作以及服装的道具,从而丧失他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
就今天的花鸟画写生而言,它是在传统“写生”意义上的一个延续,因而天然地与“写生”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血缘性关系。五代时期以花鸟画出名的画家腾昌祐表明自己的学画没有师承,仅仅是以直接描绘大自然中的动植物而学成(“工画而无师,惟写生物”)。北宋的赵昌自称为“写生赵昌”,他通常在朝露未 干的时候,绕着在花园中观察花卉,再调色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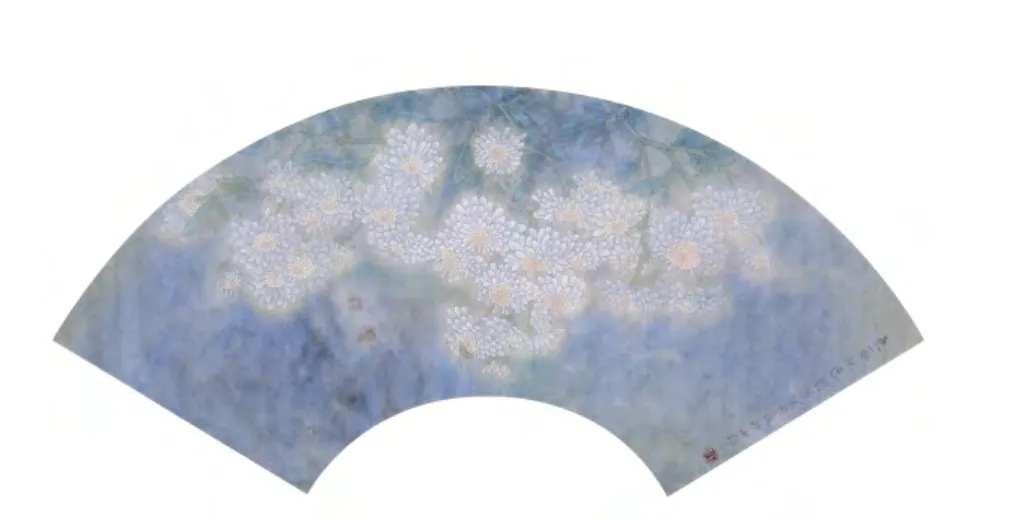
东篱秋色 刘 芳 纸本 110cm×50cm刘 芳在绘画中,题材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传统文人画题材,反复出现的也就是梅兰竹菊之类。文艺复兴时期,圣经题材的作品占了半数以上,其中又以圣母和耶稣的形象出现最多。在刘芳的作品中,物象的取材也十分普通,植物类的有菊花、莲花、蝴蝶兰等,动物类的有蝴蝶、游鱼、雀类等。并且,大多数作品都在表达对于传统的敬意,所以在她所有的作品中,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真诚。

妆 刘 芳 纸本 68cm×68cm
“写生”并非指对于自然世界地外部形态的忠实描绘(或者是尽可能忠实地描绘)。黄荃家族的画家,以淡而细的墨线勾勒画花,然后渲染色彩,将墨线淡化至肉眼无法觉察的状态,被时人“谓之写生”。南宋的赵孟坚,仅以水墨画梅、兰以及水仙,虽不赋色,但也被称为“善于写生”。表面上来看,前者主要表现的是物象的色彩,后者主要针对的是物象的造型。但是,更深刻的描述其实是,他们描绘了植物形态背后的精神。造型和色彩,都只是事物的皮毛而已。
植物的形态(在今天,花鸟画这一题材还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包括大量的人工器皿器物等),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几乎始终是一个静止状态。它可以让画家得以长时间且近距离地观察,并琢磨它的每一个角度所呈现出来的形态之美,以及形态以外的更深远的趣味。对它的写生,较为容易理解。

逸游·一 郭 月 纸本 80cm×70cm

吸·根 郭 月 纸本 180cm×97cm郭月安徒生的著名童话《海的女儿》中有一个场景让人十分难忘,他笔下的海底世界的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他写道,所有的大鱼、小鱼在海底的植物中间游来游去,就像天空的飞鸟。 郭月将这些文字的表述转换成了形象的图画。 各种鱼飞翔在空中,就好像是在水底穿行一样。 不过,鸟的存在,使得她的表述可能不止于此。 她的画面中,鸟有时候与鱼相遇,有时与鱼对话,有时它们又擦肩而过。 两种生活于不同空间中的脊椎动物,总是能够在同一画面中共存,既富有一种诗意,也产生了一种悖论。
花鸟画中的另一个重要物象“鸟”(包括所有能够活动的生物)的写生,又如何完成呢?那些掠过天空的飞鸟,花中飞舞的昆虫,在画家笔下出现的时候,我们会追问它当初是如何被观察到并被记录下来的。毫无疑问,其来源也是大自然。它们出现于画家笔下的时候,起初也许是一个幼稚而单调的造型,但是通过若干代画师对于这些形态的不断修正、积累、丰富,逐渐形成一些传统模式,普通学画者以此为基础,结合个人重新在自然中的观察,然后进行创作。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将过去的画家难以捕捉到的动物形态记录下来,再转换成绘画语言,——“写生”的意义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
不过,绝大多数普通欣赏者并不是动物学家,所以我们几乎也不会去关注它们在画面中的生理结构是否合理,飞行或奔跑的动作是否规范,而更在意对于它们的描绘是否生动。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关注到,它们在画面中的存在是否符合艺术本身的逻辑,使它们得以存在的绘画语言是否符合公认的表达方式。在具有一定水平的欣赏者看来,花鸟画物象的外部形态在花鸟画写生中只是一个基础,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尽管赵昌笔下的物象十分准确,但是欧阳修在《归田录》还是说:“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欧阳修批评的是赵昌的表达方式有所欠缺。

春分 杨欣欣 纸本 96cm×190cm

皿·之一 杨欣欣 纸本 73cm×73cm杨欣欣杨欣欣显然在努力迫使自己跳出写生这个框架的限制,将木质的雕花窗棂和瓷质的花瓶带入画面当中, 于是出现一种怀旧气息,但并不颓败, 凌空掠过的鸟以及翩翩起舞的蝶, 都为画面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的生机。然而,她的探索并没有止步。 本已残缺的断臂维纳斯石膏,被她截取中间的躯干部分, 并再次进行分割。 这种分割并非破坏性的, 而是有秩序地出现于画面当中。 这尊石膏像和同样被分隔的鸟、 开裂的瓷器一起, 在形式上达到了统一。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她的表述意义, 但仍能体会它所展现出来的美感。
莫高翔工作室成立十余年,培养的众多门生弟子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他们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除了起初一段时间的临摹,就是大量地写生训练。自南到北,从东往西,中国的各大植物园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因为有莫老师的指导,使得这种写生超越了收集素材的阶段,而具有更多的其他意义。其一,在一定程度丰富了他们的生物学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圣人诗教中的重要部分);其二,尊重自然万物,从中发现那些不为人所注意的事物并将之入画;其三,在写生过程中强调取舍、线条的锤炼以及构图的完整性,写生作品很可能就是一幅创作。写生既是花鸟画创作的基础,也是它的最高准则。因为这些思想一直贯穿其中,所以在莫家样式”的花鸟画作品中,总是洋溢着勃勃机。这成为当代工笔花鸟画创作及教学中极研究价值的个案。

徜徉 江 倩 纸本 145cm×150cm

凝露 江 倩 纸本 80cm×120cm江 倩莫氏工笔画的入门阶段, 都以临摹为主。 通过向优秀的传统学习,能更好的地掌握这种绘画语言。这种模式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学习方式。江倩的作品, 并没有从宋画中去寻找新的突破,而是通过结合写生,将宋画的一些模式向更深处发掘,诸如物象组合的疏密对比、动静对比等等,但是这种对比并不强烈,而是始终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不急不躁,平心静气,展示了宋画中格物致知的良好传统。

逐浪 李 凤 绢本90cm×90cm

心旅 李 凤 纸本97cm×110cm李 凤李凤的两幅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给人印象深刻。 二者的构图都是一样的,上面为天空,飞翔着一群鸟;下面是海水,卷起一些美丽的波纹。 中间纵向摆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使得画面无论是从上下来看还是从左右来看,都产生一种均衡感。不过,二者的差别也很明显,一幅作品中的鸟是自然世界中的海鸥,另一幅则是人工制作的千纸鹤。二者置于一起,就像交响乐一样,通过同一个乐句的不断演化,产生出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主题。

莫高翔教授与他的学生们

湖南卫视采访莫高翔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