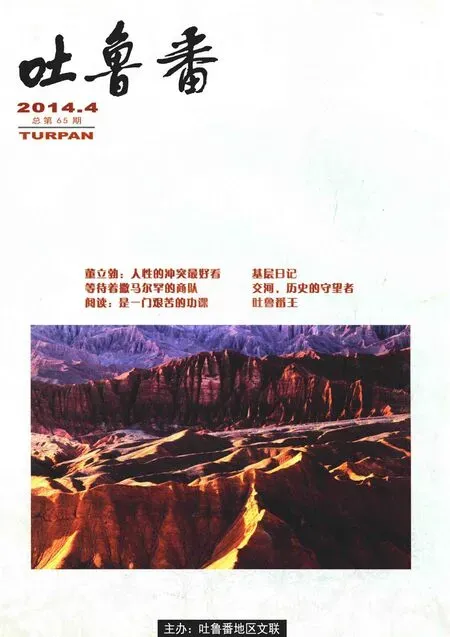奇怪邻居
2014-12-25季良
季 良

雅轩老头,与我住在同一幢楼里。他是我楼下的邻居。
与雅轩老头什么时候认识,具体的日子已记不太清楚,只记得那天,雅轩老头拉来了一大卡车的家什,就停在我住的这幢楼前的通道里。
当时,恰好我站在阳台上。看到随车来的人,把卡车上的东西,往这幢楼前卸。雅轩老头自己也帮着卸家什,并且忙得满头大汗。我便猜想这幢楼里,又添了新邻居。但是,雅轩老头到来,事前没一点儿风声。
随车来的人,卸完家什后,连个招呼也没打,就驱车走了。与雅轩老头形如陌路,好像并不沾亲带故。那些人,想必是搬运公司的临时工。
于是,我对雅轩老头仔细地打量起来:只见雅轩老头四方脸堂,面色如杏,没有皱纹,像是张女人的脸皮光滑;剃着小平头,头发虽短,但没白发,是否用染发剂包装过,不敢肯定。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的腰微往前倾,无论走路还是站着,都是那种内八字的脚。这内八字脚,就是脚尖对着脚尖,给人厌恶的感觉。甚至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瞅见就恶心,就想要呕吐。尽管我没朝他的脚尖看,但猜得出来,只有内八字的脚,走路抑或站着,才是那个难看的样子。
当然,我站在二楼阳台,往下看,也许会看走眼。这年头,看走眼的事情时而发生,弄错的事情也并不鲜见,就别说看人走眼的事情了。
这幢楼前的楼下,已只剩下雅轩老头,和他的老伴儿。那套不知被锁了多少日子的房子,被雅轩老头打开。少许,雅轩老头与老伴儿,便开始往房里搬东西。随车来的人已走,楼房前,除了雅轩老头和他的老伴儿外,再没其他人。邻居们相互又不认识,没有人出面帮助雅轩老头搬东西。
那些笨重的家什,被年轻力壮的人卸下车后,当下只靠雅轩老头,和老伴儿搬进房里去了。不过看得出来,雅轩老头的确有些力气,那些笨重的东西,被雅轩老头一个人,搂住三分之二,老伴儿只抱到三分之一。
雅轩老头搂着那些笨重的家什不累么?说不累,那可是假话,雅轩老头的脸上,那凸突的青筋就是见证,没有使出吃奶的力气,会是那个熊样?老伴儿紧咬着牙关,拖着那些东西,半天才移动寸把远;脸上的汗水,如雨点般地往下淌,这就证明那些笨重的东西,没有千斤,也有几百来斤。
几个小时后,一大卡车的家什,就无影无踪。这幢楼的邻居们,包括我在内,亲眼目睹雅轩老头和老伴儿搬家什,就像观赏了一场精彩的杂技表演,暗暗佩服不已。确切地说,雅轩老头和老伴儿,还真有点儿能耐,邻居们谁都佩服雅轩老头,和他老伴儿的力气。宝刀未老,谁不钦佩!
这幢楼前,又恢复到了平常的宁静。
每天,邻居们茶余饭后,便从楼房里走出来,聚集到并不宽敞的通道里吹牛调侃。这幢楼里,新添了雅轩老头一家人,邻居们便有了新的话题:这老头定是退休搬来的。一般退休的老头,都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度晚年。
客观地说,邻居们称呼他老头,也不准确。人们通常说,人满六十岁后,才能称呼老头。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没上六十岁。不过人们如今对保养很讲究,说不定他保养得好,才显得与实际年龄不相等的。
邻居们背着称呼他老头,尽管我为他鸣不平,但孤掌难鸣,我只能随波逐流,也叫着他老头。邻居们叫他老头,是私下里叫的,从没哪个当着他的面叫。当面叫他老头,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给他会增加几分压抑和恐怖感。世上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谁都不想就此离开人世!
他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雅轩老头,是我给他取的雅名。为他取个儒雅的名字,是我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因为他气宇轩昂,且有儒雅风度。他知道否,我想他不知道。因为,这是我在心中私下里给他取的雅名。
雅轩老头很少出门,不知什么原因,像个大家闺秀,深居简出。或许雅轩老头真的刚退休,失去平常按部就班的工作,一时不适应,便找个清静的地方,以忘记过去。往往陌生的地方,让人能够重拾生活的信心。
这幢楼里,不仅我没再看到雅轩老头,而且其他的邻居,也没看到雅轩老头抛头露面过,似乎隐遁地下去了。不但如此,雅轩老头自搬进这幢楼里后,离群索居,没与邻居们见过面,也没和哪个邻居打过招呼。
雅轩老头一家人,自搬进这幢楼后,并没让这里热闹起来,就像没添新邻居似的,仍像从前一样,依然没有朝气。这幢楼的邻居们,似乎什么东西自家都具备,不需向邻居借东西,也不需他人的帮助,平常互不往来。
闲下时,大家虽然聚在楼前聊天,但是从不串门,哪怕每天在通道里遇到擦身而过,都装着陌生的样子,视而不见,相互之间,很少寒暄。
这年头,人们整天忙碌,生活压力又大,谁还与他人打招呼,浪费张嘴的气力,哪怕只需嘴唇噏动。所以,这幢楼里的邻居们,与他人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神态,让人琢磨不透五脏六腑里,究竟装着些什么东西。
不过我的注意力,依然盯着雅轩老头。因为他是我楼下的邻居,仅一层预制楼板之隔。要是将楼板捅个窟窿,与雅轩老头就可直接对话。为了观察雅轩老头的行踪,我每天把窗扇的窗帘儿拉开,楼下的通道尽收眼底。
雅轩老头住在我的楼下,只隔着一层空心的预制楼板,我坐的这把铁架支撑的椅子,挪动屁股的时候,常常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这声音听久了,也就习以为常。陡然听到,心里必然厌烦。尤其在晚上,声音格外的响亮。我想雅轩老头在楼下,一定听得到楼上弄出的响动。在楼下,要是他听不到楼上的声音,除非他耳背;要不,他天生就是个聋子!
只说我楼上的邻居,就经常弄出响声。在楼下,我就听得一清二楚。说来凑巧,楼上住的是对苟合男女。邻居们都说那男人另有妻子和住房,本人没住在这幢楼里。楼上住的年轻女人,是他包养的二奶。究竟是他的二奶还是三奶,这幢楼里恐怕没人知情。说是他的二奶,这是我猜测的。
楼上是怎样布局的,谁也不清楚。因为这幢楼的邻居们,谁也没去串门过。我做书房的这间房子,本来不是设计的卧室,可楼上那个年轻女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这间房子却做了卧室。我听到的响声,就是他们苟合的时候,“哈哧哈哧”的颤动,继而震动着预制楼板,灌入我的双耳。
那男女混哼的声音传下楼来,就让我浮想联翩。因此,男人的本能就会有些反应,让女人欢悦的那东西,立马跃跃欲试。脑子里,便是一幕幕巫山云雨的景象。
人们常说,酒后失言。与文朋笔友几杯下肚,将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居然和盘托出。朋友们知道这个笑料后,便拿我开涮:怪不得近几年,你在文学上没有多大成就,原来你被淫秽笼罩,头顶着藏污纳垢之所。你的头上,被女人不洁净的东西经常笼罩,每天脑子里不想着风花雪月才怪呢!
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朋友们说我被淫秽笼罩,把朋友们的话哪当回事儿,无论楼上“哈哧”的声音再大,我依然泰然自若。那对苟合男女,也没碍我什么事,也没影响到我的思路,仍旧夜以继日地耕耘着。
楼上那对苟合男女,并不是我关注的对象,我重点关注的是楼下的雅轩老头,得弄清他的来历。因为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知人要知心。
我凭高临下,将楼下通道的情况,一览无余。突然,很少出门的雅轩老头,一反常态地出门了。这二楼的单元,是我精心选定的。当初就因这个位置的视野开阔,自然来风迎面轻拂,恍如世外桃源,恰似神仙居所。
这幢楼里的邻居,谁也不清楚,雅轩老头逛街,是从哪天开始的。这个秘密,我不会对任何人泄漏。否则,被雅轩老头知情后,以为我在监视他的行踪。我不是警察,哪来权力监视他的行动。他若告状,我就栽定了。
与雅轩老头相邻月余,仍不知道雅轩老头一家人的来历。譬如,雅轩老头以前干什么工作,一无所知。不过邻居们倒说出了一个消息:雅轩老头曾当过什么主任。这可不是空穴来风,是这幢楼的邻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听到有人喊雅轩老头什么主任。没承想,雅轩老头当即就答应了。
邻居们知道雅轩老头的这个官衔,与我知道我的楼上,那对苟合男女的秘密,都属于这幢楼的新鲜事。略有差异的是,一个属于隐私,一个属于被人们淡忘的主任;哪怕是个没多大实权的主任,总之是个官儿吧。
就我所知,主任的官衔较多,让人无法想像出,雅轩老头曾当过什么部门的主任。不过可以肯定,雅轩老头当过主任是事实,因为邻居们,在街上听到雅轩老头与他人谈话时,开口就“这个问题嘛,早晚是要解决的……”等腔调。要是雅轩老头没在官场当过主任,哪会说带官腔的话儿呢。
仅凭只听到别人喊雅轩老头主任,和只听到雅轩老头谈话耍官腔,就判断雅轩老头在官场上风云过,这多少有些牵强附会,谁都满腹狐疑。
可是邻居们,众口一词:雅轩老头当过主任毋容置疑,且不说其他,只说雅轩老头走路,好像怕踩死蚂蚁似的,迈着鹅形鸭式的碎步,那个叫官步呢。与老百姓匆忙走路的神态相比,天壤之别。要是雅轩老头,没经过久经锤炼,能走得那样炉火纯青?就凭这点,足可证明雅轩老头当过主任!
说心里话,即便雅轩老头真当过主任,对我们邻居又有什么好处呢,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主任的光环不可能在雅轩老头的身上再重现。可是,邻居们为这幢楼里,住着一个曾经当过主任的邻居感到自豪,每每在楼前,凑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说起雅轩老头当主任的事儿,就余犹未尽。
但邻居们,对雅轩老头又有些耿耿于怀,就是雅轩老头,至今没与邻居们打招呼,也没有语言方面的交流。姑且不说语言交流,连拿个眼神表示友好的举动,雅轩老头也没有过。邻居们异口同声:雅轩老头清高傲慢!
雅轩老头究竟是否为人傲慢,是否真的当过什么主任,目前又没有什么依据能够证实。因此,我就越发想搞清楚,这个奇怪邻居的身份。
心想,上街碰运气去吧。这世上,巧合的事情很多,说不定会遇到熟悉的人,其中就有知道雅轩老头情况的呢。当然上街去,并不只想要了解雅轩老头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想出去刺激灵感,以便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刚开始,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头顶藏垢纳污之所,被女人不洁净的东西经常笼罩,致使耕耘没有多大的收获。对这个事儿,不置可否。不过后来仔细地想来,倒又觉得还有点儿道理,人们不是常说,女人就是祸水!
这些无聊的说法,我当然不会轻易就相信。文化人要有休养,相信这些荒诞无稽的事情,让人知道后,不仅会掉面子,还会大降身价呢。
写不出作品来,是我像个大家闺秀,平常很少出门去感受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体验生活,又哪来的素材。写不出文章,是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整天坐在书房里埋头看书,或闭门造车,大脑里能不枯竭。
到街上去溜达,并不是真正去闲逛,是去寻找创作的素材。这逛街,倒真的逛出新鲜事儿来了,我亲眼目睹雅轩老头,许多非正常的举动。
在我住的这条巷子里,曾多次遇到悠然自得,迈着碎步的雅轩老头东张西望。有时候他抬起头,对街道的两旁聚精会神地、一丝不苟地观察;那模样、那神态,像在寻找什么宝贝似的。可这条巷子里,每次修楼房挖掘,都没挖出什么文物,又哪来的什么宝贝呢。这座城市里,只你雅轩老头才是火眼金睛,才认得宝贝啊。要是宝贝露在外面,早被人们一扫而空。
雅轩老头的这个奇怪现象,我没告诉邻居们,因为我想要深入地跟踪侦察,想彻底了解雅轩老头,缘于何种目的,要搬来我们这幢楼里居住。尽管我与雅轩老头,同住在一幢楼里,他住在我的楼下,我就住在他的楼上,但我俩遇上的时候,相互之间,都没有主动打招呼,和表示友善。
楼上与楼下的邻居,竟然像遇到的陌生人。雅轩老头没喊我。我也就没有喊他。平心而论,住在同一幢楼里的邻居,我该先向雅轩老头打招呼,因为我年龄比他小,晚辈得先尊敬长辈。然而,我没与雅轩老头打招呼。与雅轩老头不打招呼,是邻居们都说,雅轩老头自命清高,时常犯着当主任的职业病。我主动与雅轩老头打招呼,要是他不理睬,那我不尴尬啊!
在这条巷子里,我还有许多的熟人,听他们介绍,说雅轩老头和谁都不打招呼。时间久了,朝不看见,晚要遇到,与雅轩老头,在巷子里就经常碰上。雅轩老头是否知道,和我住在同一幢楼里,我就住在他的楼上。
或许,雅轩老头压根就不知道,我住在比他要高十几级台阶的楼上。
不过,从雅轩老头的眼神里,就可看出,他认识我。因为每次遇到的时候,他的眼神里,就射出一种亲昵的光芒,嘴角还浮出一丝的笑意。他不打招呼,也许他年长于我的缘故。世上哪有长辈屈节于晚辈的情况呢。
但是,可以肯定,雅轩老头不是哑巴。因为邻居们亲耳听到,别人喊雅轩老头主任,他当即就应承了。哑巴不可能回答,这点不需再了解。
到了这种份上,我不主动与雅轩老头打招呼,实在对不起他,毕竟我俩是楼上与楼下的邻居。当我准备张嘴说声“您好”时,可嗓子里,陡然间就像塞满了棉球,怎么也发不声来。心里明白,喉管发不出音来,就是邻居们常说,雅轩老头一副清高的神态,和他主动打招呼,他会理睬么?
人言可畏,却又得听之。其实,我不是那种没有礼貌的人。于是就改用笑容,和点头的方式,向雅轩老头打招呼示好。雅轩老头同样也用笑容,和点头的方式,给我以回答。就这样,我与雅轩老头初次接触了。
就因这一次相互示好,雅轩老头慈祥与和善的印象,便在我的大脑里记忆下来。当然也就扭转了,以前我对雅轩老头不公正的看法。与雅轩老头第一次接触,虽然只用眼神招呼,并没有语言方面的交流,也没问起他曾当过什么主任的事情,但我们以目示意,相互之间,都是传递的睦邻友好。
这幢楼的邻居们,也包括我在内,解不开的结,是雅轩老头一贯都沉默寡言。雅轩老头真的不爱说话么,除了他的家人外,恐怕没人知道内情。
不但如此,雅轩老头还有解不开的谜,他没儿女么?准确地说,雅轩老头自搬来这幢楼里居住,我们就没看到有人来串门过。且不说他以前的同事来串门,难道自己的儿女也不来串门么?这现象,让人不可思议。
在我住的这幢楼里的邻居们,都知道雅轩老头和老伴儿不爱说话,好像雅轩老头和老伴儿都是哑巴。至于雅轩老头的来历,以及在哪部门当过主任的事情,在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的情况下,就更难知道真相了。
因此雅轩老头的身世,无形之中也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这幢楼里的邻居们,便经常私下里议论雅轩老头的怪现象,并且也想解开雅轩老头身上的谜团。然而雅轩老头,仍像平常一样,在高温气流中,在大街小巷,一如既往地溜达,时不时左右顾盼,一副忧郁不安的样子。
夏天,人们都找阴凉的地方走,哪怕绕道,也要选择阴影里行走,以避免被烈日暴晒,把皮肤晒得黝黑,让洁白的肤色,变得黑不溜秋。然而这个城市里,街道两边的梧桐树,早被绿化公司砍光,新移栽的不落叶树木,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正在茁壮成长着。阴凉的地方,也就少得可怜。
人们每天上街,被毒日晒得汗流浃背,便骂绿化公司不是个东西,不该砍掉街道两边的参天梧桐树,让街道两旁的林荫荡然无存。为了城市建设就砍树,把居民遮阴于不顾,做出这样的缺德事,就不怕遭雷劈!
在这座城市里,从不找阴凉的地方走,和不骂绿化公司缺德,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雅轩老头。街道那么宽与长,阴凉的地方又有限,在似火的阳光下,雅轩老头常常顶着烈日,从不畏缩,在街道上溜达。有时候,雅轩老头对街道两旁正在成长的树木睃一眼,眼眶里似乎就有泪花闪动。
或许,雅轩老头是特殊材料铸成的。邻居们都这么议论着。因为人们从没看到雅轩老头,在街道上溜达的时候,往阴凉的地方去过,硬是顶着烈日在大街上闲逛,对街道两边新移栽的树木睃一眼,脸色就如天空的乌云。
街道两旁新移栽的树木,在烈日的曝晒和轻风中,枝摇叶晃,似乎欢迎雅轩老头到来,给它们做个伴儿,在无遮挡的阳光下一块儿受煎熬。那些树木的枝叶晃动,或许就是语言,仿佛在倾诉什么,只是人类不懂而已。
每到下午,我住当西晒的这幢楼,被残酷无情的太阳,烤得就如同一座火炉,让人透不过气儿。楼房一幢紧挨着一幢修建,楼与楼的间隔,又没多大的距离,高温气流便像懒狗一样,赖在房里不出去,令人窒息。
想必,雅轩老头和我一样,呆在房里忍受不住,才去巷子里溜达的。不过呆在家里,却有空调降温,即便再困难的家庭,也有电风扇吹着,总比在阳光下受煎熬好吧。可是雅轩老头,非要在这条巷子的入口处转悠。
我们居住的这条巷子的入口处,堆着一座如山丘般的垃圾。雅轩老头迈着碎步,总是围着那堆臭气熏天的垃圾打转,让人匪夷所思。
本来,街道对面五十多米远的街角,放置着专用的塑料垃圾桶。这条巷子的入口处,没有放置那东西,可有些人懒得走那五十多米远的路,却就地取桶。不知这条巷子里是谁带头,把垃圾随手倒在巷子的入口处了。
这年头,只要有人带头,马上就有后来继上的人。我看到邻居,把垃圾倒在巷子的入口处,大家都偷懒不想走那五十米,我又何必与自己的腿过不去,也就照葫芦画瓢,将垃圾倒在那儿。巷子入口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
环卫处的工人,不是专门放置的垃圾桶,一般不拖运。这不是环卫工人懒手脚,而是机器没有配备,铲地面上垃圾的工具。这下,就害惨了我们这条巷子里的居民,且不说苍蝇和蚊子,在巷子口飞舞叮咬过路人,只说已经发酵而臭气弥漫的那些垃圾,就让这条巷子里的过往居民难受。
巷子的入口,是每天的必经之道,不嗅也得嗅。随着日子的流逝,居民们又不自觉,垃圾越堆越多,气温越来越高,臭气也就愈来愈大。
这条巷子的楼房,修建得都不够标准,其他的不说,只说厕所通往粪便池的管道,大都短尺少寸,没按照图纸的设计安装,管道常常被阻塞。各户居民,担心把管道再给堵塞,诸如女人的卫生巾,擦过屁股的手纸等,就没再随手丢进便池里,却用便纸篓装着,提出门,倒垃圾堆里去。
巷子入口的垃圾堆里,不仅有擦过屁股的手纸,连女人来月经后,沾着紫黑色血迹的卫生巾,如同星罗棋布。养鸡和养宠物,屙下的屎,都倒到这个临时的垃圾堆。总之各户的脏东西,都倒来了入口处。那堆垃圾已经腐烂发酵,不仅臭气弥漫,而且苍蝇和蚊子愈来愈多,在垃圾堆里跳着街舞。
过往行人,便绕道走。绕道走的时候,都要把鼻子捂着,不然臭气就会钻进鼻孔里去,病菌就会随鼻而入,感染五脏六腑。每每路过那堆垃圾,拔腿就跑,生怕慢了半步,被苍蝇或蚊子叮咬中毒,以致不可救药。
可是雅轩老头,近来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旁发愣,似乎不怕被病菌感染,也不怕患上不治之症,望着垃圾入迷,哪怕烈日当头,纹丝不动。
难道雅轩老头不怕热?每天站在那堆垃圾旁,究竟想要干嘛呢?
或许只有神仙,才会知道雅轩老头的心理活动。雅轩老头那身衣服,就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般湿漉漉的。那身衣服肯定是被汗水湿透的。要是真不怕热,就不会流出汗水来。因此,邻居们就否定雅轩老头不怕热的看法。
雅轩老头不怕热,被烈日晒着,那定是假象,往往假象的背后,隐藏着秘密。究竟是些什么秘密,无从知晓。由此判断:雅轩老头是一个怪人!
我也同意邻居们的看法:雅轩老头的确有些怪异。其实,邻居们说雅轩老头是个怪人,就因雅轩老头不怕臭气熏天的垃圾,每天纹丝不动,站在那堆垃圾旁出神。这世上的怪人,还常常搞出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怪事情。
只说雅轩老头,就偏偏不怕刺鼻的臭气,和不怕被感染疾病,不仅白天站在巷子入口处的那堆垃圾旁,连晚上也站在哪儿守着呢,仿佛那堆垃圾里埋藏着价值连城的什么宝贝,担心别人捷足先登,捡走不义之财。
每天,雅轩老头盯在垃圾堆里的消息,被过路人传开,招来了一拨捡破烂的人。当下在垃圾堆里拾到存折,或未开封的红包,并不鲜见。那些捡破烂的中年妇女,听闻消息后,便如一窝蜂地涌来。与雅轩老头一样,她们也不怕臭气和苍蝇,在垃圾堆里像找宝贝似的,聚精会神地搜寻着。
那垃圾堆里,女人月经用过的卫生巾和手纸,腐烂发酵,散发出一股让人恶心的酒潲气味儿。这些中年妇女,整天泡在垃圾堆里,那股臭气便如雾霭一样,往她们的身上侵袭。可她们浑然不知,疾病可能会降临到身上。
那些捡破烂的妇女,把垃圾分为几类放在一块儿:譬如,女人的卫生巾为一类,手纸为一类,变质的食品等,分类很细致。但是,始终没有拾到金光闪闪的黄金白银什么的。当然,那么贵重东西,人家又怎舍得丢弃呢。
巷子入口的垃圾堆,被捡破烂的那些中年妇女一捣腾,臭气就四散弥漫。行人路过这里,恰好又遇到顺风,从她们身上飘出的臭气,便毫不留情地钻进行人的鼻孔里,被呛得喷嚏连天。甚至连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
过路的行人,便埋怨雅轩老头:不是雅轩老头在这儿守宝贝,那些捡破烂的妇女,就不会跑来翻动垃圾堆,酒潲气味儿也就不会融入空气中。这下倒好,整条巷子里都飘荡着臭气味儿。挨近垃圾堆的几户人家,便大骂雅轩老头:这个老不死的东西,每天像个神经病人,干嘛要守在垃圾堆旁!
刚开始,不知底细的过路人,以为雅轩老头也是个拾废品的。但对雅轩老头打量后,见他穿戴整齐干净,无论天气怎么炎热,常存礼仪之容,便否定了自己的猜测:这世上捡破烂的人,能穿戴得那样整洁?
那堆垃圾,安如磐石,仍像一座小山丘,屹立在我们住的这条巷子的入口处。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们上街去,都会避开那堆垃圾绕道走。不过除了上班簇的人们外,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就再没其他人绕道走了。
被邻居们认为自命清高的雅轩老头,每天依旧守在垃圾堆旁,似乎欣赏那些妇女捡破烂的精彩镜头,专心致志,很有专家的范儿。
那天,我从邮局回来,看到垃圾堆旁,围聚着许多人。人群中,时不时地发出助威呐喊的吼声。我出于好奇,便钻进人群中,凑过去观看。两个捡垃圾的妇女,为争抢像宝贝的垃圾,正吵得不可开交,争得脸红脖子粗。
那两个捡破烂的妇女,虽到中年,但为了争抢像宝贝的垃圾,竟然大打出手。这年头,无论什么人,都像个守财奴,当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时,便会如猛虎一般,哪怕身衰体弱,也会拼个你死我活。或许,在人们的心目中,垃圾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这是大家都可拥有的东西。
当两个妇女祸起萧墙,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我环顾周围,没人前去给她们解围。就连曾当过什么主任的雅轩老头,都站在垃圾堆旁眉头紧锁,无法琢磨透他的心事。少许,雅轩老头背过身去,掏出手机捣鼓着。
一阵撕心裂肺的警笛声后,终止了垃圾堆里的战斗,两个累得筋疲力尽的妇女,被警察带走了。虽停战了,可两败俱伤。凑热闹的人们,顿时就离开了。但是,雅轩老头依旧站在垃圾堆旁,没有打道回府的举动。
雅轩老头虽看到了我,但没拿眼神与我打招呼。我对雅轩老头,也没什么表示。在垃圾堆旁,与雅轩老头站了很久,没看到一个来倒垃圾的人。白天,将垃圾倒在巷子的入口处,被他人看到,不当面骂缺德才怪呢!
在垃圾堆旁,我不敢久留。从过往行人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人们异样的目光,好像我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一个好端端的人,为何要久站在垃圾堆旁?久站下去,我也没那个能耐,不说腿脚受不住,那似火的烈日,无遮无挡地照射到身上,把皮肤晒黑事小,可就怕被垃圾堆里的病菌感染。
我逃也似的走了。走的时候,没向雅轩老头打招呼。我走,仿佛在雅轩老头的意料之中,对我匆忙离开,雅轩老头并没露出惊讶的目光。
近几天,外面太热,就没出过家门。对街道上的事情,一概不知。
这天是个阴天,我到邮局寄稿件去,路过巷子的入口处时,那堆垃圾奇迹般地消失了。那些捡破烂的妇女,已无踪无影。让我纳闷的是,雅轩老头仍站在巷子入口处那个曾堆过垃圾的地方。只是手里多了一把蒲扇。
这条巷子的入口处,那堆垃圾已不翼而飞,地面好像被清洗过。垃圾究竟是被环卫工人拉走的,还是做好事不愿留名的个人所为,不得而知。这年头,人们都只想着,把钞票怎么捞进腰包里来,谁愿把到手的钱,花在运垃圾的事情上去。要是哪人自掏腰包运走垃圾,除非是傻逼!
那堆垃圾,尽管从巷子的入口处人间蒸发,但腐烂发酵的垃圾,或许已深入到地层里去,并没被清洗地面时完全灭绝,臭气依旧在空气中弥漫。
当下,世事多变。只说雅轩老头的举动,委实有些古怪,以前他那副蔼然可亲的神态,今天已荡然无存,如同一尊横眉竖眼的雄狮,竖立在那个曾堆过垃圾的地方,手摇蒲扇纳凉的时候,眼睛对过往行人扫描着,像一个会演变脸的演员,行为怪异,让人见了陡生几分畏惧,望而却步。
前几天,我在这条巷子里遇到雅轩老头时,他不仅露出一丝微笑,还拿眼神表示友好呢。可是今天,我路过的时候,雅轩老头竟然目不斜视,仿佛从来就不认识我似的。雅轩老头的态度,怎会变得如此之快呢?
天气虽是阴天,但气温仍然很高。我得赶快去邮局寄稿件,早些回家去享受电风扇的凉快。别再理会雅轩老头的神态变化,那股臭不可闻的酒潲气味儿,他雅轩老头的鼻孔受得了熏染,可是我嗅到就想要呕吐。
到邮局寄稿件回来的时候,雅轩老头还伫立在原地,就是以前堆过垃圾的地方。我去邮局后,雅轩老头是否离开过曾堆垃圾的那个地方,恐怕只有神仙才晓得。不过,我从倒垃圾去的邻居们,个个一副厌恶的眼神,和避开雅轩老头绕道走,顶着烈日,到街道对面五十多米的垃圾桶去倒垃圾,就可猜出几分,雅轩老头只怕没有离开那个曾经堆过垃圾的地方。
人们避开雅轩老头绕道走,想必是有些讨厌他。当然,这也是我和邻居们,都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心想,雅轩老头站在那个臭气依旧的地方,身上难免不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和病菌。当下的人们都讲卫生,担心以前腐烂发酵的垃圾,散发的病菌会感染上身,那可是要命儿的事呢。
晚上,住在这条巷子的居民,也包括我在内,都会出门倒垃圾去。这条巷子的入口处,以前那个临时堆垃圾的地方,自从垃圾被拉走后,不知什么原因,再没哪人带头倒垃圾了。如今两条腿就要多付出些力气,走五十多米的路程,将垃圾倒到街道的对面,环卫处专门放置的垃圾桶里去。
这天晚上,我倒垃圾去,远远看到,以前堆过垃圾的地方,坐着一个人,虽然有路灯光照耀,但相隔的距离太远,看不清坐着人的面孔。我边走边思忖:那堆垃圾虽然已经运走,但是那地方的臭气依旧,是什么人不怕臭气熏,坐在那儿纳凉呢?看那个人摇着蒲扇,想必是坐在那儿凉快。
今晚,我本想就近偷懒,将垃圾倒在以前堆过垃圾的地方,给两条腿省下些力气。那儿坐着一个人,这个想法要泡汤,哪敢厚着脸皮倒垃圾呢。在我前面二十多米远,也像我一样提着垃圾袋,去倒垃圾的居民。要是他们将垃圾袋,丢在以前那个堆垃圾的地方,我就照猫画虎、如法炮制。
然而,倒垃圾去的居民,或许担心被病菌感染,都绕开以前倒垃圾的地方,径直向街道对面的垃圾桶走去了。顿时,我幼稚的想法,灰飞烟灭。
凭借路灯的光亮,我走近曾堆过垃圾的地方,觉得坐在那儿的人,倒像雅轩老头的背影。愈走愈近,终于看清,的确是雅轩老头。这老家伙坐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想干嘛呢?即便晚上纳凉,也要找个干净的地方呀!
想与雅轩老头打招呼。当想起雅轩老头,近来诡秘的举动,和邻居们的议论,说雅轩老头的行踪,越来越古怪。正常人,每天昼夜会坐在臭气依旧,那个曾堆过垃圾的地方?种种迹象表明,雅轩老头的神经出了问题。
当即,想与雅轩老头打招呼的念头,就打消了。顿避开雅轩老头,绕道走,闪电般地离开曾堆过垃圾的地方,将垃圾倒到对面的垃圾桶里去。
每天傍晚,我住的这幢楼里的邻居们,呆在家里热得难受,便跑出家门在楼前纳凉,众说纷纭:雅轩老头的神经,只怕出了毛病,火热的天气,戴顶破草帽,坐在烈日下晒太阳?要不是神经不正常,那就是疯子!
人们更加惊诧的是,每日昼夜,以前堆过垃圾的地方,不知在哪时候摆放了一张弹簧床,撑着一把太阳伞,雅轩老头手摇蒲扇,躺在那张弹簧床上,逍遥自在,似乎那块地方被他买下来,已属于他的私有地盘。
过往路人,见雅轩老头每天躺在臭气依旧的地方,便私下猜测:这世上求生是人的天性,又有谁就想死呢。这老家伙不怕被垃圾的病菌感染,又不怕撒手西去,要不是神经不正常,那就是脑子出了问题,疯了!
雅轩老头疯了。这个消息,是这条巷子里的居民散播出去的。当然,我也持这种看法,一个好端端的人儿,为什么昼夜不呆在家里纳凉呢。
雅轩老头疯了,的确让人惋惜。因为雅轩老头,毕竟有过一段当主任的辉煌史。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没弄清雅轩老头,究竟当过什么主任。不过邻居们曾亲眼目睹,听到有人喊过雅轩老头主任。可是,这事偏偏就没让我撞上,要是被我遇上,就会问喊雅轩老头主任的人,真相也就大白了。
每天,这幢楼的居民们,都议论雅轩老头疯了的事情。但没人站出来推翻雅轩老头没有疯的说法。因为,找不到证明雅轩老头没有疯的依据。
说心里话,我确实无能,没把雅轩老头的身世,和雅轩老头是疯了,还是未疯查清楚。当然,我不是刑侦警察,又哪来的侦察技能呢。每天,看到雅轩老头躺在烈日下的太阳伞的阴影里受煎熬,尽管心痛不已,却又爱莫能助。因为我不是医生,无法诊断出雅轩老头究竟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尽管这条巷子里的居民,都说雅轩老头疯了,但我认为还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因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依据,可以证明雅轩老头疯了。
幸好,我给雅轩老头取的雅名,是在心里取的,直到今天还没告诉邻居们。要不然,我也会跟着雅轩老头搞得身败名裂:一个疯子,凭什么给他取个儒雅的名字?人们知道我私下里给他取个雅名后,不骂死我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