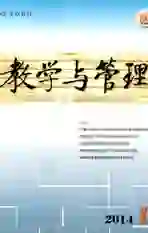文学教育的异化与本体回归
2014-12-17秦春
文学教育功能作为文学的一种在场方式,其“教育者”身份却变得越来越可疑,更多的表征为思想道德教育以及科学认知,文学本有的教育属性却被遮蔽而处于一种异化状态。究其原因,文学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审美特性异化为科学认知、价值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是文学教育沦丧的肇始,最终致使文学教育成为以“文学”为手段的教育,而不是真正的文学教育。文学教育真正的实施,就必须让“文学”归位。
文学教育 功能异化 本体回归
文学之所以能提升人生境界,让人更成为人,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接受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学的语言质料、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等表层感知上,而是要透过浅表对文学形象的深层体悟。在这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不是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教益,而是将接受者植入到文学作品中,置身于另一世界里,获得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提升,从而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内涵,远离“蒙昧”和“野蛮”。然而,文学这种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在当下却越来越变得可疑。文学教育虽仍“在场”,但未取得合法“身份”而处于异化倾向。
一、文学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
文学所发挥影响人、教育人的作用原本生成于文学自身,是文学内在精神内涵的自然显现,也才使文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相区分。一般学科的教育往往根据一定时代和社会诉求,培养合乎一定规范和标准的人,即“上所施,下所效也”。在这一点上,教育体现出先在规定性、内容系统性、行为目的性和价值上的功利性,而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文学具有自身的审美性、形象性以及精神品格,它所体现的教育目标不是根据一定先在目标的预设,而是对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把握;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实利,而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然而现行的文学教育却忽视了文学自身品行,文学教育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一种将文学作为某种“手段”的教育,文学教育作用的发生不是来自文学本身,而是根据外在意志强加到文学上来,最为典型的就是将文学作为道德教育、伦理教化,使文学肩负起另一种教育目的。
将文学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表现尤为突出。被朱自清誉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诗言志”的诗学命题,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烙印,而被清人刘毓嵩认为是“千古诗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而托名子夏而作的《诗大序》则是对“诗言志”德教意蕴的最好注本。《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的前半段明显来源于《尧典》的“诗言志”,而后面只是对诗的道德伦理教育的进一步发挥,凸现了诗在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中的突出作用。真正对“诗教”观念进行全面阐释当属孔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功能归结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后世文学的审美、认识、教育的所有功能,从而奠定了我国文学教育发展的走向。由此也说明了“诗言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观念,而是以对人的道德品格教育作为逻辑起点,最终将《诗》演绎成道德教育的载体。后来中国古代文论在“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主导下,文学注重道德教育并以道德标准衡量文学的价值就显现得更加清晰,最终致使文学背离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将文学作为达到某种教育目的的手段,即使到近代,文学在民族自强和救亡图存的召唤下,文学又在救亡图存中肩负着神圣使命,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可以说一直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教育走向,到五四时期的新人说,以及建国以后的四有新人等,都依稀可见文学教育中的道德因素和思想教育的影子。这样的文学教育过多的承载着社会道德形态的宏大命题,必然导致文学这一本体异化为教育手段和工具。
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文学自身特性规定了文学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性灵教育、精神教育,而不是道德教育。袁振国曾对美育和德育进行了区分,其实也揭示了文学教育与德育的不同。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的意志,具有强烈的客观性、确定性,美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道德是理性的,而美感是非理性的。因此,德育重在说理和模仿,美育重在感受和领悟。道德在本质上是一元的,美在本质上是多元的,美的生命力来自于审美对象的与众不同,来自于审美活动的个性化。道德的社会性意志决定了德育的规则性与强制性,而美育在本质上是反规则的,它鼓励人们自由想象。德育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它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统治需要紧密联系,而美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外在目的的力量[1]。这种对文学教育中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最终致使文学教育远离了文学本身的特点,只能导致文学教育的沦丧。
当然,我们说文学教育异化为思想道德教育,但也不否认文学教育具有道德影响。不过这种道德影响绝不是事先的一种预设,一种强制灌输,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文学接受主体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内在精神境界提升的自然体现。
二、审美特性异化为科学认知
文学的基本属性是审美属性,文学教育作用的生成离不开文学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和感悟,而这种审美体验、感悟又无关功利,是超越现实的。德国古典美学创始人康德曾从鉴赏的角度揭示了文学教育这一特性。他说:“美是不依赖概念而作为一个普遍愉快的对象被表现出来的。”因为在审美鉴赏中不关涉阅读主体的利害关系,而具有普遍性,同时他还对由美、善、快适三种对象所引起的愉快进行比较,认为“在这三种愉快里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强迫我们去赞许”,因而,“判断者在他对于这对象产生愉快时,他感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于是他就不能找到私人的只和他的主体有关的条件作为这愉快的根据,因此必须认为这种愉快是根据他所设想人人共有的东西。结果他必须相信他有理由设想每个人都同感到此愉快”,亦即在审美阅读中消解了人与他者的界限,有的只是对人心灵世界的影响,最后他还谆谆告诫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鉴赏的关键,因此值得十分注意。”[2]也就是说,文学教育是通过阅读鉴赏实现的,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在审美体验中摆脱现实的限制,进入到精神自由的心灵空间,形成一种“对于对象的存在是淡漠的”,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将审美作为沟通“现象界”与“物自体”,使人从一种“感性的人”上升到“理性的人”。
康德揭示了文学教育的审美特性而不关涉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科学认知。深受康德影响的席勒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自己的审美教育理论。他指出:“只有当他在审美状态中把世界置于自身之外或观照世界的时候,他的人格才与世界区分开,……观照(思索)是人对他周围世界的第一种自由的关系。如果说欲望是直接抓住它的对象,那么观照就是把自己的对象推到远处,使其不受热情的干扰,从而把它变成自己真正的和不会丧失的财富”,通达到人的精神世界,因为“只有美,我们才同时既作为个体又作为类,也就是作为类的代表时才能享受到它。感性的善只能使一个人幸福,因为它是以独占为基础的,而独占总是排他的。……绝对的善只有在一般无法假定的条件下才能使人幸福,因为真理只是忘我的代价,……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谁要是受到美的魔力的诱惑,他就会忘掉自己的局限。”[3]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教育发挥精神的价值,进入到精神自由的世界,使人的精神得到了陶冶和提升。
因此,文学教育的实现是以审美为前提的,如果本着认识论的思维,对文学进行肢解而作为对社会、世界的认识途径,其结果只能是对文学教育的扭曲。
然而,在当下文学教育中,基本上还是以道德载体和工具理性而建立起来的文学教育模式。温儒敏曾指出:“讲语文课特别是文学作品,阅读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反复阅读或者朗读,才能更好地进入作品世界,让学生在感受、体验和想象中得到熏陶,提升审美能力。”但是,“以往常见的教学模式主要由教师讲,而且往往是一背景,二词语,三段落大意,四主题归纳这样一类老办法,学生难以产生兴趣。”[4]在这样文学教育方式驱使下形成了强大的阐释体系,以致形成一套“规范化”、“标准化”、“格式化”的话语权威,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地分解和阉割,生硬地将文学教育分解为道德内涵、思想认识、知识结构和表现形式等几个部分,并根据一定教育目标的预设,在文学中抽象出文体知识、段落大意、写作特色和主题思想,最终文学在阐释中“削足适履”,比附其中“微言大意”,形成一套规范化的话语形式,如本文“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说明什么,揭露什么,赞扬什么,认识什么”等行之有效的套话、空话和假话。本来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在抽象概念、知识标签的规范下,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进入到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甚至我们一看到文学作品就会想到她能给我们有怎样的思想影响,能给我们怎样对世界的认识。
这种科学认知思维异化了文学教育,我们从文学中感受到的仅仅是作为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社会人”,不但不能使接受者灵魂高尚起来,精神崇高起来,反而导致受教育者的精神空间停留在假大空的抽象理性层面,自由的灵魂被禁锢在简单、教条、单向的宏大话语体系中,不但丧失文学接受者,也使文学教育沦丧。
三、价值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
如果将文学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和认识世界、获得某种确定性知识的途径,那么文学教育所固有的价值理性必然被工具理性所支配。
理性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由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概念引发而来,现在则指称观念、判断、概念、定义等。这种由“逻各斯”演变而来的理性在近代西方被推从到极致,甚至成为检验和评判一切存在和事物的标准、尺度,并且其内涵还在不断变化。霍克海默指出,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概念又演变成一种新的概念,那就是技术和理性相结合而成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就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去选择达到自己目的、满足自己需要的最有效的手段,关注实现目的的适用性,只追求一种知识、一种工具的效用性和行动方案的选择。这是一种追求实用至上的最高准则,其价值尺度就是效用,一切对象只是作为有用性而判断其价值。崇尚工具理性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促使人们只注重追求功用、效益,而放弃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自身被贬黜为对象,人只是按照社会这架机器要求在培养和塑造人,人的主体性则成为这架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就如他所说:“这种支配不仅仅为人与其支配对象相异化付出了代价,而且随着灵魂的对象化,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甚至于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神化了。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世界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统摄下并促逼着人只能听命于理性的摆布,更为可悲的是艺术也将成为工具理性的附庸。他进一步指出:“具有整体表现性的艺术,在各个细枝末节上都效仿科学,并重新迎合着世界,成为意识形态的复制品,成为一种温顺的再生物。”[5]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文学价值也成为工具理性统摄下的再生物,丧失自身所固有的价值,那么,文学教育就体现出仅仅把文学看着是达到切合自身的某种目的的中介,完全忽视文学的对象性存在。
而价值理性是一种传统理性,它追求的是人的意义、理想、信仰以及人的终极指向,以人的生存论为皈依的一种精神关怀。原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中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文学教育更应该注重人的价值理性,而且在当今社会由于过分注重工具理性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更需要价值理性去制衡。因文学在对人的精神守护、心灵陶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重新认识并确立文学的教育作用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主题。
文学教育必须回到文学固有的价值理性上来,恢复其艺术符号——价值载体上来,挣脱理性和功利的樊笼,将文学教育切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求解人类情感世界的悲欢离合,探索人类生存的精神情怀,从而将匆忙与庸碌的人们带入到文学的世界中,有可能重新清醒和从容地审视心灵感受,体悟到人生的真谛和人类的精神生存的本真生存状态。就如卡西尔所说:“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世界,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6]从而引导人们避离肤浅狭窄的庸常世界,返回到人生的原初状态,重塑人类的精神世界。
四、文学教育的本体归位
长期以来,文学教育就是在这种认识理性和科学认知的规约下一路走来,将文学作为实现某种外在规定性的手段和工具,而作为文学教育的文学本体一直游离于文学教育之外,用一种“他律”的规定性强制渗透到文学中来,文学教育所固有的价值却被异化。文学教育的真正实施,必须回到文学教育的“文学”上来,体现文学自身的品性,让接受主体主动参与、自我构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学教育应有的作用。
文学教育首先是审美性教育。文学教育作用的生成离不开对文学的审美阅读,而审美阅读是一种超功利的文学欣赏活动,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实际的知识,而是一次精神之旅、灵魂漫游。特别在近现代美学中尤为注重文学活动中这种审美的非理性特性,把审美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接受者进入文学情境中,完全是一种忘却自我的超越现实的审美境界,将主观的情感投射到文学作品中,与作品、形象甚至作者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灵魂的升腾,就如力主“移情说”的立普斯所说:“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而不是一种涉及对象的感觉。毋宁说,审美欣赏的特征在于在它里面我的感到愉快的自我和使我感到愉快的对象并不是分割开来成为两回事,这两方面都是同一个自我,即直接经验的自我。”[7]布洛的审美“心里距离”说也揭示了文学教育的这一特点。心理距离作为审美生成的条件,只有在主体同实际对象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后才能发生。这种现象在文学教育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因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世界,而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才使文学形象在我们的视界中得以呈现。在我国美学界流行的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不再是预先存在的等待审美主体去认识的美,而是强调主客体在审美活动活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审美意象,从而在审美活动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超越和升华,是一种对人生、生命的体验。
文学教育依据审美活动得以实现,但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在这过程中,文学形象则是其基础。文学的形象性是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文学正是借助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是作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表达,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特定的事物,根据自己的情趣、思想、情感以及审美爱好等对事物的一种独特感悟和理解,因此,作家往往有着与一般人不同和独到的感悟力与理解力,能够敏锐的观察到别人没有观察到的事物独特之处,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作品,并给人以生动、直观和新鲜的艺术形象。
文学正是通过形象来表达思想,传递情感,是具体直观的、也是可感的,与科学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根本的区别。其他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抽象的概括,运用逻辑、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的,直接让人们从中得到规定的、确定的、可实证的知识或道理,即使在社会科学著作中也有形象,但是这里的形象只起到证明、说理、论证的作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阐述事理,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而已,它本身并不揭示什么,而且在这类著作中的形象本身就是理论家思考的对象,他们在思考时,不会投注任何主观情感因素,仅是作为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论证。
如果文学教育中不把文学归位,而是将文学看成是没有生命的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将某种外在的目的凌驾于文学之上,对文学中的形象进行人为、片面的解构和分析,必然丧失文学教育应然作用。正如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劝友诗》中所说:“大自然给人的知识何等清新/我们混乱的理性/却扭曲事物优美的原形——/剖析无异于杀害生命。”[8]他虽非论及文学教育,但文学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一经冷静的理性剖析,文学就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这种冷静、理性是文学教育中的大忌。因此文学教育要把握文学审美属性,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对艺术形象的把握,进入到作品所营构的境界中去完善自身,在以艺术形象所营构的文学世界中忘掉现实世界,从现实中“离去”,进入到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精神世界中与作者、形象、历史、古人或大师对话或沟通,从而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形成“形而上质”,实现文学对人的教育作用。
————————
参考文献
[1] 袁振国.教育新理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 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 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 温儒敏.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5] 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 彭锋.美学的意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6.
【作者:秦春(1969-),男,江苏滨海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阜宁分院,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郑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