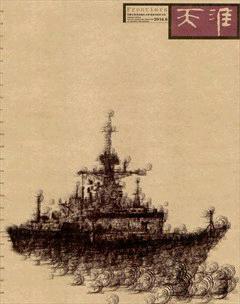我们乡下
2014-12-17马丁
马丁
招魂
我们乡下人的观念里,人的三魂六魄平日居住在身体里。身体就像一个移动的家。身体带着九个灵魂移动,从这里到那里。梦游的时候,灵魂从鼻孔里出来。它们的所见所闻成为那个人睡梦的内容。如果这时候有一种所谓“净眼”的人在旁边,他就能看见极小极小的红孩儿从左右鼻孔里钻出来,在屋子里到处走动。偶有声响,小人儿迅速钻进鼻孔。若是那人已经醒来了,而还有小人儿没来得及回去,那个人就失魂落魄了。但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不一定熟睡,醒的时候灵魂也会离身体而去。当然,我们在古代的文学书里也能看到这种醒着也失魂的情形,年轻男女一见钟情,魂魄也被对方吸了去,整日里病恹恹的茶饭不思,俗称“相思病”。对他们症状的形容常见于各种书籍和口语:“像丢了魂似的。”失魂落魄的人整日没精打采,身体失去了方向感。人们就要举行一个招魂的仪式。我们乡下为失魂的人举行的叫魂仪式与弗雷泽描写的类似仪式非常相近。从这仪式看,灵魂有时候并不熟悉自己寄居的身体,身体常常丢失自己的灵魂。为此我们要多创造机会,让身体和灵魂彼此之间熟悉和眷恋。
乡亲们的笑
我们乡下有个很阴的人,我父亲称他为“死人棺材里的一只手”。作为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人,我父亲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生动。这个“死人棺材里的一只手”,一笑就是“哼,哼哼”,我父亲对我说,听,这就是冷笑。我们那地方还有一个著名的傻子,常常对着人“呵呵,呵呵呵”,这样出声的时候,口型始终没有变化,甚至失去了控制,所以鼻涕和哈喇子交汇在一起吊在下巴上,看起来非常恶心,有的人就朝他扬尘土,一边扬一边说:“去,去,到别的地方去傻笑。”我有一个熟人,从前是瘦子,后来成了胖子,从前他的面孔小而且挤在一起,我们乡下把这种疙瘩脸称之为“小猫的膝盖”,现在他的面孔很大,像集体食堂的面盆。我这个熟人,一见面就说胡话,一说胡话就仰脖子,一仰脖子就“哈哈哈,哈哈哈”。让人莫名其妙,这大概就是狂笑。书上经常提到一种苦笑,我们乡下有许多苦人儿,照理说我对这种笑很熟悉,但实际上我并不是熟悉。后来我寻找原因,终于明白苦笑往往只是表情而没有声音。至于我父亲经常提到的刀笑,我至今还未遇到。
庙官
在我们乡下,从前有一位庙官,战战兢兢伺候神灵许多年。伺候神灵与伺候人间的大人物不同,不仅需要谨慎小心,还需要绝对的恭顺和虔诚。傍晚的时候,他端着清油灯,在寝宫的幔帐下给神灵整理床铺,弄平龙床上的蚕丝褥子,展开薄薄的缎被,做成被筒的形状。然后退回自己的住处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留心倾听,直到深夜有马蹄声进入庙门,达达,达达,响到寝殿那边去了,他才关好庙门,轻轻地躺下。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来,依次打开山门和正殿的门,洒过又细又密的水滴,扫干净前后的院子,再整理了大殿里的香案。这时太阳冒花了,他蹑手蹑脚走到寝宫门前,用手指弹一弹,进去,小心地收拾好床铺。他在叠好被子之前,总是习惯性地摸摸里边。当他感到明显的温热的时候,总是感到满足和欢喜。就这样,他侍候神灵许多年。有一年,庙官的独子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庙官已经做好了失去孩子的准备。大家劝他去求神,就像他多次替别人求过的那样。但他认为自己最了解神灵,神灵早出晚归,操心忙碌的都是天上人间的大事,所以实在不想打搅。但孩子病到万分危急了,老伴跪下求他,他没有办法了,就去跪在香案前的尘埃里:“我伺候您这么多年了,您知道我的为人。请您指点我,那孩子害的是病还是命?我不为难您,我只要实话。”神灵犹豫了一会,告诉他,他的孩子会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他千恩万谢,磕头如捣蒜,满怀希望回家,想尽了办法。结果孩子不治身亡。经此变故之后,庙官一步一步捱到庙里,最后一次跪倒在香案前的尘埃里:“我伺候您这么多年,换来的就是您用虚言哄我。从此咱们君子两百姓了啊。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站起来,长揖出了庙门,终生再未与神谋面。这个庙官不是虚构的,而是真有其人,他是上上辈人。他耳朵不好,有一个绰号,我不方便在这里说出。我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了希腊的神人关系,想起了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他后来改名以色列,意思是“与神角力者”。我的上上辈人在庙里祷告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借神力,神借人力。”人有求神灵、解决那些看不见的事情的时候;神也有求人、解决那些看得见的事情的时候。自从上上辈人之后,我们乡下的小民完全拜倒在神像前了,只见屁股,不见脑袋;屁股撅到天上了,脑袋贴到地上了。人越来越渺小了,几乎看不见了。当你看不见人的脸面时,神灵的面目也模糊不清了。唉,唉唉……
哭丧
我们乡下老人去世的时候,儿女要嚎啕大哭,要泪如雨下。据说去世的人的灵魂最初要经过一段黑暗、荒凉、阴森的黄泉路。儿女的哭声传到那里,就会变成歌声,伴随着亲人的灵魂走向候判所。传说没有提到泪水滴到那边,是不是化为玫瑰雨。我们乡下老人去世的时候,儿女们万万不能发出笑声,据说笑声传到黄泉,就是从天而降的石头。一声笑就是一颗石头,纵声大笑就是接连不断的石头雨。在石头雨中,逝者的灵魂无所遁逃。
报应
我们乡下有个懂阴阳八卦的男人给一家人驱鬼。我们到底没弄清楚,不知道是因为家道贫寒呢,还是家有病人心情抑郁呢,或者是故意怠慢?反正东家给他的吃喝很是平常。这个好吃的男人很愤慨,于是在念经时,夹杂着念了调侃的话,据亲耳听见的人说,他在咒语中夹杂了这样的观感“:……进得屋来,往上一看,椽棒檩子;锅里一看,酸菜饼子;炕上一看,婆娘女子……”不久以后,这个人的一个孩子死了,据村里人说,因为他乱念经亵渎神灵,遭了报应。啊哈,记住,在我们乡下,一个男人因为伙食欠佳,发了牢骚或开句玩笑,竟会遭神报应,我们乡下的神脾气可大哩。
坟园
他刚去世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他那样清洁的人,肯定受不了泥土的黏重和潮湿。无法诉说使得他有些寂寞。我还想,黎明和黄昏肯定是非常难熬。时间流逝,转眼二十年了,我想他不仅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而且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了。陆游的诗说:“此身行作会稽土。”他也一样,真正成为鼓楼山下的一抔土了,看,他的坟头与周围浑然一体,青草蔓长,盖住了当年祭奠的地方。我坐在坟园里,一边轻抚着墓草,一边听着无名的鸟鸣和鸟鸣衬托着的无边的寂静。这寂静里,他依然温和地凝视着我,而我,凝视着草丛中摸索着前行的一只甲壳虫。
黎明
在我们乡下,请不要在黎明醒来。这时候最静,最黑,也最柔软。这时候,狗要迷糊,鸡要打个盹。这时候,只有一个神仙,拄着拐棍艰难地走,只有这个神仙,才把借人家的东西归还。请不要在黎明醒来,如果你夜里难以成眠,请在此时入睡。钟想鸣,但太潮湿,翅膀想飞,但没有方向。你不要在黎明醒来。如果你无能为力,偏偏要在这时醒来,千万不要点亮灯盏,就在心中数星辰。数着数着,就会遇见自己;遇见自己的时刻,就有光明透进来,跟着光明开始你的白昼。
顺友
我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伙伴叫顺友。顺友十五岁的时候死了。死得很突然。据顺友的三叔说,半夜里叫唤头疼,他爹说等天亮了去找医生,孩子说他实在等不住,等不住就咽气了。顺友的爸爸天生一张苦瓜脸,儿子的死却给他带来了一星半点的骄傲:“他积修好,过去得快,没有受难啊。”说完他的苦瓜脸上竟然露出了快慰的微笑。听了这话,我们也吃惊不小,实没想到平平常常的顺友,竟有这么深的道行,把死这么难的事情弄得这么干脆利落。我们想起在学校里合伙吃馍馍的情景。顺友拿的永远是杂面馍馍,又有一种怪味道,所以大家都嫌弃,不要他一起吃。顺友呢,磨磨蹭蹭总把小布包混在大家的一起,掐一块自己的,放到嘴里嚼,再掐一块别人的,又放到嘴里嚼。掐自己的时只掐点面皮皮,掐别人的时候掰一大块。我们一起有个面皮比较硬的家伙,实在忍不住了,就揭露他每天从家里拿两种馍,一种是人吃的白面馍,一种是喂骡驹的杂面馍。白面的往往在路上吃,如遇见熟人,就把手缩进袖口里,像怕冷的样子。杂面的留到学校用来交换大家的吃。揭露者越说越来气,竟把盘腿坐着的顺友的头摁住往两腿间压,一边压一边问:“他妈的,说,我们是你家的牲口吗?我们是你家的牲口吗?”顺友一声不吭,只是配合着尽量往低处伸脖子。当然,第二天,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顺友死了约半年后,乡下就有传言,顺友托了梦,说他得的根本不是病,而是命。说是几年间乡下那地方非正常死的年轻人很多,阴魂冥世不能去,阳世不能来,就聚集在一个叫冰地的地方,日夜游荡。这帮厉鬼生前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他们中间缺个能写会算的会计。顺友正符合条件,他们就勾去了。孩子在阴间当了会计之后,乡下人见了顺友父母,就都发出啧啧的称赞,说顺友是方圆有本事的年轻人,活着的时候能看出来。顺友父母也很高兴,连声说:“不枉生他一场,不枉生他一场。”
敬神
正月初一,早早起来拜过祖先和长辈,就去拜神,拜的主要是东岳泰山大帝,他的名字是黄飞虎。《封神演义》上有他的事迹。他好像是很大的一个神灵。当然,我们村庄周围,我们的村庄上空,我们的头上和心里,还有其他一些神,将军爷、娘娘神、土地爷、财神爷什么的。有的全家老小都去拜神,他们拿了香烛纸裱炮竹,穿着一年里只洗了这一次的衣服。大家在庙院里跪下来,对着四面八方的神暗暗说着好话,来年里的一切都寄托在一跪一拜中了。当然,也有不信神的人,不去拜神,只是在大年初一的早上睡着。对这些人过去有人谴责,现在没有人说闲话了。但等那不信神的家里人有了祸事,人们会猛然想起,他不信神,他也没拜神。人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人也是一个幻想着长久的东西。人是一个有缺陷的东西,人却是一个懂得完美的东西。对人来说,神是一个寄托,神是一个想望,神也是一个尺度。
小年
当我再次回到乡下时,我发现过小年的仪式已经没落。打工回来的年轻一代忙着发短信、喝滥酒和打麻将。他们不需要相信任何神和神话。窪德忠的书里说:“把用来生火的灶视为神的象征,同对火的信仰一样,历史相当久远。孔子对灶很重视。”从孔子开始的祭灶仪式被年轻一代废除了。如果说过去我们乡下虽然遥远闭塞,但它在空间、时间和文化上仍然有所归属,它是整个传统世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乡下与世界——无论是当代的还是过去的世界——联结的脐带被割断了,我们的乡下在沉沦。在这沉沦里,我看见灶神在腊月廿三这一天两手空空,神色沮丧地飞升,飞升,消失在高高的云天。
告阴状
在我们乡下,鬼魂好像是人们的邻居,超自然现象是人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传说中,许多人都曾经与鬼魂相遇,但远没有《聊斋志异》那么浪漫,有的人被鬼魂用泥塞住了七窍,奄奄一息,有的干脆丢掉了性命。其中我知道得最为确切的,是尹寸的故事。尹寸是当地一个很厉害的人,说话果断,做事攒劲,但也心狠手辣,惹着了不是饶爷爷的孙子。话说那一年,尹寸和地方上另一个地头蛇起了纠纷,兴讼告状,打了几年的官司,最后以尹寸胜利告终。但那人即使死了也不肯服气。我们那地方有告阴状的习俗。所谓告阴状,就是阳世间求告无门了,就舍下性命,到阴曹地府阎王那里再去告。那人突然间就死了,后来我们听说是去告阴状。尹寸晚上睡梦中听见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着他的名字:“尹寸!尹寸!”尹寸起来,一边披了衣服,一边应着:“来了,来了。”等他开了大门,门外却无一人,只见麻乎乎的月亮下,门前的小路一直通向不远处的池塘,绕过池塘,没入高高矮矮的树丛。尹寸往池塘那边走了几步,突然就头皮发麻,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转身就回来了。第二天晚上同一时刻传来叫门声,但尹寸不再答应,而是抄了家伙开门,门外照例什么都没有。第三天晚上,尹寸没有睡着,和衣躺着等待,半夜叫门声传来时,他既不应声,也不抄家伙,而是镇静地开了门,走出去,一直走到小池塘的边上,在那里坐了一会。天亮后,尹寸就张罗着给自己做棺材,我们乡下的人都很惊奇,尹寸好端端给自己做什么棺材,一般来说,我们乡下做个棺材,也就是三天工夫,做到第二天的时候,尹寸病了,他开始给妻子安排后事。第三天,棺材做好了,他看了看,笑了笑,表示满意,但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不久就去世了。直到很久之后,尹寸的妻子告诉我们,她丈夫在响起敲门声的第二夜,就明白是对头告了阴状,阴曹地府派鬼来敲门,叫他去对质,他是活不下去了。只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乡下的人还惦着,尹寸和他的仇人在阎罗殿上打官司,到底谁赢了。这是在我们乡下发生的鬼叫门的故事,虽然千真万确,但我们觉得它近于穷乡僻壤的封建迷信,终究登不得大雅之堂。所以在文明发达的城市、大学和有识之士之间从来也没提起过。但近日突然看见美国的白宫也闹鬼。二十七岁的詹娜是布什的双胞胎女儿之一,她接受NBC知名主持人杰尔莱诺的专访时透露,她在白宫的卧室有个壁炉,某晚她睡得正熟,却听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歌剧乐曲,她仔细听了听,发现是从壁炉传出来的,“吓得我赶紧跑到妹妹的房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宫也发生过如尹寸经历一样的鬼叫门的事情。第三十三任总统杜鲁门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抱怨,“我整天听着鬼上下楼的声音。凌晨四点,我被敲门声吵醒,可是我打开房门时,却根本没有任何人。这该死的地方显然有鬼!”所不同的是,尹寸被鬼叫门的声音惊着了,而杜鲁门只是被烦着了。
乡下的风
乡下的风说:春天我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夏天我带着热量,秋天我带着又细又弯的刀子。风说,当我吹过古代战场遗址的时候,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个人闻到了腥味。当我赶上送殡队伍并超过它的时候,也带着这种味道。我没有立刻离去,我还在灵柩的前面徘徊,我的后面走着孤儿寡母。路边的野地里还有一些男女,无言地拾着苦苣菜。麻苦苣,真苦苣,两种苦苣他们都要。现在他们把竹篮子放在一边,他们停下手中的铲子,看着送葬的队伍。他们的目光,像是浅颜色的灰鸟,绕着灵幡飞来飞去。风说,我呼呼刮起来,挂落了那些鸟,我把灵幡卷起又扔下,它散了,乱纷纷落下,但盖不住棺材。风说,在此之后,如果我强劲了,就是前面走了,如果我弱了,就是我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