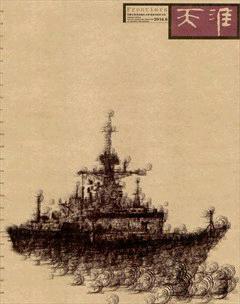从门口延伸
2014-12-17谭岩
谭岩
大门
大门像摊开的书页,凝望它就如读一部家史。有的门修饰考究,宽而厚的门扇,上了红褐斑的铜把手,青石的门凳;有的却光裸着没有漆的木板,上面的两个门环也只是用一根生锈的铁丝铰就,树蔸似的门柱已被蚁蚀去了半边,似放在门口的两个蜂窝。从门上可以读出主人的高低贵贱,富贵荣华。可是不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高贵还是卑微,大门都能让人同样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世间的风霜不会因人而分彼此。
乡村的大门总是笨重而牢固。把两扇门掩上,就像要抵挡一个世界——风雨、贫困,如蝙蝠样寻找着栖息的人间的不幸。可是人刚转身,大门吱的一声又开了,像人不胜重负的一声叹息。无论何时回过头来,大门总是张着一条缝隙,岁月的往事如一股风挤了进来,举着一片树叶在院子里跳荡,仿佛是谁拉着一张皮影,在向跨进这个大门的人们说古道今。
大门是一棵什么树放倒了做的,后人已不知晓,但是那棵树一定是很粗很高,两扇门全是四块半拃厚的木板,还有那门框,全是一拃多厚,连木纹也是浑然一体。这扇大门开始装上去的时候,那屋也一定刚刚做起,墙土还是一层光滑湿润的蜡黄色,房子的主人也还年轻,清瘦的脸上是完成一桩人生大事后疲惫而欣慰的笑容,站在大门口喜庆的鞭炮声中迎接四方的宾客。那时大门的木质还是湿的,泛着一层光鲜的木黄色,微风轻快地穿门而过,带来一股树木的香味儿,让人感受到初生般康健而向上的气息。
早晨大门打开的时候,会奔跑出一阵拍打着翅膀的鸡鸭,晚上掌灯关锁门户的时候,下门闩的声音是逝去的又一个日子的回声。在这一开一合的瞬间,一个个日子都从这大门里溜走了。
大门开合了一次又一次,就像人的一生翻了许多页,诉说了人生的许多故事。大门已很陈旧了,像一部发黄而陈旧的线装书的封面。原先光滑的门板已像苍老的皱纹似的露出了粗糙的木纹,曾是嫩黄的木板色现在已是像泥土似的灰朦——这就像人的希望,起始总是那样完美,但后来就残缺了。总见孩子坐在那已磨得光亮的门槛上玩耍,不知道从这大门里走出的孩子又将是何种的命运。也有老太太坐在门框上做针线,不知道她是不是头一次跨进大门来时,那曾经因羞赧而红了一身的着嫁衣的女子?
每到大年三十的团年饭时,人们总在大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一如既往地乞求着人生的祝福。大门总是沉默着,默默而忠实地看守着那贴在自己身上的祝福,像一个忠实的老仆,直守到这些红艳艳的祝福在又一个四季轮回中经历日晒风吹而发黄剥落。虽然它知道未来的日子并不是人们设想的坦途,新的一年也不全是人们美好的理想,但是它一年四季,总是面对空旷的未来充满了等待。
大门一生的功绩,就是开、合,每一次的打开与关闭都饱含着希望与失落,荣光与梦想,像舞台的序幕。虽然戏常不同,剧有悲喜,人有净丑,但是序幕却同样为之开合。迎亲与出殡,欢乐与悲伤,出自同一个门槛儿,从同一个地方起步。
人们的幸福与痛苦,只是增添着大门封面里的内容,打开大门,就可看见一个家族史的延续,人生剧的演出。人的一生会穿许多不同的衣服,但脸还是那张脸。如果没有大门,连风也会找不着回家的路。
农舍的大门常常有些低矮,不管是谁进出门,都要低下头来。那是告诉过坎的时候要多看一看脚下的路。当你跨出门去,回头望着那扇大门,正午的阳光正好照在那两扇扉页似的门扇上,一半是明亮的阳光,一半是忧郁的阴影,那是大门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人的一生。
从门口延伸到大路上去,总有一段距离,人们进出门的来来去去,就会形成一条小道。这条小道常常很难走,总是一片泥泞。下雨的时候,上面会垫上几方砖块或者几个石头,人们举着伞小心翼翼地踩着回家,好像踩着河里的石凳上一条船。
家里有老人的,下雨时仍要出门去掐猪草,戴一个斗笠,提一个篓子,手中拄一根棍子,小脚踩在泥地里,一走一滑,走不了几步就摔倒了,篓子棍子在一边,人在一边,如果运气好,没有断胳膊断腿,身上也要痛好几天。从外面进门来,脚上也是一层厚厚的泥,似有千斤重。用一根棍子把鞋上的泥刮下来,一刮一大堆,但是还是刮不干净,人走去走来,地面上就沾上了泥,稍不注意,脚下一闪,就会踉跄出一身冷汗。
雨下得并不大,瓦檐上的雨水也没有流成线,只是不断地滴,也不见地上有行潦,水全沁进了地里,不知道这浸不透的地到底有多厚。小路上全是自己和他人深陷的脚印,杂乱得如没有理清的家事。望着从大门伸出去的泥泞小道连着大路,大路又一直伸进了远方的雨雾里,就会费解这远方的路是不是一般难走?
为铺门口的这段路,费了不少的心思。如果是烧煤,就会把那烧完的煤球用火钳夹了丢到门外去,想填平一两个泥坑,但那煤灰被雨水一冲,又漂走了,还是一团泥,一走脚下一软,鞋陷了进去。
天晴了好多天了,那门口的一段路还没有干,坑坑洼洼,像一团绞成的麻花。想把那潮湿了的玉米抱出来晒,打开袋子一抖,那玉米又蹦到了那还没有干的泥地里,又要费工摘好半天。玉米摘出来,还是沾上泥了,见鸡在旁啄食,只好丢过去,鸡跳起来咯咯地叫得很高兴,人却惋惜万分——这是粮食呢。天晴了,那一车谷也要拖去卖。把一麻袋一麻袋的谷抱上了板车,却怎么也拖不动,一时往左,一时往右,板车轮子偏去偏来,还是不能动,不是陷进了这边的土坑,就是被原先垫着的一块砖挡着了。
于是下决心整门口的这段路。先是从河里挑来沙子,不知打了多少个早工,肩上又磨破了几层皮,终于把那一段路全盖上了石沙,再下雨,地上也不会成稀泥难行了。可是,一次又一次雨水的冲刷,将那些石沙冲走了,石子冲得七零八落,滚到了一边,那沙也流进泥土里去了,这路又是一片泥泞,人一走,鞋上又是一圈泥,像怪物的两只大脚。
但是人若一旦发起狠来,什么也阻挡不住。于是搬出了原来准备做屋泥墙的水泥,请来了瓦工。几天工夫,门口的那一截路就修好了,水泥路,笔直笔直!
雨自然对它无可奈何。黄豆大的雨水从空中落下来,也只能在那条路上撞得粉碎,最后只好怏怏地从两旁悄然流去。可是修了水泥路,有时也会让人失落。没有水泥路的时候,天晴了几天了,地上还留有深凹的脚迹,从这脚迹上还可以回想起某一天做过什么事,为做一件什么事时自己差点跌摔了一跤。可是这水泥路上却不会留下任何印迹,雨水只会把路冲刷得更干净。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不是幸福的时光,而是艰难的日子。
那水泥路上仍会沾上泥,不注意时脚下也会打滑。因为人不总是走在水泥路上,从泥路上来的脚总会沾上泥。隔一段时候,就要拿着锹去清除上面的泥。一面用锹铲着上面的泥巴,一面会想,能将所有的路都铺上水泥路吗,人的一生都不走泥巴路?
门口铺了一条水泥小道,毕竟是方便多了。下再大的雨,从门口伸出来的水泥道总是像一块跳板似地伸着,人们举着伞或者戴着斗笠从泥巴路上跳上去,就会愉快地走进自己的小巢。
庭树
稻场上有一棵古树,一年四季地青着,并不随四季的喜怒哀乐而枯荣。它不是很高,刚刚平齐屋顶,但是看上去很坚固,虬曲的躯干呈现铁灰色。它生长在稻场的边上,人们天晴的时候会在稻场上晒黄豆或者一地的高粱,如果这树挡住了投进稻场来的阳光,有一片黄豆或者高粱像打湿了似的在一片阴地里,人们就会去把那伸到稻场上空的枝柯砍去。那枝也很结实,人们砍半天,只能砍下一些骨头似的碎末,而那刀不是砍豁了一块就是折断了刀柄。
于是树只能朝场外生长,身子永远向一边倾着,像长久地用力拉纤着什么。
树是什么时候栽的,已无人知晓,只听这屋里的老太太说,哪一年涨大水,一家几口全爬在这棵树上,屋被洪水冲塌了,人却没有伤着;又是哪一年大饥荒,逃荒的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跤摔倒,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而一家人全靠刮这树皮才活了下来。因此人们只是砍上面挡住了稻场太阳的枝,并不想把它砍了作柴烧。
割过皮的树身漩着一个又一个疙包,像包藏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又像一段段岁月的句号。然而这些凸露的疙包却成了孩子们上树的阶梯。他们常常爬上树去玩耍、掏鸟蛋、捉蝉,站在那枝杈上探望平时看不见的远方,想看河水流到了什么地方,想象山那边又是什么模样。傍晚有鸟在树上盘旋,像袅绕着温暖的炊烟,夏日也有蝉躲在上面鸣唱,像对跑远了的孩子声声呼唤。若有人爬上树去,想捉那蝉,蝉必鸣叫着飞走了,流声似牵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地系住了孩子的童年。
正午的时候,人们会坐在树荫下歇凉,让那枝叶遮挡毒针似的阳光,夜晚到来的时候,那树又会摇曳着清风,让人们坐在它的下面清磨长暑的时光,而那一汪清水似的月总是浮在苍老的枝柯上。
人们的生活总是与树息息相关。那幢老屋似船,屋旁的树就像系船的树桩,而一条沉甸甸的索链,就是人们忘不了的思乡。思乡的情感让走出故乡的心牢牢地停泊在月光朗照的古树下,使在外面走天下的人儿不让自己的心一同漂泊异乡。
葱绿翻涌
走进乡村,就像走进自由的大海。那一幢幢农舍看似零乱,却像一艘艘可以任意漂泊的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规蹈矩却弥漫着散漫。
一户人家就是一个自由的世界。门前可种竹,需要作篓子、筛子、凉席的时候,可以去砍几根,堆在院子里,请一个篾匠来,看那一根根篾条在一个老篾匠手里龙飞凤舞。凉席做成了,可以摇着蒲扇坐在院子里,看夏夜的月亮如何从山顶升起来,又像一块冰样坠下竹林去。屋旁也可挖一口堰塘,种上藕,夏日里开几朵荷花,风一吹,满院是荷的清香。屋旁是一块块的稻田,在失眠的夜晚,听蛙声摇荡出一片清凉。
有院门,但那门可关可不关,夜来的关锁门户,也不过是为了防止野狗野猫的来访,听着鸡笼里一阵鸡的急迫的叫唤,那必是贪嘴的黄鼠狼来偷鸡,披衣起床一阵吆喝,只听瓦上一阵响,黄鼠狼早不见了踪影,笼里的鸡见主人的到来,仍是咯咯地吵闹着,仿佛是在七嘴八舌地向主人讲着刚才的历险记。
有客来访,谈论的也是田里的收成,家畜的生长。打开栏门,把那藏在草堆里的猪赶起来,那猪的屁股长得圆肥,还似故意哼几声向客人摇着尾。得到客人羡慕的赞赏,主人脸上顿时会增添无限的荣光,一边关着栏门,一边说这猪就是尚服人,不仅肯长,且不拱拦,吃了就睡。杀鸡设酒作食,吃着自家生产的东西,喝着春天放的一樽醇酒,透过窗子,指点着桑麻农事。
田园里也可按自己的心意种植。可以种一些豌豆,春天开满了花,春风一吹,豌豆苗低下头去,田里就像落了一地的蝴蝶在迎风飞舞;也可种一块土豆,秋收的时候,扛一把锄头来到田里,弯下腰去一掏,土里面的一窝窝洁白的土豆像埋了一地的元宝。
田园围着一圈栅栏,那并不是为了防人去摘长在菜园边的杏子,去偷那一条条水灵灵的黄瓜。栅栏上不是爬满了一墙的文眉豆,就是吊着一条条长长的丝瓜,一只小猫蹲在树荫下,望着那一只老鼠似的小丝瓜在风中秋千般摆去摆来。不知何时,谁家的鸡穿过栅栏,啄了刚出的菜苗,还有那放牛的小子自己在山坡上打瞌睡,牛跑到田里吃了一块油菜。于是便有妇人拍着巴掌站在田里大吵。这个时候,必有应声的,隔了几块菜园和几道栅栏,对骂声像两只鸟飞去飞来。吵也吵了,骂也骂了,但是最终那理亏的一方会在杏子成熟时,端一瓢刚下树的杏子到邻居家去,或者提一瓶新放的菜油到人家去,表达自己的歉意。谁家有了什么不幸的事儿,大家都合家去,倾力帮忙,仿佛从没有发生过吵骂的事儿。
房子建在一起的,大家可以隔着一道院墙说话,女人说着家务事儿,埋怨自家的孩子四五岁了还尿湿了被子,天天还得把被套抱出来晒,男人则说着田里的事儿,今年的谷种该什么时候进育秧室,今年的粮价该是什么景况。睡在床上,也可透过窗子听见邻居的洗铲锅的声音,以及不很清楚的絮絮叨叨的说话声,知道时候不早,该起床了。房子不在一起而是单家独户的,那房子必是建在山湾里。一个山湾,几亩水田,一丛竹林半掩着一幢白色的粉墙。听见几声狗吠,如果主人是刚出嫁来的新媳妇,从屋旁竹林道上迎出来,手里还端着一个摘青豆的瓢,见了是生人,脸必是红得跟她身上的嫁衣一样。一道山湾就是一道风景,一道风景就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人们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去布置房前屋后,安排春夏秋冬的四季生活。
行走在纵横的阡陌上,就像漫游在古老的画卷里。可是谁能分清,那田野里抒写的,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还是“归去来,田园将芜胡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