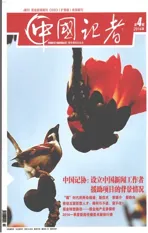忘却自我 抓住感动
——2014年新春走军营手记
2014-12-13□文/吴敏
□ 文/吴 敏
(作者是解放军报社记者)
编 辑 陈国权 24687113@sina.com
忘却自我,用心灵触摸他们的幸福与烦恼;抓住感动,不放过任何一个难忘的瞬间。2014年新春走军营活动结束了,但我的心依然不能平静。
在成为军报记者之前,我是武警总医院的新闻干事,曾多次随中国国际救援队走出国门担任战地记者,也多次在新闻现场报道神五发射、奥运安保、新疆维稳等重大事件,但这些经历并不代表我真懂新的军营新的兵。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新春走军营活动。出发前,我内心忐忑不安,基层年年走,如何写出新意?然而,当我吃住在连队,融入官兵中,很快发现:火热的军营,永远是新闻的富矿;年轻的官兵,永远是军事记者的良师益友。
难在沉入基层,贵在解决问题
农历小年,夜宿贺兰山下某哨所。凌晨1:30,我跟随指导员王家伟查哨查铺。寒风呼啸,王家伟拉着我一步一挪,生怕我被狂风吹进山谷。据说,被大风卷入山谷的兵,不止一人。推门走进哨楼,热气迎面而来。看到我把冻僵的手放到空调热风下取暖,王家伟说:“过去,哨楼里最低温度是零下20℃,穿着皮大衣还是冻得睡不着。”
回到中队部,离天亮还早。我翻开薄薄几页蹲连住班手记,不由一乐。这些简短直白的文字生动地描述出哨楼曾经的状况:“风大,沙多,训练受场地限制太多。”“我身高1.88米,床长1.8米。不睡战士的床,怎能知道蜷着腿睡一宿的别扭?”“电力不足,空调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大到执勤训练,小至吃喝拉撒睡,官兵们的需求无不体现在蹲连手记里,也已一一落实在实际工作中。王家伟打开电脑,用一张张图片对比哨楼的“前世今生”:“瞧,这是不久前建成的室内训练馆,那是四季种养的阳光温室、不锈钢玻璃的晒衣场。还有,大通铺换成了高低床……”
我眼前一亮,践行群众路线,难在沉入基层,贵在解决问题。东方渐白,《不让问题跟着官兵过年》的稿子跃然“屏”上。
沉甸甸的责任
1月24日,我走进大漠深处守卫西气东输管道的一座警营。
大漠漫漫,黄河弯弯。迎着湍急的河流,冲锋舟逆流而上,金色的阳光洒在对岸。略显单薄的少尉警官白帆站在渡口,敬着标准的军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移动的小舟。看到我们跳下冲锋舟,他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你是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记者。”短短一句话,让我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同时也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一路的辛劳瞬间烟消云散。
清冷的渡口六七个兵。一只小狗绕在脚边,不停地摇头摆尾。白帆告诉我:“小白一年多没有见过生人,很兴奋呢。”白帆的话很简短,但字字敲打我心。官兵坚守在这里,需要经受的最大考验是寂寞。寂寞如同黄沙一样漫无边际,寂寞的官兵最需要什么?最关心什么?最渴求什么呢?
“大漠里最缺少什么?”“甜美的爱情。”“大漠里盛产什么?”“纯真的爱情。”七八个人腿挨着腿围坐在一起,聊起大漠里的爱情故事。
四级警士长樊峰的妻子段学丽谈到第一次来队探亲,瘦小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晚上10点,轮到他站哨,我想陪陪他。”段学丽有点羞涩地说:“他在河那边,我在河这边。他在哨楼上,我远远望着他。”段学丽不知道,自己徘徊在河岸的身影,成为楼上众多士官眼里最美的风景。
四中队有15名士官,樊峰是唯一结婚的人。我原以为,其他士官一定都会羡慕樊峰。没想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29岁的士官刘帅说,想想段学丽忍受的孤单,就会把对婚姻的向往深深埋在心底,“当兵要尽职守责,娶妻要爱她疼她。如果没有条件在一起,我宁可等到退伍再谈恋爱。”这些朴素的白描语言,让我感受到他们纯真的情感。
指导员王金强一直忙到熄灯,才坐下来跟我聊起他远在荆门的妻子。“谁说军人不懂浪漫?每逢情人节、结婚纪念日,我都会想办法给她送花。”“那她为你做的最浪漫的事情是啥?”“离婚。”“离婚?”“结婚不久,亚慧忽然患上重病,久治不愈。她哭着说,离婚吧,你找个健康的女孩结婚。当兵苦,再娶个有病的妻子,苦上加苦。我不想拖累你。”王金强说到这里,转身抬手抹了把脸,平静了几秒钟说:“我抱紧她哄她说,我很笨,找不到别的女孩嫁给我。爱你,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谈着,记着,看着我的泪水一滴又一滴滚落在采访本上,王金强哽咽着说:“平时管着一群兵,不论工作、家庭遇到多少困难,都不敢流泪,大家叫我‘坚强哥’‘淡定哥’。可是,你不像记者,像姐姐。”采访结束,已过午夜,仰望苍穹,星斗灿若水晶,一颗颗都是他们纯净的心灵。我含着泪水,写出了《爱的坚守》一稿。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背过战士的枪,才有资格坐进指挥所
地震、抛锚、高烧,一个又一个突发情况接连而至,不断敲打着我紧张疲惫的神经。从银川到固原,一天走一个城市,一天访一座军营,每日奔波数百公里,睡眠不足四个小时,时间还是不够用。我上车睡觉,下车采访,边吃饭边提问,边等人边写稿。深入基层就像扎根大地,我卯足劲汲取新鲜养分。离开宁夏时,天天陪同我采访的新闻干事雷铁飞说:“你不像个女人,像个冲锋的战士。”我哑然失笑,告诉他:“新春走军营,就是记者上战场。在战场上,只分指挥人员和战斗人员,没有男人和女人。”
战士要有战士的样子,记者要有记者的样子。在甘肃平凉某部,我听说当晚有场随机拉动的演练,立即请求到现场采访。“平凉的冬夜冷呢,坐在指挥室里看视频直播吧。”团领导提议。我一边感谢他的善意,一边坚持要到现场。我知道,战士应该坚守自己的战位,记者必须站在新闻发生的现场。
19:30,紧急集合的哨声吹响。我掐着表,站在指挥员身后观战。西北风打着旋儿,飞沙刮得脸生疼。冷,真冷。我嘴唇打着颤,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冷风呛回去。整建制连队执行处突任务,应该携带多少枪支?多少警棍盾牌?多少给养物资?我大脑里储存的军事知识不足以拉直一个个问号。为了不露怯,我走进队列中,背起战士的枪,打开他们的背囊。那一晚的采访,我记下的最准确的素材就是携行装具的重量和种类。
第二天,我又巧遇一场小规模战备演练。两场不同规模的演练有何异同?如何跳出热闹的场景写出战备工作的新意?我思来想去,坐立不安。在工化营防爆连采访的间隙,我再次背起战士的携行装具。好沉!手一松,背囊砸在脚背上,也砸开脑中那扇紧闭的门。
为战而备,难在真备,贵在常备。写战备,写战车出动的过程容易,写出将士们的精气神难。无形的精神需要借助有形的载体展现。对!这精气神就在操场上的喊杀声里,在路边随时待命的战车里,在全师上下数千人整齐划一的迷彩服里。将士枕戈待旦日,百姓万家团圆时。只要将士们始终保持这夜不卸甲、衣不解带的状态,不论战争何时打响、在哪里打响,百姓都可安枕无忧。
下午,我采访部队长何良奎时,放弃了精心准备的提纲,直接谈起自己的感受。这位对女记者抱有怀疑态度的师长笑了,说:“作为一名指挥官,最难的事莫过于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寻找到作战的最佳战机。”我接过话茬,说:“作为一名记者,最难的事无疑是从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挖掘出报道的最新角度。”他抚掌大笑,说:“你拥有进入作战核心区采访的资格了。”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原定30分钟的采访时间一延再延。随后,他邀请我一同走进作战指挥中心,观摩分布在三个省数千公里防线上的全员全装拉练。演练结束,暮色四合,《征衣不解除旧岁》的文字在键盘上欢快地跳跃而出。
新闻采写需要技巧,但更需要真情投入。20天里,我从六盘山下走到三峡大坝、青岛海关。一路上,我进过炊事班调馅包饺子,拉着新兵的手擦去想家的泪,揽过军嫂的肩亲过军娃的笑脸,端起相机捕捉节日执勤的卫士身影,牵起巡逻犬穿过寒夜的浓雾,坐进指挥所见证战备拉练时的紧张氛围。每一个哨位都有难以用文字描摹的情怀,每一座军营都有无法用相机捕捉的瞬间,每一位官兵都有令我感动的故事。我不停地走,不停地睁大眼睛去寻找,不停地张开双臂去拥抱,用最虔诚的心去记录身边的感动。那些来自一线、接了地气的新闻故事,先后变成一篇篇报道。
新春走军营虽然只有短短半个月,但对于我这个军事记者岗位上的新兵来说,收获的绝不仅仅是15篇报道。新战士赵逸轩给我发过一条短信:“新春走军营,军报记者从报纸上走到我们身边。赞!”而我,由此记住了军报记者的光荣与使命、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