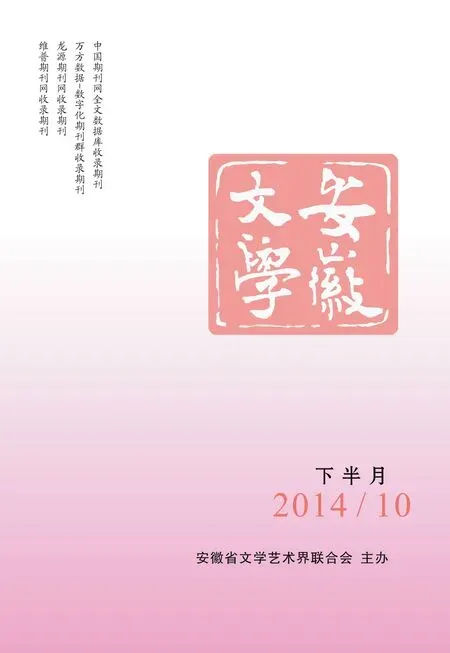论《巨型收音机》中的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与异化
2014-12-12梁意意白陈英
梁意意 白陈英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巨型收音机》(An Enormous Radio)问世于 1953年,被马尔科姆·考利认为是约翰·契弗短篇小说中具有无可企及的风格、且标志着其小说艺术真正成熟的作品。[1]192约翰·契弗(1912-1982)为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通常以纽约郊区为创作背景,精耕细作,集中描写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展示他们的孤独心理,揭露他们精神的空虚。《巨型收音机》也不例外,其故事发生在纽约萨顿场附近一幢公寓楼内。安宁幸福的女主人公艾琳·韦斯科特无意间从一台魔力无穷的收音机里收听到了邻居们的隐私,认识到邻居们生活的肮脏恐怖,并为自己的幸福而焦虑,最终发现自己的生活并不比邻居们体面多少。评家们已从该小说的创作技巧、圣经原型、道德主题、消费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解读。本文拟聚焦于主人公的中产阶级身份,指出艾琳出于中产阶级身份认同之需,拒绝承认自己生活中不体面不光彩之处,一味逃避现实。在这一身份认同过程中,她人格分裂、自我异化,最终迷失自我。下文将详述其身份认同与异化。
一
认同,英文表达为identity,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2]它含识别与归类之义,一是“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一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3]68由此,认同可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对人自身意义的反思。社会认同是对人所在社区之共同价值、文化和信念的态度,是对人的社会意义的反思。总之,认同是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是人获得生活意义的来源,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对认同的研究也即对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的研究。[4]
《巨型收音机》的主人公吉姆和艾琳·韦斯科特夫妇是中产阶级典型代表。契弗笔下的中产阶级往往居住在郊区,拥有汽车洋房,丈夫出外工作,妻子则忙于应酬交际。他们以宴请社交为乐,经常出国度假,甚至旅居他乡,生活富足而悠闲。吉姆和艾琳也力争融入这样的阶层。他们选择定居于纽约萨顿场附近中产阶级聚居区,与社会地位相当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医生、律师之类的白领人士为邻。他们的收入、事业正好相当于一般大学校友通讯录上统计出来的平均数。他们结婚九年,育有两个孩子,每年平均上剧院十点三次。他们还积极参加鸡尾酒会等各种社交活动,力求与朋友、同学、邻居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当吉姆因艾琳花销不当而朝艾琳大声嚷叫时,艾琳的第一反应是把收音机关掉,生怕被邻居们通过有窃听功能的收音机收听了去,家丑外扬以致被排挤出本阶层。这种有意识的自我归类无疑体现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期望。正如米德所述,主体只有融入社会团体并与该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个人的认同。[5]认同就是个人与他人、群体在情感、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他们正是通过与邻居等本群体其他成员的同化来确定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
艾琳除了主动将自我归类以融入中产阶级群体外,还积极认同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维持并强化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她费尽心思挑选衣物,亲手布置起居室的装饰和色调,购买收音机等在当时还算奢侈的物品;她还期望有朝一日能搬到上层中产阶级聚居区——韦斯切斯特去。她深知消费对于身份的重要性。一方面,中产阶级身份认同决定了她的消费方式。她竭力选择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消费方式,以划清同其他地位较低阶层的界限,确保自身的身份等级。哪怕家庭收入已大不如从前,她仍然处处向邻居们看齐,绝不甘居人后。另一方面消费方式也可以强化其身份认同感。Goldsmith等认为,消费的重要动机是通过商品可获取地位和社会声望。一个消费者越想获得社会地位,他(她)将越表现出一定的消费行为。[6]可以说,消费社会中,任何商品化消费,都是消费者文化心理实现和文化身份识别的代码;日常生活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是一场为寻求区隔而进行的符号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消费者可以确立其地位与认同感。[7]因此,尽管支付能力欠佳,艾琳仍在皮大衣、收音机和沙发套等奢侈品中寻找着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
认同是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然而,巨型收音机的出场打破了艾琳的和谐。这台其貌不扬的收音机对声音有着不寻常的灵敏度,它将左邻右舍的隐私展露无遗:他们有的夫妻不和,争吵不断;有的体貌端庄,却行妓女之实,甚至不惜和勤杂工通奸;有的病入膏肓,却没钱医治;有的贪婪自私,捡到别人财产占为己有;有的整夜宴饮作乐,狂欢至极;有的透支无度工作不保而忧虑丛丛……这些丑陋肮脏的行为另艾琳感到震惊和不安。她希望从吉姆那里证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比邻居们高尚。然而不堪生活重负的吉姆脱口道出他们经济拮据、难以为继的实情,并撕破艾琳伪善的面纱,使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原来,她一直生活在自己想当然的幸福梦幻中,其实她和邻居们一样为钱发愁,她的衣服账单尚未付清,她的貂皮大衣是由鼠皮染成的,她独占母亲遗产,在妹妹需要钱时拒绝出手援助,她打掉胎儿却毫无愧意……艾琳理想中的正派、诚实、幸福的自我与现实中贪婪、伪善、困窘的自我互相冲突,她丧失了自我支配下的确定一致的行为模式。当她对“自我”进行反思的时候,不能把关于自己的各种观念整合到一个自我概念中形成统一的自我观念。她便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分裂状态。
小说所处的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时期。然而,经济繁荣和丰裕生活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自由幸福。相反,垮掉派的兴起、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蔓延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社会不安全感增强,人的地位、作用、价值、命运等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在物质天堂中人人自危,陷入对金钱的欲望与恐惧、对未来的迷茫与焦虑中,没有满足感,也没有安全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了生活的危机。但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也无力改变。吉姆说他对未来毫无把握,事实上没有人对未来有什么把握。无以名状的焦虑笼罩着他们。他们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也不能肯定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因此,他们只能靠幻想来掩盖。艾琳那染得像貂皮的大衣,吉姆那故作天真的举止,无不昭示着他们内心的迷惘。这种粉饰太平、随波逐流、苟且偷生的方式正是其异化本质的外在体现。
“异化”指人与社会、自然、他人乃至自我之间的疏离与对立。异化的人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他被自己行动的结果或创造物所主宰,以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8]95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物质化、欲望化,如艾琳在母亲遗产的诱惑下,置亲情于不顾,对妹妹麻木不仁。她与吉姆关系淡漠、貌合神离。她对吉姆工作进展不顺、收入减少竟然毫不知情,可见并不真正关心吉姆。而吉姆也借口工作艰辛,回来连家常话也懒得讲。他对艾琳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颇有微词,对其沉迷于收听他人隐私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优越感甚为反感,于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艾琳曾经的丑恶行径。爱情、亲情的缺失,使人成了悲剧性的孤独存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再和谐。侯维瑞指出,“在高度物化的世界里人的孤独感与被遗弃感,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冷漠与隔绝”即是异化。[9]19自我分裂与异化的艾琳不得不回到冰冷的现实世界,她又是屈辱又是难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完全丧失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巨变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运行机制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0]15这一巨变产生于消费主义语境,来源于人们在本质上无法得到实现的永无止境的欲望。艾琳等中产阶级出于身份认同之需,耽于物欲、道德堕落、自我分裂、走向异化,最终难免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小说结尾,艾琳渴望收音机能和她说几句温柔话,可收音机已经恢复了正常,正用平稳的语调播送火灾和火车事故,这是否预示着如艾琳般迷失在物质世界里的现代人之前途堪忧?这是作为中产阶级身份寻求者艾琳所面临的困窘,也是金钱至上的当代美国社会必然存在的问题。在如今物质繁荣与精神空虚之落差强大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归属与身份定位,确实是值得现代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1]马尔科姆·考利.翰·契弗[J].徐齐平,译.世界文学,1990(6):192-209.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孙频捷.身份认同研究浅析[J].前沿,2010(2):68-70.
[4]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Goldsmith,R.,Flynn,L.and Eastman,J.Status consumptionand fashion behavior:An exploratory study[J].Association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roceedings,Hilton Head,SC,1996(15):309-316.
[7]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9]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文出版社,1983.
[10]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