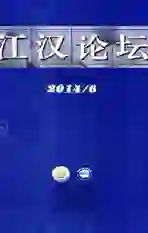女神式人神恋原型积淀的人性美及文化价值探析
2014-12-05万桂红胡立新
万桂红 胡立新
摘要:中国古代的人神恋故事以女神式居多,从作者的身份和作品的文化立场以及来自民间传说等要素看,女神式人神恋故事绝大多数是持民间文化立场及价值选择的。女神式人神恋作品对美丽女性的赞美、爱恋,女性对自由平等式的男欢女爱之唯美爱情的追求,女性主动追求性爱情爱的婚恋生活,他们超越官方文化的制度律令和世俗功利婚恋的美好自由情怀等,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先人的人性之美,具有现代社会之人性美的审美性、现代性、超越性品格。
关键词:女神式人神恋;人性美;审美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1 14-05
人神恋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许多美丽动人乃至凄婉哀绝的故事至今仍然活跃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赓续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对远古神话、传统文化、民间文学中的人神恋故事的持续性眷恋,除了满足民族大众的文化“返祖”情结、文人“白日梦”补偿心理等集体无意识心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文化发展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原型符号(人神恋就是其中之一),内蕴着该民族人们的人性建构历程,从而形成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文化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将这个民族大众的人性真实地记录下来。不管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价值导向如何规约与扭曲,都无法阻止民族大众人性正常健康地发展,并在现世个体有限的生命时间阈限中,演绎生命生存的悲情与礼赞,给未来者提供有关自己祖先美好生命的深层眷注。人神恋故事所承载着的被主流文化压抑与扭曲的真实美好人性,是吸引后人永恒性关注的内在文化价值。官方和精英文化中的人性导向和价值观体系建构属于显性文化,它们贯穿在教育、制度、法律、礼俗等制度文化中,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意识形态范型;而民间和大众文化中的人性导向和价值观体系建构则属于隐眭文化,它们贯穿在民间的文化、文学、艺术、民俗与生活中,被官方的精英的文化遮蔽和压抑,但却在人性发展和价值观体系孕育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与官方文化遵循的权力原则构成互补,体现出人性发展和价值观体系孕育中的现实性和理想性并重的特质。透过人神恋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都是以民间文化身份与立场,将我们先人人性的丰富性及其正面价值全面展现出来。
蔡堂根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神恋分为“男神式”和“女神式”,“男神式”是男性神灵与女人的婚恋,“女神式”是女性神灵与男人的婚恋。笔者认为这种分类与称谓可以成立,所以应用这对概念,并且“神”也包括神、仙、妖、魔、鬼、怪、精、魂等一切超现实的人化幻形。但笔者的“人神恋”概念只包括神灵与人类之间的恋爱、结合、共同生活的故事,不包括感生神话(如《诗经·玄鸟》、《诗经·生民》等)、人牲献祭(如《史记·滑稽列传》中的“河伯娶妇”、《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中的“郡主妻河”等)等缺少恋爱与婚姻的故事。蔡堂根认为,中国古代的人神恋故事先秦时期以男神式为主,秦汉以后逐渐演变为以女神式为主,到《聊斋志异》则主要是女神式,足以说明中国的人神恋是由男神式向女神式转变,并且逐步由女神式占主导地位。②笔者认为,蔡堂根所谓人神恋实际包括了不应该包括的感生神话、人牲献祭之类的非恋非婚的故事。如果按照笔者的人神恋所指称的对象来看,则不存在男神式向女神式转变,而是一开始就是以女神式为主体的。如《楚辞》中的《九歌》《山鬼》、《少司命》等抒写的人神之间的爱恋之情,宋玉《高唐赋》中高唐神女向楚王“自荐枕席”的性爱行为等,这些才是中国古代真正的人神恋故事的缘起。综观中国古代的人神恋故事,“女神式”主要是对应民间和大众文化。人神恋故事主要来自文学领域,包含在中国文学的辞赋、古代叙事小说、民间故事、戏曲及大量笔记体散文中。它们或来自民间神话传说,由文人收集整理,保留了民间意识,如干宝的《搜神记》、戴孚的《广异记》等;或由文人创作,其作者主要是被官方和精英文化遗弃在民间的文人,具有民间文化立场的,如冯梦龙的《情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或是隐逸了的文人,也是立足民间文化本色的,如陶渊明、袁枚等;即使是身为官人的作者,也具有民间的或者大众的文化立场,如干宝、沈既济、牛僧孺、洪迈、纪昀等。人神恋作品除少数是站在官方和精英文化立场上,借人神恋故事警戒人们遵守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维护封建礼教等秩序外,绝大多数是持民间的和大众的文化立场和价值选择的。这些作者和讲述者,在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遮蔽和压抑的世界里,本着真实的人性需要,编织出超验的人神恋故事,蕴藏他们认定的正面价值诉求,描绘出著述者作为人的色彩斑斓的精神世界。所以,笔者将女神式人神恋定位为民间和大众文化层面。透过女神式人神恋故事,我们可以发现被官方的主流文化遮蔽和压抑了的华夏民族大众的美好人性和价值观体系,这就是我们要探寻的文化价值。
先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是笔者否定的对象,而是作为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互补的对象。从价值选择方面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精英还是大众的文化,都存在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交汇的现象。笔者以女神式人神恋故事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它们被主流文化(含官方文化与精英文化)遮蔽和压抑的正面文化价值,立足点则是人性。从人性出发,我们会发现女神式人神恋的许多文化价值都被主流文化遮蔽了,它们以民间场域为实现场所,是构建正常健康人性和正面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发展的普适性正面价值——“真善美”这一肯定性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依靠不同文化类型的互补来完成的。儒家肯定人性中的“善”,把仁义道德之“善”作为最高价值,规约人性之“恶”,孔子所谓“里仁为美”实则是用“善”取代了“美”,因而实际上是取消了“美”。以老庄为代表的早期道家文化则肯定人性之“真”,把素朴自然之“真”作为最高价值,规约人性之“假”,老子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等,是用“真”取代了“美”,从而也取消了“美”。那么,人性之美是什么?从人性之美延伸出来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们从中国主流文化中几乎找不出一家之言。既然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分,那么用真和善取代美就显然是缺憾,是不完善的。儒道可以“互补”,但也只是“真”和“善”的价值互补,它们都缺乏“美”这一元价值追求。所以说,作为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儒道文化,把人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美”这一元价值给压抑或遮蔽了。但是,我们可以从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领域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之美的价值诉求。笔者从女神式人神恋的文化原型符号中似乎寻找到许多讴歌人性之美的带有正面价值的文化信号。
其一,女神式人神恋作品对美丽女性的赞美与肯定,是对人性爱美天性的价值认同。体现出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审美性品格。
欣赏肯定女性美是人类的共识,是对女性价值的一种肯定和尊重,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一般说来,女神式人神恋都是美丽的女性神异与人类社会男性之间的婚恋故事,女神式人神恋对美丽的女性神异都进行了大胆的赞美和描写。然而,对女性美的大胆赞美是儒家和道家等正统文化所规避的。我们看到的是,儒家虽然也承认人有美丑之别,如四大美男和四大美女之说都属儒家正统文化所包容的,但在价值取向上则强调美人是祸水。中国自商周开始就是一个重礼教妇德的社会,女人的品德比美貌更重要。普通男人娶妻室要重德不重色,但帝王却除外,可以美女如云,公侯次之,这就是儒家礼教的伪善和不平等。道家是以“五色令人目盲”式清心寡欲的规劝来引导人们放弃对美色的追求。只有在民间文化中,美女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是被讴歌与赞美的对象。
人的美丽是天生的,但人类发现并重视自身的美却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人是万物的精华,是大自然中最美的,女性美更是美中“精品”。主要从民间采集而来的《诗经》中最早大胆描绘女性的美,及至屈原,其《九歌》中的《湘夫人》、《山鬼》、《少司命》等人神恋作品,塑造出温柔多情的神女形象,更是历经千载而魅力永存。宋玉是第一位全方位描写女性美的作家,其《高唐赋》和《神女赋》突出而详尽地描绘了女性的外貌、形体和情态之美。唐代的志怪和传奇有大量笔墨描绘女性美,到明清之际,女性神异不仅美丽动人,热情主动,而且多才多艺,能文能诗,谈资高雅,可亲可爱。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关于花妖狐魅之美的描述广为人知。“这些女鬼都洋溢着青春少女的美,个个都是美的精品”。
如果说对女性神异的赞美还不足以深刻体现出人们对美丽女性的赞赏与肯定,那么,作品中的男性对象即使知道了对方是神灵鬼怪。也无惧无悔,深爱不绝,就足见作者或男性爱美之心的真诚与执着。如郭瑛的《玄中记》之《姑获鸟》、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之《白水素女》等都是如此。唐《任氏传》中,郑六知任氏为狐后,秘不泄人,“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再见任氏“郑子连呼前迫”,发誓不以异物见憎。《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们大都如此。书生们虽然知道狐女们的身份,但仍依恋不舍。这是“爱美”还是“好色”呢?这就要看评判者站在何种文化价值立场,如果从主流文化立场批判,自然是“诲淫”,如果从美的价值选择上看,则是最为率真自然的审美心理了。女人作为人的另一半,其美好的一面理应获得尊重和赞美,人性之美如果离开了女性这一元。无疑是残缺的。然而,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却极力压抑、遮蔽女性之美,只有在民间文化场域,特别是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才能看到这些讴歌女性美的大胆而率真的美妙文辞,唤起世间民众对女性美的肯定、赞美和追求。
其二,女神式人神恋作品对男欢女爱的肯定,特别是对女性性欲、情欲、爱欲的肯定,是对人性美的价值认同,体现出传统民间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品格。
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对人性中的性欲、情欲、爱欲是予以肯定的。但在具体的文明礼仪和文化价值选择中则是压抑性欲、情欲、爱欲的,孔子倡导“乐而不淫”,孟子主张“男女授受不亲”,荀子提倡“以道制欲”。人的性欲、情欲、爱欲产生了,就要“发乎情”而“止乎礼”。越到后代愈严酷,班昭《女诫》倡导“夫为妻纲”已渐升级,至宋代理学家则“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因此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女性的性欲、情欲、爱欲的压制、扭曲和否定的态度。但在民间文化中,则有许多的自由和解放,女神式人神恋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
在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女性神异更多是作为引诱凡间男子欢会的主动者而出现,甚至她们现身的唯一目的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女神一般都主动地向男人发出求欢、求爱、求合的信号,她们不仅美丽动人,而且热情主动,完全抛开了现世婚姻的礼俗桎梏,表现出现实生活中被礼教约束规范的女性完全不可能表现出来的行为。女性那天真无邪的自由人性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性欲、情欲、爱欲的自由宣泄成为她们来到人间的根本目的。在她们的带动下,男性对性、情、爱等的怯弱、害怕、恐惧等礼教束缚的态度也得到改变。在现世生活中,由于礼教束缚,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只是性欲和生育的工具。按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分析,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遵循的是父子轴文化。“性的中心意义是传宗接代,人的正常的性向往受到严重的压抑,女性自不必提,即使男性看似远多于女性的性自由实际上也受到延续子嗣之类问题的严重困扰……”在男权文化的性爱中,男人身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性爱活动中缺乏人性本真的爱欲、情欲的释放与享受。但在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在美丽女性神异的热情感召下,许多男性都为之动情,爱得缠绵悱恻。即使知道她们是神灵鬼怪也乐于相守不离,用情专一真挚。于是。我们在远离主流文化的民间文化场域,看到我们的先人在男女平等、互爱互尊的氛围中,男欢女爱的自然人欲作为美好人性得到民间文化充分的价值认同。
不仅如此,女神式人神恋中的神女可视为备受封建礼教束缚、压制而主动追求爱情的人间女子的化身。她们的“自荐枕席”,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女性正常欲望的外化。虽然学界大多学者认为人神恋故事主要是反映男子对女性的一种性期待,是男权文化下男性的“白日梦”,是落魄的下层文人的心理补偿,但是,在女性受到压抑、女性作为男权社会附属物的古代中国,延绵不绝的神女“自荐枕席”的故事不自觉地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肯定了女性在婚恋生活的主动性方面具有与男子同等的人格与地位;这是极其可贵的积极因素,是超越时代的人性观与情爱观。因此,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的男欢女爱是平等互动式的现代两性之爱,这种人性美已经具备了现代性品格。
其三,女神式人神恋作品对现实婚姻制度和功利性婚恋的超越。是一见钟情式唯美之爱,是对人性美的价值认同,体现出传统民间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品格。
人性之美的又一重要表现是能够从现实世界的实用价值体系中超越出来,去追求一些能够让人超脱的自由的理想化生活。戈蒂耶所谓“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强调美是对实用性的超越,王尔德所谓“唯一美的事物是跟我们无关的事物。”是强调审美的无利害性、超功利性。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也要求人们超越,但这主要是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而且带着深厚的社会功利色彩,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大道大德,忠君报国、遵守礼教等。儒家文化是肯定功利的,个体功利和社会功利、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这都是维系社会关系和秩序而必然选择的实用价值体系。一切社会性的事物都可以用功利价值权衡,婚嫁之事自不例外。所以才有所谓“门当户对”、“门阀婚姻”,社会地位、家庭财产成为权衡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主要标尺。从奴隶社会到整个封建社会,不允许贵族与平民、良民与贱民通婚的律令从未间断。这种制度形成的风气到20世纪初还盛行于世。在众多功利因素的影响下,主流文化领域中的婚恋基本都是极端功利的,没有自由平等互爱的可能性。但在民间文化场域,特别是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主人公的相遇、相爱、结合、生活的婚恋整个过程完全超越了所有功利因素的制约,体现出人性对世俗功利的超越之美。
在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主人公的相识与结合是不受世俗法规律令制约的,既不受身份地位的等级支配,也不受嫁妆聘礼的财产限制,双方偶然相遇便自由相恋结合。这种对功利世界的超越,正是人性中审美境界的生成。早期的女神式人神恋作品还存在地位、等级、财产等方面的制约,如《高唐赋》中是高唐神女向帝王献身,但偶然相见就相恋结合,也能见出其无功利欲望,无世俗礼教约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人神恋作品,无论仙女下凡型、入山遇仙型、还是升仙型,人神结合的角色是女神和一般的男性平民或小吏,女神都表现出对感情的主动大胆、不计后果、热情主动,不再对凡人摆出君临臣仆的架子。虽然少数作品的现实色彩较浓厚,有门第观念,是对高门显族的影射,但仍表现出对自由超越的爱的追求,对门第观念的冲破。如刘义庆《幽明录·刘晨院肇》、陶渊明的《搜神后记·袁相根硕》等。唐传奇中的各种女神式作品,多是凡间男子、文人与仙女、地位尊贵的女神的相恋结合,男主人公对仙女也没有了六朝人的仰视与敬畏,甚至没有一点仙凡的距离,更没有门第、财产观念对他们爱情与自由欢会的阻隔。虽然有少量作品也蕴涵着寒士对高门的向往心态,但更多地表现出渴望冲破门阀婚姻的藩篱、追求婚姻的自由平等,突出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家长阻碍自由婚恋的不满和反抗,如《裴航》、《柳毅》等。这时期的作品展现了唐人对自由美满婚姻、性爱的向往追求,以及妇女在婚姻性爱方面的主动性和开放性,他们保持自己与神灵完全平等的、独立的人格,没有世俗之见。到明清时期作品中就完全消除了等级地位、财富条件的观念影响。男性多为贫寒、失落的读书人或村夫或流浪儿,女神不仅不嫌弃他们,还深爱着他们帮助他们,如《聊斋志异》中的《神女》、《翩翩》等。男女主人公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无身份地位等级之支配,更无门第财产功利之限制,体现出对世俗婚姻制度、功利观念的超越。
无论是在早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中,女神式人神恋模式几乎都突破了社会等级地位和财产婚资的制约,主人公完全逃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嫁法令等主流社会文化的规约,从实用的、功利的、世俗的世界超越出来,完成了男女婚恋的人性唯美之爱的升华,许多作品还演绎出一见钟情的唯美之爱。一见钟情是青年男女对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抗门第观念、世俗功利观念,追求自由爱情的美好途径。如《任氏传》及《聊斋志异》中的《婴宁》、《青风》、《红玉》等,都是真挚动人的一见钟情式唯美之爱。爱情惟有真情才显得可贵。因为真情所以刻骨铭心,因为真情愈显其美丽。这些作品中的女性神异与男性的爱情婚姻都是唯情的,一见如故,相互爱慕,相互信任,难舍难分。这类作品就是一见钟情的唯美之爱。然现实世界中的唯美之爱往往因为律令风俗、功利因素的干扰与阻挠而成为悲剧,只有在人神恋作品中,这种不计较任何世俗功利和物质条件的情爱才能自由实现。女神们择婿或以“男子貌美”、会种五色香草(《园客》),或以男子品德可嘉、至孝(《董永》),或因男子有才(《霍小玉传》),或因男子风流倜傥(《情史略类》中的《织女》《张女郎》《清溪小姑》)等。他们的两情相悦、自由地欢爱。这些男子都是无名无财的小人物,多为潦倒、落魄的书生,他们的结合既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是“门当户对”,更不是唯财是从。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又一次见证了流淌在民间文化血液中的中华民族民众在婚恋嫁娶中超越律令、功利而追求自由、唯美的人性之美。这样的唯情唯爱唯性唯美的情爱,是自由的,也是男女平等的,从而具有现代人性美的超越性品格。
综上所述,女神式人神恋作品对美丽女性的真诚赞美,男性对女性的执着爱恋,即使明知是神异女性也甘心爱恋相守:女性对自由平等式的男欢女爱之唯美爱情的追求,延绵不绝的神女“自荐枕席”的故事不自觉地凸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肯定了女性在婚恋生活的主动性方面具有与男子同等的人格与地位:他们超越官方文化的制度律令和世俗功利婚恋的美好自由情怀等,充分体现出华夏民族先人的人性之真善美合一的价值认同,这是人类普适性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中的建构,它弥补了华夏民族传统主流文化之片面与残缺,是一股流淌在民间文化场域的鲜活人性之美的图景,具有现代社会之人性美的审美性、现代性、超越性品格。
如果说女神式人神恋作品将人性中正面价值维度的“美”给予充分发扬的同时,却没有肯定人性之真与善,或者否定了真与善,那么,它们就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支畸形文化。事实是,在大量的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人性之真、善、美的三元普适性价值相互协和统一,它们不是分离的。绝大多数女性神异都是集美丽、善良、率真于一身,以真善美合一的面貌来到人间上演一曲曲关于男欢女爱的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之“真”强调的是真情、真性、真爱、真婚、真生活,有似道家之所谓“真”,即顺其自然之道。然作为女性神异的身份之真则属艺术真实,不具备客观真实性,这是艺术对生活的超越。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之“善”则大量违背儒家文化所建构的伦理价值体系中的“善”,这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儒家之所谓“善”的伦理价值尺度去作为,就无以产生自由解放、一见钟情、平等互爱、超越功利等等人性美的行为了。因此,这里的“善”就只能取人性之善良的基本含义了。在女神式人神恋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也有少数出于摄命夺魂等“恶”的目的而残害异性对方,这是出于惩戒情色而维护正统礼教的目的,它们自然成了主流文化的辅助。但绝大多数作品中的男女主角都是善良之人,他们多属出于男欢女爱之情的真实需要而相识相交与结合:也有部分作品是直接对“美女是祸水”的正统文化价值观的否定,美女不仅不给男性带来灾难,还能拯救男性,让男性走出灾难和困苦。可见,根植于民间文化场域的女神式人神恋文化原型所推崇的人性之真与善,是与美能够协调统一的。这就使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性的正常健康发展,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由真善美组成的完整价值观体系,是由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元文化共同完成的,它们的互补性正是它们各自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在当代新中国文化建设中,文化“返祖”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学时,既要从古代的官方和精英文化中区别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文化,也要从古代的民间和大众文化中区别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文化,特别要多回想那些民间文化中的具有积极性和正面价值的文化基元,用现代社会的人性美和正面价值观为导向,建构民主、自由、科学、健康的现代新中国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的女神式人神恋作品,成为演绎美好人性的一面镜子,照亮华夏民族人们追求真善美合一的普适性价值,值得后人心仪与敬仰。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