箪食瓢饮光明有日——读《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2014-12-05蔡思明
○ 蔡思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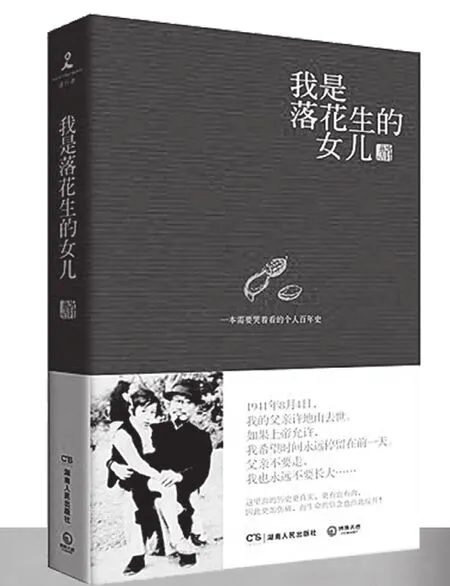


一直记得小学语文课文《落花生》中许地山先生(1893-1941年,笔名“落花生”)的父亲借花生而教育子女们的那句话:“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花生成为了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优秀人品的代名词。
多少年后,“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将花生低调、有用的品质坚持到底,在其如麻花一般扭曲的人生中始终坚持“花生精神”,做一个为社会有用的人。她的36万字的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一部通过个人人生的曲折反映时代复杂变迁的回忆录,尤其是其中的求学经历、“文革”期间的遭遇,国家干部变成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白丁老农,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段珍贵纪实,读来令人唏嘘不止。
上
许燕吉女士在1932年出生于北京。她的祖父许南英(1855-1917,号蕴白,台湾安平人)是台湾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曾投笔从戎,当过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外祖父周大烈,是一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父亲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著名作家、文学家;母亲周俟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成长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许燕吉有着幸福快乐的童年。在她两岁时,全家人搬去香港,住在香港大学附近一处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地方,父亲任教于香港大学,母亲全职在家,管理着一大家子的生活,家中还添置有一辆小汽车,生活富足而幸福。
在那个不太平的时代,本就没有长久的幸福而言,可对于许燕吉一家来说,幸福似乎走得太早一些。1941年8月,父亲许地山猝死在家中,享年47岁。8岁的许燕吉居然自始至终也没有掉一滴眼泪。母亲当时说她没有感情、无情无义,其实其父陪伴过她的桩桩件件事情,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记得父亲会在母亲惩罚她和哥哥的时候来及时“救驾”,会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会天上地下地给他们讲故事,会带着他们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那些快乐的瞬间,就算跨越了数十年光阴,也还是清晰地印在许燕吉的脑海中。她不是无情,只是未谙世事,当日根本不懂得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在8岁女孩幼小的心灵中,或许根本无法建立起对于“亲人离世”这一事实的认知感。“1941年8月4日,我的父亲许地山去世。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前一天。父亲不要走,我也永远不要长大……”,这是许燕吉留在该书腰封上的一句话。
4个月后,香港沦陷。母亲顶起了家里的一片天,带着兄妹俩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无忧无虑的童年说再见,许燕吉在随着母亲的奔走中,开始尝尽生活冷暖,懂得人情世故。在湖南的三年(1943-1946年),许家备受刘娘(她母亲周俟松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刘兰畦)的照顾,她的呵护备至以及谆谆教导让幼小的许燕吉难以忘怀。
可是这样一位贤良慧智,一生投入教育事业,曾在1955年代表中国去瑞士参加过“世界母亲大会”的女性,晚年却十分的凄惨。刘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山区农场改造,后不幸骨折,因医生不肯给她进行治疗而致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的她,在儿子、儿媳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慰和照顾。最后离世时,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可是在许燕吉心中,刘娘是给过她母亲般关爱的亲人,她唯有将自己满腔的悔恨和遗憾付诸笔端。“无处凭吊,无处寄托哀思,只有常常地悔恨,我活着一天,刘娘就在我心中。这也是我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
1950年,许燕吉被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录取。四年大学生活,有着满含同学情的欢声笑语,学习之余,抬水、掏粪、抢吃饭,养兔、打狗、抓刺猬,在课堂学习和农耕学习中,她依然不改直爽、冲动、好强的性格。1954年,从北农大毕业后,许燕吉被分配到石家庄奶牛场。同年,她和同班同学吴富融结婚。原以为新生活在召唤她,正准备满心欢喜迎接时,“不料马失前蹄,栽得鼻青脸肿,意乱情迷”。
1955年,因暗查“胡风反革命”事件,许燕吉被隔离审查半年;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自此开始了她六年的囚犯生涯。对于不了解当时社会环境的读者来说,反复阅读她入狱前后的经历,只是莫名的心酸。可随着她的笔触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明明书写的是“满纸荒唐泪”,却时时能够读到她的坚强,她的宽容,她从不曾失去的乐观,她对生活的希望,正是这些元素,感动着我把这本自传,一页页地不断读下去。
1958年9月28日,许燕吉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听到判决书之后,经历了短暂而强烈的思想冲击,她很快便发挥高级“阿Q精神”,给自己打气鼓劲儿:“我诚实,不损人利己,不两面三刀,是我的做人之本,走到这一步是别无选择,没做不道德的事,问心无愧、年轻体健是我的好条件,一定下狠心争取提前释放。现在刑期已过了两个月,还有70个月,光明有日,箪食瓢饮,不改其乐。”
艰苦的狱中生涯,摧残了很多正常人的心智。而那时的许燕吉,所遭受的不只是入狱之难,还有丧子之痛和丈夫离弃之苦。这样的遭遇,很多人都会抱怨世事不公,可她却抱着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心态,秉承着父亲“做一个有用人”的精神,在艰难困苦中努力过着每一天,等着新生活的到来。许燕吉很鄙视监狱中那些靠污蔑别人而立功的犯人,“我想,一个人专注于找别人的缺点,怎能纯洁自己的灵魂?”于是,在很多人忙于寻找别人的缺点时,她却在监狱中发挥着自己的光与热,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书中写道:
过去每天劳动12小时还多,人跟着机器运转,得思想集中手疾眼快,顾不上想家想不愉快的事。现在空闲了,往事、亲情都浮上心头,加上饥苦难挨,许多人低头垂泪,或凝神发呆。监舍的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我请示了管教,把她们都赶到院子里,编了几节活动量不大的体操,再教大家念几段报上登的或自己编的顺口溜……每天再搞个“联欢会”,做点儿游戏,会唱会说得再来上一段儿,消磨时间,驱散沉闷。我不能把“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思想灌输给她们,但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乐观上引。有好几个乐观的年轻人支持我的工作,共度困难的日子。
尽管许燕吉从未放弃自己,从未放弃生活,但在那个因遭遇“文字狱”而成“阶下囚”的时代,她的心中确实也曾迷茫过。她向往着新生活,可对于自由她却心生胆怯。1962-1963年,由于她在监狱的杰出表现,连续两年被评“记大功”,获得了减刑的机会。可是管教同她商量将第二次机会让给一位刑期十年的犯人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除了那位犯人的为人是她所推崇的,她还有着自己内心的纠结。她说:“就像俄罗斯的《囚徒之歌》里写的:‘我已习惯于铁窗,我已习惯于囚粮。’哈姆雷特说过:‘整个社会就是座大监狱。’电影《流浪者之歌》里唱的:‘我没有约会,也没人等我前往。’自由对我的吸引力比初入狱时淡漠得多了。”
失去自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当自由来临时仍不知何去何从。1964年7月,许燕吉刑满释放,可她努力改造了六年,仍然是一个社会不容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社会定位让她觉得无比可悲,禁不住失声痛哭。她被政府安置到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虽然还没有冲破牢笼,但好在不再是囚犯之身。
下
1968年底,因政府遣散就业人员的政策,许燕吉离开了河北监狱,这才迎来了新的生活,但这新生活的历程也是百转千回。之后,她被分配到石家庄新乐县的坚固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孤身一人,暂居在村里的农户家,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好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养活自己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那个按工分进行分配的年代,一个人所分配的物资有限,就算她拼命劳动,也只能勉强挣得口粮,难以有结余。长此以往,必然是行不通的。何况在慢慢地适应村里的生活后,她也发现了:
原来村里家家都养着猪,猪无论刮风下雨都有工分,而且还不低,起码比我这七分多,猪的工分还分粮。另外,小孩子不论大人也是一个人,也分一个人的粮。孩子多的人家,生活更富裕些。这一年我实分得的粮,麦子104斤,玉米带芯子是140斤,豌豆26斤,荞麦10斤,谷子8斤,花生10斤,鲜山芋400斤。这些都是未经晒干的原粮,去壳去水分,只有300斤。我的估计还是对的,这不是我能自食其力的地方。我还有几百元的积蓄,贴完后怎么办?我妈妈已是古稀风烛之年,就算是倚靠她,也不是长远之计,人活在世上,得站在自己的脚后跟上,这是我从小就明白的道理。
经历世事沧桑,对婚姻对爱情早已失去希望的许燕吉,这时才觉,为了生活,她得找个安身之处。在这里她始终是个外乡人,“我若得了病还没家回。我不能死在这个地方,我得谋个生路”。有了这样的决心之后,她前往陕西找她的哥哥周苓仲。在和哥哥分析了现在的处境之后,哥哥劝她离开新乐县,来到关中富庶之地成家落户。这似乎是当前摆脱困境的唯一方式,就算有万般无奈,许燕吉也只好接受。在一家人的把关下,经过相亲谈判,1971年,许燕吉和比她大10岁的陕西武功县杨陵公社魏振德登记结婚。名家才女自此下嫁白丁老农,开始过上了农妇和老头子的生活。
前尘如流水,夭折的孩子,离婚的前夫,六年阶下囚的生活,狱中被掐断的爱情……一切苦厄都随着新生活的开始而放逐。魏老头的宽厚、体贴,让许燕吉慢慢地接受他,适应了新家庭的平凡日子。1979年,终于迎来了“春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告其无罪,撤销了对于许燕吉的“反革命”的判刑。长达20年的冤枉,使得快年过半百的许燕吉百感交集。1981年,为照顾年迈的母亲,许燕吉调到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牧医所,她的丈夫和孩子也随迁到了南京。
罗曼•罗兰说过:“生命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整个生活贯穿着痛苦。”许燕吉在临终前出版的自传中,曾形容自己的人生如同一只“麻花”,不断地被拧来拧去。虽然对于苦难,很多人会选择遗忘。可毕竟有的痛苦是人们承受得起的,有些却是生命所难以直面的。纵观许燕吉坎坷悲苦的一生,她所承受的,似乎已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该书之所以一问世被广为关注,或许是因为作者系许地山之女的身份。但展读该书,读者会暂时淡忘其“名家之女”的身份。在作品中,古稀之年的许燕吉直面苦厄,以平实的口吻,以及时常带着自嘲式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但那种发自心底的悲愤,那种对于时政的控诉,却是力透纸背,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的,原来“物不得其平则鸣”,这就是情感和文字的力量!因此,读者在汲取作者坚韧不拔、乐观未来的人生勇气的同时,更难以忘怀的,应该还是作者在晚年坦然面对过去事、看淡人间不平事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