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真相——佛法的知、行与隐藏
2014-12-05王大智
○ 王大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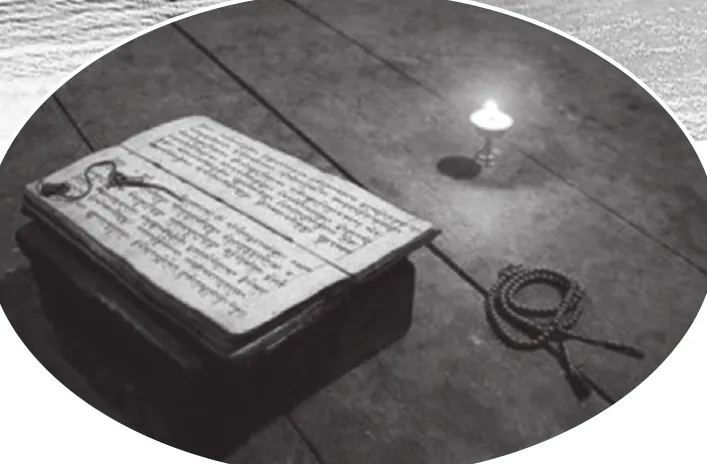
孙中山说过:“思想、信仰、力量”。他认为,思想、 信仰、力量之间,有一种逻辑上的关系——思想的深刻化,便产生信仰;信仰的具体化,便产生力量。这种关系显示出:思想存在的目的,便是为了获致力量。类似见解,西方的笛卡尔也说过,“我思故我在。”(思想,决定他的存在与否)只是孙中山是革命家;对思想的要求,除了知,还要行。笛卡尔是知识人,能够到达知的地步,也就满足。
我主张思想家要知行合一,不过我对于知、行的先后次序有看法。先秦诸子都能够知行合一: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齐聚一堂,绝不会是看来雷同的四个教授样子。他们都有不同的背景、经验,并且,经由不同的背景、经验,总结出不同的思想路数。他们都可以知行合一(可见,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并不是发明了一种思想,只是发明了一种术语)并且还是“先行后知”。(以一生行为,归纳出一种想法;而非根据一种想法,模铸出一生行为。)“先行后知”才是思想的创造者,“先知后行”已经是思想的追随者了。同为知行合一者,其间却有很大的差别。
佛教是不是一种思想呢?佛教当然也是一种思想。只是,它不是政治、经济思想,而是人生思想——指导人类如何过活的思想。因此,佛教的存在目的,也是通过“思想、信仰、力量”过程——转化佛学思想为佛法力量。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两千年。国人对佛教的了解,可以说趋于两极化。一者以为佛教的诸佛菩萨,和其宗教神祗相同;可以与信徒发生感应,可以息祸降福。一者以为佛教与其它宗教很不相同;不同处,在于信徒可以通过修行,而晋身为佛菩萨。这两种看法的依据,自然是由佛教的两大宗派——净土宗与禅宗而来。净土宗讲究上天堂下地狱,的确和西方宗教很类似。禅宗呢,讲究立地成佛;讲究因为开悟而与佛等同。
不过,两千年来,儒家孔子的理性态度(“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等)始终与天堂地狱相抗颉。因此,尽管净土宗也相当受欢迎,却无法真正接管中国思想界,使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定义下的宗教国家。相对净土宗而言,禅宗地位显然不同。禅宗轻松宗风,接近中国原有的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 。因为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推崇,禅宗在中国的佛教宗派中,独树一帜。甚至到了宋朝,思想界融合儒、释、道而汇集为理学的时候,那个释的部分,就是禅宗。禅宗是完全被中国接受、吸收的一种佛教宗派。
禅宗或者与道家接近,但是绝对有异于道家的地方;那便是它的修行观念。禅宗的修行以开悟为核心。开悟就是开智慧;开智慧,修行者便与诸佛菩萨等同了。然而,智慧是什么呢?(“智”字之于佛家,很像“气”字之于道家;用处多广,难以定义。大凡“旧瓶装过太多新酒”的文字,都有这种“言语道断”的情况。)或者,我们先用逻辑中的“删去法”,说说智慧不是什么吧。首先,智慧不是聪明。因为佛教不重视聪明,聪明是世间法中的斗争机巧。其次,智慧不是智商。因为智商显有高低,但是众生平等皆有佛性(有佛性自然有佛智) 。那么,智慧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佛教说的智慧,是“选择力”(power of selection)。选择力和判断力(good judgment)似乎一样,却又很不一样。判断力是知,“选择力”是行。判断在先,选择在后。了然于胸和具体行动之间,有一道高大的门坎。
人类智力,受制于先天;青春期以后,便不容易有大改变。但是“选择力”,却会因为观念的改变而改变。会改变的事物,才和修行有关。如果一种事物,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改变,那么,怎么修也修不出结果来。在佛教中,智、愚相对——智慧的相反即是痴愚。愚也不是智力问题,而是缺乏“选择力”;不能做出适当的选择。(古人说“宋人多愚”,是指宋人固执不通——国王宋襄公是其代表人物。宋襄公不是智力不够,而是错误观念导致了错误选择:与楚国作战,在战场上高唱仁义,结果“伤股,三日而死”——被敌人伤了大腿,三天就死了。)
佛教说的智慧,就是“选择力”。任何人皈依佛教的时候,师傅都会念一个偈子,作为佛法传承。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偈子来源很多,不少早期翻译的佛经中,都曾出现。佛法说的善与恶,可以是道德上的对与错;也可以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而只是两种相对的选择——对的选择为善,错的选择为恶。(“自净”两个字,当然自我修持的意味很浓厚。)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句话,就是“不做各种错的选择,做各种对的选择”一个人如果总是做对的选择,当然离苦得乐;可以称为有智慧了。然而这句话理解容易,做到很困难。因为,理解是“知”、做到是“行”。理解,或者便可以判断,但是唯有做到了,才算是选择。这是我不断强调“选择力”,认为选择是一种“力”的原因。“力”和“行”之间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力”方能行,欲“行”则必得有“力”。
佛智,不是聪明、不是智商,也不是知识。佛智,是一种经由观念改变而获致的精神“力”。这个“力”,和孙中山说“思想、信仰、力量”的那个力并无二致。这个精神的“力”,当然就是勇气!除了勇气,还有什么是精神力呢?或者有人以为,精神力和意志力接近。意志力,不是勇于面对世界与自我的力么?那个力不是勇气,又是什么呢?
试看《佛种姓经》罢:佛陀的修行缘起,是因为“游四门,观四相”,看见了“生老病死”。佛陀见着“生老病死”,为什么就开始修行呢?一般说法,是他起了烦恼迷惑之心。烦恼迷惑,不是对于不能解决的事、无法理解的事产生的恐惧么?“多么可怕的人生啊!”不是悉达多太子的内心写照么?“多么可怕的人生啊!”不是所有接触佛教者(或者接触其他宗教者)的内心写照么?佛陀的菩提树下开悟,不是因为他不再恐惧四相,敢于面对这个婆娑世界了么?《大般涅盘经》讲到诸法真谛时,连说六句“不可说”。是什么事情那样的不可说呢?(这个“不可说”不是一句玩笑话。《大品般若经》《大方等大集经》等大乘根本经典,也都提到佛法的“不可说”。)
再试看《法宝坛经》罢:唐朝时候,六祖惠能见五祖弘忍。弘忍问“欲求何物?”惠能答“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几番对话之后,弘忍说“这獦獠根性大利”,把他支到伙房劈柴,掩人耳目。惠能不识字,这“根性大利”四个字,是指惠能的聪明、智商、知识,还是指惠能的勇气呢?五祖弘忍最后传衣钵,给了这个敢于选择做佛,将菩萨、罗汉、天堂、鬼神(甚至和尚)都视为“余物”的“獦獠”。弘忍赏识惠能什么资质呢?
宗教的目的都很相似,都是要经过“思想、信仰、力量”的过程,使信众获得勇气,以为生存的精神支柱。佛教说的那种因为修行、开悟而获致的力量,就是勇气。至于说,明明是勇气,为什么要叫它智慧呢?这种有话不直说的别有所指,是佛教的特殊思维方式。
佛教说的智慧,的确是别有所指。《金刚经》的论述方式,就大量运用了这种别有所指。这种思维法门,我在《<心经>义理的逻辑问题》文中曾经说过:“《金刚经》讲相,是为了破相,是为了让人了解相的虚幻。若是让一种虚幻的东西影响自己,多么划不来。因此,《金刚经》借着释迦摩尼和须菩提的对话,反复运用一个公式,阐述名相的虚幻(名是听见的虚幻,相是看见的虚幻)。那个公式为:“佛说…即非…是名…。”白话可以翻译为:我说的那个东西,并不是真的有那个东西,只是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虚幻的相,并不存在。那个什么,可以泛指智慧、功德、净土、大千世界、佛等等。)这个“佛说……即非……是名……”的公式,贯穿整部《金刚经》,它是释迦摩尼的智慧和婆心,是打开佛法的锁匙。
明白这个别有所指道理,佛智的真相,可以思过半了。《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专门讲智慧的经典)中,竟然出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没有智慧,得不到智慧)这样的话,也不足为奇了。这句话,是观音菩萨婆心,把“佛说…即非…是名”的公式讲白了,把佛曰“不可说”的事情,说出来了。事实上,它不但把智慧是“名”这件事讲白,也把智慧到底是什么?得到智慧的状态是什么?都讲白了。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后半,观音菩萨说,依法修行智慧,可以“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布,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这五句话的前后关联,就是中间那句“无有恐怖”——不恐惧。不恐惧,不是勇气么?佛教很柔和,不强调力量。但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的这句“无有恐怖”,却有万钧之力。它直指修行的结果,智慧的真谛,涅盘的状态。我们说佛菩萨在智慧的状态,我们说佛菩萨在没有烦恼迷惑的状态;我们不是也可以说,佛菩萨在“无有恐怖”的状态么?那么,他们不是充满勇气,不再恐惧,敢于面对任何境况,永远做出善的(对的)选择么?
宗教(包括佛教)的产生原因,都和人所共有的恐惧有关,都和如何令人免于恐惧有关。佛教在这种宗教的发展初衷上,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它认为可以免于恐惧的勇气,并不来自于未知的神祗,而来自于自我的修持。更特别的是,它不说修持者越来越有勇气,它说,修持者越来越有智慧。这种特别的地方,让佛法有神秘感;也让接触佛法,成为一种可以长期玩索的有趣思想活动。(如果烦恼、智慧即是恐惧和勇气,那么,所谓的苦与乐,又是什么呢?我这样直指的谈佛教,好不好呢?考虑良久,最后,还是把它写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