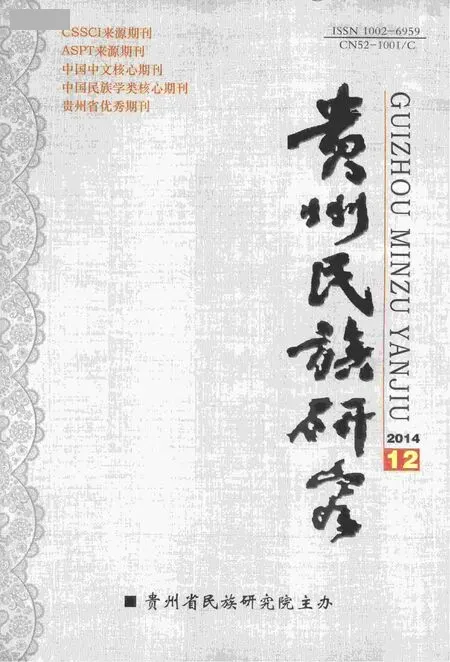传说在历史现场中的记忆与失忆——以桑植白族仗鼓舞起源传说为例
2014-12-04欧阳岚
欧阳岚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湖北广播电视大学 湖北·武汉430074)
一、引言
2011年桑植白族仗鼓舞被列入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仗鼓舞是由桑植酉水一带白族原创的民间祭祀性舞蹈,具有极强的地域性。仗鼓舞创于明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笔者2012-2014年到桑植白族聚居地进行田野调查,对仗鼓舞传承人进行深度访谈,并收集到关于仗鼓舞起源的民间传说及地方性文献资料,对其形态进行了历时性研究。
从古至今,传说与历史总是纠缠在一起,“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1]本文正是以历史记忆为切入点,走进历史现场,对收集到的桑植白族仗鼓舞起源传说进行梳理、比对,在古代方志、宗族族谱、地方性资料以及民间遗留的历史碎片中找到客观的证据,破解传说所隐喻的历史事件,厘清历史传说在传承过程中传播者对历史的误读,尽可能地还原仗鼓舞起源本来面目。如何从传说找到线索还原历史本真呢?势必要将传说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进行考量。在考量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对同一事件或同一内容的传说在各个不同时期在族群内部及外部的集体记忆里,由远端向近端推移的过程中,这种记忆在衰减,最终甚至完全失忆。
二、“三个土匠斩恶龙”神话传说文本所隐喻的历史事件
《三个土匠斩恶龙》传说:在民家人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恶龙危害生灵。三个土匠把它斩杀后,饱食龙肉。龙在肚里作怪,胀痛难忍。三人为消胀,以龙皮蒙长鼓,通宵舞蹈,因此起名“跳胀鼓”。显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因为“传说大都跟神话和民间故事一样,是一种虚构性的作品,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1]难道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首先,从关键词入手进行解析。“在民家人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恶龙危害生灵”,“恶龙”很明显是个隐喻,隐喻地方恶势力。“恶龙”隐喻是谁呢?明永乐年间《安福所志》记载:“洪武三年,茅岗土酋长覃垕,因‘征上得功’,恃倚山夷,僭肆百为,尚自艳曰:‘扶竹杖,卧龙床,半朝天子在茅岗’。”不言而喻,自诩为“半朝天子”的覃垕就是传说中的那条恶龙。何以覃垕为“恶龙”?因为他居土司自傲危害乡里。1364年,上峒土司向仕金与茅岗土司覃垕结亲,向居住在酉水地界的谷、钟两姓宗族借钱财作嫁妆,这嫁妆名为借实为强占。茅岗土司覃垕的巧取豪夺,“遂致仇怨”。谷、钟两姓因讨不回钱财,在“槟榔孔地方两起争杀”。时值元明交替,时局混乱,“衙门无存”。谷、钟两姓族人无处申诉。[2]当社会剧烈动荡,国家失去了保护人民的能力,这时只能依靠地方精英组织力量进行自保。落桑的“爨僰军”后裔,以谷、钟、王三姓为首组织了一支战斗力强的乡军,公举谷均万第四代孙谷永和为统领,与恶势力抗争。
明朝初定,予“斩恶龙”带来了契机。1370年,覃垕多次与三叔商量谋反之事,“叔不附从”。“覃杀叔起事”。1371年初,明太祖朱元璋命荣阳侯杨璟讨伐。1372年春,再命江夏侯周德兴率军再剿,兵至慈利,覃垕遁入山寨。至闰四月,信国公汤和克蜀归州,调动添平、麻寮两个军民宣抚司助剿,谷永和被周德兴荐为前部先锋,领兵捣敌。覃退至七延寨固守,久攻不克,后设计攻破,假儿覃德章脱逃。擒覃垕,解至南京,剥皮楦草。[3]“恶龙”被斩杀了,但叛乱余孽还“在肚里作怪,胀痛难忍”。1373年,“下酉州18峒蛮夷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州作乱,旁掠州县”。朱元璋命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率兵平48峒。谷永和复从征邓愈帐下,跟随左右5年。1378年,邓愈率部打完征剿百元峪一仗,回酉水所演武场操练兵马,后班师回朝。谷永和因参与平叛,功勋卓著,由总旗授锦衣卫驾前校尉。
我们对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进行梳理。从“恶龙”横行乡里始,到“恶龙”起势作乱,到“恶龙”剥皮楦草,到“龙在肚里作怪”——峒蛮再次叛乱,到“为消胀,通宵舞蹈”——谷永和从征邓愈5年平48峒,班师回朝前校场军演。一系列具体行动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终在“校场军演”的启示下,完成了创造“跳仗鼓”思考。邓愈为什么班师回朝要进行一次军演?古代,部队凯旋,军演目的有二:一是威慑敌方,二是鼓舞士气,即“班师振旅”。
而“班师振旅”正是仗鼓舞产生的动因。桑植自古以来就是阻挡西南蛮夷侵犯中原的战略要地,自土司覃垕叛乱事件,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个弹丸之地更是倍加警惕,屡屡重兵征剿,采取种种措施和策略瓦解地方武装。在控制与反控制中,中央统治与民间武装展开了博弈。当帝国强大时,民间武装便转换形式,将武装演练转为宗教仪式,既达到自卫目的又使之合法化。跳仗鼓就是民间武装转换的产物。并且“三个土匠”文本从开始就被地方精英们“固化”了,使之在流传过程中保持原貌,传承属于“爨僰军”族群的历史记忆。
三、历史现场中宗族记忆增强族群记忆减弱的传说文本
《钟氏祖先跳仗鼓》传说:钟千一(桑植白族的始迁祖)同潘氏到大屋峪,生四孩,第四个小孩叫仕慧,住狮子岩附近。他在那里种地,野兽常来糟蹋庄稼。他去狩猎时,发现三只山羊吃麦子。仕慧追山羊,山羊逃入崖洞,仕慧追入洞中,发现三只石山羊,同时仕慧妻便生下男孩汉渊,十二年后又生下汉圣,两兄弟长大了,进崖洞抢神羊,玉帝将神羊断与汉圣,并命其为兄长。汉圣大喜,当即命制长鼓,欢庆,取名叫跳仗鼓。汉渊拒跳,所以此后仗鼓舞仅为汉圣后裔掌握。由于汉圣家规很严,没学会仗鼓舞的人不得参加游神,也不得到游神活动中请客的人家去吃饭。会跳者则尽可畅饮。每隔十二年,由汉圣后裔一支支派轮流举行一次游神活动,祈求丰收,祛除瘟病,除疾清灾。
当战乱停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繁衍过快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洪武中,太宗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一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以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民间仿效皇室,纂修族谱形成高潮。[4]这一时期,桑植白族宗族凝聚力提高到空前的地位,客观地削弱了族群凝聚力,导致族群历史记忆减弱,宗族历史记忆增强。
《钟氏祖先跳仗鼓》说明“跳仗鼓”在宗族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汉圣家庭家规很严,没学会仗鼓舞的人不得参加游神,也不得到游神活动中请客的人家去吃饭。会跳者则尽可畅饮”。这也是本主游神跳仗鼓民俗事象的乡约民规。乡约民规也就是民间的法律,人人都要遵守。没有严明的族规约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不能传承至今的。《钟氏祖先跳仗鼓》“蕴藏着丰富的、真实的民众生活和历史资料,蕴藏着无价的民众心理学”,[5]虽然文本“仗鼓舞起源”方面是失忆的,但对仗鼓舞发展与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叙述有着不可替代历史记忆。
四、现代传说文本在历史现场中的失忆
目前引用最为广泛的是《白族兄弟斗官兵》传说,这个所谓“考证”文本一经出现,人们就把它当成“仗鼓舞起源”真实史料来看待,由于思维惯性驱使此现象仍在继续。传说内容是这样的:据考证,白族始祖初来桑落业时,人单势薄,常受当地官府、“地头蛇”的欺侮与勒索。某年岁末,有三个白族兄弟,在屋场上用木杵捣糍粑。突然,闯进几个拿着水火棍自称是官差的人,翻箱倒柜,无理取闹,因而发生口角殴斗,兄弟们来不及拿刀剑,操起手中捣糍粑的木杵直打向官差,三人上下腾挪、左右开弓,如秋风扫落叶般,打得官差头破血流,抱头鼠窜。为了纪念胜利,白族兄弟乐得狂舞。此后,每逢年前打糍粑,都要手舞足蹈一番,代代相传。[3]
与历史文献与口传史料进行比对,这个现代文本出现了三个失忆点。
第一个失忆点。将传说“白族始祖初来桑落业时,人单势薄,常受官府、‘地头蛇’的欺侮与勒索”与地方文献“‘寸白军’(即爨僰军)的校尉谷均万、王鹏凯、钟千一等,从江西来到桑植马合口、芙蓉桥一带,乐其风土,解甲归田,结庐山野,开田辟土,繁衍生息”[3]进行比对,同是“初来桑”时间段,结论截然相反。一个是“乐其风土”,一个是“常受官府、‘地头蛇’的欺侮与勒索”。如果“欺侮”与“勒索”成为常态了的话,富有社会经验与战争经验的“爨僰军”军人们为何要选择这样一个社会生境险恶的地方来落业呢?况且,他们十多年来一直都在频繁地迁徙、堪舆,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宜族群落业的地方。如果不合适,他们可以继续漂泊,再寻找一个理想的地方。实际上,初落桑时,地广人稀,可以插草为标,进行拓殖,一个汉夷交织的边境地区,各方面限制较少。由于荒蛮,官府和地方势力很少涉及或干预这里。选择这样的地方繁衍生息,体现了桑植白族始迁祖的智慧。由此可见,《白族兄弟斗官兵》的所谓“考证”是违背社会规律和族群历史记忆的。
第二个失忆点。“人单势薄”的三兄弟与“官差”单打独斗与历史事件“覃垕占取嫁妆不还”引起“槟榔孔地方两起争杀”进行比对。“爨僰军”后裔谷、钟两姓与土司王覃垕的两起争杀,以武装力量对抗武装力量,在势均力敌情况下是理性行为,“斩龙”事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和对“爨僰军”族群内部的影响力都是深远的、强大的;而单打独斗的形成影响力对整个族群来说是有限的,对当地社会来说更是微不足道。历史事件从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有一个时间累积过程,是对某一事物认识进行累积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某一事物的过程。这足以证明《白族兄弟斗官兵》文本在族群重大历史事件记忆这一点上是失忆的,因为经过祖辈军事素养熏陶的“爨僰军”后裔,不会因为区区小事,毫无理性地去与代表地方政府的“官差”不计后果的单打独斗。
第三个失忆点。“初落桑”历史背景下忧患意识的失忆。“爨僰军”军人及其后裔从大理到桑植都是蛮夷地区,土著强悍嗜血。元朝人李京在《白人风俗》中描述道,“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则白刃相专剸。不知事鬼神,若枭獍然。惟白人事佛甚谨,故杀心差少”。[6]桑植地方也是天高皇帝远,土官土司专权自拥,置身于如此的社会生境中,让人怎能不忧患?唯一解除忧患的办法就是族群自强不息,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其目的不在于侵略而在于自卫。“斩龙”胜利后,感受到的是“龙在肚里作怪,胀痛难忍”,也就是说虽然剪除了恶人,但恶势力依然还在,必须想应对措施,哪有心情狂欢狂舞。“为消胀”制定措施“以龙皮蒙长鼓,通宵舞蹈”,教育族群教育后代,警惕如覃垕那样的恶人及恶势力,为此要不知倦怠,积极操练,加强自卫力量。而现代文本却说成是为了一点糍粑,打走几个官差是值得纪念的胜利。并且“为了纪念胜利,白族兄弟乐得狂舞”,有那么值得狂舞吗?“官差”走了还会来,而且他们的背后有官府撑腰,卷土重来后的报复是变本加厉的。
为什么“仗鼓舞起源”传说会在现代文本中失忆?究其原因,就是现代文本的制造者忽视了历史记忆的规律,忽略了历史现场的重要性。然而,任何将个人的意愿、个人的世界观、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强加于集体记忆之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较之于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7]
五、结语
“劳动人民战胜官府公差”的现代文本,几乎统领了当前关于“仗鼓舞起源”的传说,成为人们引用最多的文本,是因为惯性的驱使,还是因为那句“考证仗鼓舞的来源”,然而这个没有考证的考证,长期以来竟然没有听到一个质疑的声音。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衰减间或出现失忆,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确切的标志已经不复存在,大量谜团不断产生……一代复一代,记忆并没有更加准确,而是恰恰相反”。[7]对某一事物历史记忆的衰减和失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怎样正确解读历史遗留下来的传说?怎样正确看待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只有走进历史现场,从某一事物的源头看起,也就是说从这个事物的历史端点入手,并且要重新审视这一地域的“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机制,才能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1]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3,(2):175-188.
[2]安福所志.转引自:澧水溇水流域白族钟氏宗谱[M].2009:881-882.
[3]谷忠诚.桑植白族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
[4]谷利民.桑植白族博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29.
[5]钟敬文.钟敬文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1.
[6]田怀清.从考古资料看白族的源流[A].白族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11.
[7]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