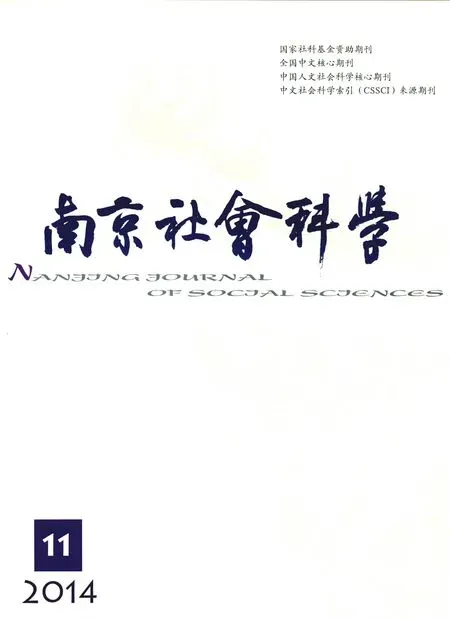微信成瘾:社交幻化与自我迷失*
2014-12-03蒋建国
蒋建国
微信成瘾:社交幻化与自我迷失*
蒋建国
微信体现了媒介化社交的诸多优势,随着微信的普及和社交功能的延伸,微信化生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值得高度关注。微信成瘾不仅具有网瘾的一般特征,其过度虚拟社交导致生活紊乱和精神空虚,陷入“越微信、越焦虑、越冷漠”的怪圈,也进一步地疏远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容易产生人格分裂、社交幻化和自我迷失。如何培育微信的社交理性,是合理运用微信的应有之义。
微信成瘾;社交;自我
从2011年以来,微信作为社交媒体迅速崛起,目前全国至少有6亿个微信用户,且数量在持续攀升,微信已超越微博成为最受欢迎的社交方式,作为微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圈子文化,微信所创造的“朋友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微博迷”们的社交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网民而言,如果有一天离开微信,简直是一种严重的心理恐慌。显然,以微信为代表的“微时代”,极大地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时空概念、文化氛围和心理方式,它所创造的新型社交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身体、情感、话语与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现出“微文化”的巨大影响。对于微信社交的自由、平等、随性和开放的优势,已经被不断地放大且形成了巨大的营销效应。但是,关于微信成瘾所导致的社交幻化和自我迷失问题,却鲜有专文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微信成瘾视为网瘾的一种表现方式,以微信社交功能作为研究的重心,探讨微信成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微信社交:交流并非意味沟通
按照字面的理解,微信是通过简短的文字进行交流的“信”,是私信、短信功能的扩张,它延伸了互联网的诸多互动与交往功能。随着web3.0时代的来临,网络本身已经成为“社交图谱”。①尤其是多媒体交流方式的发展,使微信交流充满了文字、图片、视频的丰富想象。而微信聊天对外部设立界限,使其圈子文化限定在“朋友”的范围之内,让参与者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但是,作为Web3.0时代的时髦交往方式,微信既是一种“圈子文化”,又是网络亚文化的重要源头。它虽然属于私人交流方式,却是网络世界中的一种“亚媒介”。其朋友圈可以随时携带各类信息进入“内群”中,微信圈所展开的交流和讨论,仍然与网络公共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微信的“写作”与手写时代的书信有着根本的区别。书信首先是由于地理空间的存在而产生的双方交流,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表达了手写文字区别于复制文化的情感效应。“写信”与“读信”是在特定的情感空间里进行的仪式化“场域”,手写的书信是书写者的叙述、思想与情感的交织,是对特定对象一种空间上的倾诉,并通过书信旅行时间上的差异期待对方的回应与交流,“我”和“他者”在书信交流中存在着情感互动与依恋。字里行间表现了对人物、事件和生活世界的勾连,具有文本的完整性、逻辑性和想像力。而对于“读信人”而言,读信犹如“读人”,远在千里可感知友人过去的思想和生活踪迹。因此,书信和眼泪一直是感情的一种凭证,而见字如见人、睹物思人仿佛也就具有了更充分的理由。②这种时空的回响和情感的互动是书信作为私人交往方式的魅力所在,也是体现手写文本的思想性、逻辑性和生命力所在。
但是,微信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书信的交流功能,却与书信的情感沟通功能有较大差异。首先,微信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圈子文化,缺乏对个人的专注和投入。对于那些建立微信圈的用户而言,尽管他们可以通过电话号码、QQ群、群聊号、公众号和社区寻找合适的交往对象。这看起来似乎有较大的交往选择性,但是,从实践层面上,一般人经常联系和交往的圈子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而大多数微信号加入的朋友远超过这一数量。由于一般手机用户存储的联系人达数百乃至数千人之多,似乎每个人都抽象成为一个手机号码。对于手机中许多“陌生的熟悉人”的微信邀请,按照许多微信用户的经验,从礼貌的角度考虑,一般不会轻易拒绝。因此,微信号所连结的朋友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朋友”,而是交往意义上的“熟悉人”,有些甚至是仅知其名而不知何时见过的“过客”。一位报社老总谈到不设微信号的原因时就很坦率地说,他手机上有近8000个手机号码,许多手机号是工作和业务上的“保持者”,如果建立微信圈,对于那些突然撞入的“发言者”,如果不回信不太礼貌,而回信又“无话可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微信朋友圈与现实的社交圈有着较大的差异。微信圈并非完全基于信任而建立的小众社交圈,圈中的“陌生面孔”也并非个别现象。微信圈将社交圈子进行符号编码和再度链接,并没有强调交往的个人属性。相比较而言,“微博是社交化的媒体,而微信是媒体化的社交。”③尽管微信与微博的公共交往有较大差异,但微信仍然是虚拟交往世界中的一个中介和连接点,其点对点、点对多的互动交流方式,与书信用信封限定单一的联系对象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这个层面上看,微信的多元交往方式虽然便捷,也具有“强联系”的社交功能,却难以体现对某个交往对象的专注和情感归属。
其次,微信交往是一种“有限度”和“碎片化”的交流,缺乏完整的文本意义。在网络所建构的“片断主义社会”中,微信具有网络文化“涣散”的一般特征。从表面上看,微信用户可以打破时空的局限,随时随地联系朋友圈的任何人。但是,根据大多数微信用户的经验,微信聊天存在着“选择性交往”的问题。对于数百乃至上千的“朋友”,如果平时缺乏联系,突然向对方发信,无论从意愿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缺乏“交往动力”。而既便是偶尔与多年未联系的朋友在线聊天,也会由于“话语贫乏”而难以持续。因此,对于许多微信用户而言,“聊天”并非是随意找人,而需要考虑对方的“回应度”。而进入微信聊天环节之后,互动就显得特别重要。然而,与书信互动由于时空差距而存在思考与记忆的环节不同,微信的即时化互动则是“随意”的交流。由于双方并没有为了聊天而准备充足的“主题思想”,微信聊天往往是“漫不经心”或者“三心二意”的。对于聊天者而言,文字的输入并非是完整的思想表达,而是某种即时性思绪的电子书写。双方在交流时很难集中精力讨论某一主题,往往会随意性地转移话题。当一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回应,另外一个问题又会凸显,这种杂乱的信息碎片让双方难以深入交流,更难以形成深度的情感体验。而由于片段性的输入和漂移,聊天的文字往往缺乏逻辑关联和系统思维。这种漫不经心的互动很难实现情感上的交融和交往上的“凝视”,加上双方的身心状态和网络情境的差异,许多话题并非出于真实情感的流露,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逃避”式的回应。“交流的无奈”是微信交流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随意性的文字更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杂烩,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对于“聊过即走”的用户而言,“聊天”仅仅就是“聊聊”而已,那些杂乱的聊天记录根本毋须保留和记忆,聊天内容很快成为瞬间即逝的信息符号,难以在聊天者的思想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主题的不断转移中,许多聊天者甚至是在“向微信说话”而已。
再次,微信朋友圈的“分享链接”制造了“共享文化”的虚假繁荣,并消解了微信的互动沟通价值。微信区别于一般网络社交工具的重要功能就是朋友圈的信息共享。微信用户利用朋友圈建立的各种链接,能及时了解圈子内外各种信息,可以说,每个“分享链接”就是一个超级文本。而每个文本则建构一个具体的“事件”,让阅读者能够获得新的信息消费通道。然而,由于每个微信用户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数据库,而圈子里的朋友们将“分享链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如果说有些朋友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聊天”的困境,而向自己的朋友圈发表信息则享有充分的权力与自由。这些漂移的链接拥有无法计算的即时性指令,信息可以在数亿用户之间通过各种链接进行复制和传播,任意“转发”是任何微信用户轻点手机界面即可完成的事情。而用户利用微信平台的自我展演,则实现了“微时代”人人都是主角的技术跨越。“我”与“他者”都可以随意到朋友圈任意发表言论,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即时性的文字、图片、视频成为书写网络人生的基本方式。如果说“我微信、故我在”是一种新媒体生活方式,那么,“我链接、故我在”则成为微信自我表达的重要动力。而每个链接所具备的评论功能,则为每条信息发布者提供了获得赞赏的机会。在信息“链接”组成的圈子共享文化中,“赞”与“不赞”尽管是阅读者的自由,但是被信息充塞却是无奈的选择。尽管用户也可以遮蔽某些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但是,却难以逃离朋友圈提供的信息杂烩。当我们进入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之后,情感沟通功能已极大退化,而不自主的浏览却让我们无法“全身而退”。
二、微信成瘾与社交幻化
据《指尖上的网民》在2014年的最新统计,中国网民中,20%的人每天查看100次手机;23%的人生活必需品没有手机会心慌;34%的人起床第一件事看微信。④所谓“早上不起床,起床就微信;微信到天黑,天黑又微信”。这一网络流行语,反映了当下微信热所导致的微信成瘾状况。微信成瘾是网瘾的一种类型,具有网瘾的一般特征。但是,由于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特殊属性,微信成瘾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交成瘾”,或者说陷于虚拟社交而不能自拔。与传统的SNS社交方式不一样,微信用户拥有真实的身份,对于每个参与者而言,这种身份符号在网络世界的真实存在,对微信用户的网络交往具有一定的规约性。但是,由于微信强调圈子交往的“小社群主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实社交的双向性互动模式,尤其是微信聊天群的广泛存在,极大地增强了集体社交的功能。因此,微信对“熟悉人社会”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户对圈子文化的归属感。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指出的“内群认同”,个体能够在内群认同中获得“自我利益”⑤。这种虚拟的群体交往也折射出现实生活中“集体文化”的缺失,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学习压力的加大,许多人为生计而奔波,社交圈子日益狭窄,生活方式也极为单调,很少与同事、朋友进行深度交流,对于许多深处焦虑和孤独的人而言,打开手机,虽然能找到无数个号码,却难找出几个合适的倾诉对象。这种现实社交的狭窄和无奈,让许多人以“屌丝”、“宅男宅女”自嘲。而微信则从技术上改变现实社交的时空问题,试图让用户随时随地抵达他的交往世界。但是,微信本质上仍然属于网络虚拟交往,并且带有“符号社交”的基本特征。当用户过度依赖这种虚拟化交往之后,就会陷于“他者世界”而茫然遨游。
首先,微信成瘾是对社交价值的一种消解。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必然需求,也是人性的本质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被社会接受、“被他人喜欢”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它们可以阻止孤独感的迫近。⑥朋友是体现自我价值并获得社会赞赏的基本对象。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是强调人的社会归属感。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而言,没有朋友就意味被孤立,很难获得无私帮助和精神安抚。因此,获得赞美和认可是正常人的社交动机。但是,微信将现实社交转移到网络空间,试图以“符号社交”代替“现实交往”,以此实现人的交往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社交的专注和情感价值。在现实社交中,双方需要用眼神和身体语言表达情感,需要身体与思想的高度统一,需要从内心表达真实的想法。但是,微信社交则体现身份符号与交往情境的矛盾,用户试图联系一个朋友,这个“他者”的交往状态却是不确定的,他也许在工作、也许在应酬,也许根本无心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网络表达就是一种没有边际的交流应对。而微信成瘾者如果经常寻找交流对象,遇到这种“无聊应对”的概率就更高。其结果是,“我”经常叩问“他者”,“他者”却在进行“无聊”式应对,双方无法进行深度互动,更难以达到情感和思想交流的目的。微信成瘾者打开了一个朋友圈子,却没有开打一个心灵世界。尽管他可以不断地点击不同的朋友符码,但是,交往心理和生活节奏的不同步,极大地影响到微信对话的质量和效果。尤其是对于圈子中存在的大量“陌生的朋友”,会对对方的频繁打扰而心存不安,应付式的交流也只好用“呵呵”体来表述。
其次,微信成瘾会导致“公共价值”的消解。微信强调朋友圈的信息共享,创造了一对多、多对多的信息分享方式,这显然有利于用户分享圈子文化的诸多红利。尤其是一些朋友发来的具有独特性、思想性的文章,会给用户诸多启迪和思考。但是,微信成瘾者则陷入了“信息消费主义”的泥潭,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朋友圈,力图不放过任何一条新的链接。然而,他们是“浏览”而并非“阅读”,他们并不在乎链接的文本价值,而是以“我看过”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漫无目的的消费倾向,导致了他们对朋友圈的“信号”极度敏感,一旦有提醒的标识他们立即投入到浏览的情境之中。事实上,朋友圈提供的分享,除了少部分体现朋友旅游、居家、工作的“生活现状”之外,大部分是转发的时政、育儿、养生、保健、娱乐、杂谈之类的信息,重复率很高,是一种典型的“复制文化”。尤其是所谓的修身养性的文章,初看几条尚有收获,但每天接触到大量所谓的“感悟”之后,其文本的思想性已经被稀释甚至消解。此类所谓的“心灵鸡汤”很难具有教化意义,与诸多其他杂乱的信息一样,仅仅是被浏览的对象而已。既便这样,微信成瘾者却对朋友圈的链接心向往之,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沉浸在飘渺的信息杂烩之中。他们没有预设观看的目的,“浏览”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一般的上网浏览新闻网页情形不同,由于这些链接经过朋友们的“推荐”,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圈子”所带来的信息,而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信息共享环节,似乎能够找到一种“社群主义”的存在感。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各类链接的内容,就不难发现许多信息不但重复,而且已广为传播,甚至许多朋友圈的链接文本具有较多的雷同,尤其是朋友圈的相互转发,使任何一条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地流传于无数个朋友圈。由此可见,朋友圈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复制性、随意性、混杂性,很难体现朋友圈“共享文化”的个性。
微信成瘾者每天不断浏览大量的“转发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虚假的消费需求。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读什么,不理解朋友链接的目的是什么,也很少有时间对各种链接进行“点赞”。过度信息分享往往让他们轻松离岸,却无法找到上岸的通道。他们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者,在朋友圈制造的信息杂烩中看到的是“无心之果”。频繁的浏览并不能带来心智的提升、精神的愉悦、身体的放松。相反,浏览越是频繁,他们就越感到焦虑。由于过渡地沉溺于一个小圈子信息,他们往往对朋友圈的文化共享和互补功能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他们而言,谁在转发,谁被转发的意义并不重要。因为复制和粘贴是通用的工具,到朋友圈里并不是看“朋友”,而是看热闹。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不断更新圈子里的各种分享信息,比思考信息的价值要重要得多。随着无数链接和垃圾信息的大量累积,朋友圈里的朋友意识逐步淡化,信息共享与互动的价值也逐步消解。
最后,微信成瘾会导致群体交往的失语。从理论上看,微信所提倡的圈子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圈子有一定的耦合,但是现实社交重在实际联系,需要双方的身体在场。比如聚会、谈心、互访等等,往往需要双方投入一定的时间和情感,更需要尊重对方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但是,微信创造的群体交往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实社交的规则,尤其是在“议程设置”上,微信用户的社交往往以“我”为主,“他者”是不确定的多数,“户主”所建构的朋友圈,在交流中处于主动的地位。对于圈子中的朋友,用户拥有选择的自由。而微信成瘾者片面追求这种自由,试图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群文化中始终把握话语主导权。在一对一的交往中,也许朋友圈里的个体会根据情境进行选择性对话。但是,微信成瘾者往往会对积极回应者较为关注,并“及时跟进”,不断制造“话题”要求对方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交往暴力”,“他者”的被动应对即便是心不在焉,也会因此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朋友之间性情不合,便会以各种理由避免见面。但是在微信交往中,“我”把握了交往主动权。对于那些微信上瘾者而言,话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要“冒泡”,要有人不断来“接茬”。这就造成了微信交往的自我中心主义。然而,这种中心主义并非以“舆论领袖”为标识。由于朋友圈的人缺乏话题关顾,微信成瘾者如何说、说了什么,在一对一的交往中,往往不被圈子里的人所发现,所以,朋友圈的人被视为随意挑选的“陪聊对象”,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互动。虽然朋友圈有无数个体,但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他就是“主人”,无数被加入到圈子里的朋友,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显然脱离了社群文化的本质,更谈不上民主协商的精神。
微信聊天群与QQ群有类同之处,但看起来似乎更为紧密,以同学、师门、小团体、同乡等为社群符号的各种聊天群,使群体参与变得便捷和多元。由于这些聊天群设立了40人的上限,以此限制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但是,它仍然属于小型的公共文化圈,并为核心成员的多元互动和信息共享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然而,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由于许多微信成瘾者对“群聊”极度偏爱,往往利用这一公共平台来体现“与众不同”,经常在群里发表各种意见,提供各种链接,引发各种议题,意图主导小群体的话语权。对于许多群聊者而言,加入一个新的群体,并非要屈从某个意见领袖,而是寻求新的集体交往方式和群体归属感。但微信成瘾者则将群聊作为个人展演的舞台,根本不顾忌群聊成员的感受,任意闯入群中发表各种奇谈怪论,并要求群里的“亲”们及时回应,体现了明显的话语霸权和自我中心主义。这就让许多参与者被“边缘化”,无法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有些成员由此而中断此类群聊,不再在此类群里出现。而微信成瘾者似乎不顾忌“他者”的观感,仍然不断地挑逗其他人回应,并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的群现身,试图自己强化在群体中的地位。然而,随着此类话语暴力的不断蔓延,许多微信群已逐步丧失了群体交往的功能,参与者不断减少,微时代的“微民主”在现实运作中,受到了微信成瘾者话语霸权的挑战,并导致“小社群主义”的话语危机。
三、微信上瘾与自我迷失
微信是以单个用户为中心而建立的社交圈,其目的是利用网络平台实现社交方式的便捷化和多元化,但其社交关系建立在现实朋友圈之上,没有平时的社会交往,网络社交也就没有人脉基础。然而,过度微信不仅使现实交往的频率和动机大为降低,也会使用户陷于盲目的虚拟社交怪圈而无法节制,这种虚拟的社交上瘾行为,不仅没有有效地提高社交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反而使社交主体的作用和价值不断地被淡化,形成了“我微信,我茫然”的社交焦虑与恐慌。
首先,微信成瘾者的过度展演导致“表演崩溃”。在现实社交中,向朋友倾诉是一种交往行为的正常方式。而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他始终将自己当成朋友圈的主角,以自我展演作为主体性存在方式,将微信圈视为自我展示的舞台。因此,他们频繁地进行聊天与转发,并不是为了与圈中朋友沟通与交流,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评论和赞美,以此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甚至将微信作为全景式的个人博物馆和剧院,“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⑦,他们努力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不放过任何可能“公示”的机会,一回朋友聚餐的美食,一条小狗的新装,一次旅行的小插曲,一幅自家孩子的小画作,等等日常的见闻和琐事,都成为微信圈里的通用性展示话题,尤其是裸露身体已经成为日常的表演。有时,为了获得“点赞”,这些主动的话题发起者还自设竞猜题目,比如,你知道照片上的景观是哪里?照片上的人是谁?此类故弄玄虚的设问,就是要等着朋友圈的赞美。有些80后“小清新”们还将自己旅行、睡觉、吃饭的图片发在微信圈里,急迫地进行设问。对于这些过度自恋的展演者而言,我“微”故我真,我“秀”故我在。一切深度皆丧失,唯有造成神经短路、思想锈蚀的“秀逗”,才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感觉。⑧然而,此类表演秀却很少得到回应和赞美,偶尔被点赞的朋友也许是睡在下铺的室友。狂发各种图片已成为上瘾者的流行偏好,而在微信中暴露隐私也屡见不鲜,尤其是身体展演的方式层出不穷,“无节操”式的暴露甚至成为获得关注度的手段。表演者将身体作为展演的道具,关于身体的审美已演变为肉体的暴露。尽管如此,微信成瘾者却难以获得“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之类网络红人的知名度,甚至连几个“点赞”都难以呈现。此类自我暴露式的展演,根本没有区分前台和后台的关系,将自我进行透明化的放大,却在费尽心机之后,茫然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陷入越展演、越寂寞、越焦虑的困境。
其次,微信成瘾者沉醉于圈子消费而导致自我“缺位”。由于微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添加朋友,偶尔的扫一扫、摇一摇便会新增不少新朋友。这固然有利于增加“偶然性相遇”的机缘,也可以扩大微信圈的信息来源和交流途径。但是,微信毕竟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化媒体,它一方面可以使用户融入“微时代”的信息潮流之中,但另一方面却需要用户进入网络联系的节点之中,成为虚拟世界的一个客体。因此,它是主我与客我、主体与客体、祛魅与魅惑的杂糅。理性的用户应该适度地运用微信进行社交与信息共享,一旦微信成瘾则导致自我迷失和消费迷乱。由于过度关注自我,微信成瘾者往往会不断观看“朋友”的表现,一个议题、一张图片、一段视频,虽然是日常生活的小插曲,但许多微信成瘾者却视为生活的仪式,迫不及待地发起议题,有时实在没有人回应,便只好自问自答。这种博名的心理,势必导致微信成瘾者不断追逐新的话题,如果自己缺乏表演的话题,便需要通过转发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因此,他们便不断地刷新朋友圈的链接,寻找合适的文本进行转发,并急切等待下一个点赞。所以,许多微信成瘾者本身便成为信息复制的媒介。“不转发、就会死”,他们认为,从朋友圈发来的单个文本具有“观赏”价值,每条转发的信息都会对其朋友圈有用,因此,他们极度紧张地浏览各种链接,对于“心灵鸡汤”和煽情话题尤为看重,不断“分享到朋友圈”,并自以为在为朋友提供精神食粮。显然,此类具有无数通道的超级链接,并非为某个微信用户的专利,微信信息的高度重复性已表明许多转发不仅没有意义,还极大了影响了其他朋友圈的阅读质量,造成信息过剩和视觉疲劳。因此,微信成瘾者多度地进行信息消费,并利用信息的无成本消费让渡,使圈子文化充满着大量无聊、无用和重复的信息。而许多“转发”不仅没有促进其他读者的价值认同,反而因为此类复制文本的泛滥而对转发者感到厌恶。从这个层面上看,过度消费和转发朋友圈的信息,尤其是不加分辨地转发各种谣言,极大地损害了微信的公信力,导致微信圈的散发式个体被迫进行混浊的信息接受和再消费,这不仅没有提高转发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反而导致许多用户“设置朋友圈权限”,不愿接受这些狂热转发者泛滥的链接。因此,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他们沉醉于圈子信息的自我制造和重复传播,造成“不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双输结果。既没有有效地提高自身的影响力,也没有为圈子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次,微信成瘾者的虚拟化生存导致现实自我的社交焦虑。“我微信、故我在”,微信上瘾者已经在网络上构筑了一个新的虚拟交往世界,他们已经成为网络多面人,无论身在何处,只有看微信就才能确定“我是谁”。人们常常调侃“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而你却在玩手机”,现在玩手机已经演变为“玩微信”。现实当中的“我们”,由于有了微信的存在,既便是见到久违的朋友,也缺乏交流与沟通的欲望,手机和微信似乎成为人体的器官,许多人通过浏览微信来表达主体存在。既便是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大家相见无语,却在对着微信傻笑,人机对话似乎远比面对面交流有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朋友见面也越来越疏于交流,甚至连一个正视对方的眼神都难以见到,更难以深度沟通。但是,在虚拟的空间里,微信成瘾者却自愿展示隐私,毫无顾忌。现实的社交焦虑和虚拟的社交狂欢形成鲜明的对比。多重而矛盾的自我在两个世界中游走,使“我”的身体、思想产生分裂。在虚拟的交往世界中,心与身,灵与肉是分离的,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上线便是一种游走的方式,如何说、说什么都不重要,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观看微信,犹如检阅一座虚拟的剧院,只要有足够的观众即可。他需要热闹,需要打发时光,需要自我消遣。至于他为何而来,交谈有何价值,则不要进行意义的建构。这种交流很难体现人的“自反性”价值,是自我导向与他人导向的矛盾性结合。但是,情感、记忆是人性的基本标识,微信成瘾者的社交泛化却很难体现真情、专注和关怀,这就导致虚拟社交的无意义漂移,交往双方都很难通过对话建立互信、增进感情。沉溺于微信交往的成瘾者拥有了一个看似庞大的圈子,一旦“下线”,却找不到几个可以谈话的朋友。相反,“越微信,越疏远”似乎是一些现实社交的写照。
如果网络精神的本质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技术文明的进步,微信作为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至少应该是促进朋友之间的交流与信任。如果微信成瘾者由于过度微信而导致自己的孤立、茫然和无助,那此类微信社交就异化为身体的枷锁和自我的牢笼,现实中的朋友圈就会不断远离生活世界。这显然违背了人性的本真和社交活动的原初意义。由此可见,正确地使用微信,不仅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需要,更是提升网络文明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注:
①【美】安德鲁·基恩:《数字眩晕》,郑友栋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②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③张颐武:《“四跨”与“三改”:“微生活”新论》,《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
④《〈指尖上的网民〉——2014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分析》,http://www.iydnews.com/2323.html。
⑤【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亚·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⑥【美】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⑦【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⑧韩琛:《“微/伪/萎托邦”:自由的幻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
〔责任编辑:御风〕
WeChatAddiction:SocialFantasizingandSelf-lost
JiangJianguo
WeChat reflects many advantages of social media. However, with its popularization and extended social functions, ”Being WeChat” has begun to reveal its negative impacts which are calling for our high attention. WeChat addiction not only shares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but also has the symptoms of excessive virtual social, which can lead to life disorders and spiritual emptiness. The addicted WeChat users will trap in a vicious cycle, the more often they use the tool, the more anxious and apathy they will be. As a result, they will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relationships in real life, and much more easily to have the problems of split personality, social fantasizing and self-lost. How to cultivate rational social among the WeChat is a necessity for the proper use of it.
WeChat anxiety; social; self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13AXW013)的阶段性成果。
蒋建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广州 510632
G206
A
1001-8263(2014)11-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