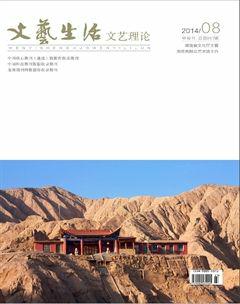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艺术研究
2014-11-28陶如意
陶如意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艺术研究
陶如意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在经历80年代的辉煌后迅速退出文化中心的舞台。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诗歌也是源于现实的,所以中国当代诗歌所呈现的沉沦之势,一定是时代环境、历史经验、个体意识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本文将以80年代的诗歌为参照,探究90后诗歌精神失落的原因,在庞杂的线索中通过对两者历史经验、诗人身份认同以及传播环境的分析来理清思路,以呈现一个较为明晰的逻辑框架。
历史经验;精英意识;平民化;大众传播
一、诗不是徒有情感,而是经验
里尔克说,诗不是徒有情感,而是经验。情感是诗的荷尔蒙,让诗充满感染力和号召力,但徒有情感没有内容的诗是肤浅的,容易沦为空虚琐碎的情绪宣泄。只有将情感置于现实经验之上,才能获得一种超凡的精神体验。可是说,经验是一首诗的材质和肌理,它决定了情感的纯度,精神的深度。但是经验从何而来?有些经验是可以靠主观努力去主动获得的,但有些经验却是时代的烙印,历史的积淀。
80年代,诗人的情感借以诗如洪水开闸一样倾泻而出,势不可挡。这些诗感性而抽象、天真纯朴、浪漫、理想主义、宏大叙事、粗疏但又生机勃勃。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诗真实反映了一代人的心灵,抒发出了当时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热情和激情。所以,80年的诗人是从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凝练情感,又用情感去回应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他们能赢得世人高度的认同和赞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步入90年代后,理想主义渐渐被物质主义所取代,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秩序中。
二、从“我不相信”到“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80年代是一个“大写时代”,充满时代朝气的青年诗人们在整体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探索着了一代人与现实的关系。80年的诗人还具有精英意识,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气魄。他们对诗歌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些诗承担的是启蒙和先锋的角色,而绝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和谈资。北岛诗歌在怀疑、否定中所表达出的“觉醒者”对于理想世界的争取,顾城诗歌对纷乱社会的记录与“一代人”式的反思,舒婷诗歌对社会重大主题的主动承担,以及江河、杨炼在80年代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探寻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透着积极入世的人格追求。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一种“众语喧哗”的语境下,任何一种写作及其言说方式都可以在寻找合理性的过程中得到一种认同。诗人们活在当下,他们再无意扮演时代的英雄,他们拒绝深度,甚至拒绝现实,在自己的精神夹缝里游走,写的诗枯燥而浅薄,梨花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6年,赵丽华的诗在网上走红,召来网民的炮轰和戏仿,就拿她的《一个人来田纳西》举例,“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这样一首把一句话分两行罗列拼凑而成的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作者似乎想用平实的语言来传达出深沉的情感,但却弄巧成拙,使诗歌完全丧失了审美性。
从北岛的“我不相信”到赵丽华的“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反映出的是诗人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感的弱化,这也是一种启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淡化。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必然性,还是个体的变异,亦或者这两者并无区别?也许在社会前进的大潮面前诗人是无力的,现实似乎也缺少培育诗人的土壤,但至少,他们应该有一点点坚守,有一点点为坚守而放弃的勇气,再一次回忆起,我是个诗人,可能在行走之时只照亮了自己,但至少通体发光。
三、一边“丰富”,一边贫瘠
传播环境的不同也是造成80年诗歌和90年诗歌呈现不同状态的原因之一。
80年代,电视电影都还不普及,人们主要通过书刊来获取知识,《诗刊》《星星》《读书》等一系列的文学刊物成为了诗歌发展的主阵地,推动着诗歌的传播和推广。到90年代,网络开始兴起,小说、散文、戏剧都日益网络化、通俗化,只有诗歌还蜷缩在一些小众的文学刊物中,让读者难以接触,似乎诗歌在通俗化的进程中总是显得有些尴尬。一方面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有着超越其它文学形式的意境和美感,诗歌的解读需要时间成本,而这恰恰是与网络的快节奏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某些已经通俗化的诗成功激起了网民的兴趣和热情,但却在网民的戏仿中被消费把玩一通,终还是沦为了娱乐的附庸。
网络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个性和品格。我们的价值看上去多元而开放,但其实都没有逃脱网络这张大网,我们都是被“塑造”出来的。不疯魔不成活,也许一部分个性的丧失也使我们不再拥有诗,也不再拥有诗人一般的理想和情怀。
总的来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时代大背景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诗歌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中,“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虽然中国当代诗歌处在这样一种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但我从未怀疑过诗歌的价值。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我一直相信我们能在诗中找到生存的原因。
[1]何雄飞.八十年代思想交锋史.新周刊,2013:134.
[2]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05.
[3]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鸭绿江,1988:(7).
I227
A
1005-5312(2014)23-0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