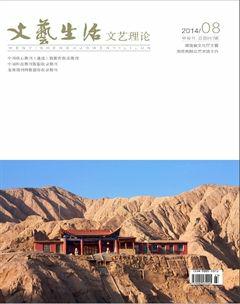深植土地的精魂
2014-11-28林婷
林婷
摘 要: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乡土文学的视域,对莫言的早期短篇小说《大风》做了一些分析与评论。
关键词:莫言;大风;乡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005-02
《大风》是莫言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相较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名篇佳作,《大风》受到的瞩目可谓寥寥。王安忆先生近来做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时谈到,《大风》最应该进教科书,一时间才使得这篇作品备受关注。借着这股“热风”,笔者也来谈谈这部作品,做些浅要的评论。
故事很简单,讲述的是祖孙俩一起去荒草甸子割草,归途遭遇一场大风的事。小说是以“我”的视角进行叙述的。美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在《大风》中,“我”担任了两个角色,一个是追忆往事的叙述者“我”,即里们·凯南所说的“叙述自我”,另一个是正在经历事件的被追忆的“我”,即 “经验自我”。前者是成人视角,后者是儿童视角。小说开篇的叙述者“我”得知八十六岁的爷爷去世的消息,赶赴故乡。追忆爷爷及其好把式这部分显然是一个成年人,是“叙述自我”。而当追忆起和爷爷一道去荒草甸子割草的经历时,叙述者就由追忆者“我”转换成七岁时正去往荒草甸子的儿童。路途上的风景都是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展开叙述的,将儿童对于世界的感官以一种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爷爷唱起了史诗般的歌谣,“我”的“小鸡儿”慢慢翘起来。作者正是用性成熟暗喻着“我”正在爷爷的引导下渐渐成长乃至成熟,跟随着我的祖先走向亘古,走向地老天荒。正是在此处,作者的叙述视角悄悄从儿童转向了成人——“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奠定了文章的情感基调与主题要义。接着割草、扎捆、装车以及归途又切换到儿童视角,叙述被追忆者“我”在经历的一切。在一个儿童的视野里感受自然,感受孙子对爷爷的爱与依赖,感受爷爷在面对大风时的坚韧不屈(“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结尾处又转换成叙述自我的成人视角,大风虽然刮走了一切,只剩下一根夹在车梁的榫缝里的草。这根草成为“我”相册里最宝贵的一页,“正好镶着我的比我大六岁的未婚妻的照片”。这一方面印证了老年人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想念儿孙、依恋童性的本能,他们在生命的某一点上相距最近,最易相通;另一方面也表达,遗忘的风可以把什么都刮走,但是刮不走我对爷爷的记忆,以及我从爷爷身上延续的农民的品质(早早地找好了比自己大六岁的未婚妻本身就代表了农民对于生命原始形态的一种保护)。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①以儿童视角讲述童年经历是莫言小说的一大特质。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偏僻农村,家里有十几口人,大人们都忙于生计,没人管这个又丑又懒又馋,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当时又正处中国经济最凋敝的时期,饥饿、水灾导致的死亡不计其数,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以及内部世界爱的缺失成为了莫言写作的情感基调,这些充满暴力血腥的童年经历成为了他写作的直接素材。《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便是一个典型。尽管《大风》中的“我”相对于黑孩来说,天真而有童趣得多。与母亲的关系也不同于《枯河》、《石磨》等作品中叙述得那般紧张,不过“我”仍然以最直接最赤裸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仍然带有沉重的思绪与恐惧的心理。并且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张望“我”的爷爷,从孙辈的角度来审视和叙述祖辈。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莫言的叙述视角与其说是儿童视角,不如说是一种审祖的视角。“他把笔伸向历史,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上,叙事先人在过去年代的生活,他们(‘我爷爷、‘我奶奶)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莫言总是以一种饱含敬意的笔调与情感塑造祖父母形象。他们几乎都是性情剽悍、血气方刚的能人好汉,《红高梁》中的余占鳌、《秋水》中的奶奶、《老枪》中的奶奶等等。《大风》中爷爷却是另一类好汉。他是“数一数二的庄稼人”,精通各种活计。尽管文本中并没有对他的外部经历有任何的描述,但从他漫不经心唱出的小曲中,我们便能发觉,这是个饱经沧桑、历经忧患的老人。“干什么事都要干好,干什么都要专心”,这是老人生活的智慧,也是农民最朴实的品质。当他遭遇大风,他所能做的便是把双脚更深刻地扎入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个人物顽强而坚韧的性格也在大风袭来的时候豁然展现。虽然莫言笔下的这些祖父母的形象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却有着相同的气质禀赋。前者是勇敢抗争,后者是勤劳耐苦,他们都共同体现了乡村中国人的坚韧的风骨,这也正是乡土中国的精神所在。张志忠先生在谈及莫言小说的特质时说到:“这个特质的背后是有底蕴的,什么底蕴呢?他(莫言)是站在农民文化的立场上,站在农民的本位上,他有一种说,就是农民的信念、农民的执着、农民的质朴,农民怎么肯认输,中国农民强悍的生命力。”②
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的相互转换,使得小说在轻松和沉郁之间来回跳跃,产生叙事的张力的同时,也奠定了两种基调,传达出乡土带来的快乐和忧愁。结合审祖视角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轻松的童趣、田园般的诗意是一个引子,莫言真正要表达的是深植于那片记忆中的土地上的坚韧的生命力,小说题目是“大风”,选取这个对生命的磨难物作为标题,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倾向。
有别于《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等作品中充满了苦难与暴力的乡土农村,在《大风》中,在“我”的眼光里,乡土是雄浑沉郁的,充满了生命的原力,却无暴戾之气,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视、听、嗅、触等全部感官参与的自由的叙述。梁鸿鹰先生在谈及莫言的小说时提到:“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色彩感,大红大绿,大黑大白,大苦大甜,爱憎分明,也包括他的叙述方式的汪洋恣肆,很宏大,很大胆,风格华丽、神奇、有力。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而是排山倒海式的、倾倒式的,具有巨大的体量与源源不断的流量”。笔者大致数了《大风》中的色彩词汇竟有28处,并且多是敏感而细致地呈现了色彩细微的变化。endprint
雾越来越淡薄。河水露出了脸几,是银白色的,仿佛不流动。灰蓝的天空也慢慢地明亮起来,东方渐渐发红,云彩边儿是粉红色的。太阳从挂满露珠的田野边缘上升起来,一点一点的。先是血一样红,没有光线,不耀眼。云彩也红得像鸡冠子。
天变得像水一样,无色,透明。后来太阳一下子弹出来,还是没有光线,也不耀眼,很大的椭圆形。这时候能看到它很快地往上爬,爬着爬着,像拉了一下开关似的,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照亮了天,照亮了地,天地间顿时十分辉煌,草叶子的露珠像珍珠一样闪烁着。河面上躺着一根金色的光柱,一个拉长了的太阳。我们走到哪儿,光柱就退到哪儿。田野里还是很寂静,爷爷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作者运用大量的色彩词汇把天亮的过程描述得非常壮观,甚至有些绚烂。他在描述时并不使用单一色调,而是诸如银白、灰蓝、粉红、金色等复合色调来再现原生态的乡村自然风物,并且运用诸如粉红、血红、金色这样的渐变色来细致描述太阳升起过程中颜色的变化。同样地运用渐变色的情况还出现在作者描述天空上,从灰蓝到无色,再到大风来临前的茶色,最后到大风过去夕阳西下的淡黄色。不难发现,作者所运用的色彩大多是浑厚的,巨大而具有冲击力的色块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片气势恢宏的油墨效果。另外他用细笔勾勒的乡村风物,“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等等语调轻快,意象飞扬,它们连同着河水泼剌的响声,小车轮子 “沙沙”的声响,草梗拨弄车辐条“劈劈劈劈、叮叮叮叮”的声音,秃尾巴鹌鹑 “哞哞”的鸣叫,混合着烤熟的蚂蚱香、扑鼻的甘草气息、野嵩子的苦味和野菊花幽幽的药香,形成了独特的乡土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轻盈的童趣在雄浑的土地上奔跑,他的笔使完全相反的两种声调和谐共鸣,那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他在这短篇的限制中充分的享受着叙述“自由”,用直观可感的语言酣畅淋漓地表达他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二是寂静与喧闹的氛围形成的强烈对比。“现代小说的所谓气氛,实则是由主观性的、感觉化的风景(环境)描写制造出来”③。祖孙俩清晨赶路,没有言语,作者运用间或的河水泼剌声、车轮的沙沙声、草梗拨弄车辐条发出的细微的声响来烘托天地间的安静与肃穆。太阳“一下子弹出来”,之后又“像拉了一个开关似的,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照亮了天,照亮了地”。动词“弹”的使用把原本安静的画面突然打破,接着一系列的“拉”、“射”、“照”更像是在为一个喧闹的场面做铺垫。然而“田野里还是很寂静”。爷爷悲壮苍凉的歌谣响起,天地间再次回归平静。这样的动静对比在大风来临前后显得更为突出。天地没有了界限,鸟儿也不叫唤,庄稼叶子即便动了动,也没有声音。一切都不发声。似乎世间万物都在静静地等待大风来临。在这寂静的氛围里,蚂蚱变得长长的,甚至还瞪着我,野兔也自由地出没着。这更加加剧了周围的“静”与“我”的恐惧。“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飞旋而来,紧接着是雷鸣的呼噜声,“我们钻进了风里”。这里的动词“钻”同之前的“弹”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达到了一种划破寂静的逼兀感。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闪电,伴随着我一次次的叫喊声形成了喧闹动荡的场面。这两次寂静与喧闹所形成的对比中烘托的是爷爷岿然不动的“静”。他绷得像弓一样背脊,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凸起的腿部肌肉,让我们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普通农民不屈的灵魂,他像钉子一样钉在这片赐予他生机也给予他重担的沉郁的土地上。莫言便是出生在这样的土地上,它是沉静的,也是浑厚的;是郁郁葱葱的生机之下,也有沉重的生命之愁。
“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莫言语)。
注释:
①[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②摘自《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会议材料。
③摘自莫言散文《超越故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