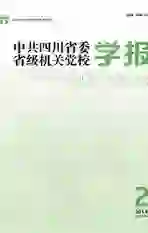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基于“和合思想”的思考
2014-11-28李丰
〔作者简介〕
李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在前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对抗关系;在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现实中则是分立甚至是对抗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能包容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和合思想,是一种既追求同一性又包容差异性的思想,它强调通过对差异性与同一性的承认和超越来形成新的和合体,这一思想对于合作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思想层面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心边缘结构;和合思想;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44-06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文化精神,它不仅能从一个方面分析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失灵的原因,还能够启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进而建构起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机械、封闭的结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机械、封闭的特征正是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失灵的根源。和合思想作为一个能够包容并超越差异性和同一性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按照和合思想的主张建构起来的将是一种超越“分化观念”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在《左传》所载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中,景公问晏子:“和与同异乎?”晏子答道:“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在晏子看来,“和”是包含着差别与矛盾的“同”,就像调汤一样,需要将各种不同味道的食材、作料加以调和,才能成为美味。同时,晏子还将“和羹”的道理引入政治关系之中,认为君臣之间也应该也要有不同的政见来调和治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可见“和”是一个包含着差异与矛盾,甚至是冲突的辨证统一体。《国语·郑语》也有史伯关于“和”与“同”的论言,史伯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在这段论述中,史伯讲出了“和”的本质——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调和、补充,而不是去除差异后的机械同一。此外,史伯的论言中还包含着实现“和”的方法,即“以他平他”。
《左传》和《国语》中所包含的“和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先导,影响着其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在继承了史伯与晏子的和同论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的思想中,“和”既是政治原则,也是人际关系原则。在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继承发扬了儒家的和合思想。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在战事频繁的战国时代,要想在群雄纷争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孟子认为应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而“人和”在此三条件中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荀子作为先秦末代儒家,他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世间万物千差万别,它们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出于“和合”的缘故。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和合”,就是在自然界、社会、人际关系、心灵和人类文明等诸领域中,有形的和无形的事物之间相互冲突与融合,并最终生成新的事物、生命和关系的过程。
和合思想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条思想线索,而非某家某派所特有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着很大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仅仅体现在儒家学说里,是儒家学说特有的思想内容。与这种看法不同,有许多学者也认为和合思想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某一家某一派的思想。张立文教授就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便是和合或合和,它不是某家或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摄儒、道、墨、法、阴阳、释各家各派的普遍的文化精神。”〔1〕所不同的是“儒家从差别中(社会有等级)求和合,道家从人与自然的分别中求和合,佛学从因缘中求和合,墨家从兼爱中求和合,阴阳学从对立中求和合,法家从守法中求和合,名家从离坚白与合同异中求和合。”〔2〕可见,和合思想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都有体现,而非专属于儒家。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总的称谓,而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绝大部分的学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具体方面或某一具体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比如: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但这个“中”所指的不是折中,“所谓‘不偏之谓中,不偏在这边,也不偏在那边,这一个‘大中,是全体……,是一个‘大中至正之中,是一个大局面全体之中。”〔3〕张岱年从哲学的高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哲学有六个特色,其中三个为:合行知、一天人、同真善。〔4〕不难看出,在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虽然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和不同范围来进行研究,但其中都包含着对“和合思想”的不同表述,这表明“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今天研究它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它、发扬它以及运用它。因此,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观念,在动态的图式中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转生”为前提。“这种转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再生的延续,而不是传统文化原封不动的单传;它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蕴涵,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固有的意蕴。”〔5〕为此,中国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的研究而形成了一门学科——和合学。“所谓和合学,是指在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6〕从对和合学的涵义的定义中可知,它是以社会中各领域存在的冲突与融合现象为研究对象,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超越的方法与途径,进而实现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
二、社会治理失灵的思想根源
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水平,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走过的历程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阶段。前工业社会是一个物质贫乏的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觉识甚至崇拜的水平上,只能靠使用简单的技术和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来维持生存。同时在前工业社会阶段,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个人被淹没在强大的家族体系中,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副未分化的混沌面孔。与社会混沌一体的状态相对应,社会治理模式与政府行政体制之间也呈现出一种重合的关系,政府体系就是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发挥着统治的职能。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通过对权力的垄断来对社会进行统治,除了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是作为被统治的一方而存在的。前工业社会阶段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依附于土地之上。然而,前工业社会中的土地是统治阶级的私人财产,主要控制在统治集团的手中。如此一来,统治集团通过对土地的控制而实现了对社会的控制,最终使得人们对土地的依附转换成了对人——统治者——的依附。从本质上看,前工业社会的社会依附关系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此外,我们知道在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依据身份的贵贱高低将社会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的等级之间有着明显而确定的边界,由于这种等级差异而使得——在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层级之间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统治集团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异己”的矛盾关系。因此,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或者说差异和冲突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在“主权在民”思想的基础上,人们建构起了政府垄断的单中心社会治理模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身份差序逐渐被权利平等所代替,人们之间不再是一种高低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形式上人人平等。同时,在人民主权思想的指导下,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中的委托-代理过程创立了得到公认的政府。加之人类社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被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政府成了公共领域的代表并承担者社会治理的功能。所以,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人民在形式上拥有主权,在实际上则是政府掌握了社会的治权而成为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人民和政府之间在形式上是统一的,而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则处于治理体系的中心,人民处于边缘。如此看来,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在形式上是融合统一的,而在实际上却是分立甚至是对立的。
毫无疑问,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立,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公共行政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以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爆发过几次危机,这些危机在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框架内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化解。但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危机,政府显得有些应接不暇,社会不可治理的问题日益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扩散就是很好的佐证。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摆脱工业社会通过践行形式理性来追求社会的同一性的思维模式。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完成的,面对社会分化的事实,管理行政通过对科技理性、形式理性的绝对推崇来追求抽象的同一性,使社会在一切方面都向形式理性靠拢,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导致社会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刻板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中心-边缘式的社会治理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形式同一的情况。
启蒙运动的发生,解构了前工业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和羁绊,人类社会从权力主导的阶段向权力至上的阶段进化。启蒙运动是对工业社会的启蒙,它是人类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工业化开始前的清道工作。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天赋人权的思想得到普遍接受与宣扬,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受到高度的赞颂,一切变化与进步都要服务于人的权利、价值、尊严和追求幸福的需要。以至于有人认为现代性具有一种宗教性,其“集中表现为人定胜天的进步观念和人权。进步观和人权意味着人的神权,意味着人决心把人变成神,尽管在现实上尚未实现为神,但已经在概念上先行自诩为神,而且以概念作为抵押而预支了神权”〔7〕。因此,在启蒙运动后的工业化过程中,进步思想成为人们普遍的信仰,形式理性、工具理性作为启蒙理性贯穿其中。“由于工具理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手段;它把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消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屈从于现实并为现实辩护。”〔8〕因此,当科学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时,人们模糊了对科学技术本来面目的认识,不假思索地将其作为生活的目的甚至全部。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之改变——将自己和他人都看做是工具,结果将科学技术神话、将人物化。启蒙运动本来就是一场要将人类从恐惧和蒙昧中拯救出来的运动,但随着启蒙理性的发展和扩张,技术理性压抑了价值理性和人文理性,并成为支配人类的强大力量,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如霍克海姆(M.Max Horkheimer)所说:“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8〕“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起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9〕可见,启蒙运动之后,随着人类向工业文明的全速挺进,科学技术变成了统治者人们的强大力量,启蒙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集中体现在社会、人、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的形式化和单向度化。
不可否认,工业文明事实上在很多的方面都远远地优越于前工业文明,而这一切正得益于对技术理性的推崇与深信不疑。启蒙运动激活了人的创造性,而工具理性和技术文化迅速发展,推动着人类从落后的农业文明进入发达的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中,科学的管理和社会分工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人类第一次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丰富的食物、舒适的楼房、发达的医疗、先进的交通工具、神奇多彩的电子世界等等,这一切都得益于技术理性的优异表现。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倍增的状况,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自身以及不同的文化模式之间……各种矛盾与冲突不断涌现,社会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要想继续很好地生活或生存下去,不可能通过单方面地强调冲突或者同一而得以实现。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深度分化,整个世界的复杂化、多样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若一味地突出冲突与矛盾,人们将有可能在冲突和矛盾的裹挟下走向灾难,特别是随着生化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和运用,其结果对发生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是毁灭性的,最终有可能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甚至世界的灭亡。另一方面,世界本身呈现出的多元化、复杂化与个性化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客观上不具有通过消除矛盾、差异来获得全面的同一性,进而达到消除冲突的可能性,所以,通过只强调同一而回避矛盾与差异来追求社会发展的思想日益显得不合时宜。
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工业文明那种化繁为简的思维以及形式理性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风险四伏、危机频发。其根源就在于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通过刻意地回避与剔出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追求机械的同一性,当社会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当中,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鉴于这种情况,在后工业化浪潮正汹涌跌宕的当下,我们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思考必须要摆脱工业社会话语体系的束缚。进一步说,我们必须要跳出近代以来追求形式理性、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去寻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三、和合思想对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启示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每个民族国家都包含着许多历史事件、创伤、失败和成功的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创立了特殊的习惯、习俗、制度化和行为方式、世界观甚至民族心理。人们不能认为公共行政学能够摆脱这些条件作用的影响,或者认为它能以某种方式独立于和隔离于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10〕在人类社会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正具有这样的思想作用。与西方文化重分析思维的传统不同,“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含在这个整体之中。”〔11〕而且这种综合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是普遍存在的,和合精神就是其焦点性的呈现。因为“和合学所研究的和合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和合遂成为中国人把握宇宙、理解人生的一种主要观念,成为中国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12〕它既承认矛盾与冲突,又力求在承认矛盾与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并通过“和合”来实现对冲突与融合的超越。所以,即使在高度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今天,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如前所述,在人类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之后,既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将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变革,但这种变革需要深入到思想层面。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都将难以完成社会治理的重任。我们需要建构起一个能够包容冲突与融合的、能够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意味着对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解构。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的变化趋势,我们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将会是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由于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政府这个唯一的治理主体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所有能够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主体加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中。这些新的社会治理主体与政府之间不是“参与”和“主导”的关系,因为如果这些新加入社会治理过程的主体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来开展治理的话,那在社会治理的关系格局中仍然没有改变“单中心”的局面,只是政府通过对其他主体的吸纳而多了几个听话的“帮手”而已。后工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多元化、个性化、主动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单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体现出的是一种单一化、片面性的特征,是与后工业社会的情况背道而驰的。因此,多元化、个性化、主动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意味着政府垄断治理地位不复存在,政府和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随之由“中心与边缘”向“中心与中心”演变,所有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它们相互为伴、合作共治。
不难看出,社会治理模式从中心-边缘结构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和合的过程。和合思想强调“如只强调斗,或只想调和,都只是一面,不能把一个统一体分割了。事物发展一定是这样的:在一个和合体中,有冲突事物才能发展;同样,有融合事物才能发展。”〔13〕合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代表的是一个和合体,这个和合体是包含着冲突与融合的统一体——冲突代表着和合体中的多元性,融合代表着和合体中的合作关系。所以,在建构合作型社会治理模式时,既不排斥各合作者所具有的个性,也不刻意强调各合作者之间的机械同一,而是在多元化的基础上来促成社会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既是对多元性主体的包容,又是对多元性主体的超越。
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是与一种特定的政府模式相对应,社会治理模式和政府模式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强化的关系。所以,对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解构,也意味着要对管理型政府进行变革;同样,在重构新的能够适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思考建构起一种新的政府模式。由于合作型的社会治理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政府失去了在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核心地位而成为一个合作者和行动者。在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政府体系几乎等同于社会治理体系。因此,我们在解构中心-边缘的社会治理模式时,对管理型政府的变革既是重点,也是切入点。反过来看,我们在建构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时,也应该从探索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政府模式入手,这种新的政府模式不管在本质特征还是在核心价值上都应该比管理型政府更加合理。虽然如罗森布鲁姆(David H.R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Robert S.Kravchuk)所言,管理型政府在实际的公共行政中政府具有管理、政治和法律的职能,但这并没有反映出它的本质特征。就管理型政府而言,总体上具有三个特征——治理地位的垄断性、职能定位的简单化和行政人员的工具化。管理型政府的这些特征,都是在追求公共行政的同一性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政府的垄断治理,获得了治理关系上的同一性;通过政府职能定位的简单化,保证了政府职能的确定性;通过行政人员的工具化,获得了行政体制的科学性。
管理型政府对同一性、确定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是以牺牲多样性和人为地抹杀矛盾来实现的。主体的同一化排除了多元主体的可能,职能的片面化、确定化排除了灵活多变的可能,行政机制的形式化、物化排除了对治理理念和行政思想兼收并蓄的可能。然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与人有关和需要人来完成的事情,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同一化,因为人是有意识、意志和价值判断的存在。从结果看,这种几近僵化的同一性在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的工业社会阶段是有效的,但是在后工业化正迅猛推进的今天则难以为继,需要通过政府模式变革来化解这个困局。前面我们论述过,合作型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它是一个和合体。在这个和合体中,既强调冲突和矛盾,又重视融合与与互补,是冲突与调和的共在。
首先,从治权的形式上来看,由于多重治理主体来共同行使治权,那些过去被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的主体与政府一样获得了治理社会的权力,他们与政府之间不再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是一个和合体中的共同行动者。这个和合体是由形态各异、职能多样互补、能力各有所长的行动者构成的,它们之间由中心与边缘、主导与附属、主体与客体、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向合作共治的关系演变。其次,随着治理关系的变化,社会治理体系、政府本身,也不再从属于过去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各种合作共治的行动者所尊崇的将是一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导向、以社会和谐的总体发展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最后,在社会治理关系和主导价值变化的同时,带来的将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变化。在前工业社会政府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发挥的主要是一种统治职能;在工业社会政府扮演的是管理者角色,发挥的主要是一种管理职能;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将会是合作者、服务者、行动者的角色,发挥的将主要是一种服务的职能。依据新的治理关系、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建构起来的将会是服务型政府模式,它是本质上不同于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的全新政府模式,是一种指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然会引起政府角色和职能体系的变换,这是一个解构与重构同时进行的过程。经过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由管理型政府扮演的唯一治理主体变成互相有别的众多行动者中的一元。政府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来处理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在和合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要正视并明确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行动者之间的个性差异,以此来形成灵活性的、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同时还要注重政府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在职能上融合与互补。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不应仅仅停留在突出政府自身与其他行动者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而是要实现对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超越。也就是说,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和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建构起一个作为新的和合体的服务型政府。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它强调的是一种包容冲突与融合的理念,通过和合的过程来实现对冲突与融合的超越,既不单方面地强调冲突,也不单方面地追求机械、刻板的同一性。“中华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会通精神。对待文化学术,有远见的思想家、学问家们都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赞成多样性的统一,反对单调呆板的一致。”〔14〕在这种文化精神和思维模式启示下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对管理行政将会是一种本质性的颠覆,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会是一个能够包容不同的冲突与融合的、能够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合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作为一个和合体的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当中,政府模式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既能够与其他社会主体取得共识,同时又在尊重彼此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凸显出各合作者之间的互补性和社会治理的灵活性,进而在合作共治中超越“差异性”和“同一性”。
四、结语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垄断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已然难以很好地承担起社会治理的任务,究其根源,在于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本身所具有的机械性。“和合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其包容差异性和同一性的思想主张,对于解构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建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意义重大。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和合思想”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结构与重构的启示主要存在于思想上的启发和引导。因此,我们在涉及到具体的社会治理事务时,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研究,让和合思想对社会治理的改善具体化,当然,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进行长期系统的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5〕〔6〕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18,22,37.
〔2〕〔14〕张立文,包霄林.和合学:新世纪的文化抉择〔J〕.开放时代,1997,(1).
〔3〕钱穆.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36.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序5-8.
〔7〕〔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M〕.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9(导读).
〔8〕王风才.批判与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9.
〔9〕〔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3.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
〔11〕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竹立家,等编译.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60-161.
〔12〕季羡林.季羡林自选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425.
〔13〕李振纲,方国根.和合之境〔M〕.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87.
〔15〕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7.
【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