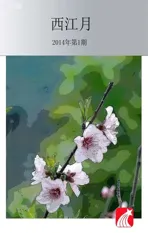少女的憧憬与记忆
——诗人黄咏梅访谈录
2014-11-17钟世华
□ 钟世华
少女的憧憬与记忆
——诗人黄咏梅访谈录
□ 钟世华
编者按:10岁就开始写诗的黄咏梅,在20世纪80年代曾以“少女诗人”的身份引起梧州文坛关注。怀揣着自己的文学梦,那个充满憧憬的少女十几年来笔耕不辍,至今已在《诗刊》、《散文》、《钟山》、《花城》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100多万字,出版有小说集《隐身登陆》,诗集《寻找青鸟》、《少女的憧憬》等。
少女的憧憬:一首诗和一个诗人的诞生
钟世华:听说你从小就被当副刊编辑的父亲带上了一条文学的道路,你父亲是如何把你带上文学之路的?
黄咏梅: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氛围很浓的家庭。父亲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他平时话不是特别多,但只要一谈到文学的事,话就明显多起来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由于当副刊编辑,时常有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到家里来,吃饭喝酒聊文学。我喜欢坐在他们旁边,似懂非懂地听,那种热烈的氛围,让我终生难忘。我记得,除了有在本地当时写作比较活跃的张丽萍、何德新等人,还有外地的著名诗人杨克、傅天虹,以及我父亲崇拜的作家秦牧、张永枚等。可以说,文学的位置一直就存在于我家的客厅,存在于我的生活。
在这样的氛围和熏陶之下,我自然就喜欢上了写作,从而走上了文学道路。父亲对我的创作很重视,除了在写作上给予我建议之外,还推荐我读了大量优秀的作品。阅读优秀的作品,使我比起当时的同龄人少走了很多弯路。
钟世华:你认为写诗需要天赋吗?
黄咏梅:写诗当然需要天赋,起码应该具备对事物体悟的敏感性,那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敏感,对于写诗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它并不是通过练习能获取的。所以,在创作领域当中,花同样的功夫,有的人就能走得远一些。诗歌这种体裁,在文学作品里尤其需要天赋和才华。
钟世华:你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萌芽文学社”,当时文学社开展的活动多吗?加入文学社对于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黄咏梅:我在梧州一中加入了“萌芽文学社” ,在梧州师范又加入了“红杏文学社” 。可以说,文学社伴随着我的成长。
文学社活动很多,朗诵会、读书心得交流会、写作交流会……不仅仅在校内举行,还经常在社团之间举行。我记得那个时候,梧州还组织过一个很大型的“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夏令营”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文学社老师,带着优秀的文学爱好者来到梧州,有上百人吧,除了开交流讲座之外,还举行即兴作文比赛。几天时间,天南地北的同龄人,怀着同样的兴趣聚在一起,很兴奋啊!后来,因为这次夏令营,交了不少朋友,回去之后大家还经常写信交流创作。
可以说,文学社在当时的兴旺,对一个在写作中成长的孩子来说,是很幸福的,它让我早早地感受到,写作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集体的精神寄托。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孤单的,但文学社又让我感到写作并不孤单,好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共鸣。至少,在那个信息传递困难的时代,分散在天南地北的各个文学社,让我感到温暖。
钟世华:80年代的梧州文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咏梅:那时梧州的校园文学很繁荣,文学社推出了不少创作新人。梧州的文学阵地就是《梧州日报》的“鸳鸯江”副刊。当时整张《梧州日报》只有四个版,其中一个版就是“鸳鸯江”副刊,占了报纸的四分之一篇幅,可以想见,当时对文学的重视。很多梧州作家都在这里发表文章,还有不少外省的作家,我记得我还在上边读到过顾工、秦牧、贺敬之、柯岩、陈残云、肖复兴等一大批当时很火的作家的文章。
此外,梧州文联还不定期邀请一些作家来给文学爱好者讲课,我印象很深的有秦牧在中山纪念堂讲文学,贺敬之、柯岩在学校讲诗歌。这些作家的到来,给当时的小城带来很大的轰动,而他们讲授的知识,无疑也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总体来说,80年代的梧州,文学创作者很多,文学创作热情很高。
寻找青鸟:从小天地步入大世界
钟世华:你的诗和传统诗歌、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你更多地从哪一方面吸取营养?
黄咏梅:由于那个时候的阅读资源很有限,我所阅读的诗歌主要是国内古典诗和一些现代、当代诗人的作品。大量阅读西方的好诗,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少写诗了。所以,应该说,还是中国的传统诗歌对我影响比较大。传统诗歌的抒情性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写的诗也属于抒情诗居多。传统文化里对于意境的讲求,对我影响很大,不仅仅诗歌,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我也很喜欢营造一个合理的叙述意境。
钟世华:你总共创作了多少首诗?
黄咏梅:大致有三百多首吧。
钟世华:80年代,你曾发表了很多作品,收到过读者的来信么?交笔友好像是那时比较流行的。
黄咏梅:那个时候,写信交流是一般文学爱好者很喜欢的形式。就像写作一样,给一个不曾谋面或只见过一面的笔友写信,倾吐自己的情绪、困惑、情感,谈谈自己的写作体会,等等,这些都是笔友之间最主要的目的。我那时候经常在全国的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所以能收到全国各地很多的读者来信。
我记得,在我读师范的时候,上海《文学报》的“未名园”栏目刊登了我的诗歌和创作谈,还附上了我的照片和个人简介,之后,广州的《羊城晚报》介绍了我,广西电视台也播放了我的专题片……大概因为这样,不少读者知道了我的学校,所以,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一直到我离开学校了,还不时能收到转到我家的一捆一捆的信。由于还在上学,无暇一一回信,当时《文学报》的编辑老师建议我,写一封给读者的回信刊登出来,我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刊登在《文学报》上。
钟世华:大学里的教育对你的文学之路有影响吗?你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专业化的文学训练有哪些影响?
黄咏梅:可以这么说,在梧州的成长阶段,对于创作的启蒙大多来自于学校和家庭,感性成分居多;而在桂林读大学的阶段,对于创作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于专业的教育和训练,理性成分居多。
我所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并不是说如何具体地指导写作,而是通过专业化的赏析大量的优秀作品,庖丁解牛式地对文学史的主要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由此获得解决创作问题的有效方法。实际上,这些收获也是我在以后慢慢才领悟到的,是潜移默化的。记得后来有一次余华告诉我,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把西方大作家的作品,看了许多遍,还在每个段落每个句子标注上自己的解读,密密麻麻写了很多,这对他的创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想想,当时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跟我们分析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吗?只不过每个人领悟和学到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有不少人认为专业化的文学训练,那些条条框框会限制作家的才华。更有人认为,中文系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可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专业化的文学训练有坏处。在我写小说的过程中,我读到不少西方作家写的演讲稿、创作谈,包括略萨的《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等,他们都对文学创作进行了很棒也很坦诚的阐述,其中也不乏技术上的分析。那些认为专业化对写作有伤害的人,我觉得太过于强调文学的神秘感和灵性。实际上,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门技术活,除了需要作家自身的思想和才华之外,还需要像一个优秀的工匠一样琢磨研究,所以,专业不可能有害。阅读较多的文学作品,对自身的创作有益无害。
钟世华:当时写诗,对你影响较大的作家是谁?是如何影响你的?
黄咏梅:可以说,当时读过的我认为好的作品,多少都对我有影响,因为那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能读到的好东西实在不多,而且又加上创作还是起步阶段,没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所以,作家的影响对我来说是驳杂的,比较朦胧。但我比较喜欢的中国诗人古代的有李商隐、李清照等,现当代的有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北岛、舒婷、席慕容等。至于小说家,我从小就喜欢张爱玲、王安忆、三毛等。
钟世华:古人云:“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梧州是一个山水小城,而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梧州作家,请谈谈你对梧州最深切的感受。梧州与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
黄咏梅:我看到不少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都认为我写的是广州市民生活。实际上,一半一半吧。有部分小说的确是在写广州,有更多部分的小说,是写一个模糊的城市,也可以说是广州也可以说是梧州,但是这个城市再模糊,它的气质都是很清晰的——南方气质。事实上,除了现代化气质之外,广州和梧州的气质是很相似的,饮食习惯、文化传统、市井味等方面都很相似。广州是梧州的文化上游,它影响着梧州人的生活,这方面,你只要看街上的流行风就可以体会到了。一种流行,它也许只需要一夜就能从广州传到梧州了,但内地城市也许需要几天几夜。
除了地理位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广州与梧州在文化认同上的密切性。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所以,我写小说选取的地点人物并没有什么困难,在广州发生的事情,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放到梧州,反之也可以,并不会显得隔膜。
由于发展进程的不一样,梧州的市井味更足一些,所保留的岭南气息会更浓一些,这种气息不是刻意地保留几座旧骑楼,或者保留几处旧牌坊所能体现的。这种气息在梧州的河东旧城区里,四处游荡,也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最喜欢也最容易捕捉到的一种氛围:它有的时候化作一股去湿汤的味道,弥散在小巷里;有的时候是一股酸笋田螺的味道,蒸腾在街角处;有的时候又是一声声讨价还价的声音响在耳畔;还有的时候是一串绝尘而去的摩托车声……总之,对于我记忆中的梧州,那样的氛围简直信手拈来。而这种氛围的得心应手,对于我写市民生活,也就是市井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把梦想喂肥:写作路上漂亮的“三级跳”
钟世华:到广州《羊城晚报》后,你改写小说了,你当时“改行”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在一篇访谈中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我不读这个大学,我想可能,我也就停留在写诗上,然后诗歌毕竟也冷落了,可能现在我也不再写诗了。”其实你当时在桂林的创作,已大部分偏向散文了。
黄咏梅:从写诗转向写小说,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很多,比如毕飞宇、韩东、朱文等等,还有很多以前自己默默写诗后来转向写小说而成名的小说家。我不觉得这个转向在我身上有多么戏剧性,反而认为是很自然的。文学的质地在一个人身上都不会轻易改变,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都是文学的热爱者。只不过我转向写小说的时间地点,有那么一点标志性。从地点上看:在校园里,我写诗和散文,到社会工作后,我开始写小说。也可以说,校园生活很单纯,没有太多的故事,对文学的需求仅仅限于抒情和思考,但社会则相对复杂,再加上我在广州从事的是媒体工作,获知的传奇性经验比较多,所以,喜欢上叙事,想讲讲故事了。从时间上看:年纪的增长,本身就是生活经验的积累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了,觉得自己可以尝试着写写生活,而写生活,我认为小说这种形式最适合不过。
另外就是,诗歌这种文体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确已经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热了,读诗的人和发表诗的园地也不如小说多,这种时代氛围多少也影响了我转向写小说,但不是最主要的。
钟世华:刚开始写小说写得顺利吗?我读到你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花城》上的《路过春天》,好像那时你用的是笔名,为什么要用小说中主人公“每每”这个笔名呢?
黄咏梅:“每每”这个笔名在小说里只用了这一次。事实上,我写小说之前在一些报纸上开专栏,用的也是“每每”这个笔名。写这篇小说没什么纠结,所以现在看来,也很不成熟。只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写完了,也没怎么修改,就投给《花城》了,要是现在再写,就不会那么草率了。
责任编辑:傅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