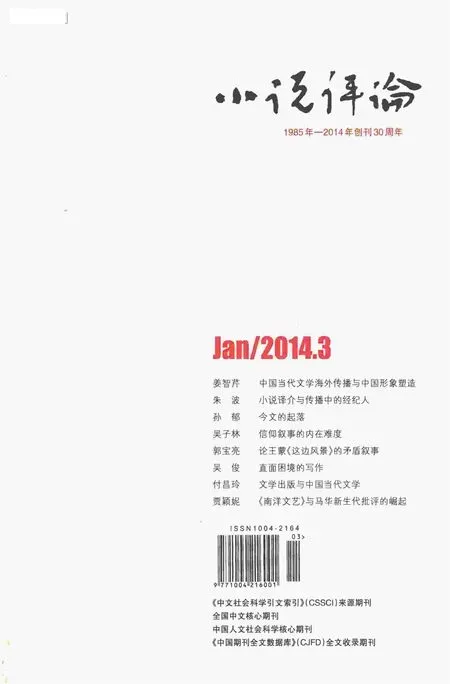今文的起落
2014-11-14孙郁
孙郁
白话文里的问题,很早就被人意识到了。自从发现新文体里还有旧思想,关于文风的思考,就时常在人的言谈中。白话文学是在古文衰微的时候出现的,它起初不被人看好,早先的士大夫者流对其轻视的原因是浅白无味,悠远的余韵不多。自从周氏兄弟出现,这一格局才有了变化。不久连一些文学史家如钱基博,也在书中肯定了鲁迅与徐志摩。其实白话有新老白话的区别,老白话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有点关系,而新白话的传统也各异其趣,书斋体与乡间文都有。口语入文,也存在智慧的呈现的技巧,它的伸缩度能否有玄机与诗意,不久就被证明不是问题。但不幸的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今文和古文一样,后来渐被污染。如今它的八股气较文言文不差,这也是五四新文人所未料到的。
有文体意识的人对此是敏感的,我注意到刘绪源有一册《今文渊源》,谈及的就是这个话题。作者敏感于言说的体例,对百年间的白话文脉作了梳理,有许多厚重的意味在。书从五四以来文章的流变看文化的起落,会心的体味和奇思都有,看到了常人体察不到的一面。今文内在的复杂性,其实也与古文相近。百年间的起起落落、忽明忽暗,也是得失皆在的。它的流变过程,也呼应了古代文学历史的一种规律。
我猜想刘绪源写这本书,来自对当下文章表达方式的不满,忧虑的是流行的文风。因为往返于新旧朝代之间,对比感就强,对当下文章之弊看得颇清。今文也面临着和古文相似的命运,我们对比一下古文的变迁史,可说是高低互见。先秦的文学和两汉不一,唐宋的音律也是各异的。要是对比晚明与晚清的文章,似乎在不同的世界里。这其间“道之文”多,“心之文”稀少。好的文章,多不是“道之文”,而是“心之文”的呈现。白话文的发展,也有曲直不一的流脉。刘绪源从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的写作,看到了中国文章的多条路径,真的彼此映照,各有千秋。五四新文学,也是“道之文”与“心之文”并存的,但“心之文”却多见异彩,有着脱俗的冲动。周作人对此形容为言志的文章,认为较之那些只会布道的人而言,有心性的自白。中国最缺少的,是这类率性无伪的文字。
但只能率性,缺少见识,似乎也是个问题。汪曾祺就说,好的文章多是杂家所为,那些有学问的人以不正经的方式所写之文,往往有奇思与趣味。报人喜欢杂家的笔墨,刘绪源的报人经验,有别人没有的气韵在。他看文章自有自己的眼光,其文字有时让人想起苦雨斋的笔意,有着诸多学识与趣味。言谈之间说的是学院派里不说的话。报人兼学者在今天不多,他们衔接了旧文人的气息,故对旧文与今文的区别是颇为熟悉的。《今文渊源》写的是白话文演变的历史,从周氏兄弟到胡适、林语堂、钱钟书、李泽厚,是无数驿站里的微火,流动着明快的光泽。
五四以来的文学注入了新风,那是叙述主体的位移所致,《今文渊源》将此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作者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胡适的笔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兴”与“赋得”的差异,都与心口是否一致有关。“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地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布道之作,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可心者却数目寥寥。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后来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与基本审美理念有别而言。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旧文章的理路偏离了许多。但那些多是形式的变迁,许多文字还是儒家正格的再版。五四白话文在根底上是与其不同的所在,主要是有了现代性的涵义。表现在审美的意识里的是,精神的逆俗、超时空的凝视增多,与西洋的个人主义衔接起来。《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看梁启超的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晚清的主流写作不同,开启了新的写作的风气。但因了知识结构的限制,诗文的总体特点还在士大夫文化的层面。词章的构成难出古文传统的左右。其实那时候上海的小报里的文学作品,在词语上已经有所变化,趣味的地方多了。但梁启超没有小说家的洒脱,文章不免多韩愈的气味,或者说是韩愈的变体。中国好的文章,多在不正经的小品文里,因为离经叛道,又有斜逸出的诗意,在审美上有突围的快感。民间的小说不在意这些,故每每有精巧的表达。我们看《海上花列传》,就比同时期许多士大夫的文字要好,传神的地方殊多。
作家之文消解学者之文的迂腐之气,在历史上很多。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都使当时的学人文人黯然了许多。晚清的作家,为文风的变化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以苏曼殊为例,其文不是正宗的士大夫之文,他的日语与梵语的背景,加之译介欧洲诗人的经验,使其文字多了内容,词语便有了奇音。我读他的作品,觉得在语言上已经多了梁启超、康有为、章士钊所没有的真气。黯淡而肃杀之间,置换了士大夫的酸腐之迹。到了鲁迅那里,因为有多语境的渗透,词章也从旧境里走出,汉语的内蕴也随之深广起来。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这原因一是“新民体”衔接的是正宗儒家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六朝以来的溪流在的,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者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我们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乡土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过去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到里,又带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是除旧布新的。
五四以后有趣的文人的语言表达,并不都排斥古文,他们改造了古文的句式,用了另类的笔法。也借助于野史的笔锋,毫无正宗家法的套路,自由行于天地之间。钱玄同文章背后都有文言文的元素,梁实秋作品的书面语意味一看即知。后来的张爱玲的写作,决不放弃明清以来的俗文学与士大夫的传统,曹雪芹的幽魂一直游荡其间。连赵树理这样的人,文章亦土中有味,古文和大众口语的因素被平和地呈现着,老少咸宜,象牙塔内外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些人是没有古今之分的,并不把自己划到笼子里。白话文的健朗的时期,恰是思想无所限制的自由时期,表达的样式其实是思想的样式,这是古人就曾说过的。文白之间,本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由文言到白话的过程,也恰是人的戴镣铐舞蹈到自由奔跑的过程。只是动作的方式不同罢了。
《语丝》周刊的文章,今天看来都很有趣。那些作者自称是“学匪”,坦言所写的不是正经的文章。他们故意把自己矮化,目的不过与士大夫的文章区别开来。这些撰稿人痛恨正人君子,喜欢以戏谑之笔指点江山,说一些不中听的话。鲁迅概括他们这一群人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因为那目的是催促新的思想的产生。看那些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表达的幽默的快慰。因为不想与主流为伍,又带有民间性,有趣的笔法汩汩流来,沁人心肺。他们看重晚明小品,和英国随笔,大概就是意识到不正经文章的重要性。对伪道学与伪思想者,以嬉笑怒骂笔触对之,确有爽然之处。
鲁迅的文章,有六朝的意味,这是前人就指出的。但日语和德语的因素偶能看到。他翻译的作品多,对洋人的笔法颇为敏感,于是偶尔拿来,显得异样。胡适最早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说颇为准确。周作人的文章取之明清小品者多,日语和希腊语的表达式也有所借鉴。他们都是中外互为参照的。至于废名,取禅意而为之,又得周氏兄弟的内蕴,遂有奇音流转,好看得很。而与其关系密切的梁遇春,则幽玄里有惆怅之调起伏,英国小品的味道在汉字里跳来跳去。这是纯粹的美文,思想与诗意的因素恰得好处,很有意思。那时候许多人的文章在努力从文言文的套路里走出,像张申府的随笔,挣扎的痕迹很浓,每每在新的词语里左右突围,虽然显得幼稚,但已经脱离了士大夫意味,我们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新文学在短短的期间,就有了各类流派。模仿鲁迅的,跟随周作人的,暗袭胡适者均有。文章的发展,有师承,有突起的创新,内中的情况复杂。以师承为例,今文的流派时间均短,谈不上大的传统。但追求周氏兄弟的人大多形似而神不似,是一个问题。周氏兄弟的特别的地方,是在思维方式上与人有别。这些都非文章学内部的位移,而是生命哲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打破了过去的诸多樊篱,士大夫与平民、雅士和农夫的界限消失,遂有了开放的文体。这里有诸多神奇的地方未能被人们总结。比如新文学家的知识结构,翻译实践与整理国故的关系等,大约都和白话文的成就有关。后来的文人写作只管写作,翻译只是翻译,学问只问学问,互为呼应的文体不见了。细细分析那时候的文章,杂家的智慧多,杂识也暗含其间。模仿《新青年》诸君的人,笔力里没有那些暗功夫,文章要超过前人,也是难的。刘绪源从一些文章的关联考察审美的起落之间的问题,都让人有不小的联想。他对神似与形似的看法,关于模仿与创新的思路,都是历史经验的产物。我们今天文学里的问题,其实还在相似的范围里。文章的风格,乃智慧与素心使然,还有和上苍与大地的交流,后人在笼子里做思考状,其实是远离本源的。
白话文取得地位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原因是对传统的表达的断然拒绝也窄化了汉语的内蕴。周作人在三十年代的文章,文言的因素加多,喜欢文白相间的句式,其实是对白话文的窄化的担忧。后来才意识到,不仅文言里有赋得的文字,白话文也同样有此弊端。他在《药堂语录》《书房一角》里所写的文章,古风缕缕,大有晚明之气。这种书斋气的文本,可能不是遗老味可简单解之。
自从左翼思想从文坛蔓延开来,文学出现了未有的气象。但因了苏联教条思想的传播,白话文一度遭到泛意识形态话语的袭扰。白话八股渐渐出现,其音流转不已,对后来的文化伤害很大。毛泽东当年提出反对党八股,其实是受到一些延安左翼青年思想的暗示,意识到了汉语思维里的惰性。不过,他没有意识到,在那时候,他自己的文章可以信马由缰,而别人不行。丁玲、王实味、萧军都在抵抗这样的语境,但不幸的很,他们最终也在文坛消失了。
延安之后的文学,提倡大众化的写作,未尝不是一个创举。但许多人对大众语和知识分子语的关系描绘得极为简单。能够自然运用其意的惟有赵树理、孙犁等人。赵树理、孙犁的作品好,是把古文与大众语化开,不留痕迹。在朴素的词语背后,有悠远的东西。其后写革命文学的人,不太讲究词章之意,下笔随意,以意识形态为最高存在。汪曾祺曾经讥笑那些泛道德化的写作,以为殊乏趣味,并非没有道理。他在晚年力赞洪迈、蒲松龄等人,其实是校正白话文日趋浅俗的弊病。他提议人们关注“文体学”与“文章学”,大有深意的。
对白话文内在的问题看得很清的,多是那些有历史感觉的人。钱钟书在“文革”后期写《管锥编》,故意用文言,乃避开世风,有深意的沉潜。丰子恺“文革”间悄悄留下的作品,也没有泯灭禅风。张中行日记里的行文,是文白相间的,绝看不出什么流行的气息。这些人的写作,知道文章的走势该从何处进行,自然就有了别人没有的风景。张中行有一本书叫《文言与白话》,对其间隐含作了细细分析,意思是文言自有文言的好处,白话有白话的特长。不必割舍彼此的优长。新文学之所以被百姓接受,按照张中行的解释,“唐宋以来的白话几乎都限制在俗文学范围之内,三十年代的白话既打破了‘俗’,又打破了‘文学’,活动范围大了”。这个看法,是把握到了命脉。文学家的成就,多是外于文学的因素成就之,从文学到文学来讨论文章之道,只能是循环之路,出奇的妙文是鲜能见到的。我们看张中行的文章,是有苦雨斋的笔意的,他把白话作文言式的使用,古朴和深切缓缓流动着,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沧桑感。这里的哲思的痕迹可能得之于废名的传统,而趣味上是周作人式的。季羡林对其文字的老到与典雅颇为惊奇,叹为“至人”,是心心相映的夫子之道。白话文在张中行那里的力量,确乎是出于时代的。
有人在“文革”的文学里发现,那时候的词汇少得可怜,人们都在一种格式化里思维,文章自然也就败落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是多种语境的对话。章太炎弟子式的古奥,英美留学生的雅致,东洋归国者的深远,几乎把时代的各类风景片断都折射过来了。从五四到“文革”,是白话不断普及的时代,也是白话文的魅力逐渐消失的年代。“文革”语言是一种奴隶的语言,只是单一的维度,很少智性的因素,人们在狂热里变得麻木,几乎没有美质。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文学的各种可能才浮出水面文,有文体意味的作家得以重新出现。但也止于老一代文人,新派作家,在文章学的层面上,对汉语的贡献甚微。中断的传统要恢复起来,其实要有很长的时间。
汉语的演变,民间与象牙塔的互动一直存在。柳永的词,就是市井与书斋人的情境的对话的产物;张岱的文章,是士大夫与浙东风俗的对话的精品。但如果各自分裂,互不相干,那就是单一的路径。大众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一些草根的写作,也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像萧红的文章,乃天籁的吹拂,至今读了也不觉过时。赵树理的短章,是从泥土和古风里来的,乡间有生命的存在被吸纳进来。但是,改变一个时代文风的,有时不是大众的流行语,却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司马迁、苏轼、曹雪芹、鲁迅都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乡间的民谣却是一种陪衬,未得呈浩大的气势。这个现象,左翼的文学注意到了,他们试图改变此状,可惜走到“文革”的路上,连一点新生的意味也没有了。所以,问题不是单一性的行走,而是互为对应,上者而能得地气,下者而会接玄思。老舍就是民间也来得,书斋气也兼得,遂有大家的气象,那是为伧夫俗子所不及的。
近三十年间,许多作家在苦苦寻找精神的表达方式,有成就者真的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孙犁、汪曾祺、黄裳、张中行、木心的写作。他们都有学问,又带性灵,对古人遗产留意颇多。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赏他们,在读书界也非显要人物。大众与主流作家,对这类作者的写作不太关心。看不上他们的人数众多。以木心为例,陈丹青推出其作品系列,被嘲笑的话语很多,以为不值深谈。这里显示了一种差异。人们对汉语失去敏感度,已经久矣。
木心五十五岁去美国,七十九岁归来。期间写了诸多美文,在华语世界颇多反响。老人懂古诗词之道,又读了许多外国作品,形成自己的文章学观念。喜欢以修辞学的方式为文,不免有点为艺术而艺术。诗歌与俳句的内蕴深广,打破古今的界限而为文,真的颇见气象。他觉得汉语可以有悠远的未来,潜力远未被发掘出来。于是苦苦寻觅,骎骎于道中。木心说近代的文人文字,少有古人的光彩。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华,古者诗之大国,诰谟、诏策、奏章、简札、契约、判款、酒令、谜语、医诀、药方,莫不孜孜词藻韵节,婺妇善哭,狱卒能吟,旗亭粉壁,青楼红笺,皆挥抉风云,咳唾珠玉——猗欤伟欤,盛世难再,神州大地已不知诗为何物矣”。这类感叹是对白话文割断传统的叹惋,挽救母语之重任在肩上。他在纸上涂涂抹抹,不过换回汉字的魔力,其写作的变革意味,尚未被清楚看到。
我们在木心的作品里看到经营的精致,词语推敲无数,处处埋伏,步步为营。乃至有点做作。细心一看,则深意在焉。因为流行的词章过于顽固,在修辞上反动一下,读后便有刺目的感觉。批评家拒绝这类写作,与思维惯性有关。所以,探索者在今天的寂寞,实属必然。这个特点在一些边缘人的写作里也可以看到。比如缪哲、刀尔登。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的叛徒,其写作自觉不自觉延续了汪曾祺、木心的精神。我看他们的写作,词语不在当下的逻辑里,思想向四方洞开。缪哲在为刀尔登《中国好人》所写的序言里说:刀兄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的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
在缪哲看来,语言乃文明状态的一种暗示。他认为:霍尔姆斯(Oliver Holms)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不知孰为表,孰为里,是可得而言的。
参之这个看法,我们发现,汪曾祺与木心等人的写作,其大意不过借挽救语言而挽救世风。虽有点堂吉诃德相,但可敬之处是显然的。民国的时候,废名讨论梁遇春的小品文,说其作品是当今的六朝文,自然怀有深意。梁遇春以西洋小品为参照,回到母语的幽暗之所,以生命点燃烛光,就有了现代的意味。民国文人讲六朝与晚明,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再造文明之语,以新精神注入自己的母语。这个情怀,当今的作家,有几人可以为之?
不到百年的时间,今文走了曲曲折折的路。流派众多,经验与教训均在。看我们今天的文章,言说者大多还病着。不能自由的表达与自由的书写,便只能回到“道之文”的传统。语言有传染性,文风亦然。胡适当年就说,我们现在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那原因是心与文脱节,或者说因文生情多于因情生文吧。如今关注白话文文体的人,多是对旧文学有过研究的学人。木心、汪曾祺就深味其间的优长。他们的写作,有意和时代拉开距离,五四的余风暗转,吹拂着贫瘠的文坛。忧文章者,其实忧的是世道。如今的人与文,不太统一。是世道影响了文风呢,还是文风影响了世道,确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但无论在什么样环境,如有几个脱俗的人弹起轻柔的夜曲,以清静的心划分出真伪之界,让人们知道还有无伪的灵光在,总还是好的。今文与古文一样,衰落与发达,实在也有共同的规律在。古今相似,心理攸同,人类未多进化。说历史还在老地方盘旋,也并非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