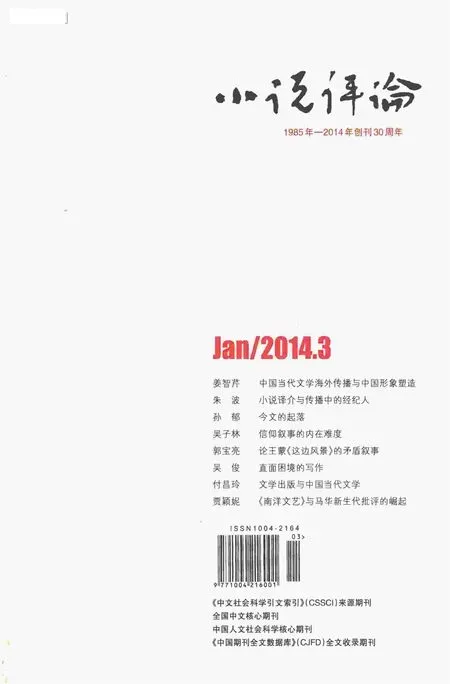王祥夫与现实之关系——以“黍庵笔记”为例
2014-11-14贾梦玮
贾梦玮
《钟山》请人开专栏,于编辑部,于我这个主编,都是大事:关键是请什么人写,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但也不至于要开会研究,进行可行性论证,有些事情的确不是研究出来的。过去请王彬彬、请李洁非等人在《钟山》开专栏,很成功,当初的决定其实都是跟着感觉走。这次请王祥夫还是如此。记得我那天下午在办公室翻报纸,碰巧看到祥夫的文章,那篇文章还没有看完,我就操起电话给祥夫打过去,问他能不能给《钟山》写一年专栏。印象中,电话里的他可能觉得事出突然,有些警惕地问我:“写什么内容?”我未加思索,轻松地说:“随便你写什么。”气氛立马就融洽了。一拍即合。好比两只狗,各自嗅了嗅,便知底细。此事从动议到确定也就花了几分钟。不久,《钟山》上就有了祥夫的专栏“黍庵笔记”,不仅与王彬彬的“栏杆拍遍”也与李洁非多个系列的专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看。
王祥夫与王彬彬、李洁非观察、思考的问题完全不同。他完全从另外的通道进入历史记忆与现实人生,形成自己独特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必须处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家除了处理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外,还得处理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的观察,这两种关系在祥夫这儿是统一的。比如,出世与入世,祥夫当然不是出世的,但绝不是勇猛精进的入世。再比如鲁迅所谓的匕首投枪和他兄弟周作人的所谓平和冲淡,风格不同,祥夫偏向后者。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祥夫不“穷”也不“达”,因此“独善”与“兼济”在祥夫身上兼而有之。
黍庵笔记,顾名思义,多数与植物有关。他的这个专栏,属于通常所说的“小品”与“笔记”,用来写植物真是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自己说:“我喜欢植物,喜欢植物的气息。”还因为喜欢“一黍一世界”这句话,祥夫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黍庵”。黍庵主人喜欢植物一定有他的道理。动物有其食物链,需要靠植物和其他动物为食物来让自己存活下来,因为要寻找食物,所以是“动”的;因为有“牺牲”、有争抢;因此必然有厮杀和血雨腥风。我想,祥夫肯定不喜欢这些。而绝大多数植物不需要以他者为食物,有土地、有阳光雨露,植物就可以进行光和作用,自我生长,开花,结果。菩提果自成。而且,植物就在那里,没有追逐,静。植物又是“变化”的。大多数动物,不论老幼,五官四肢等各种器官不增不减,仅仅是体积大小的不同,小狮子、小老虎乃至幼儿,一出母胎其身体各器官、部件就已齐具,它们的成长只有大小之别没有变化之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蜕化、退化。而植物从小到大,各种器官一直在发生不同的增减变化,例如幼小时期只有根、茎、叶,成年之后长出了花朵,花朵凋谢后再结出果实种子,种子可以再生出无数的新的植物。植物的生长是不断的惊喜,是涅磐。
“黍庵笔记”涉及许多种植物,名目繁多。文章涉及的其他事物也是“植物性”的,可以自生,可以自喜,无关乎军国大事,甚至避开精神与思想。祥夫从他的亲身经历,所接触的人,读的书,看到的、或者自己画的画,来说这些植物,而且是就植物论植物,不拿植物说理,不在植物身上过多地寄托情感,不让植物承担额外的任务。他说:“就饮食而言,我们的现世是既不安稳也不静好,人事罔论,连市上的瓜果都暗藏种种杀机。”但也说到此为止,不要说人事,就是食物究竟如何暗藏杀机,甚至食品安全,都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他根本就不愿意去说这些。在祥夫这里,植物真正成了它自己。祥夫是直见性命,植物本体。在“黍庵笔记”里,祥夫的“独善”表现在他确实很喜欢、享受这些植物,哪怕是在很多人看来于人于己都没有很明确的功用;祥夫的“兼济”表现在不厌其烦地将这些在很多人认为是琐屑之物的东西娓娓道来:为了别人,至少我读来是兴味盎然,心境清凉;也为了他自己,不是津津乐道,虽无郁积在胸,竟也是不吐不快。
“黍庵笔记”的植物本位似乎不针对什么,但客观上有其针对性,因为我们现代人更多地是动物性的。动物世界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追逐金钱、官位,我们总是在“动”,“静”不下来,忘了“静”的可能性和妙处,只顾了“动”的向外,忽视了“静”的向内。高烧不退。人处在食物链的顶端,既吃植物也吃动物。消化不良。高度物质化的生活追求,环境破坏因此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受摧残的不仅是植物,还有包括人在内的动物。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面对无边的荒漠、发臭的河水、被砍伐得像瘌痢头的山岭,还有无家可归的动物、百花凋零的田园,人类才会认识到:自己“真不是东西”!人,诗意地栖居,如果不能与动植物们和谐相处,哪有“诗意”可言?在丰富健康的动植物面前,人才成为了人,人因此才能自重,自喜。
祥夫的文字也是植物性的,多立少破,祥和。他不借助外力,不扯旗,自说自话,居然也可以开花、结果。那样琐细的食物,在他的笔下,竟也可以思及千古、纵横天下,行当所行,甚而不止于当止,好似一条河流,回看来路,竟也是迂曲而下,并未进入另一河床。读“黍庵笔记”,可以感觉到黍庵和黍庵主人的独具的美感。
黍庵主人说:“人类最根本的东西‘食色本性’便是建立在这些琐碎之上的,多少年来艺术完全忽略了这些,忽略它的真正原因或许是人们在思想和理想的重压之下完全无法真正享用食色本性……”“黍庵笔记”偏爱这些琐屑之物,因为事关感官享受。比如佛手做成的青红丝、豆子做成的豆腐、桂花的热香、佛手置于北魏玻璃器上清供的氛围、木瓜的异香、熏衣草的紫蓝……吃也好嗅也好看也好,这些事关人生本质的感官享受都是祥夫所喜爱的。其实也是大家所喜爱的,因了黍庵主人和黍庵笔记的“提醒”。通常,人们只是“占有”,不是“享受”。
“食”与“色”也都应是享受,而不是占有。孔老夫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男女”与“食”、“色”相对应,是“人之大欲”的两大基石,或者竟是全部。如果“食色”二字是人的本质的全部,百分制计算,各为五十分,“食”在祥夫这儿几乎就是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