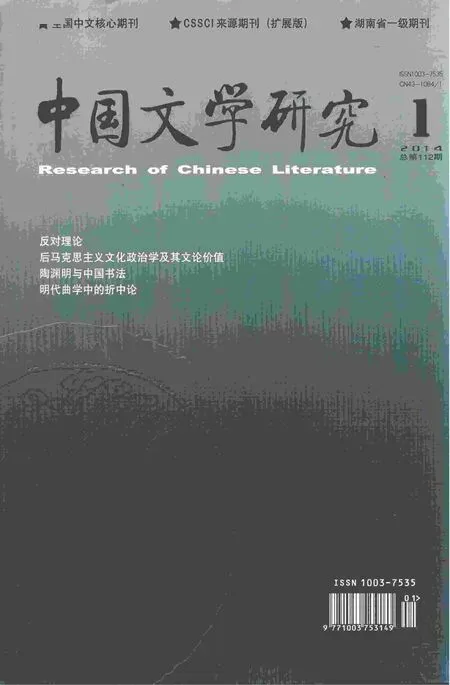实现知识分子心灵自审的雍容话语: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主体话语形态论之三
2014-11-14李良
李 良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13)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这一段话,道出现代散文(小品文)“挣扎和战斗”之一面品质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现代散文因“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而“带一点幽默和雍容”的特点及其这一特点在当时“和旧文章相合”以致一脉而下的“趋势”。
散文“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尤其是供“青年摩挲”,以致“由粗暴而变为风雅”,鲁迅是不大意愿的。鲁迅说话的背景是1930年代初,此时《语丝》已经停刊消逝文坛约三年时间。就是几年之间,时代的巨变和心态的位移,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丝体”散文作家于身份裂变后心灵自审之下话语书写的雍容一面。不可否认,“语丝体”散文的创作实践,的确存有“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挣扎和战斗”的抵抗话语的品质。然而,只要把时间稍微拉长,当以一种后视角度来努力考察,鲁迅这段话恰恰提示了在抵抗话语的“主流”之余,“语丝体”散文主体雍容话语的实际存在以及“非主流”的可贵。
雍容是话语主体特定心理涵蕴制约下的一种表现形态。论及“语丝体”散文创作主体,我们能够看出这一同人群体在192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时空下文化身份的裂变:一方面,五四延续而来的革命者身份使他们激荡着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责任心,另一方面,时代政治风云的高压和五四新文化群体的分道扬镳驱使他们走向内心自我书写一己精神。
不可否认,鲁迅发表于《语丝》上散文的大部分都是杂文体色,充分体现了其作为斗士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颗伟大心灵平静蕴深、宽柔有容的一面,《野草》中大部分文本可作如是观。例如诗性散文《雪》中一开始便写到:“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想到南国的温暖,却以疑问开篇,醒人阅读。接下去这样描写江南雪之“滋润美艳”: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象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这一段江南落雪景象的描写,一派深情笔调。有研究者做出如此阐释:“这是怎样一番山花烂漫、生机盎然的景象啊!在这幅‘冬花雪野’图中,使人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和生活的快乐。鲁迅描绘了这幅图后,又绘声绘色地再现了江南雪天孩子们塑雪罗汉的欢乐情景。他为孩子们稚气天真的创造而欢愉,也为雪罗汉的消融坏掉而惋惜。在这些‘江南的雪’的情景描写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多少向往、景慕的深情!美好的图景,深寓了追求美好理想的心境。”作为一篇即景抒情的文本(1924年12月30日,鲁迅日记有“雨雪……下午霁,夜复雪”的记述),行文中无论是描写还是叙事,都是那样的从容随便、有条不紊。最后,于“朔方的雪花”的鲜明对比之中显露自己强烈的个性色彩:“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淡色叙述“朔方的雪花”,蕴藉冷酷与反抗之外有斗争拒绝之意;浓彩描绘“朔方的雪”,涵容“温暖”与“快乐”之余存雍容敦厚之态。绵中藏力,相反相成。
鲁迅此类描写、叙述中兼有议论的“语丝”文章,比例不为小。就是《野草》第一篇描写梦境的《好的故事》同样呈现如此雍容话语形态。先写自己在辞旧迎新的“鞭爆的繁响”的“昏沉的夜”里,一边看书,一边进入梦境,以至于“灯火渐渐地缩小”和石油把灯罩熏得很昏暗而皆不察。看似漫不经心、随笔带至,然而社会的现实况味已轻轻慢慢地浮现出来,读者亦在如此平淡的叙述中因感觉不到直接显在的浓烈灼热而渐渐不自觉间一同进入作者的“梦境”,得以感受“好的故事”: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鲁迅笔下的江南水乡这样绮丽、美好,这样亲切、动人,其中充满了作者对绍兴家乡风物人情的眷念和热爱。”“在这里,描写的是睡梦中自然景物的变幻,抒发的却是现实中内心感情的追求,寄托了鲁迅更幽远的思绪。”如果能进一步注意到文本当中“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的结构连缀以及“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的重复强调功能,我们更能够感受到文尾梦境醒来追梦而不得的合理性:“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全文从看书写起,笔随梦走,纵意闲书,又仿佛随意涂抹,看似没有任何章法与技巧。但细致的读者能够发现这里以不见技巧的高妙技巧营构了一篇没有故事的“好的故事”,雍容闲散背后有铭心刻骨的技巧与深意。
其实,我们也可以比较鲁迅于《语丝》散文同期创作的其它散文文本,发现雍容话语于其人生同一阶段的显在。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于《语丝》周刊之外领衔创办主持的《莽原》上陆续刊载结下的果实。作为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内里篇章既各自独立,又连贯成体;从传记散文角度看,行文活泼自由,篇篇优美。其话语形式,有一种“纵意而谈,放得开,收得拢的雍容品格”。“关于这种雍容的写作风格,鲁迅在写《朝花夕拾》的当年曾经对一个青年作者说过:要锻炼撒开手,只要抓住辔头,就不怕放野马。过于拘谨,要防止走上‘小摆设’的绝路。这说明鲁迅确实是有意形成一种雍容的写作风格,而他所追求的雍容又是和作为绅士阶层‘小摆设’的雍容泾渭分明的。”“撒开手”是一种能力,“抓住辔头”是要点,“放野马”就是雍容一态。《朝花夕拾》和《野草》两个集子是鲁迅被迫离开北平南下时期,心理相对压抑逼仄而回归个体怀旧与心灵自审之特定心境下的产物,压抑一定程度上得以纾解,逼仄变得相对宽缓,虽不能说活泼温暖,但雍容之态已然。
谈到“语丝体”散文的雍容话语,尤不能不提涉周作人。在现代散文的发展过程中,《语丝》无疑是继《新青年》后散文一体新的重要的生长点。时人梁遇春曾经在《小品文选》之“序”中说:“有了《晨报副刊》,有了《语丝》,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鲁迅先生的杂感”。然而,《语丝》时期周氏兄弟身上体现了丰富的历史复杂性。鲁迅对自我生命的关注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以及反抗绝望的悲剧性;而周作人缘于政治文化和亲情反目挤压下的内心世界则存在着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对自己人格的矛盾纠结,周作人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街头街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两个鬼有时又被周作人自己称为“叛徒”与“隐士”。
在进入《语丝》的前一年(即1923年),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已经表露了五四退潮后的心境:“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裂变中“寻路的人”的身份认同已然出现危机,内心的迷茫驱使周作人日趋归于日常生活。两年之后,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那种于彷徨中寻出路却不得几乎了无痕迹,他对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似乎已经胸有成竹——走向“自己的园地”,从而做出一系列“平和冲淡”的文章。在《泽泻集》“序”中他明确否定了“载道”而突出了“言志”:“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些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渐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现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也还有三五篇。”这“三五篇”大概也就是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谈酒》、《乌篷船》和《苦雨》等。很明显,1920年代中期,周作人几乎完成了由“叛徒”向“隐士”的裂变。
《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小品散文征引材料分量最多的篇章之一。从浙东妇幼视搜采荠菜为“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自然地引出儿歌“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从姊姊的婚嫁引出“颇有风雅的传说”,从古籍《西湖游览志》说“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桃李羞繁华”到古籍《清嘉录》所载古时把荠菜花“置灶陉上”来驱蚂蚁和置于“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的习俗,从儿歌“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到日本《俳句大辞典》有关记述、再到“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紧扣三种野菜,古今中外,周作人以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腕力,把儿歌、古籍、谚语以及国外典籍中有关上述三种野菜的记述自然地融合为一体,徐徐而来,娓娓诱人。一千一百来字的短文,引文却占据了近四分之一,然而却毫无酸腐与炫耀之姿,只有随意从容、文雅大方之态。而《北京的茶食》一文,则从买来的日本书《我的书翰》中的点心说漾开去,比较日本茶食,言及“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吐露自己雅致生活之态度:“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1924年2月的北京时空,阴霾如磐,上述两文既不存有于现实世界的灰心,也了无苦闷生存的绝望,而是于生活中领受平常生活的诗意,一股浅浅的温暖的忧伤自然荡漾,甚至可以说是把痛苦艰难内化为美丽的存在,锻冶和强化了一己生命。生活情趣之摹写中隐现的丝缕幸福感觉映现作家在命运之神面前保持了一种孤独、宏大而庄严的贵族姿势。静水流深,雍容典雅的精神内里,我们暗嗅到周作人话语里面的脉脉馨香。
紧承而下,《喝茶》、《谈酒》、《乌篷船》等文本进一步表现出主体地雍容之态。《乌篷船》以书信体的形式,写给自己,“收信人与写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是作者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大部分人看到此文闲适之风,但我更愿意以雍容形容之。谈家乡的乌篷船,从小处、平凡处构建文学话语,并非表明作家的狭隘与平常。从船的名称、形制到陈设,再到船的功用和坐船的乐趣,一路写来,真实而无拘束。娓娓说道,恰如与“良朋话旧”。《谈酒》,于“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入笔,谈到做酒、饮酒、“我”之于酒,最后论曰:“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醉了,困倦了,或者应当休息一会儿,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说酒的真趣是在此间。昏迷,梦魇,呓语,或是忘却现世忧患之一法门;其实这也是有限的,倒还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里的耽溺之力还要强大。”饮酒,本是琐小、常见而平凡的人间事相,在这里却能够被叙写为具有一种特殊韵味的。语言及语言所荡漾出来的气氛里氤氲一股不急不紧、雍容典雅,读来超凡脱俗而底蕴十足。尤其是《喝茶》一文,真是得文雅大方之道、现从容不迫之势。从徐志摩讲“吃茶”起兴,承认“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比较了绿茶红茶之别,慢条斯理道出自己的“喝茶之意”、“喝茶之道”: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这一段被众人以冲淡名之的文字,成为现代小品文的经典代表。读如此话语,我们好似看到一位元气在心、心清香嗅、端坐如泥塑神的妙人,一派晋陶(渊明)气象。“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周作人确有司空图所言“冲淡”品格,但我们实在不能回避这冲淡之余的自然与沉着、典雅与疏野。“俯拾即是”、“幽人空山”、“绿林野屋”、“落日气清”、“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若其天放”、“如是得之”。“闲适”有其自身极其复杂的话语运作模式及其发展脉络,它需要长期的文化浸润和训练才能达到,“闲适”中必须有“自我”。然而,只要从一己之情感脉络出发,超越具体的人与事,延及对整个人类、甚至宇宙的思考,显示出对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把握能力,那么,文章就会因为浸染了浓厚的文化底色而脱小离凡、趋大就深,渗进自我主观情丝感受的作品也就形成富有张力的艺术空间和超脱的文化气韵,一脉雍容自然笼罩全篇。
很明显,同现雍容,周作人和鲁迅是不同的。因外力的挤逼而退还内心的鲁迅,雍容是纾解宽缓紧张精神的结果;战场退却渐趋“隐士”的周作人,雍容成为品味生活超然世外的习惯。郁达夫曾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他口口声声在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通的说法,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周作人是怀了人间温爱似无意似有意地摹写心里心外,手法之文雅、心智之高迈、气度之雍容,幅长而不令人烦嫌,倒是过目难忘。
还有,郁达夫言及的周作人的“中庸”自评,亦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理解“语丝体”散文的雍容品格。中、中庸以及中和在中国哲学和美学史上是相邻近的概念。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实际上存在着既有本质区别也有一定联系的两种中和之美,即作为普遍艺术和谐观的中和之美(以《乐记》为代表)与作为特定艺术风格论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之属)。可见,雍容确显中和之美。“‘雍容’,本指人的神态大方,从容不迫。《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汉书·薛宣传》:‘宣为人好威仪,进止雍容。’‘雍’本意和谐,《书·无逸》:‘言乃雍’。当指人或文学作品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一致显示出平和的大气度,心胸宽,不急躁,少锋芒。”周氏兄弟为代表的“语丝体”散文,博大深厚的胸怀使现代散文有了宽广和气度,不能说包容万有。但他们笔下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往往于无声的静穆中,启示和澄明了风云时代里面苦恼、冲突或绝望的心灵,显示出博大、包容、平等与仁慈。在抵抗色彩之余,也能看到现代知识分子于精神独立、健全人格以及探求真理等方面的积极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成为语丝同人实现自我精神救赎通途的可能。同时“语丝体”散文也正因上述雍容话语之姿,成为富于个性的文体:叙述的从容、美妙的意境、诗化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这是一种“平实”中带有“诗意”,“雍容”中含了“智慧”,“温和”中蓄着“炽热”的文体。“如果我是一个几个世纪以后的文学史家,当我审视整个二十世纪文坛上光怪离奇的流派更迭时,我想,无论如何,我总是要感到困惑不已的。差不多整整一百年,文艺的殿堂失去了雍容和壮严,变得喧嚣而潦乱。最虔诚的圣徒和最玩世不恭的浪子都在这里发出的声音居然同样的刺耳。”由此看来,相对偏激的整体时代话语之中更见“语丝体”散文雍容话语的可贵魅力。换言之,正是雍容话语,使“语丝体”散文给读者留下坚硬阅读之余的另一种感受:仿佛春天里与作者一起轻松愉快地散步,也似于严寒的北方棉衣在身、温暖在心。
〔注释〕
①此三篇文章分别载于《语丝》第7、85、107期。
②详细论述可参见张国庆《论中和之美》(《文艺研究》1988年3期,18-28页)、《中和之美的几种常见表现形式》(《文艺研究》1992年4期,23-29页)等成果。
〔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A〕.鲁迅全集(第 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李良.“后五四”时期革命认同下的抵抗话语〔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3〕鲁迅.雪〔J〕.语丝,1925.1.18(11).
〔4〕孙玉石.《野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鲁迅.好的故事〔J〕.语丝,1925.1.28(13).
〔6〕温儒敏.雍容·幽默·简单味——《朝花夕拾》风格论〔J〕.鲁迅研究月刊,1989(12).
〔7〕启明.两个鬼〔J〕.语丝,1926.8.9(91).
〔8〕钱理群.周作人散文精编〔C〕.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9〕杜黎均.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M〕.北京出版社,1988.
〔10〕孙联奎.诗品臆说〔C〕.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齐鲁书社,1982.
〔11〕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选集导言〔A〕.郁达夫全集(第11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2〕方锡球.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J〕.求是学刊,2000(5).
〔13〕李良.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主体话语形态〔J〕.学海,2010(6).
〔14〕孙绍振.病态的牺牲——惨重的二十世纪文学〔J〕.文艺争鸣,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