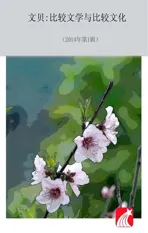“原始文本”抑或“多元文本”?——《伊利亚特》新校本争论回溯
2014-11-14吕健
吕 健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
在古风诗歌的研究当 中,“作者”(author)、“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诗歌权威性”(poetic authority)问题一直是研究者所乐于追逐的。美国著名古典学家格里高利·纳什(Gregory Nagy)在论及当下古典文学批评研究(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时就曾明确指出:“要理解早期希腊对于诗人和诗歌的诸种看法,那么具体的关注点是:‘经典之形成’(formation of canons)所正遭受的不间断的危机……另一个广泛关注的领域是‘文类的发展’(development of genres)……还有就是‘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分化(differentiation)与个体化(individualisation)……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即是希腊人之于‘模仿’或‘再现’(mimēsis
)的诸种观念,以及诗歌如何教授的问题,特别是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公元前5世纪。”我们已经知晓,来自原始印欧语heugeie(现在时形式),heugs(现在时或过去时形式)的拉丁文动词augeō
拥有诸多印欧语系内部的同源词,其中就有希腊文auxō
,aexō
和auxanō
,都分享了原始印欧语祖先的“生发、加强”之义,但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证据来支持上述三个动词与希腊文中惯常的指称“作者”一词authentēs
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性。其实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古希腊文自身的词源与措辞(lexis
,diction)特色以及由此凸显出来的带有历史语境烙印的文化涵泳中来理解authentēs
一词。目前古典学界对该词的词源解释其实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基本可以确认的是,authentēs
是autoentēs
一词的缩合形式,该词由两部分组成:auto
+hentēs
,前一部分很明显来自反身代词autos
,意指通过自身完成或达到某一行为;后者严格来说在存世文献中并不存在,由于是根据字形构拟而得的,学者们对其的含义莫衷一是。法国著名古典语文学家皮埃尔·谢丹耐(Pierre Chantraine)认为该词的后半部分可能与动词hauō
(影响、完成、达到……)有亲缘关系或相似特性,所以autoentēs
一词的基本含义即是“通过自身以施行、完成或达到某一行为”,由此引申出“作者”这一义项;但谢丹耐同时还指出存在着另一种构词的可能性,即auto
+thentēs
,这一构词的后半部分来自动词theinō
(攻击、伤害……),由此引申出autoentēs
一词的另一基本义项即“谋杀者”、“自杀者”等。所以在现存文献中,autoentēs
一词拥有诸多的义项,比如“凶杀的原因”、“杀人者”、“自杀”等,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u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演说家安提丰(Antiphon)等人的作品,以及若干零星的铭文与纸草;“作者”、“事物的原因”、“有权威的大师”、“实践者”等,出现在欧里庇得斯、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人的作品中,以及存世的一些铭文与纸草,但学者们注意到这几个义项似乎集中出现在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的文献中。从以上义项的罗列可以知晓,古典文献中autoentēs
一词恰好凸显了古希腊文化之于“作者”观念的某种文化投射,正如希腊文“诗歌”(poiēma
/poiēsis
)、“诗人”(poiētēs
)、“诗艺”(poiētikos
)等语汇皆来自动词poieō
(制作、生产、施行、创造……)一样,autoentēs
所传达的也正是一种行为主体的实践性和动作的完成性,这与上文强调的拉丁文auctor
所包蕴的“生发、来源、权威”等义并无抵牾,反而颇有亲缘关系,只是所强调的语义层面不同而已。两者最为契合并且最能引导人们充分认知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中“作者”与“作者身份”观念的正是下文会着重讨论的“权威性”观念,而这也绝好地体现于autoentēs
一词的不同词性形态的语义层面上,如动词形式authenteō
(对……拥有权威性;赋予……以权威性);形容词与副词形式authentikos
,authentkōs
(可保证的、权威性的、最主要的)以及抽象名词形式authentia
(权威性)。但正如谢丹耐等学者早就提醒我们的,authentēs
一词的集中出现以及其语义的广泛弥散其实是比较晚的语言现象,这就表明对authentēs
的探究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同质性的与历时态的(diachronic)参照,但终究无法正面解释古风诗歌中的“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正如美国著名古典学家安德鲁·福德(Andrew Ford)的研究所揭示的:poiēsis
,poiēma
,poiētēs
等词开始成为“诗歌”与“诗人”等的专属指称其实要等到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形成规约,所以若要准确索解古风诗歌中的“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之于authentēs
与poiētēs
的问题意识势必须要转化为对古风诗歌传统“措辞”(lexis
,diction)的充分语境化的体认,由此我们的目光便被引领至对aoidos
(歌者)与rhapsōidos
(诵诗人)的考察上,以及这背后所潜藏着的最为原初的古典学命题——“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二
1998年,牛津大学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马丁·里奇菲尔特·韦斯特(Martin Litchfield West)受邀为古典学界享誉已久的三大古典文献校勘本文库之一——“托埃布纳希腊拉丁文献丛刊”(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所编辑校勘的新版《伊利亚特》前十二卷出版,两年后余下的十二卷也顺利问世,由此古典学界拥有了最新最权威的《伊利亚特》精校本。旋即作者又于2001年推出了编校《伊利亚特》新校勘本的副产品《〈伊利亚特〉的文本与传承研究》,也即对于《伊利亚特》文本从“前亚历山大里亚时期”(PreAlexandrian)一直延续至中世纪的演化与传承历史的古典语文学研究,当然更为主要的也是为新版《伊利亚特》中的文句读法(readings)提供辩护与支撑,主要包括原新校本正文前用拉丁文写就的长篇导言(praefatio
)的扩充翻译版,以及以注疏形式呈现的具体文句择取上的考量,呼应于新校本“校勘记”(apparatus
)中所作出的择取并作了进一步详细深入的阐释。而十年之后的2011年,韦斯特又出版了专著《〈伊利亚特〉的形成:专论与分析性注疏》,体例上显然承袭十年前的作品,但所论却更为澹详周正,总结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篇重要论文的研究成果,全面反映了作者在《伊利亚特》文本演化与传承史上的权威意见,事实上也是对整部《荷马史诗》乃至作为整体的希腊早期六音步长短短格史诗(dactylic hexameter poetry)之形成演化历史与若干原则的整体性观照,更是对发育于19世纪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古典学)语境中的核心问题——“荷马问题”所作的一次历史性的推进。然而,在古典学迅疾的现代转型中,韦斯特的工作并非没有批评,相隔十年的两部著作的催产士正是这十年间围绕《伊利亚特》新校本的诸多争论,折射出不同学术立场与方法论倾向在更为广阔的古风诗歌研究领域各自攻城略地的学术历险。其中最为猛烈的批评来自“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坚定捍卫者,哈佛大学古典学系与比较文学系的纳什教授。在著名的电子期刊《布瑞·冒尔古典学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上,纳什就这一新校本发表了近35页的长篇书评。在纳什看来,韦斯特此本的最大问题便是完全忽视了自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及其弟子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1912—1991)以来逐渐完善丰沛的口头诗学诸种理论与实践对于早期希腊史诗文本演化、传承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在《伊利亚特》的新校本导言中,韦斯特压根没有援引帕里与洛德的作品,⑲甚至连纳什在这一领域积累颇深的一系列著作也皆付阙如。自1979年《最卓越的阿凯亚人:古风希腊诗歌中的诸种英雄观念》(The
Best
of
Achaeans
:Concepts
of
the
Hero
in
Archaic
Greek Poetry
)这一成名作出版以来,纳什一直致力于构建一种针对作为整体的古风诗歌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的基本构成便是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遗产和拥有考古学与古史研究支持的“泛希腊”(Panhellenism)解释模式;而在这一框架下作出的对古风诗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认知反过来也促进了传统“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诸多学理面相的更新与理论本身的整体性推进。在纳什的解释框架中,古风诗歌是具有内在整一性(unity)、独特性(uniqueness)、系统性(systematicness)与艺术精巧性(artistry)的传统(tradition)的产物,而传统的形成则是一种由“编创”(composition)、“表演”(performance)和“流布”(diffusion)等口头诗学的动力学要素相互纠葛、嵌套起来的动态的演化历程(process),而非某一时间断面上突然而降的“事件”(event),编创、表演与流布所呈现的是“共时态”(synchronic)和“历时态”(diachronic)交互融合的动态机制,所以口头诗学的基本观念如“程式”(formula)、“步格”(meter)、“主题”(theme)等也必须从共时态与历时态交织的视角予以审视,并且时刻受制于形成中的诗歌传统——不论是地域性的诗歌传统[比如特奥格尼斯(Theognis)的挽歌对句(elegy)所体现的麦加拉诗歌传统],还是通过流布与“扩散”(proliferation)进而获得“泛希腊”地位的诗歌传统[比如以荷马、赫西奥德、荷马颂诗(homeric hymns)、史诗诗系(epic cycle)为主体的早期史诗传统以及阿基洛科斯(Achillocus)的讽刺诗(iambus)和梭伦(Solon)的挽歌对句等]。而对诗歌传统的全方位考量则意在回答口头诗学因之一直饱受争议的一种诘难:高度程式化的编创方式如何能够形成像荷马史诗这样具备高度整一性、系统性与艺术精巧性的传世佳作?并进一步索解古风诗歌所蕴含的以不同方式隐藏或呈现自身的诸种古风观念(比如“英雄”观念)以及隐遁于其后的文化基壤——“神话”(myth)和“仪式”(ritual)。所以在对古风诗歌的存在与展示的方式及其背后涵泳着的神话和仪式维度有了整体性的认知与把捉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纳什的一系列作品便试图为古典学创立之始的原初问题——“荷马问题”——的解答提供某种索解路径和阐释模态,纳什所关心的是从口头诗学的原则出发,我们应该如何解释现存的“荷马史诗”所具有的高度整一性、系统性与艺术精巧性;“荷马诗歌”(Homeric Poetry)的演进模式(evolution model)与 “荷 马 文 本”(Homeric Texts)的 传 承(transmission)是如何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纠葛的历史语境中得以可能的?换句话说,从学者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所有荷马史诗的中世纪手稿[包括手稿行间与页边的“古注”(scholia
)]、传世文献中 的引 语(quotation)以及更为早期的纸草残篇,能否以及如何复原出一个“荷马史诗”的定本;再反向回溯,在正式形成文本传统[或者说史诗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之前,作为口头诗歌的荷马史诗如何获取阶段性的演化经历,并且这种口传和表演语境中的演化是如何在共时态与历时态组成的时间坐标中与诗歌的文本化相互纠葛、依存,直至达成某种妥协?毫无疑问,纳什试图建立某种荷马史诗演化、传承历史的解释框架的努力势必会牵涉到这一学术历险的终端操作,即以何种原则与方法编订一部荷马史诗的权威校勘本。韦斯特等传统的古典语文学家之于“荷马问题”的总体学术取向和解释策略与“口头派”的忠实传人纳什等学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所以《伊利亚特》新校本的出现策动纳什就这一终端操作发表如此篇幅的书评,也就变得不难理解。在书评的开首,纳什归纳了韦斯特之于《伊利亚特》文本演化与传承的总体性看法:
韦斯特认为荷马并不存在。但否定了荷马的存在并非意味着他认为“荷马”这位诗人是一种“神话式的建构”(mythical construct)——正如我所主张的那样。对韦斯特而言,只有“荷马”这个名字是虚构的,在他的校勘本前言(praefatio
)中说得十分明白:即使我们从未知晓他的名字,写作《伊利亚特》的这位诗人也绝不会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real historical figure);这位诗人是“原初诗人”(primus
poeta
),他是“最为卓越的”(maximus
)……《伊利亚特》是在这位诗人的有生之年被写定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诗人也拥有对这部卓越的诗篇进行修改的机会:韦斯特认为诗篇中很多的“篡文”(interpolations)就是由诗人本人一次次引入已经写定的文本中的。待到诗人去世之后,遗留下来的这些《伊利亚特》的卷轴(scrolls)便被“诵诗人”(rhapsōidos
)所占有,受其澹妄之思所侵,诵诗人在不同的“表演”(performance)场合中不断篡改着文本,非常类似于后来一个时期的某种“表演者”(actor),这些表演者持续篡改着由欧里庇得斯遗存下来的史诗文本(rhapsodorum
...qui
Iliadem
nihilo
magis
sacrosanctam habebant
quam
histriones
Euripidem
)。越来越多篡文被引入文本的机率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这位大师级的诗人所作的诗篇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雅典的泛雅典娜大节(Panathenaia)上崭露头角,但一开始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段得以被表演。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僭主希帕尔库斯(Hipparchus of Athens)统治时期,史诗文本才正式被采录为泛雅典娜竞技吟诵表演内容之一,同时也被切分为二十四个吟诵部分(rhapsodies);换言之,这一切分形成的诗歌系统与那位“原初诗人”自身毫无干系。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诗篇传承的这个“雅典阶段”(Athenian phrase)不断得到巩固,期间史诗表演的“教授者”(teachers)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贯穿荷马史诗的这一传承时期,原初的文本由于“雅典式的篡文累积”(Athenian accretions)而损害很大……所以作为文本编校者,韦斯特试图重构(reconstruct)公元前7世纪这位大师级诗人的伊奥尼亚方言的文本(Ionic text),清除附着其上的“雅典式的篡文累积”、由于诵诗人的表演而产生的各种文本变体(variations)以及后世文本编辑过程中形成的篡 文(editorial interpolations)。在纳什看来,上述韦斯特“原初诗人”、“原初文本”的构想无疑是不尊重古风时期荷马史诗口传表演这一本质特征的结果,所以以此为本的具体文本编校策略也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纳什在一系列著述中反复强调,从历时态角度看,“荷马诗歌”与“荷马文本”是两种前后相继的荷马史诗的存在形态;而从共时态角度看,在荷马史诗演化与传承历险的某些历史阶段,两者又互为表里,是荷马史诗表演传统的不同面相之表征。所以在如此漫长的一个诗歌演化与文本传承的历史中,荷马史诗的“文本化”就绝对不能以类似某种一次性的历史“事件”(event)来衡量与裁定;而是必然地呈现为一种活态的、具备自身完整的动力学机制的“进程”(process),纳什运用了一个隐喻,将这种“进程”描绘为一种“结晶化”(crystallization)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史诗的编创、表演、“编创中的表演”(compositioninperformance)等要素所培育并表征的荷马诗歌与荷马文本的发育史——在纳什看来——体现为一种荷马诗歌与文本的“多样化”(multiformity)倾向,换言之,诗歌演化与文本传承的多样化才是荷马史诗在“流变性”(fluidity)至“稳定性”(rigidity)逐渐过渡的长时段中的真实存在样态,这无疑本质上来源于口头史诗长时段、即时性(improvisational)、区域化(regional)的表演传统,以及此种表演传统最终所要归属的“泛希腊”的存在样态。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在具体的荷马史诗文本编校策略(editorial policy)方面,纳什主张必须要追求一种“最终的‘多重文本’(multitext)意义上的‘版本’(edition),它不仅可以反映诸多‘异读’(variant readings),只要有可能,也可以将这些异读与文本传承历史中的各个阶段相联系”。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纳什就以将这一“多重文本”的观念应用于对麦加拉的挽歌对句诗人特奥格尼斯的文本传承之研究上。在纳什所构建的荷马问题阐释框架中,荷马史诗真正意义上的“文本化”肇始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雅典,其历史语境便是由实际掌控雅典城邦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家族(Peisistratidai
)所奠定并完善的泛雅典娜大节,特别是节庆中颇受欢迎的诵诗人竞技吟诵传统。借由书写技术的完善,在这一时期,潜在的文本以“誊录本”(transcripts)的形式出场。纳什明确指出,在口头诗学所倡导的文本“多样化”原则下,一份誊录本并非是一次诗歌表演的“等效物”(equivalent),而仅仅是达成表演的手段,或者说是表演得以顺利实现的某种帮助,所以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后期这一演化阶段,誊录本无疑是以复数的形态出现,并且深深介入当时雅典城邦僭主统治的历史话语构建中,正如希罗多德(Herodotus,c.484—425BC)在《历史》(Historia
)记叙的庇西斯特拉图家族对“神谕诗”(oracular poetry)的掌控(kektēmai
)一样,僭主们对诵诗人的荷马史诗吟诵表演方式的设定,以及对诗歌誊录本的掌控—— 即所谓的“庇西斯特拉图修订本”(Peisistratean Recension)——不可避免地服务于僭主统治的意识形态构建,客观上也正是对“多样化”的誊录本传统的一次聚合,使得诗歌演化进程的“流变性”渐弱而“稳定性”渐强,在这样一个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稳定状态中,文本“结晶化”的趋势明显,同时正是出于僭主意识形态构建的需要,诗歌文本化的过程必然需要召唤某种“通行本”(koinē
或复数koinai
/Vulgate)的出场,纳什用了一个精巧的隐喻——“泛雅典娜瓶颈”(Panathenaic bottleneck)——来描绘活态的口头传统流变性渐弱而稳定性渐强的历程,以及史诗文本的样态从“去中心化的多样性”(decentralized multipicity)逐步演化为“中心化的单一体”(centralized unity)这一趋势,颇为遗憾的是,正是由于这一“泛雅典娜瓶颈”的存在,源流于古风早期的史诗表演传统的丰富性被大大弱化了,“只有《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在公元前6世纪顺利通过了这一‘泛雅典娜瓶颈’;另外一些古风希腊史诗传统——最为著名的当属由《克普瑞亚》(Cypria
)、《阿伊特奥匹斯》(Aithiopis
)、《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
)与《伊利昂的陷落》(Iliou
Persis
)等组成的‘史诗诗系’(Cyclic poetry/Epic Cycle)——则已不存”。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已经存在着一种作为“通行本”的稳固的“泛雅典娜文本”(Panathenaic Text)或“泛雅典娜原型文本”(Panathenaic archetype),但纳什坚持认为这一时期荷马史诗的文本形态仍旧是以“多样化”为表征的“誊录本”系统,以及逐渐形成的“通行本”观念,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原型书面文本”(a single archetypal written text)。但在随后的一个文本演化阶段,即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公元前2世纪中期,肇始于雅典将军法雷翁的德梅特瑞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um,350BC—?)与公元前317年至307年间对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以上的泛雅典娜大节诵诗人竞技吟诵这一史诗表演形态的改革,传统的“诵诗人”逐渐被新式的“表演者”(homēristai
)所取代,由此一种作为史诗表演的先决条件——或者说“脚本”(scripts)——的书写文本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史诗文本演化的主要形态。我们有理由推测,原先的“通行本”演化为如今的“脚本”,这一转化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就已初露端倪,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诗文本的“多样化”特征在这一阶段被消弭殆尽,事实正好相反,虽然雅典的“通行本”最终演化成与整个城邦生活休戚相关,并且某种程度上随着古典时期“雅典霸权”的确立而辐射至整个希腊世界的所谓“雅典的城邦版本”(Athenian City Edition),但史诗表演的传统并未衰弱,文本的诸种“变体”(variations)仍处在演化与流布的进程中,并且在整个希腊世界,荷马史诗也拥有诸多相切己又相异的“城邦版本”,如开俄斯岛(Chios)的版本、阿尔戈斯(Argos)的版本、马萨利亚(Massalia)的版本等,所以大体而言,这一时期史诗文本的“多样化”存在样态并未改变:1.一种新的由城邦控制的表演传统与“脚本”,由史诗的“表演者”所配合,在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307年间的某个节点在雅典由德梅特瑞乌斯所创立。
2.然后,随着公元前307年德梅特瑞乌斯统治的垮台,雅典城邦失去了——或至少放松了——对荷马史诗表演传统的控制,由此导致越来越多的文本“变体”得以在雅典及雅典以外扩散。这些变体反映在所谓的“离心的荷马史诗纸草版”(eccentric Homeric papyri)中。这一表演传统的不稳定时期持续到公元前150年左右。从公元前307年至公元前150年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期望获取一种荷马史诗表演者的“通用指称”(generic designation),以此来取代过往的专名“诵诗人”(rhapsōidoi
)。3.这次文本变体的爆发逐渐湮灭——大致在公元前150年——之后,以“表演者”为主体的荷马史诗表演传统得到重申,并与一种更为“经典化”(canonical)的文本传统紧密契合。这一文本传统是由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220—143BC)所重新构建的。
由此,从公元前150年开始,荷马史诗的文本传承步入最为稳定的时期,源自表演传统的“多样化”的文本形态逐步收紧,进入一个纳什称为“定本”(scripture)的时代,从这一文本传承的时间节点开始,史诗的文本形态与活态的表演传统之间的关联渐渐被稀释,“结晶化”进程最后的表征日趋显明,诸多史诗表演的“脚本”等待着被整合进具备一定整一性的“定本”中,在纳什看来,这一变化首要地应归功于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殿军、于公元前180年之后的某一时间接替另一位伟大的学者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ces of Byzantium,c.257BC—c.185—180BC)担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阿里斯塔尔库斯,而韦斯特与纳什就具体的文本编校策略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如何看待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上。
用不着特别指出,阿里斯塔尔库斯对史诗文本传承“多样性”的“定本化”重构并非无源之水,纳什已经明确指出,从“脚本”到“定本”的旅程其实从法雷翁的德梅特瑞乌斯就已开始,德梅特瑞乌斯奠定了雅典城邦的“脚本”系统并进一步促成更为完备的“通行本”即“雅典的城邦版本”的问世,这自不待言,但易被忽视的是,他也是召唤“定本”出场的先导人物,在创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伟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且很可能为图书馆获取雅典城邦成熟的“通行本”提供保障;继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诸多学者的努力——特别是首任馆长芝诺多托斯(Zenodotus)与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为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文献显示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就亲自编订过荷马史诗的定本(ekdosis
/diorthōsis
),阿里斯塔尔库斯还就此本专门撰写了“注疏”(hupomnēmata
)。阿里斯塔尔库斯所继承的学术遗产无疑是十分丰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要处理的问题较之于前辈而言更加简单,恰恰相反,他所面临的文本状态颇为繁复,源自表演传统的文本传承的“多样性”是其需要打理的根本问题。洛德早就指出,文本“多样性”的基本表征乃是诸多“文本变体”(textual variations)的同时流传,以及由此而来的诸种“变体”间 文 句 “异 读”(varia
lectio
/variant readings)现象的弥漫。而阿里斯塔尔库斯面对的文本世界即是如此弥漫:不仅存有雅典城邦的“通行本”和其他各个城邦自己传承的“城邦版本”,还有旁溢出去的所谓“离心的荷马史诗纸草”,当然还有前辈学者们广为搜集、编订的其他纸草文献与校本等,由此,阿里斯塔尔库斯的编校工作便是要与繁复的“异读”作整体性的抗争,毫无疑问,首要工作便是收集尽可能多的抄本,而后再从中选择一个最为稳妥的版本——纳什认为无疑应是雅典的“通行本”——作为“底 本”(texte
de
base
/the base text),在此基础上,阿里斯塔尔库斯分别从“垂直”(vertical)与“水平”(horizontal)这两个文本“异读”的主要维度入手,重建基于文本“多样性”的“多重文本”:1.垂直变体:阿里斯塔尔库斯在其底本中保留了“通行本”中他已决定“撤除”(athetēsis
/athetesis)的若干异读诗行,但在其“注疏”中保留了判定这些诗行系篡伪的理由,以备后续讨论(文本中恰当的边注将会提示这些讨论);只有当针对某一既定诗行的抄本证据非常薄弱时,他才将之“删除”(delete/omit),而非在其底本中标记为“撤除”,而后很可能在其注疏中给出删除的理由。2.水平变体:阿里斯塔尔库斯在底本中保留了通行本的“读法”(wording),同时将针对相应的“非通行本”(nonvulgate)中的读法对错与否的意见留存于其注疏中,以备讨论。这些非通行本中的相应读法来自那些“更为讲究的”抄本(khariesterai
);只有当针对通行本某一既定读法的抄本证据不可靠时——即是说,同时出现一个以上的通行本读法,但没有一个读法是明确比其他读法来得可靠的——阿里斯塔尔库斯则会在底本上作出他的选择,而后在其注疏中讲明如此选择的理由。通过以上垂直与水平两个异读维度的辨析,阿里斯塔尔库斯极有可能已经生产了荷马史诗的一部权威汇校本,当然颇为可惜的是该本没有存留下来;与汇校本并行的“注疏”也踪迹杳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主宰了希腊化之后荷马史诗的文本传承,现存于威尼斯的荷马史诗最为重要的中世纪手稿Venetus A(codex Marcianus 454)中存有了大量的“古注”,学者们发现其中保留了许多阿里斯塔尔库斯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坚定地认为该手稿最为迫近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很有可能是其直接后裔。
而在纳什看来,阿里斯塔尔库斯卓越的工作虽然其原始意愿是重构某种“原初文本”,但其实际导向的却是一种“多重文本”,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当时存世的通行本、抄本、纸草等文本形态的广泛搜罗并全部资以精审的比堪利用:
1.阿里斯塔尔库斯所知晓的古代抄本证据远超于我们所掌握的。
2.基于他所搜集的全部抄本证据,阿里斯塔尔库斯不能也不会生产一种单独的荷马史诗的“整一本”(unified text)。他在其“注疏”中为文本“异读”——包括“垂直”维度与“水平”维度——的择取理由预留了空间。
3.基于现今我们所能得到全部抄本证据——无疑这是无法与阿里斯塔尔库斯所占有的材料相提并论的——包括韦斯特在内的那些编校者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他们无法生产一种单独的荷马史诗整一本。他们那些所谓的“整一本”(Urtext
/unitext)其“整一性”(unity)必须借由“重构”(reconstructions)与“推测”(conjectures)的方法才能达成,而这些重构与推测只是基于对“年代学”(chronology)、“方言”(dialect)、“历史出处”(historical provenance)等因素的考量。用不着特别强调,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之所以为纳什等学者所激赏,正是由于其对荷马史诗文本传承样态本身的充分尊重,他所提炼出的版本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版本,以文本汇校与独立注疏的形式再现了荷马史诗文本传承的“多样化”这一根本特性,而这一特性无疑源自长时段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纠葛的活态口头史诗表演传统,所以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最终导向的是一种“多重文本”而非韦斯特意义上的“整一本”:“‘多重文本’的观念必须能够解释体现为文本异读(textual variants)的荷马史诗‘多样化’这一特性……荷马史诗的‘多重文本’这一版本的重构理论上就是为了最为明晰地展示所有存留下来的文本异读,包括垂直维度与水平维度。它必须拥有一个已经排除诸多颇具任意性判断的底本,这些任意性判断包括比如根据编校者个人之于文本异读孰优孰劣的观感(或判定标准)而对文本异读作出择取。换言之,这一底本的构筑便是为了能够显示全部存在异读现象的文本缝隙,进而所有的文本异读都能被安插进这些文本缝隙中——但没有任何一种异读具有优先权。”所以在纳什看来,韦斯特等学者试图依靠推想中的“原始文本”重构荷马史诗的“整一本”的努力无疑是徒劳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古风早期就以被写定的“原始文本”,荷马史诗文本之历史性的本真样态即是经由口头表演传统逐步“结晶化”而成的“多重文本”。大体而言,纳什等学者是顺着文本演进与传承的历史进程,做文本编订的“加法”;而韦斯特等学者则反其道而行,试图通过整合现存的各式材料,采用“剥洋葱”的手法去伪存真,做文本编订的“减法”,最终收获古风早期由那位大师级的“诗人”亲自写就的荷马史诗“原初文本”。
三
虽然纳什与韦斯特探求“荷马问题”的学术路径本质上而言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部新校本表示足够的尊重,书评的篇幅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继纳什的长篇评论刊发后,法国学者那赫德利(JeanFabrice Nardelli)也在《布瑞·冒尔古典学评论》上针对该新校本发表了长篇书评,相较而言,后者的评论涉及了更多的文本编校方面的细节,比如文本传承史的梳理、“校勘记”(apparatus
)的组织、“异读”的择取标准、“古证”(testimonia
)的罗列利用、方言问题、正字问题(orthography)等。虽然那赫德利推崇韦斯特此本超越了阿伦(T.W.Allen)的老版OCT与泰勒(H.Van Thiel)的版本,体现了某种新的校勘标准,但总体而言他并不完全认同韦斯特之于荷马史诗文本传承历史的意见和重构“原始文本”的努力,在诸如文本演进与传承的“雅典阶段”、古风时期荷马史诗的现实影响力、卷数区分问题(BookDivision)、希帕尔库斯统治时期之于文本演化的意义、“文本传承层累说”(text accretion)、对“前亚历山大里亚时期”(preAlexandrian age)纸草文献和中世纪抄本传统的处理等问题上,那赫德利均有不同意见,并且实际上很多地方与纳什的看法暗合。所以虽然韦斯特的工作是如此得艰苦卓绝,但评论者仍是认为他处理材料和异读择取的标准与方法显得过于独特;之于文本演化与传承的整体性看法又有陷入“独断论”(dogmatism)的嫌疑,而这无疑源自韦斯特对作为“整一本”的所谓“原始文本”的坚定信念,但在评论者看来这只是“假想性的荷马史诗原型”(hypothetical Homeric archetype)而已。那赫德利与纳什很可能拥有共同的学术立场,即口头诗学的立场,这一点韦斯特在回应文章开头就已点明。从这一简短的回应来看,韦斯特显然并没有特别多的耐性来回应批评者的攻诘——特别是那赫德利集中呈现的文本异读择取等校勘细部方面的异见,因为从一开始韦斯特就已替自己设定了“写定的原始文本”这一讨论的基点,而纳什与那赫德利所秉承的口头诗学立场以及由此而来的“多重文本”观念无疑使韦斯特认为双方根本就不具备讨论校勘细节所必需的某种问题意识上的共识,所以仅以区区几页篇幅就打发了两位批评者的宏论,并且以为在新校本中回避口头诗学派的研究成果并无不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纳什对韦斯特的编校策略最为突出的不满就是后者坚持找寻或“复原”某种“正确的异读”,也即是说,显现于现存的抄本、纸草等载体中的诸种“文本变体”与“语汇异读”有且只有一种是具备“源真性”的,其他的皆是原初的“整一本”写定后在传承过程中滋生的各种干扰,韦斯特派给自己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现存材料的条分缕析,特别是借由步格、方言、语言的历史比较等要素发掘文本的“内证”(internal evidence),排除传承过程中的各种文本干扰,进而作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文本择取。纳什无疑坚决反对这种之于文本异读的带有独断论色彩的“对错之分”,在他看来,诗歌演化与文本传承的历史中形成的诸种变体与异读恰是表演传统和文本“多样性”的体现,也是荷马史诗的本真存在样态即“多重文本”的根本表征,校勘者必须对其一视同仁,不可偏废。当然韦斯特是不能苟同的,所以在这一简短的回应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语带讥讽地宣称果断地判断异读之对错恰是称职的古典语文学家和文本校勘者的分内事。
而就在这篇短论发表的同年稍早时候,韦斯特新校本的副产品——即前揭《〈伊利亚特〉的文本与传承研究》——也顺利问世,原本用拉丁文撰写、致使作者基本的问题意识与编校策略只能囿于专业学者圈内的长篇导言经过大幅扩充,以英文印行,使得作者的立场与观点可以整体性地为大众所获知。在韦斯特之于荷马问题的整体性认知与解释框架中,前亚历山大里亚时期《伊利亚特》的文本演化与传承不啻是对“原始文本”的持续性的腐蚀、降解与重构的“异化”过程。韦斯特援引考古学、碑铭学和图像学等领域对“早期诗体铭文”(early verse inscriptions)与瓶画(vasepainting)的研究,并结合传统语文学之于古文字的历史形态学、方言等层面的考量,坚定地认为《伊利亚特》的“原始文本”早在公元前688或前678年至公元前630年这一历史区间内就已由一位主要活动于小亚细亚西岸、并操用具有二十五个字母的伊奥尼亚东部方言的卓越诗人以该种希腊语方言在纸草或羊皮纸卷轴上写就全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在这一历史区间之前不存在《伊利亚特》的口头表演传统,韦斯特也认可《伊利亚特》在被全本写定之前是以诗人的口头表演形式首先在小亚地区流布的,但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变体——体现在史诗的叙事片断排布、叙事细节等方面——却已在最初的“原始文本”被写定之前就已消逝了,“原始文本”是被“一次写定”的,具备不可辩驳的源真性。
82M.L.West,Hellenica
:Selected
Papers
on
Greek
Literature
and
Thought
,vol
.1
,Epic
,180,18586;Studies
in
the
Text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Iliad
,34,2122.颇为有趣的是帕里的儿子亚当·帕里(Adam Parry)——也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家——却是这一观点的最早提出者,他并不无极端地认为自乃父始的将上古诗歌的口头表演传统与现代塞尔维亚史诗诗人(guslar)的表演相类比这一传统古典学与人类学、民俗学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路径根本上是错误且无效的,参阅 Adam Parry,Have We Homer's Iliad?inYale
Classical Studies
20(1966):177216;“Introduction”,in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ion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Adam Parry ixixii,esp.xxxviii;M.L.West,“The Transition from Oral to Written”,inHellenica
:Selected
Papers
on
Greek
Literature and
Thought
,vol
.1
,Epic
,163164。不同意见参阅Stephen Mitchell and Gregory Nagy,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inThe
Singer
of
Tales
,A.B.Lord,xvxviii.但随着这位“原初诗人”(primus
poeta
)的陨落,荷马文本便开始了四处流散的命运。追随这位“原初诗人”并以吟诵荷马史诗为业的诵诗人群体成为这一“原始文本”最有可能的占有者,由于诵诗人群体相较于“原初诗人”在智识、创造力与表演技巧等方面的绝对劣势,他们每个个体只能掌握一些相应的吟诵篇章或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对原初的“全本”毫无概念,恰恰相反,很可能诵诗人毕生所追求的就是获取并表演全本的《伊利亚特》。韦斯特提出了四种最有可能的“原始文本”去向:由诗人的家族妥善保存但秘不示人,不利于流布;由诵诗人群体保存并表演之,这大大利于史诗文本的誊录与流布,但无疑是以吟诵篇章或段落的形态而非全本;由诗人所依附的“保护人”(通常是城邦的“王”或后来的“僭主”)保存,诵诗人很可能会受指派而学习这一文本,客观上也有利于文本的誊录与流布;被献于某个神庙,成为神明的财产,这只有理论上的可能,而且极大地妨害了文本的流布。不论“原始文本”以上述何种方式被保存,在流布过程中,诵诗人群体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这种流布是以诵诗人对史诗文本的篇章或段落的口头表演与这些篇章段落的誊写本(written exemplars)的流转相复合的形态呈现的,从公元前620年左右至公元前520年左右,这一长时段的流布过程——也即诵诗人的史诗吟诵竞赛表演机制——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并成功地在整个希腊世界为人们所熟知。鉴于诵诗人群体在史诗文本流布中的关键地位,文本传承过程中多种变体与异读的出现也就可以想见,这取决于诵诗人对其所据有的篇章或片断在表演与传抄过程中的态度,韦斯特指出,诵诗人往往倾向于将自己所据有的文本变为“自己的版本”,由此诸多“窜入”(interpolations)和“修改”(emendations)逐渐湮没了“原始文本”的本来样态,而被次第包裹起来的文本则成为传承史上的主流样态。大体而言,对“原始文本”的侵蚀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种情形:大篇幅诗行的整体性窜入,往往很可能是其他诗人的完整作品,比如学界普遍认可《伊利亚特》第十卷“多隆尼亚”(Doloneia
)系整体性窜入;小型的窜入与修改,主要表征为出于某些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文本流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地域性分歧和认同代入(如所谓的“雅典阶段”、“史诗诗系”传统等)以及文句修辞、句法等层面上的变异而刻意作出的若干变动,大体都是针对某些具体诗行、措辞、程式、明喻等要素的小型变动,且从公元前6世纪始就已显露端倪;另一种小型的变动则主要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韦斯特称之为偶发的但已被保留在现存抄本等材料中的“口头异读”(oral variants),诵诗人依凭记忆进行史诗表演时所连带的即兴特色与记忆的不确定性无疑是这类“口头异读”产生并混入文本之中的因由;从文字、方言等史诗载体自身的发展而言,文本流布过程中的传抄行为势必会受到文字变迁历程本身的极大影响,最为突出的当是阿提卡方言(Attic)及其正字法(orthography)的成功介入,以及一直贯穿整个史诗文本发育史的文字“现代化”(modernization)问题,即是原始文本在语汇、文字形态、书写规则、发音等方面的古风特色逐渐被消弭乃至替代的过程;最后一类变动则出于古风时期以来诸多“拥有智慧的人”对史诗文本的多样化解释,从最早的古风诗人们到“寓言式阐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学派(如赫瑞基姆的特阿戈尼斯 Theagenes of Rhegium,6BC);再到前苏格拉底学派,以及古典时期以来流行于希腊世界的诸多智术师们(sophists)和作为他们的对立面出现的哲学家们,之于文本的多样化阐释不可避免地会累及文本本身的纯洁度,随意改写诗行、更换表述倒还算小瑕疵,更有甚者会炮制符合其意的新抄本,并且添加不算少的“道德或品位方面的修改”(moral or aesthetic emendations),颇似于基督教主导时期对古代文本的处理。当然我们无法回避史诗文本传承的前亚历山大里亚时期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即文本传承的“雅典阶段”。上文已经提到,纳什等学者将庇西斯特拉图家族所最终确立的泛雅典娜大节史诗吟诵竞赛机制视为荷马史诗“文本化”这一漫长的“结晶过程”中决定性的一环,通过这一诵诗人的表演机制,不光是催生了后来成为古典时期“通行本”的“雅典城邦版本”,更为吃紧的是在于依凭某种“瓶颈”效应,使得完整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与“荷马”这个名字达成实质性的对应,并使其情节、形式、叙事等广为古代世界的人们所熟知,在这一层面上,韦斯特与纳什似乎达成殊为难得的一致,韦斯特也着重指出“雅典阶段”是第一次整全的荷马史诗的表演,经典的二十四卷分卷工作亦借此塑形,使得当时的人们对整全的归属于“荷马”的两部史诗日渐熟稔,并且客观上使雅典在古风晚期以降成为整个希腊世界中阅读、传抄和阐释荷马史诗当仁不让的中心,乃至形成某种荷马史诗的“大众阅读群体”,当然,在韦斯特看来,这也意味着对“原始文本”的侵蚀在“雅典阶段”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用不着特别指出,我们之于史诗文本的知识主要还是来自存世的各类中世纪抄本、各个时期纸草残篇以及传世文献中的引文,而这其中又以各类中世纪抄本与较为晚出的纸草文献因其量大且相对完整而成为学者们工作的主要依凭,所以古典学学术史会告诉我们,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学者们的努力直接决定了后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史诗文本传承的样态与路径,换言之,正是由于芝诺多托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阿里斯塔尔库斯等学者的卓绝贡献,现代学者才有了进一步探究文本传承史的基石,也使得具备现代形式的校勘本的顺利面世成为可能。上文已经指出,纳什与韦斯特之于荷马史诗文本编校策略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即落脚于对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工作(特别是阿里斯塔尔库斯)的评估上,纳什认为阿里斯塔尔库斯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重建了史诗文本传承的格局,虽然他所编校的本子以及与之配套的单行“注疏”并未存留下来,但依靠保存在中世纪抄本上的“古注”,我们依然能够窥见阿里斯塔尔库斯在文句择取上的谨慎态度,依靠对当世抄本的最大化占有,他为几乎所有在表演语境下文本演化与传承过程中所产生的变体与异读预留了被阐释的权利和空间,由此客观上阿里斯塔尔库斯的贡献即如纳什所言,为荷马史诗的“多元文本”提供了原初的范型。
但韦斯特显然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光质疑阿里斯塔尔库斯的权威地位,更为激进的是毫不犹豫地质疑整个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作为现代意义上文本校勘学渊薮和古典学术史肇端的合法性,而这一合法性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各类古典学学术史的认可与维护,所以某种意义上言,韦斯特似乎意在与整个学术史传统搏斗,而其第一枪便是刺向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先行者芝诺多托斯及其“版本”(ekdosis
/diorthōsis
,似乎也主要可由Venetus A中“古注”窥见一斑)。韦斯特无情拒斥了将芝诺多托斯视作荷马史诗文本校勘奠定者的习见论断,认为芝诺多托斯的本子并不能称为“校勘本”,虽然据说他也发明了一种称为“欧贝洛斯”(obelos
,希腊文意即吐出、排除)的符号,用以标注认定是篡伪的诗行或篇章,但本质上言,芝诺多托斯并未搜集尽可能多的当世抄本进行文本的汇校,而只是依据所据底本语言风格与措辞等层面的“内证”进行判断,对所谓“抄本的权威性”(authority of manuscripts)如此重要的“外证”未置一喙,所以韦斯特断定这一本子不论如何称不上是一项从不同抄本材料中谨慎选取读法这一“理性过程”(rational process)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该本子措辞、字形等方面的细致考量,韦斯特断定所谓的diorthōsis
充其量只是一份公元前4世纪伊奥尼亚地区[很有可能是芝诺多托斯的家乡以弗所(Ephesus)]诵诗人的誊录本(或者直接来自该誊录本),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校勘本,虽然杂糅了大量的口传变体、武断的删节、“现代化”的字形等不利因素,但由于其传承走的是异于阿提卡传统的伊奥尼亚传统路径(前者无疑是从古典时期一直到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史诗“通行本”的发育土壤),使得该本保留了很多“原始文本”才有的古老要素,颇利于对“原始文本”的迫近。那么现代意义上的文本校勘究竟始于何处?韦斯特的答案将我们引领至另一位更为晚近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法学家第丢莫斯(Didymus,1BC),据其考证,首次以众多当世抄本为基础来辨别择取文本变体与异读的并非纳什等学者所主张的自阿里斯塔尔库斯始,而是其同时代的学者卡利斯特拉图斯(Callistratus,2BC)与克拉忒斯(Crates,2BC);真正以现代校勘精神来处理广为搜罗的抄本,并以“校勘记”(critical apparatus)的形式呈现文本传承的复杂历史则是发轫于第丢莫斯。反观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韦斯特坚持认为其主要依据仍是史诗文本的语言、风格等“内证”,对抄本等“外证”的关注则付阙如。在韦斯特对亚历山大里亚学术史的理解中,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几代大师的贡献(特别是阿里斯塔尔库斯)充分吸收并结晶为自己的“校勘本”,当属第丢莫斯的贡献。概而言之,第丢莫斯所倚仗的文献大致有三种来源:其一是当世所见的各种通行版本(hai
ekdoseis
),不仅包括希腊化时期各位学者整理的私人本与通行本,还有很多仍在希腊世界流布的地域性城邦版本,当然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助益尤多;其二是学者所单独撰述的“注疏”(ta
hupomnēmata
),如阿里斯塔尔库斯倾力撰写但未完整留存下来的“注疏”;其三便是之前诸多阐释荷马的派别所遗留下来的材料(ta
suggrammata
),由此,第丢莫斯即能顺利展开一种类似“汇校汇注”的工作,以某一“通行本”(但明显不是阿里斯塔尔库斯的本子)为底本,广采各家各本,从而形成初步的“原始文本”及其“校勘记”。纳什对韦斯特如此推崇第丢莫斯而贬斥阿里斯塔尔库斯抱有极大的不满,韦斯特将阿里斯塔尔库斯的工作仅仅视为希腊化时期众多流布的通行本中颇为普通的一种,并且在诸多读法的择取上实属对“原始文本”的损害,所以在其新校本中多处取中世纪抄本或纸草文献的读法而舍阿里斯塔尔库斯的读法,这在纳什看来完全站不住脚。由此,两者之于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荷马史诗文本传承与编校的学术史的迥异看法直接导致了双方就新校本编校策略的矛盾,上文已经提及,纳什等学者所倡导的是对所有现存的文本变体与异读一视同仁并进而形成一种开放式的“多元文本”;但韦斯特坚信这种看似宽容、充沛的编校策略实则完全违背了校勘学者与古典语文学家的基本使命——即为学界和大众提供一种尽可能完备、可靠的本子,在他看来,这种完备可靠的本子无疑需要无限迫近于那位“原初诗人”在公元前7世纪以伊奥尼亚方言写就的“原始文本”。韦斯特认为纳什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看到一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口头传统与一种荷马史诗诵诗人的再生产传统之间的区别,后者主要的任务即是表演那些从某部完整定型的史诗中挑取的片断或篇章,当然,他们的那些篡入与‘口传异读’作为他们自己技艺的体现无疑也是有效且有趣的,但这些文本相较于那个‘原始的’、‘第一位的’文本——这也是诵诗人群体所试图呈现的——无疑是颇为不同且较为低劣的。我的这个本子就是为那些对‘原始文本’更感兴趣的人们所准备的。”
所以韦斯特强调一个合格的现代校本不仅需要尽可能迫近“原始文本”的正文;而且也能提供给读者这一“原始文本”传承历史的相关痕迹,这主要就由丰沛的校勘记与“古证”(或“古代引文”,testimonia
)来呈现;当然文字的字形、拼写、送气等正字方面的细节也需适合现代读者的要求。现代校勘者完全没必要躺在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的遗产之上,而是完全有可能迫近“原始文本”,因为现存的中世纪手稿传统很有可能直接来源于第丢莫斯的整理成果。而就在韦斯特的这本著作出版之后,接踵而至的书评又将这场围绕《伊利亚特》新校本的争论推向深入,但相较于之前的评论,希腊学者瑞伽寇斯与纳什的攻击火力集中于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学术史的讨论,特别是阿里斯塔尔库斯与后来者第丢莫斯在史诗文本传承与校勘方面的地位问题,纳什最终所要证明的仍是阿里斯塔尔库斯的绝对权威性。韦斯特最后的回应仍旧简短而有力,特别指出口头诗学诸原则在荷马文本上的不适用。至此,关于《伊利亚特》托埃布纳新校本的争论暂告一段落,但明面上争论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学术主张上的日渐趋同,事实恰恰相反,两派的理论主张已经到了具体的文本编校上,各据战阵实践学术取向的局面已然拉开。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的古典语文学家蒙塔那里创办了一个专注阿里斯塔尔库斯学术遗产的在线资料库,十分丰沛;由哈佛大学驻华盛顿的希腊研究中心组织的“荷马的多元文本”(The Homer Multitext)这一长期的在线合作项目已经上马;而由拉塔奇、韦斯特、格拉夫、德·容等一批欧洲学者共同担纲的、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伊利亚特》注疏本“巴塞尔注疏本”(Basler Kommentar)自新世纪始即开始陆续面世,目前已出六卷十二分册,外加综论一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之于上述两种荷马史诗文本编校策略的争论仍在继续,各有优势又皆有短板,所以目前而言无论哪种都无法真正取代旧著而成为学界定本,所以谨慎的学者必须选取有度,有时还不得不依赖较为稳妥的老版OCT
。四
应该不用特别指出,上文较长篇幅对围绕《伊利亚特》新校本的争论回顾绝非与原初的论题——古风诗歌中的“作者身份”与“权威性”毫无瓜葛,恰恰相反,笔者着力介绍这一争论意在引起对古风诗歌“作者身份”问题的重新认知。如果说关于荷马文本的具体编校策略是某一问题链中符合逻辑的终端呈现,那么之于某一“元问题”的整体阐释模式就是对这一问题链中各环节——哪怕是那些具备高度确定性的知识——的不同认知,最终规定了可能相迥异的文本编校策略,正如上文笔者着力呈现的那样。那么这个“元问题”究竟为何?答案无疑是显明的,“荷马问题”作为古典学学科草创期学者们的核心关切,经由两百余年学术史的沉淀,已然获取某种“建构性的”元问题身份与地位;且从另一方面看,每一次对这一元问题进行重新整理与阐释的努力几乎都会成为推进整体的“荷马研究”(Homeric scholarship)的第一策动力。自18世纪末德国学者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在其开创性的作品《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
,1795)中首次将古已有之的“荷马问题”以现代形式重新包装推向世人,“荷马问题”便成为古典学家致力解决的第一要务,从“分析派”(Analysts)与“整一派”(Unitarians)的争论到20世纪上半叶“口头诗学”这一“新荷马研究”(New Homeric Scholarship)的崭露头角,再到从另一种更为广阔的史诗流布与传承角度看待荷马史诗形成和发育过程的“新分析派”(neoanalysis),学者们总在试图捕捉荷马史诗文本背后一直潜隐着的“作者”这一幽灵。如果正如美国学者特纳所指出的,所谓的荷马问题实际上是一种19世纪的发明,是多种颇具时代特色的学术思潮——比如对“作者”与编创行为的浪漫主义想象;古典语文学的兴起与学术专门化的趋向;以及19世纪的历史主义等——所共同孕育而成的,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确信:荷马问题这一古典学的原初问题本质上即是作者与作者身份的问题,之于荷马问题的不同阐释模式不外乎是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学术倾向而不可避免会呈现的正常学术生态;借此基础更可以展望,对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坚持不懈的探究很大程度上规定与引导了整个荷马研究的基本样态和走向。由此,追问学术史中关涉荷马问题的不同阐释模式之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风诗歌的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就显得尤为紧迫且重要了。那么究竟何为“荷马问题”?在此不妨援引三位权威学者的表述。韦斯特在为新出权威工具书撰写的“荷马问题”词条中说:“这一术语用来指称荷马史诗的起源问题已经远超一个世纪了,它特别关涉荷马史诗的作者身份问题的整一性、‘荷马’此人的私人贡献以及他身处的时空等”;特纳认为“荷马问题”主要回答“《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是否为同一人所作?史诗编创的具体情境为何?是否存在一种原始的‘核心’使得两部史诗得以以此为根本而被编创?两部史诗之间是何种关系?”等问题;而纳什则认为:“荷马问题首要的是关涉《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编创、作者身份和年代等问题……荷马是谁?他生活于何时何地?只有一位‘荷马’存在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同一位作者所创,还是分属不同的作者?每部史诗是否都拥有成世系的作者群体抑或编校者群体?由此是否存在一部整一的《伊利亚特》或《奥德赛》?”
以上引述的一般界定无疑可以支撑我们的论断,即传统的荷马问题本质上言是作者与作者身份的问题。自20世纪上半叶帕里与洛德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口头诗学——或者说“帕里—洛德理论”——这一新兴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范式几乎从根本上松动了日益固化的阐释模式,甚至可以说完全重构了20世纪以降学者们之于荷马问题的阐释图景,由此对整体的荷马研究的推进效应无疑怎么估量都不为过,所谓的“新荷马研究”正是肇端于帕里在塞尔维亚艰苦卓绝的田野工作。所以在这一令人振奋的学术光谱中,我们之于荷马问题之当代解答的问题史的探究势必需要去正面触碰这一问题域中的核心旨归,即荷马史诗的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换言之,我们需要知道“荷马是谁”这一原初问题在上述以韦斯特和纳什两位学者为代表的学术倾向中是如何被看待与解答的;这并有助于进一步索解学术界对整体的古风诗歌的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的一般性态度。
上文所着重回顾的围绕《伊利亚特》新校本的争论其背后潜隐的根本性学理分歧即在于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韦斯特在其新校本出版十一年后,面对学界据此而生的种种争论,深感有必要重申其关于荷马问题的基本预设、学理倾向和阐释模式,并深信己说之正确,由此催生了前揭新著《〈伊利亚特〉的形成:专论与分析性注疏》的问世。在之前的作品中,韦斯特着力讨论的乃是史诗文本形成之后的流布与传承之历险,而在这一新著的申论部分,韦斯特特别为读者呈现了那位“原初诗人”编创《伊利亚特》之“原始文本”的简要图景及其所本,颇为有趣但也在意料之中的是,这一简要的申论建筑在对口头诗学理论的轻哂斥驳之上。
韦斯特着重提出了关乎《伊利亚特》形成的五条重要预设:《伊利亚特》几乎全部是一位诗人的作品;但这位诗人并没有写作《奥德赛》;他并不叫“荷马”;《伊利亚特》的编创借由书写的帮助才能完成,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诗人并非严格遵照从第一卷至第二十四卷的线性递次进行创作,而是切分成诸多“写作部分”(writing sessions),并在整个长时段的编创过程中反复地咀嚼、打磨已写就部分,进行更合乎现下诗人创作灵感、叙事模态与技巧的修正、扩充、插入、调整等编创方式,由此《伊利亚特》这一长篇史诗得以成型,整一性、系统性与高度的艺术精巧性无疑是其最为显明的特征。但整体上的有机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史诗文本内部的绝对均质化,恰恰相反,正是出于诗人这种长时段的反刍式编创方式,史诗文本中的叙事缝隙与断裂、情节之重复、节奏不协调以及小到具体措辞、文法等方面的前后不一致等现象并不鲜见,韦斯特以著名的《伊利亚特》第九卷“使团场景”中使团人数的双数问题(duals of Embassy)为例作了进一步阐释。虽然史诗文本存在着上述诸多看似不和谐之处,但韦斯特坚持认为这些皆从属于诗人对整部诗篇的叙事意图与结构模态的整体性精彩把捉,诗人无疑知晓自己要创作什么,而这正是史诗文本之整一性、系统性与艺术精巧性的本根之源,也是韦斯特判定文句择取、剔清后世各类脱夺衍误,以最大可能恢复“原始文本”的基本根据。
所以在韦斯特之于荷马问题的解释框架中,主张口头诗学诸原则的学者们无疑具有某些学理上的“原罪”,其实并无甚新意。由此在作者与作者身份的具体考量上,韦斯特强调口头诗学派推崇的“多重的作者身份”(multiple authorship/plural authorship)观念从根本上无法解释史诗文本的诸种特性,因而是不成立的,我们必须接受“单一作者”(individual poet)的论定,但这位诗人是不是叫“荷马”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自1988年始,韦斯特开始怀疑是否真有这么一位叫“荷马”的原初诗人,而从1995年开始,“荷马”这一用来指代原初诗人的名字也几乎在其作品中消失了,代之以“P”(这位诗人)。
无须特别指出,在纳什看来,韦斯特之于荷马问题的这一解释框架属于避重就轻,远未触到荷马问题的实质——也即荷马诗歌在历时态与共时态相互纠葛的坐标中借由“编创”与“表演”两大要素的互动与融贯而逐步发育为成熟的“多样化”诗歌,并进而演化成书写下的“多元文本”。纳什将这一解释框架凝练地归结为荷马史诗的“演进模式”(evolution model):
1.一个相对而言最富流变性的时期,没有书面文本的存在,从公元前两千年早期以降,至公元前8世纪中叶。
2.一个更具“程式化”(formative)或“泛希腊化”(panHellenic)的时期,仍旧没有书面文本,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
3.一个决定性的时期,以雅典为中心,以“誊录本”为潜在的文本(potential texts),具有若干个分布点,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肇端于雅典庇西斯特拉图家族统治时期对荷马史诗表演传统的改革。
4.一个标准化的时期,拥有“誊录本”乃至“脚本”意义上的“文本”,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是从雅典的荷马诗歌表演传统的改革发端的,当时正是法雷翁的德梅特瑞乌斯的治理期,从公元前317至公元前307。
5.一个相对而言最具稳定性的时期,拥有以“定本”形式存在的“文本”,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降,这一时期是从阿里斯塔尔库斯完成了荷马诗歌文本的编订工作开始的,约在公元前150后不久,这一年也以所谓的“离心式的纸草”整体消逝为 标 志。
在这一“演进模式”的指导下,纳什之于荷马史诗的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的基本立场就与韦斯特截然相反,他彻底排斥了“单一作者”的观念,坚定地认为荷马史诗诞生于长时段中不断进行表演与编创的“歌者”(aoidos
)与“诵诗人”(rhapsōidos
)这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的职业群体之口,在他看来,“作者身份的问题取决于表演(performance)与文本性(textuality)的‘权威性’(authority),以及从表演到表演的历程中编创之恒常性(invariability)的程度”,换句话说,看似显明的“作者身份”的提炼实则源自表演和编创这一长时段的互动过程从流变性日趋于稳定性而造成的关乎“作者”的结晶效果,但口头诗学诸原则再次提醒我们,这一关乎“作者”的结晶化效果更多的只是一种“文化构建”(cultural construction),简言之,“荷马”绝非“单一作者”或者说“实有其人的人物”(historical figure),而是指称某种“特定类型的诗人”(generic poet)群体,这一群体性身份认同的产生必须归因于某种泛希腊的意识形态构建之需要:“我们或许已然失去了那位‘历史性的作者’(historical author),其实我们对他并不明了,但我们已经逐步召唤出一位‘神话式的作者’(mythical author),他并非仅仅是一位‘作者’那么简单,他是荷马(Homēros
),希腊主义(Hellenism)的文化英雄(cultural hero),是全体希腊人最为珍视的老师,他将复苏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每一次崭新的表演之中。”以上之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荷马史诗作者与作者身份观念的勾勒其实并没有遮蔽这两者之间一个颇具意味的趋同点,即对“荷马”这一“符表”(signifier)之建构过程的考量,这将会是我们反思古风诗歌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与生长点。毋庸置疑的是,借由对荷马问题的不同阐释框架的解读与比对,我们试图达成的是对整体性古风诗歌(特别是史诗传统,以荷马与赫西奥德为重)的作者问题的深层次认知,而在现代荷马研究与早期希腊史诗研究光谱中,这一认知的索解过程已然细化为之于不同问题层次或环节的具体解答,无疑这些问题层次或环节仍是隶属于整体的“荷马问题”,相互之间不乏视域重叠和互为佐证之处,比如关于“荷马”这一名字的词源学解释(etymology);史诗编创的年代问题(dating)以及早期史诗的系年问题(chronology);“歌者”与“诵诗人”群体的区格问题(兼及Homēridai
与Homēristai
等专业群体);史诗文本的分卷问题(book division);文本传承问题(text transmission);诗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与传记(biography)研究,也即史诗的早期接受研究(early reception/invention of Homer);文本化(textualization)过程的研究,将会触及诸如口传(orality)与“书写”(literacy)之关系、口述记 录理论(oral dictation theory)、早期诗体铭文 (early verse inscription)研究以及图像学(iconography)和艺术史研究等面相;学术史的整理;从程式到表演的理论转变(formulaperformance shift)以及文学的经典化(canonization)等,学者们通过对以上诸类问题层次的横向论述,意在借由对若干确定性的知识的综合阐发,进一步说明荷马问题的不同解释框架正是相互迥异的学理倾向在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上的集中投射,由此呈现早期史诗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的表象与实质。所以说传统的荷马问题本质上言是作者与作者身份的问题,而对这一传统问题的新见迭出的解答庶几促进了学者们之于古风诗歌之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的整体性认知,同时也正如上文提到了,总体的荷马研究的学术史代际演进之策动力很大程度上也即源于此。无需特别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两派学者关于荷马问题解释框架间的冲突似乎并无缓和的迹象,韦斯特于2010年11月12日受邀为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作了一场题为《当下的荷马问题》的主题演讲,简明扼要但又不失重点地为北美学界的听众——很显然这似乎应该是纳什等口头诗学派的主场——介绍了传统的荷马问题之渊薮与两百余年来的流变,以及晚近学界纠结于此的诸种争论,当然在韦斯特的笔下,纳什与他相异的学术立场必是阐发之重点。在韦斯特看来,20世纪以降,特别是“一战”之后,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不外乎如下三种学理倾向与阐释模式:整一派、口头诗学派和新分析派,而新分析派可以界定为是整一派的“某种更具分析性的变体”,这两者皆倾向于认定那位“原始诗人”的存在。而在口头诗学派的观念中,很多在韦斯特看来可以确认的荷马史诗编创要素都变得“漂浮”起来,充满了诸多“关乎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bout the authorship),在他看来,如果《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一直在被持续性地表演与编创,那么再提出诸如“荷马史诗的创制”这样的问题是否显得意义阙如?这一质疑无疑针对的是纳什的观点。
但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韦斯特对新世纪荷马问题的新气象仍抱有极大的期许,荷马问题并未过时,因为有太多的细节与问题层次亟待学者们去索解并使之明朗化,“……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断言,相较于五十甚或一百年前,学者们所直面和处理的诸种问题层次与论断无疑更为集中、也更为切近传统的问题本身。分析派、整一派、口头诗学派与新分析派都已(在学术史)上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而将我们(对荷马问题的认知)引领至此,并且现下仍旧在发挥效应。上述路径皆有其局限,但无一不被证明是极有益处的。现在我们已然达到了一个最佳的节点,借此可知这些路径并非必然相互冲突的(分析派对整一派,口头诗学派又紧接着取代了这两派,而新分析派则正在占据上风并以口传派为驳斥标的):我们正试图使它们共同发挥效应”。
从单纯的荷马问题的索解到广义的荷马研究全息图景,作者与作者身份问题无疑是一条顺络文理、潜隐其间的红线,正是借由这一常辩常新的问题意识的滋养,诸多时兴的荷马研究乃的新问题、新方法才得以层出不穷,荷马问题的学术史回顾某种程度上可重合于荷马史诗研究本身的学术史回顾,但现下荷马研究,乃至整个早期希腊史诗研究甚或作为整体的古风诗歌研究越发呈现多元共生的样态,毫无疑问这一健康积极的学术生态的出现即是发轫于对荷马问题的多元阐释。2000年7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大学举办了新千年第一次荷马研究的国际会议,众家云集、堪称隆众,主题亦颇具深意,直面荷马研究之现代转型——“三千年之后的荷马”(Omero tremila anni dopo)。但从后续出版的论文集选目来看,学者们所讨论的问题仍旧囿于传统模式,分别从文本细节、文本传承和史诗所涵泳的历史、考古语境这三个传统问题域来推进荷马史诗研究,正如书评作者芬克尔伯格所言,该书最为珍贵的学术价值恐怕不在于这三部分的正式论文,而在于作为“附录”出现的十六篇由年轻一代荷马研究者撰写的“短论”(short papers),凡涉“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叙事学”(narratology)、表演研究、仪式与神话解读等新式路径,正是这一批作品昭示了新世纪荷马研究的可能图景,迄今为止这十余年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昭示,而这段学术史中潜隐的原始触发力也是学者们无可否认的,它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口头诗学诸原则与方法的普及和渗透。
而十年之后,即2010年5月在希腊色萨洛尼卡的亚里士多德大学举办的另一场荷马研究国际会议——“荷马在21世纪:口传性、新分析派与阐释”(Homer in the 21Century:Orality,Neoanalysis,Interpretation)——则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热那亚会议的直接承续,两者较为显明的区别在于后出者之论域和问题意识更为集中显豁,正如主编蒙塔纳里在前言中试图申述的,这次会议意在将新世纪主导的两种荷马研究路径——即口头诗学与新分析派——勾连起来,打通彼此,形成某种整合效应,以此来塑形与规约荷马研究的健康走向,而这篇前言恰恰以“当下的荷马问题”(The Homeric Question Today)为题即可说明这并非是毫无来由的,荷马问题始终占据着荷马研究图景的中心位置。简而言之,这两种路径有着共同的基本关切:“荷马史诗成型前有何存在样态,它们成型之过程如何,史诗较之于其‘先行者’——也即是它们缘起于此的传统——有何关联?……(我们)所致力的就是确认诗歌符码(poetic code)得以构建所借由的那一传统之种种面相;确认流传至今的史诗得以在其间被安置与理解的那种‘系统’(system)……这实际上表达了如下这种永恒的渴望:充分理解荷马史诗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并且在某种由‘系统’与‘符码’所构成的结构中去阐释它们,而这一结构则蕴含着一种‘传统与创新’(traditioninnovation)的辩证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新分析派将着力点放在了探究荷马史诗与传统的“史诗诗系”的关系,但在作者身份这一基准问题上,两者的出发点仍旧是不尽一致的,这或许说明,至少目前看来,荷马问题仍旧处于争论的中心,而争论之内涵与外延的更新和展拓无不昭示且阐明着荷马研究的进阶图景:
口头理论认为荷马史诗产生于一种颇具流变性的口头诗歌传统的多层面背景中,其间措辞之要素与(诗歌)内容则隶属于一种共同的(传统)遗产,而诗歌活动的产物是不归因于任何作为“作者”的“个体”的(authorial individuality)。进一步说,诗歌编创是以一种“即兴表演”(improvised performance)的方式存在的,这种“表演”得以施展则仰赖于某种共享的但却并无定型的技艺与知识;而新分析派——它无疑采取一种显明的整一性立场——认为《伊利亚特》——大致以现今留存的面目——是一位伟大的个体诗人,或者说一位卓越的“作者”的作品,他精研覃思,在古风口头史诗的最终阶段编创(借由书写)完成(可能大致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与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之间),新分析派进一步认为在这一时期已经存在若干作为个体诗人之作品的诗歌在(希腊世界)流布,而荷马被认为是在这些前贤之基础上广采各类不同的主题与片断,进而进行自己的编创,这些早期的编创似可视作荷马足资利用的范型与资源。
缩写表
LSJ
H.G.Liddell and R.Scott eds.,A
Greek
English
Lexico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OCD
S. Hornblower and A. Spawforth 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BMCR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ZPE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CP
Classical
Philology
JH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CR
Classical
Review
CQ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TAP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OCT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
(Oxford Classical Texts)GRB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