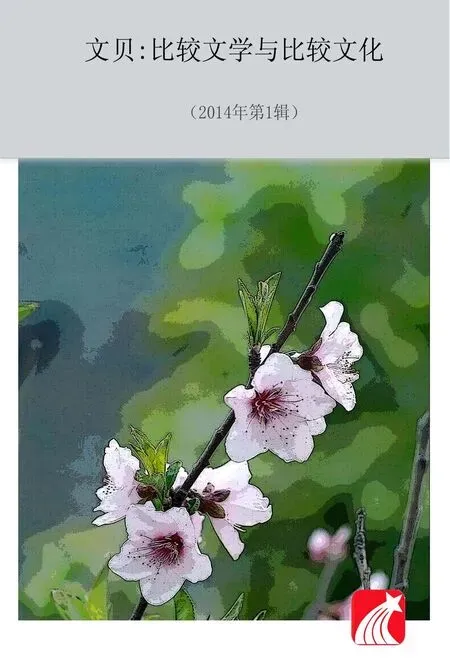薪传与新诠:《古新圣经》的解经之道*
2014-11-14郑海娟
郑海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薪传与新诠:《古新圣经》的解经之道
郑海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论文摘要]
:作为现存最早的白话《圣经》汉译本,《古新圣经》在《圣经》汉译史上意义独特。该书全本近一百五十万言,仅注解部分已有三十余万字,所涉庞杂,含蕴丰富。乾嘉年间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为一部汉译白话《圣经》做注,显然与天主教源远流长的注经传统密切相关。从内容上看,《古新圣经》的注解不仅大量挪移西方解经学巨擘的观点,而且借解释名物典章、异域风俗之机,向中文世界舶来西方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此外,注者亦秉持来华耶稣会传统,不断结合当下语境,以天主教信仰为绳,对经文加以新诠。有鉴于此,本文拟将《古新圣经》的注解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讨论译注者所遵循的解经之道,并尝试分析注解中负载的西方宗教文化观念与中国乾嘉时期的语境相遇后,是如何相互碰撞、相互融通的。《古新圣经》;贺清泰;《圣经》解经学
Notes on Author:Haijuan Zheng,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is currently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issionaries to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Chinese biblical translations.
一、引子:解经的缘由
《圣经》汉译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唐贞观九年(635),景教的阿罗本(Alopen)已“占青云而载真经”抵达长安,并奉太宗之命“翻经书殿”。其后景教教众再接再厉,所译《序听迷诗所经》等经卷涵括了〈创世纪〉与〈福音书〉,在中国首开《圣经》中译的先例。后世形成的众多汉译《圣经》中,《古新圣经》应属现存最早的白话译本。全经共三十六卷,近一百五十万言,由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3)于乾嘉年间译成。贺译虽为残稿,但几乎全译了天主教拉丁文的武加大本《圣经》(The Vulgate Bible),且经文各篇后均附有白话注解,累计约占全书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贺清泰于1771年抵达北京,1813年辞世,滞守京师四十余载,为乾隆、嘉庆两代帝王效力。这一时期,重视考据的朴学盛极一时,借由训诂、注疏、考据而“治经”的风气大行其道,甚至出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贺清泰在译经之余为《圣经》做注,“治经”对象与乾嘉学派虽有不同,但宗旨则同为彰明经文的语词意义、语法修辞,明辨名物典章、异地风俗,且贺氏所注尽管不以考据见长,但时或也钩沉典故,列举历代解经学家的观点以阐幽抉微。
《古新圣经》注解中常见“多圣师说”、“按圣贤讲论的话”或“圣贤辩论的话”等字样,这些“圣师”、“圣贤”个个都是西方史上知名的解经学家,经由贺清泰的“召唤”,奥斯定(即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热罗尼莫(即哲罗姆,St.Jerome,347—420)、伯大(St.Bede,673—735)、巴西略(St.Basil,323—379)与基利斯督莫(St.Chrysostom,347—407)等青史留名的《圣经》解经学巨擘遂在《古新圣经》注解中一一现身。这显然意味着《古新圣经》注解与西方《圣经》解经学传统难脱干系。
“解经”一词对应希腊语“exēgēsis”,原指“解释”、“阐释”,后专指解释宗教经典。注解《圣经》即阐释《圣经》的字面义、寓意等,从神学、历史或社会的层面挖掘其内在涵义。《圣经》解经传统始于犹太拉比对希伯来《圣经》经文意涵的阐释,而天主教《圣经》解经学发轫之初亦颇受犹太解经学影响,其后于中世纪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门显学,甚至影响了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等人开创的现代诠释学(hermeneutics)。
《圣经》是基督宗教的唯一正典,但关于解读这部经典的方式,天主教与新教的态度并不一致。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召开之前,天主教会并不鼓励信徒阅读《圣经》,而是强调教会训导权,视解经为神职人员的特权。16世纪中叶,罗马教廷召开天主教史上意义重大的特利腾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在第四次会议上奠定了武加大本《圣经》的正统地位,明文规定《圣经》阐释权归教会所有。解经不但应遵从教会规定,也应符合早期教父的阐释,严禁个人凭私意解经。掌控《圣经》的解释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掌控宗教话语权。天主教会冀图借此将经文意涵定于一尊,从而操控教徒的信仰。正因为此,天主教《圣经》大都附有注解,可资为证的是,明末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以《福音史义笺注》(Commentaria in Concordiam et Historiam Evangelicam)为底本,摘录《新约》经文,用典雅的文言编译成《圣经直解》,不但正文内有夹注,每节末尾还附加上一段名之为“箴”的按语,用于阐发经文大意。迤逦至今,天主教会认可的汉译本思高《圣经》依旧在各章均附有边注,书名页上还特意标示出“思高圣经学会译释”字样,强调其本身不仅是译本,也是注释本。
与天主教传统不同,新教一般支持信徒在圣灵的指引下自行解经,宗教改革即以“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为其口号。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就曾规定,该会印制发行的《圣经》应当“不含注释或评注”,以免误导读者。新教第一本汉译《圣经》——马礼逊的《神天圣书》,以及后来在汉语世界流行极广的官话和合本《圣经》都绝少注释。不过,新教内部也有个别人士意识到在华解经的重要性,“差会本”《圣经》汉译者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就曾致信《圣经》公会,请求准许他在译经时添加注解,尽管这一请求最终被负责监管《圣经》翻译出版的英国《圣经》公会循例驳回,但仍能从侧面反映出在华新教译者亦深感解经确有必要。
《古新圣经》无疑萌蘖于漫长的天主教解经传统。贺清泰能够如数家珍,一一列举前述“圣师”与“圣贤”的观点,足见其解经学功底不薄。关于注解的缘由及其方法,贺清泰在《古新圣经》的“序言”中陈明如下:
因经上难懂的话,做一记号,到后编上看有注解。若不解明,人看不懂,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若本文、注解写在一块,《圣经》的本文就零零碎碎,人看难懂,也不成篇章,所以注解都在后边。(〈化成之经〉,3)
“经上难懂的话”固然是由于《圣经》经文中暗含曲折幽隐的奥义,潜在读者——尤其是神学修养有限的望教者及平信徒——难以理解,阅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注解的意义正在于解明经文晦涩难懂之处,补益去害,引导读者领悟“天主之意”(〈化成之经〉,1)。另一方面,“经上难懂的话”大多是硬译的残留,《古新圣经》译文欧化痕迹明显,文中夹生的音译名词、量词必然给明清时代的中国读者设下重重阅读障碍,而注解的任务之一便在解释这类音译词。只有阅读注解,当时乃至今天的读者,才有可能了解“克鲁宾”是“上等天神”(〈化成之经〉,17),“阿尼蛇”则是“一种蛤蚌”(〈救出之经〉,74),而一“西其落”银价值清朝“四钱多银”(〈化成之经〉,80)。
此外,贺清泰采用的注释形式也值得我们注意,因其格式颇似今天的章节尾注,与中国传统注解方式不同,不啻为一种体例革新。上段引文中,贺清泰确立了《古新圣经》的注解体例:正文中标注序号,于章节后统一注释。中国古籍一般采用夹注的注解方式,阳玛诺编译《圣经直解》,同样沿用双行小字夹注的中国传统注解模式,贺清泰则别开新境,用中文数字标记正文待解之处,再于文后以双行小字逐条解释说明,从而将“本文”与“注解”分开,保持了《圣经》正文的相对完整性,也令注解更加集中。
注解之外,《古新圣经》各卷正文前常附有序言,说明经卷的作者、历史背景,少数卷目如《达味圣咏》、〈智德之经〉等各章标题下还有简单的题记,概括各章主题,这些内容与注解一样,均属诠释性文字,共同构成了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所谓的“副文本”(paratexts),不但从多角度呈现“文本”(text),而且也和“文本”一起建构意义空间。至于注解的具体功能,除了解释译文中生涩的音译词,还体现为补叙经文、评点、串珠等,本文第四节再予详谈。
《古新圣经》各地现存抄本以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最为集中。该书手稿应在北京北堂译毕,今天香港思高圣经协会仍藏有思高本主要译者雷永明1935年亲赴北堂拍摄《古新圣经》抄本后留存至今的经文照片,共计308页,我们从中可以略窥北堂抄本原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亦藏有三卷《达味圣咏》,卷首可见徐家汇藏书楼印章,系耶稣会为躲避战乱自沪携出。《古新圣经》注解所涉内容丰富庞杂,不仅得西方解经学余绪,而且注者也因地制宜,适时参照中国语境加以新诠。中西宗教文化在《古新圣经》注解中交替互现,屡见碰撞融通之处。目前学界虽不乏对《古新圣经》的整体研究,但尚未见对注解部分的专门讨论,本文拟以笔者在徐家汇藏书楼所见之抄本为据,参照描述翻译学的方法,集中研究《古新圣经》的注解及注解背后的文化历史现实,探求注者所奉行的解经之道。
二、西方传统
贺清泰青年时代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耶稣会神学院修习,神学教育是修士培养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环,而解经则是天主教神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新圣经》注解植根于西方传统,对西方科学、哲学、历史风俗等多个面向均有涉及,其中贺氏用力最勤者,当非神学莫属。无论是宏观的解经方法还是具体的解经观点,《古新圣经》注解对西方天主教解经学都不无因袭。
落在纸页上的字句与字句可能生发的意义之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圣经》多用减省的白描手法勾勒行动中的人,虚化细节,呈现人物、事件时尤其惜墨如金,很少铺陈人物动机、事件背景,叙述因之存有大量留白,文本颇富象征意味。这一点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在其名篇《奥德修斯的伤疤》(Odysseus'Scar)中借《圣经·旧约》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比较,已经从文学角度详加说明。关于解经的缘由,奥古斯丁曾从神学角度特意阐发,强调天主的超越性,认为人类无法企及天主的智慧,《圣经》中晦涩难懂的内容能够激发读者向深幽隐微处探寻天主之意,而要把至高无上的“圣言”转化为明白易懂的“人言”,解经显然是不可绕开之路。远在奥古斯丁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已开始用寓意法贯通神话与哲学。公元1世纪,犹太解经学家斐罗(Philo of Alexandria,20BCE—54CE)更将《圣经》区分成字面意与寓意两个层面,认为寓意是《圣经》的“灵魂”,发掘经文字面背后的寓意方为解经正道。此后,卡西安(John Cassian,365—435)吸收早期天主教父的观点,提出日后盛行于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四义解经法”,即从“字面”(literal/historical)、“寓意”(allegorical)、“伦理”(moral)与“属灵”(anagogical)四个由浅及深的层面理解《圣经》经文。
奥古斯丁认为,首先应解明经文的字面意思,进而才可从“比喻”的角度,理解经文寓意。贺清泰参照此一原则,在注解过程中首先扫除字面障碍,特别是翻译产生的音译词,只有诉诸注解,才能清楚说明。除此之外,贺清泰尤重解析字面之外的寓意,一再指出正文中的部分语词是“比喻”或“比方的话”(〈化成之经〉,8),将读者关注的焦点引向言外之意。〈化成之经〉第八篇的一条注解提道:
说的“陡斯悦乐闻祭献之味”这几句话,不过是比方的话,但要说天主喜欢诺厄(Noah)恭敬的心,乐受他献的礼物。(〈化成之经〉,37)
这里为强调天主“超性”(transcendency)之说,将经文中的“乐闻祭献之味”解作一种西方概念下的修辞(rhetoric),认为“不过是比方的话”。“比方”或者“比喻”一般由本体、喻体构成,注者的暗示话是告诉读者不应拘泥于字面的“本体”,而应探求“喻体”,即字面之外的寓意。关于天主、天神(angels)、人的灵魂的无形超性之说,《古新圣经》注解中亦时时可见,这里不妨再举一例:
天神、人的灵魂都是纯神的体,不能吃喝。若有天神取气成的肉身,虽然像吃喝,本来真不吃,也不喝,到嘴里的饮食一咽下去,立刻散了。(〈化成之经〉,64)
中国传统中祭拜天地、神灵、祖先,习惯以五牲、蔬果、熟食、酒醴为供。倘若中国读者从自身习俗出发理解《圣经》中的祭献,则难免会把《圣经》中的天主、天神混淆为中国传统习俗中的祖先神灵,误以为天主和天神同样接受世俗供奉,从而引发“异端”之思。因此,贺清泰在注解中反复强调天主无形超性之说,不断指出天主(包括供天主差遣的天神)是气化而成的“极美威严圣像”,不但不食人间烟火,而且无形无像,是纯神之体,无法用人的肉眼及灵魂之眼窥见。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神学大全》第九卷专门讨论天神,并特别论及天神有形无形的问题。阿奎那主张天神由气化成(angeli assumunt corpora ex aëre),无形无像,并援引《圣经》中的〈多俾亚经〉,证明天神不能如常人饮食。这一观点后被晚明传教士携入中土,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诠解天神魔鬼,即强调天神——以及由不肖天神转化而成的魔鬼——“声色全无”。《古新圣经》注解继承“无形超性说”这一神学观念,文中多次提到天主、天神是纯神之体,为肉眼所不能见,似乎唯恐读者曲解,误以为天主、天神化身人形都是实指。
除此之外,注解中也不乏对神意的揭示。如同贺清泰在序言开篇既已陈明的,即使是用白话写成的《圣经》,也并非“人说的平常话”,故此需要以浅显易懂的注解阐明蕴藏在字里行间的“天主之意”。于是,当经文中提到撒罗满(Solomen)立堂的“西雍”(Zion)圣山时,注解中便把这座尘世山脉超拔为“天堂”的代名词。注者亦不忘为天主代言,向读者揭示天主本意。经文中禄得(Lot)的妻子背主之命,回望琐多玛城,不幸变身盐柱,注解中便道:
天主的意思,大概是使世上的人早晚吃饭每次用盐,容易记想禄得的妻子因为悖命,遭这大祸,提醒人要小心。(〈化成之经〉,69)
注者解说“天主的意思”,讲明天主使禄得之妻变身盐柱,是因为天主欲以此常见之物警戒世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天主之意的揭示近似推测,注者并不认为自己全然洞悉天主的智慧,而仅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语气上的游移反而凸显出天主之意无比神圣,凡人未必可以参透。
就以上诸点来看,从字义的解释到寓意的阐明,再到神意的揭示,《古新圣经》注解可谓深得四义解经法之三昧。《圣经》各卷由不同写经人在不同时期草成,前后文间存在不少罅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新、旧两约之间。盖因成书先后有别,两《约》在神学观念上各有侧重:《旧约》本是犹太教圣典,《新约》方为天主教自创。为了弥合两约的裂隙,预表论(typology)解经法脱颖而出,并且广为《圣经》解经学者采用。预表论一般借助《旧约》与《新约》中具体的人与事,在两约间建构联系,填补文本的裂缝。贺清泰取法前人,每每采用预表论诠释《旧约》,把犹太教经典转化为天主教经典,为天主教服务。《古新圣经》第一卷中,天主命亚巴拉杭(Abraham)献祭其子依撒各(Issac),文后注解便把依撒各视为耶稣的预像(figura):
依撒各担祭祀用的柴,被绳子捆着,默尼亚山上情愿要舍命,这都狠对吾主耶稣二千年后甘心担十字架,被绳子捆,默尼亚山上为补赎万民的罪,要受死,流尽圣血。但主陡斯止住亚巴拉杭的手,保护依撒各的命;论吾主耶稣,任凭恶人用极苦的刑罚待他,主陡斯总不止住他们。因为吾主耶稣这一死,关系天下万民永远的福,陡斯圣父过于疼爱人类,必定要他圣子耶稣受死。(〈化成之经〉,78—79)
贺清泰在依撒各走上祭坛与耶稣赴死两者之间建构类比关系,使新旧两《约》间的鸿沟消失不见,变得水乳交融。《旧约》中的元素不再是孤立的,而是《新约》内容的预演。《旧约》总是指向《新约》,这正是预表论的典型特征。通过这样的解读,整部《旧约》遂转化为一个巨大的能指,文中的人、事、物处处指涉《新约》,预示耶稣的降临及天主教会的确立。预表论始于早期教会,在〈哥罗森书〉(Colossians)中,保禄(Paul)已采用这种方法解读《旧约》(〈哥罗森书〉,2:16—17),贺清泰在《古新圣经》注解中借预表论收编《旧约》,使其更贴近天主教教义。
无论是寓意解经法还是预表论解经法,贺清泰运用起来都驾轻就熟,而在基本的解经方法之外,对后代教会影响深远的几位拉丁教父的解经观点,《古新圣经》注解中亦屡屡援引。〈圣若望书札〉第三札中一条注解提道:
若问:灵是纯神,怎得死呢?圣奥斯定答:天主离灵,灵即死,如灵离身,身即死。(〈圣若望默照经〉,6)
熟悉奥古斯丁《天主之城》(City of God)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条注解所引“圣奥斯定”的话,几乎是对《天主之城》中奥氏所言的逐字翻译:
Thus the death of the soul results when God abandons it,the death of the body when the soul departs.
对照两段引文,贺清泰在注解中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回答部分则直接引“圣奥斯定”的话作答。奥古斯丁认为,人的肉体灭亡后,灵魂仍可凭借天主获得生命,因此它具有某种“不死”的特性,只有被天主弃绝才会逝去,此即身死之后的第二次死亡。“第二次死亡”(second death)即灵魂的死亡,这一表达频频出现于《圣经》正文(启2:11;20:6;20:14;21:8),为奥古斯丁的论点提供了文本依据。《古新圣经》的注者忠实秉持此一神学观念,不但逐字引用奥古斯丁所言,在〈圣若望默照经〉相关注解中亦不忘再次强调:“第一死是灵离身,第二死是灵下狱。”(〈圣若望默照经〉,41)
拉丁文武加大《圣经》的编译者哲罗姆译经之余,曾撰写大量解经文献,贺清泰在〈圣徒玛窦万日略〉第十四篇第一条注解即援引这位“圣热罗尼莫”的话,论道:
圣热罗尼莫说:黑罗弟亚得(思高《圣经》译:黑落狄亚)接了若翰的头,为雪恨,用簪尽戳舌。他们任意作罢!不久,天主义怒降他们身,革了黑落得(按思高本《圣经》译为黑落德)的王位,同淫妇黑落弟亚得充军远方,在彼死的狠惨。论黑落弟亚得的女,一日遇冰河,水忽开了,他身沉到脖,水一复合,切断他头。
这段注解参照哲罗姆(即文中“圣热罗尼莫”)的观点,勾勒出若翰死后的遭遇及黑落得一家的下场,令《圣经》叙事更为完整。哲罗姆在《驳儒斐努》(Apologia adversus Rufinum)第三卷中提到施洗者若翰惨遭砍头后,黑罗弟亚得用发簪力戳其舌,发泄心中仇恨。至于黑落德一家的下场,亦可见于黑落德与比拉多的来往书信(Letters of Herod and Pilate),这批信札并未收入《圣经》,属于游离在正典之外的“次经”(apocrypha)。贺清泰把它们编进注解,足见其对天主教解经传统谙熟于心,而此处注解对圣师前贤的引用,已经不再仅限于他们的解经观点,进一步变成照搬对经文具体文段的阐释。
18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命运多舛,先是在欧洲多地遭到驱逐、迫害,后终至1773年惨遭解散。贺清泰是当时在华末代耶稣会士之一,解散之后,他和其他几位在享同侪一起归入法国遣使会,但直到1802年,他还致信当时的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Ⅶ,1742—1823),试图加入俄罗斯地区尚存的耶稣会。贺清泰对耶稣会矢志不渝,《古新圣经》注解中亦有所流露,其中部分内容与《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中提倡的“默想”、“默观”等灵修方式关系不浅。《神操》乃耶稣会创会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所作,是耶稣会士灵性修炼的基本指南。在该书中,罗耀拉为灵修者设计了为期四周的避静修习,使灵修者通过默想、默观、省察、祈祷等神工,探求天主真意,达到拯救灵魂的目的。由于每天的灵修都配合阅读或默想《圣经》经文,《神操》引导的修习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圣经》阅读法。
《神操》的“默想”(mediation)、“默观”(contemplation)强调想象力训练,修习者首先要设定《圣经》中的特定场景,然后调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五种感观,想象自己置身其境,与经文中的人物感同身受,积极地融入《圣经》叙事当中。若设定地点为地狱,修习者就要在想象中用双目窥看地狱之火,用双耳倾听此间受刑者的哀号,用嗅觉感知此处的硫黄味及腥臭,用味觉品尝期间的辛酸,用触觉感受烈火的灼烧;若设定地点为耶稣受难地,修习者就应设身处地体会犹大卖主的悔恨,并变换角色,想象亲身钉上十字架的痛楚。
灵修既然是耶稣会士的必修课,贺清泰自然也应遵循会中惯例,根据《神操》定期修习。灵修的观念体现在《古新圣经》的注解中,便是贺清泰不时以绘声绘色的描摹启发读者想象,激发他们深刻体会人物的所见所感。举例来看,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一节的经文,《古新圣经》如此解说:
耶稣不肯饮那酒,四兵脱他衣,但不摘茨冠,赤在偒在十字架,用力拉他二臂、二足,用大钉钉后,立起十字架,安在先备的窟窿。我们想想:十字摇撼,落那窟窿,手足的钉孔,怎样疼痛?耶稣受的苦到甚么地步?但耶稣无怨言。(〈圣徒玛窦万日略〉,78)
较之《圣经》正文,注解中这段描述更具临场感,场景、人物动作均历历在目,贺清泰用文字引导读者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在想象中默观。“十字摇撼,落那窟窿”诉诸观感,如同特写镜头一般,颇具视觉上的冲击力,“手足的钉孔,怎样疼痛”则诉诸触觉记忆中的痛感。读者若在阅读时适当发挥想象力,其效果势必如身临其境,仿佛亲眼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惨剧,亲身感受钉子穿透身体的切肤之痛。借由一连串反问以及“我们想想”的召唤,贺清泰极力督促读者运用想象力和多种感官,体会耶稣蒙受的苦难。注解中的这段文字,与《神操》所指导的“运用五官”、“清晨默观由十字架竖立至耶稣气绝”(《圣依纳爵神操》,208—209)等系列方法暗合,与耶稣会强调的默想、默观等神工在本质上相通,体现出鲜明的耶稣会神学特征,令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仿佛参与了一次灵修。
《古新圣经》的注解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天主教神学传统,并与西方科学、哲学、历史文化紧密相关。一提到罗马天主教对科学的态度,我们可能首先想到受恶名昭彰的宗教裁判所,但实际上,罗马天主教会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亦不容抹杀。单是天主教神职人员内部,就曾涌现众多科学人才,为现代科学的诞生打下基础。贺清泰所属的耶稣会更是一枝独秀,该会历来重视修士教育,会中才俊在地震学、物理学、天文学、光学等方面均有突出造诣。明清之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耶稣会士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他们通过讲授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赢得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的青睐,为传教打下了基础。由明入清,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人也曾凭借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效命清廷,先后任职于钦天监。贺清泰继前人之踵涉足中华大地,虽系一介画师,不司钦天之职,但他青年时代亦曾在佛罗伦萨耶稣会学校攻读,不可避免受到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佛罗伦萨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镇,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科学、文化底蕴,在贺清泰求学的18世纪中期,伴随美第奇家族的衰落,佛罗伦萨江河日下,但仍不失为一座科技文化繁荣的城市。
贺清泰旅华多年,深谙以西方科学传教的便宜之计。他大概和利玛窦一样,明白天文学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古新圣经》第一卷〈化成之经〉,开篇即讲到天主化育宇宙万物。贺清泰译经之余,也把西方盛行的天文学知识写进篇后注解,向读者一一介绍地球周长、太阳直径、太阳与地球的体积比、日地距离、太阳公转速度、月球直径,以及月地距离等,列举的数字甚至精确到十位数,如太阳距地球“三十四千七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里”,月球距地球“八十六万三千二百四十里”(〈化成之经〉,8—9)等。值得一提的是,贺清泰呈现这些数据的方式形象而生动,与历书中常见的刻板陈述完全不同。为了说明地球与各星的距离,他假设有一只鹰,“这鹰往天上直飞,天天飞一千里,总不歇着,要二十五万九千零七十二年的工夫,才飞得到星的去处”(〈化成之经〉,9)。所用语言通俗易懂,富有兴味,将原本单调的数字娓娓道来,仿佛给清代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有趣的科普课。
更为重要的是,注解中的部分内容似乎已溢出明末清初传教士输入中国的天文知识。拿太阳与地球的体积比来看,贺清泰指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一百四十万倍有余”(〈化成之经〉,9),这虽与今天科学界公认的一百三十万倍有所出入,但若与清初盛行的《西洋新法历书》、《历象考成》等历书相比,则准确度远远高于后者。《历象考成》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历书,参照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编订的《西洋新法历书》而成,全书以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天文学体系为基础。书中谈道:“《新法历书》(按:即《西洋新法历书》)载日径为地径之五倍有余……今依其法用日月高卑两限各数推之,所得实径之数,日径为地径之五倍又百分之七。”据此计算,太阳体积应为地球的一百二十五倍有余,与实际数字可谓千差万别。乾隆七年(1742),戴进贤(Ignatius Kgler,1680—1746)等人奉旨编制10卷本《历象考成后编》,该书计算太阳半径为地球的96倍有余,即太阳体积为地球的88万倍,准确性大大提高,但仍远不及贺清泰所给的数据。
《古新圣经》注解中列出的一串串数字具体而翔实,极有可能来自17、18世纪欧洲蓬勃发展的天文测量学。17世纪,法国天文学家皮卡尔(Jean Picard,1620—1682)用三角测量的方式,借助千分仪等工具,首次以精确的方式提出测量太阳、月亮以及其他星体的直径与高度的方法,促使天文学进入定量测量的新阶段。皮卡尔本人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早年曾接受耶稣会教育。他的同代人中,法国天主教士莫顿(Gabriel Mouton,1618—1694)于1661年首次较为准确地测量出太阳直径,1672年,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又测量出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古新圣经》相关注解中谈到日月直径、日地距离等数据时,颇显言之凿凿。贺氏所据,具体出处仍有待查考,但可以肯定,他的数据来源一定深受17、18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天体测量学影响。
在科学之外,《古新圣经》的注解显示,贺清泰对西方哲学亦有所涉猎。经文中曾提到“有厄必古肋约、稣多意各二旁门的格物穷理人”与保禄辩论,而这里的“厄必古肋约、稣多意”即伊壁鸠鲁思想(Epicureanism)与斯多葛主义(Stoicism),贺清泰不但在注解中介绍两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还从天主教的立场出发,对他们的哲学思想展开批评:
这二旁门之首,一是厄必谷落,一是则农。厄必谷落讲人的福全在身安闲逸,故与畜不异;则农讲人的福在顺情理。二人都讲天命是根本,人在世所作所为,都由命定,即天主亦不能改。若追问天命是什么,他们解不明。(〈诸徒行实经〉,40)
此“厄必谷落”今译“伊壁鸠鲁”(Epicurus,341—270 BC),“则农”今译“芝诺”(Zeno of Citium,334—262 BC),二人分别为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学派由伊壁鸠鲁本人于公元前307年创立,该派上承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460—370 BC)的“原子论”,反对宗教迷信,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斯多葛学派则由芝诺等人创立于公元前3世纪,主张修行与禁欲,具有泛神论(pantheism)倾向。相比而言,主张无神论的伊壁鸠鲁学派对天主教构成的威胁更大,也正因为此,二者当中,贺清泰对伊壁鸠鲁的抨击尤烈,直骂其“与畜不异”;对芝诺的批评则温和不少,虽然将其与伊壁鸠鲁一道归入“旁门”左道,但对他的具体指责只有“不明天命”四字。个中原因,大抵在于斯多葛思想不重现世,主张克制节欲,与天主教确有类似之处。天主教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曾对斯多葛主义大肆收编、重诠,将其转化为自身所需的知识资源。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所著对伊壁鸠鲁主义颇多讥讽,对斯多葛思想则相当宽容,利玛窦甚至曾把经过天主教收编的斯多葛主义著作译为中文,亦即颇受徐光启、冯应京赞许的《二十五言》。贺清泰对待这两类“格物穷理人”的态度有别,与他的耶稣会前辈们几乎一脉相承。
介绍科学、哲学之外,《古新圣经》注解还常常解说西方历史、风俗。〈达尼耶尔经〉第八篇正文谈到达尼耶尔所见的异象及其影射物,但语焉不详,贺清泰遂在注解中总说西方古代历史,从“亚立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今译:亚历山大)登基到他去世后国土一分为四,四位将军——多落默阿、塞禄戈、斐里伯和安弟郭诺——各自称王,以致后来塞禄戈的第八代孙安弟约渴(Antiochus Ⅳ Epiphanes)打败埃及国王,进而占领如德亚国,玷污耶路撒冷圣堂,禁止天主教,甚至安弟约渴后来惨死野外的史实,都在注解中一一道来。不仅如此,在《旧约》最后一部经卷《玛加白衣经》的末尾,贺氏还指出,从玛加白衣(Maccabee,《古新圣经》亦译为“玛加白阿”)去世到耶稣诞生,中间尚有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空缺,这一段历史《圣经》未提,贺清泰“便从若瑟甫史摘要紧的作一总论”,用一千多字的长注解介绍这一百多年的重大事件。至于这位“若瑟甫”是何方人士,贺清泰并未详谈,但熟悉基督宗教史的人当然明白,他正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37—100)。“若瑟甫”当然并未皈依天主教,但他对希伯来《圣经》极有研究,笔下记录的历史事件多与经书记载吻合,所著二十卷《犹太古史》更是特意按照希伯来《圣经》的叙事顺序,从创世开始,讲到犹太人与罗马的战争为止;另一部《犹太战史》则从玛加白衣时代谈到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贺清泰借助若瑟甫的史书,以史注经,撮其大要,一直讲到“黑落得在位的三十七年,吾主耶稣在栢得冷从童贞玛利亚取人性而生”(〈玛加白衣经〉,40)方才作罢,补缀起《旧约》与《新约》之间一百多年的时间缝隙,与此同时,也把这一段此前从未见于中文书籍的西方历史引入中国。
贺清泰借古人之言、之法“治经”,汇总了西方史上重要解经学家的观点,同时又假西方科学、历史、文化多种元素阐名经义,勾勒出与《圣经》内容相关的西方语境。《圣经》借由一代又一代的阐释获得了历久弥新的生命,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阐释必须与当下的语境密切相关,西方解经学固然“体大而备周”,沿用起来不无便宜,西方科学文化中自然也不乏令中华士林耳目一新之处,但相对中国传统而言,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且“新”且“异”的特征,施之于清代中期的中国,未必就是实现弘教大旨的最佳途径。作为补充,贺清泰也常常参照前代来华耶稣会士的做法,结合中国当下语境对经文施以新诠。
三、中国新诠
耶稣会在世界范围内奉行本地化的传教策略,为了让天主教在中国更好地生根发芽,研习儒家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成了每位来华会士的必修课。《圣经》新旧两《约》分别脱胎于希伯来、希腊文化,其中的因子难免与乾嘉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合,译成汉语的《圣经》因此随时有可能对中国传统习俗观念构成挑战,亟须译者借解经之机加以说明,从而规避可能的误读。贺清泰用中文俗语翻译《圣经》时,预设的理想读者显然是乾嘉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所谓的“引车卖浆者流”。为了因应潜在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心理,《古新圣经》的注解明显本地化了,体现出贺清泰将《圣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沟通中西的尝试。在这类注解中,贺清泰仿照前代来华耶稣会士,对《圣经》中一些带有异域文化色彩的元素予以语境化处理,因地制宜,加以“新诠”——这里所说的“新诠”,并非仅靠贺清泰一人之力完成,更多是贺氏在来华耶稣会前行代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现实,再行发挥得出的。其中既有贺清泰个人的尝试,也有早期来华传教士在本地化实践中结晶的集体智慧。
对于乾嘉时代的中国读者而言,西方历史、文化、风俗无疑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他们能否顺利接受这些陌生的信息,是译注者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贺清泰对此可谓煞费苦心,〈创世纪〉二十九篇写雅各布(Jacob)离家前往哈兰寻亲,在旷野井边偶遇母舅之女,亦即他后来的妻子。《古新圣经》中的相关译文如下:
亚各伯一见了他,知道他是自己的表妹,放的羊是他母舅的,移开盖井的石,饮了羊后,亲了嘴。
中国传统礼教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礼记·曲礼》),然而译文中亚各伯与表妹二人刚一邂逅就罔顾男女之大防,亲嘴示爱,以清朝中叶的社会文化氛围而论,实在有伤风化。若有卫道士将此段文字斥为晦淫之说,恐怕也不为过,“圣书”因之大有沦为“淫书”的危险。贺氏之前,来华传教士对《旧约》的译介多停留在亚当、厄娃故事,对《旧约》人物为表亲爱,无论同性、异性动辄相亲的内容未曾涉猎。贺清泰逐篇翻译《古新圣经》,不得不面对这个前人无解的问题。为经文添加注解,说明这是异域风俗,此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贺清泰道:
亲戚不分男女、大小,或临远方去,分手的时候,或回来头一次见面,为表大亲爱亲嘴。亚各伯不过随地方的礼,并没有怀着别的意思。(〈造成经〉,11)
在儒家传统中,“礼”是规约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也是儒家倡导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重要内容。晚明传教士来华不久,便深刻体会到“礼”的重要性,罗明坚在《天主圣教实录》中把中国称作“礼义之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与《辩学遗牍》中亦频频援引《礼记》入文。贺清泰居华多年,熟谙中国文化习俗,是以颇能预设中国读者心理。《古新圣经》译出了《旧约》中绝大多数篇目,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雅歌》弃而不译,原因大抵在此。孟子有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孟子·离娄上》),对于熟谙孔孟之道的清代中国人来说,此处《圣经》经文的内容正与礼有违。贺清泰解经时便特意从“礼”字切入,说明亲嘴虽不合中国礼数,却是异国他乡之“礼”,并强调亚各伯“没有怀着别的意思”,只是循礼而行。如此,他既为《圣经》人物的行为做了辩解,也为《古新圣经》在乾嘉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求得了一定的合法性。
“礼”是对人伦的规约,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伦之道又以孝道为首。贺清泰敏锐察觉到孝道在儒家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屡屡以“孝”为道德标杆,褒贬人物,试图将《圣经》中的元素与中国孝道融合。〈禄德经〉一卷讲述禄德(Ruth)捡拾麦穗奉养婆母,贺清泰在注解中借题发挥,大力旌表禄德之“孝”,更在该卷序言中将其标举为“贤孝的表率”(〈审事官经·禄德经〉,62)。〈化成之经〉第十篇,贺清泰又借注解之便批评《圣经》人物加母(Cham),用于指责他的话竟是“上不恭敬天主,下不孝敬父母”(〈化成之经〉,42)。此处“孝敬父母”与“恭敬天主”并举,不但表明诠释者对儒家固有孝道文化的尊重,也在中国语境下道出了“恭敬天主”的重要性。换言之,“恭敬天主”就是孝敬人类的“大父母”——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数次以“大父母”称呼天主(《天主实义》,70,96),因为根据《创世纪》,天地万物都由他化生,人类也不例外。天主教本质上轻“俗世”、重“天乡”,强调钦崇天主,召唤人对天堂的向往,这与儒家注重现世五伦的观念存在一定差距。在〈路加福音〉里,耶稣曾明言:
如果谁来就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路14:26)
《古新圣经》译为:
若有从我的,不恨父母、妻子、弟兄、姊妹兼己,不能为我徒。
类似的表述,我们在《玛窦福音》(《玛窦福音》,10:35—37)中同样可以看到。天主教强调超世之思,将包括孝道在内的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都视作现世羁绊,认为它们腐蚀人的信仰,是通往天国路上的障碍。儒家思想则强调人世的伦理纲常,并把孝道推崇为“天之经”、“地之义”(《孝经·三才章》)。天主教重超越与儒家重现世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在伦理价值观上有所区别。早在贺清泰之前,晚明来华耶稣会士已到这种差异认识并试图予以弥合,利玛窦在五伦之上将恭敬天主标举为“大伦”(《天主实义》,75),与张载在《西铭》中将天地乾坤视为“大父母”的泛化孝道隐然相关;高一志(Alfonso Vagnoni,1566—1640)则以五伦为纲编译《达道记言》,用儒家伦理调和天主教教理。贺清泰为《古新圣经》做注时步武前人,充分贴合现实语境,大谈孝敬父母之道,而且特别突出耶稣对圣母、天父的恭敬,试图把耶稣树立为举世人的“奇孝之表”(〈圣史路加万日略〉,8)。由于上述引文中耶稣的话读来明显有违“孝道”宗旨,注解中便对译文中“恨父母、妻子、弟兄、姊妹”的“恨”字特加解释:
此“恨”非恼怒,是尊二亲之命在天主命之次。若父母命行逆主之事,即不可遵,因天主在二亲之上。(〈圣史路加万日略〉,8)
经此诠解,此处的“恨”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忤逆父母”,而是变得相对化,有了明确的限定:所谓“恨父母”是指当“父母之命”违背“天主之命”时,“父母之命”退而居其次。易言之,遵父母之命仍为必要,只不过其重要性不及遵天主之命。因此,这里的“恨”字应该理解为一种修辞:人与天主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人应尊崇天主,与这种尊崇相比,人与父母、父亲、兄弟等亲缘关系尽管都居于次要地位,但并非不重要。如此解释令意在超越的天主教教义变得富有人情味了。思高《圣经》译文虽使用“恼恨”二字,但脚注中也对该词设限,说明“所说‘恼恨’即置诸次要地位之意”,与贺清泰的解释殊无扦格。
所谓“百孝顺为先”,在贺清泰的注解中,《圣经》人物常因孝行获致褒扬,就连耶稣本人也顺从天父,甘心被钉十字架,为世上万人树立“奇孝之表”(〈圣徒玛窦万日略〉,53),那么中国信徒效法耶稣,在钦崇天主的同时孝敬父母,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处理,贺清泰既维护了儒家固有的伦理价值观,也尽量消弭孝道与天主教信仰的不和谐之音,为预想中的读者认同天主教做好了铺垫。
儒家之外,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力不小。对于佛教信仰,贺清泰往往借注解着力抨击,与利玛窦等晚明耶稣会士奉行的“补儒辟佛”策略如出一辙。明清间在华天主教视佛教为异端邪说,传教士及当时中国本土天主教徒的护教作品中,辟佛之论层出不穷,利玛窦的《畸人十篇》,高一志的《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徐光启的《辟释氏诸妄》、《破迷》,杨廷筠的《代疑篇》、《鸮鸾不并鸣说》,以及刘凝的《觉斯录》等,都曾一一对佛教展开痛击。贺清泰踵武前辈耶稣会士,在《古新圣经》的注解中对佛教大加挞伐。最为典型的是,佛与诸菩萨在他的笔下俨然都成了邪神的代表。每当需要向中国读者解说某个陌生的邪神时,贺氏往往会搬出中国读者熟悉的佛、菩萨,视之为邪神的基本范例。《众王经》第一卷提到邪神大宫(Dagon),就在注解中如此描述:
大宫是古时一个行横霸道的人,因他在地方初创造犂,后人胡乱封他为神。大宫的像似佛像,脸胖肚高。〈审事官经·禄德经〉正文中提到邪神,注解亦道:
所说的“巴哈耳巴”、“哈里母”是男邪神,佛一类;亚斯大落得是女,菩萨的赃[脏]像。(〈审事官经·禄德经〉,4)
在这类批注中,贺清泰不但将佛、菩萨斥为邪神,而且语出不逊:佛像“脸胖肚圆”,菩萨则被直呼为“赃[脏]像”。佛、菩萨无疑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佛教神灵,自汉代以来,借助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其庄严、慈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贺清泰毫不留情,统统视其为异端邪神的代表,戮力攻之。佛教与天主教同为世界性宗教,两者的相似性较之儒家与天主教的相似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罗明坚、利玛窦初来中国,也曾自比“西僧”,后来发现儒者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僧人,转以“西儒”自谓。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儒生,如韩愈、张载、二程、朱熹、王夫之等,都曾有过辟佛宗儒之论。贺清泰参照前辈传教士,采取同这些名家大儒类似的立场,对佛教鞭笞尤力,用意乃在迎合处于强势地位的儒家文化,打击宗教劲敌,促使更多人改宗天主教。
佛教信仰之外,受道教影响的中国本土迷信风俗是贺清泰着力抨击的又一对象。正如在佛与邪神之间建立类比关系,贺清泰格义连类,把“假先知”(思高《圣经》译法)译为“算命的”,做注时更是一再将矛头指向中国本土的迷信风俗:
说的巴哈耳并树林内有的那些先知者不是正经的,是如中国卜卦、算命、巫人之类,胡言乱语,哄人苟图衣食。(〈众王经·卷三〉,55)
注解中明确提到“中国”二字,意在将读者的视域引向中国语境下天主教信仰面临的处境。在贺清泰眼中,讲风水、观天象、看吉凶、卜卦与算命等无一不是“邪术妖怪”(〈造成经〉,59),种种流弊引得他慨叹连连:“现在世上的人这样行的好不多呀!不勉力善德,尽心求谋龙脉风水左道的事,往往求福反倒遭了祸。”(〈数目经〉,57)对于中国固有的丧葬习俗,《古新圣经》的注解也不肯放过:
迷惑异端的人埋没这个道理,尽力胡乱花钱:埋葬尸首头里,或看地方形像,挑选好日期;埋葬之后,或供献食物、奠酒、烧器皿、缎子、纸银、衣服,行这等虚假的事,叩头又叩头。若问死人的臭烂肉、干骨头还能吃喝穿戴么?烧物的灰能使用么?他灵魂既然是
纯神,越发不能饮食,越发不用供献的东西。(〈化成之经〉,81)
引文虽未明确提到“中国”二字,但所谓择日下葬、看风水、烧纸钱、祭奠死者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习俗而言。贺清泰有感而发,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与中国语境结合,提出严厉批评,将迷信视为异端邪说。这类抨击,见于早期来华传教士以及部分中国信徒的著作中,清初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就曾在所著章回体小说《儒交信》中借人物李光之口批评迷信陋俗,而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1603—1666)的《烛俗迷篇》则几乎通篇皆是对风水丧葬等习俗的直接驳斥。
自16世纪创立以来,耶稣会就以外方传教会中为最重要的使命,并因其极强的灵活性、应变性和适应性而著称。《古新圣经》注解所做的本地化处理,可以说与耶稣会常用的“适应方法”若合符节。相对翻译而言,注解的自由度较高,不必受源文左右,可视具体情况“或添或减”(贺清泰语)。《古新圣经》的注解着力迎合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打击佛、道等宗教劲敌,试图沟通中西文化,拉近天主教神学观念与儒家文化之间的距离,并建构天主与邪神、正教与异端、信仰与迷信之间的二元对立。除此之外,为了满足传教的现实需求,贺清泰还往往在注解中刻意添加中国化元素,以求唤起本地读者的关注。〈诸徒行实经〉讲到宗徒受圣神默引,能说各地方言,贺清泰便趁机在注解中补充道:“不然怎能到印度、日本、中国、高丽等国传教呢?”(〈诸徒行实经〉,6)这无异于暗示,贺清泰等明清传教士同样受圣神默引来华,接续宗徒未竟之事业。概括来看,本地化、语境化是耶稣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传教方法,在具体的传教实践中,普世化的方法必然具象化,呈现出各自独有的特色。本节开头提到《古新圣经》注解呈现出中国式的“新诠”,指的便是注者结合现实社会语境,诠释经文。其中既有贺清泰根据中国历史与文化,因地制宜添加而成的,也有对前代来华耶稣会士既有成果的借鉴与模仿,其目的当在吸引潜在中国读者的关注,引发他们的共鸣,为传教事业做好铺垫。
四、小结:注解的功能
事实上,像贺清泰一样为一部白话《圣经》做注,极易被诟病为狗尾续貂,因为译者已经宣称正文采用最接近口语的白话翻译了。不过,本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说明,《古新圣经》的注解委实不可或缺。不但天主教解经传统中的四义解经法、预表论等方法借注解之便在贺清泰笔下再行发挥,天主教传统解经学家的观点也得以赓续。为适应乾嘉时期中国教区的特殊语境,贺清泰还时发新诠,力图使译文契合中国当下的道德伦理观念。尽管由于教廷禁令,《古新圣经》未能在当时出版,但贺清泰本人确曾有意将其付梓刊行,从卷首两篇序言中,我们可以明确感知译注者强烈的读者诉求,而要为这个译本争取到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在采用白话译经之外,还应辅以必要的注解。
在天主教传统中,书面解经与口头讲道两者关系密切,源远流长的解经学传统为教士讲道提供了必要的方法与神学支持。布道宣教本是传教士专司之职,但《古新圣经》撰写之际,正值清朝禁教之时,贺清泰长住京城,官方控制尤严。嘉庆年间,清廷上谕(1805年5月16日)规定“西洋事务章程”,不但派兵在北京四座天主堂门前稽查,禁止百姓入堂,亦不准其与教士来往,还规定传教士因公出门必须由士兵陪同。照此章程,传教士在公开场合的行动几乎处处受限,贺清泰即使心存布道理想,也只得以隐幽曲折的方式实现。贺氏采用白话撰写《圣经》注解,折射出他试图面向平民大众发言,以注经代替讲道的诉求。清初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口述,杨多默笔录的教理书籍《盛世刍荛》,就在篇首的“仁爱引言”中述及以白话著述代替当面讲道的便宜之处,认为读者翻阅白话书籍时,阅读即形同布道,就连不识字之人也能从他们的朗读中倾听受益。在此问题上,贺清泰极有可能受前辈启发,借注解之便,为阅读与布道合二为一埋下伏笔。
《古新圣经》的注解承担着多重功能,不仅包括利用话语权抨击异己,迎合主流文化以获取更多受众,还具体体现为补叙经文、评点、串珠等功能,以下分别论述。
前文提到,《圣经》中的大量留白为诠释提供了广阔空间,留白之处,贺清泰往往通过注解予以补叙填充。〈化成之经〉第四章提到天主轻看加音(Cain),偏爱亚伯耳(Abel),经文中并未透露天主嫌弃加音的原因,《古新圣经》的注解于是补充说:
亚当、厄娃尽父母职分,教训他生养儿女们恭敬感谢陡斯的恩,与他祭献礼物——这些紧要的道理,无有不讲给他们听的。但加音过于贪恋自己的物,先收的好粮食留下不供,后收的平常粮食才供。亚伯耳不是这样,头胎下的羊羔内,拣选肥美的、好的祭献天主。主陡斯要挽回加音贪恋的心,又要表出亚伯耳的忠心,从天降下火焰,把亚伯耳贡献的羊羔一时都烧尽了,不降火焰烧加音贡献的粮食。(〈化成之经〉,24—25)
一经注解阐明,天主对亚伯耳的偏爱便显得合乎情理了。然而,贺清泰此处似乎并不甘于简单交代事情原委,而欲尽心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亚当、厄娃对子女的教训、加音企图蒙骗天主乃至天主为辨忠奸降火焚烧祭物等情节,都不是《圣经》内容,而是注者的补充说明。贺清泰利用《圣经》既定的故事框架,再以妙手“锦上添花”,补充额外的情节,理顺了《圣经》的叙述逻辑,巩固了经文的合法性。
〈救出之经〉里,天主亲自拣选每瑟(Moses),委以重任,命他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然而,该卷第四章却突然提及天主欲击杀每瑟,每瑟之妻瑟拂拉遂用石头给次子行割礼,助其逃过一劫。天主前后态度大相径庭,令人莫名所以,思高本《圣经》因而称这段经文“不易解说”,又赓续论道:“此事的神秘性,和雅各布伯与天神搏斗的事一样神秘。”(思高《圣经》,87)对这段“不易解说”的文字,《古新圣经》注解如此诠释:
说的瑟拂拉以块石给“儿子”割损,不说给“儿子们”,因为长子热耳桑已经行了这个礼,第二[子]耶理耶则肋因为新生养的,还没有割损。想是每瑟刚要起身,意思恐怕路上过于疼痛,到了厄日多再割损罢。但陡斯差天神吓唬每瑟,瑟拂拉因为有天神默动不能得别的刀,拣起快石给小儿割了损。每瑟本是陡斯特立的,为给众人传他的旨意,他若轻忽天主的诫命,他怎么教别人守呢?(〈救出之经〉,10—11)
《圣经》原文对此事的描述仅一笔带过,读来自是神秘感十足,正好符合奥尔巴赫的归纳。贺清泰在注解中不但补叙了此事原委,还添加大量细节,把整幅场景描摹得活灵活现,驱散了原本笼罩在经文之上的神秘气氛。这段经文,思高《圣经》的译释称天主的杀机并非源于每瑟次子未行割礼,而是每瑟本人未行此礼所致。贺清泰则从单复数切入,分析“儿子”与“儿子们”这一字之差,以细读文本的方式,解说天主盛怒的原因,与思高的解读殊异。相形之下,《古新圣经》的注解似能较好化解读者疑虑,把天主态度前后不一的矛盾讲得合情入理,因此更加令人信服。
注解的补叙功能不仅体现在补充细节,罗织“故事”以解释经文晦涩难明之处,有时还表现在注者以“代疑”之法,就文本再行演绎。〈化成之经〉写亚巴郎(Abraham)携妻撒拉依(Sarah)前往埃及,为避灾免祸,假称其妻为妹,后为法劳识破。相关注解便以修辞设问的形式展开:
到底法劳是怎么知道撒拉依是亚巴郎的妻呢?答:或是梦间陡斯责备他,也告诉他真话;或因为见那许多灾祸,心惊胆战,详细问撒拉依,才明白知道。(〈化成之经〉,49)
法劳如何发现真相,《圣经》正文并未提及,情节逻辑的因果关系链原本就有缺失,贺清泰在注解中以设问自答的形式提出两种可能,为事件之“果”补足了必要之“因”。问答体在教义问答中应用最为广泛。贺清泰参照其法,首先模拟读者口吻,提出疑问,再予解答,其特点是针对性强,形式活泼,容易捕获读者的注意,用问题引动其寻找答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此法在贺清泰笔下运用自如,一问一答始终牵引着读者的目光,规避了阅读中可能的失焦。
同样,奥尔巴赫所谓《圣经》中空缺的人物心理刻画,《古新圣经》注解里往往也会适当补写。〈化成之经〉中亚巴拉杭奉天主之命上山献祭其子依撒各,依撒各不明就里,询问祭品是什么。贺清泰特意在这句话后面加上一条注解:“这几句话真如刀刺亚巴拉杭的心。”(〈化成之经〉,78)寥寥数语便道出了人物当下的内心感受,亚巴拉杭的“父亲”形象旋即丰富起来。
此类注解在《古新圣经》中常见,一般表现为设身处地为人物着想,或者从旁观角度出发,对人物事件加以评论。〈化成之经〉里禄得(Lot,思高本《圣经》译作“罗特”)之女灌醉父亲后与其同房受孕,生子名为“默哈伯”。贺清泰先用一大段注解评论禄得父女是非,引出“酒里有邪淫”(〈化成之经〉,70)的说教,然后又在篇末用一条注解说明“默哈伯”的意思就是“从父亲得的子”,从而评论道:
真真的那个女孩,给他养的儿子取这个名字,好不没脸!明显他是不害羞的女人。(〈化成之经〉,70)
贺清泰借评点式的注解臧否人物,与中国传统小说、戏曲评点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可与金圣叹、脂砚斋等人笔下小说人物的月旦对读。其中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中国传统小说、戏曲评点在臧否人物之外,更常见的是品评作品章法、文笔,兼及人物形象塑造,审美性的文学批评占据大半;《古新圣经》注解中的人物评点则重在道德说教,注者的神情跃然纸上。贺清泰借由道德训诫的力量传达其价值观与天主教信仰,以此感染并规训可能的读者。
补叙与评点之外,《古新圣经》注解兼具串珠(cross-reference)的功能,常在一章篇目后标注其他卷目中的相似或内容,以资参考,为读者阅读经文甚至“以经解经”提供了方便。这在三部对观福音(synopticgospel)——〈圣徒玛窦万日略〉、〈圣史玛尔谷万日略〉、〈圣史路加万日略〉——中尤为明显,因其内容多有重合,注解中指明相关经文,便于读者参照查阅。《古新圣经》注解便常将所涉内容串联起来,在不同经卷间建立横向参考,打通经卷内容,行使串珠的功能。
在《古新圣经》的各类注解中,对《圣经》人物、事件的品评,连同对儒家文化的迎合,对佛道的抨击等语境化内容,或为贺清泰有感而发,或属借鉴在华耶稣会前贤既有话语资源,并再行发挥。至于补叙经文、沿袭天主教解经方法和解经观点,大体则应其来有自。
《古新圣经》注解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大可能是译注者从前辈解经学家、史学家那里集腋成裘,一点点搜集而来,而更像是在翻译时以某部注释本《圣经》为底本,既参照源文已有的注解,又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中国特色”的补充。在华期间,贺清泰主要住在北堂,《古新圣经》应该就在此地译成。翻查法国遣使会士所编《北堂书目》,我们发现北堂确曾藏有多部注释本拉丁文《圣经》,而贺清泰极有可能取其中一部随译随注,并在做注时“或添或减”,完成《古新圣经》的解经工作。本文仅就注解内容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展开分析,至于译注者所据底本为何,仍有待查考。
在语言技巧与个人诗学外,翻译本身几可谓诠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早有明言“一切翻译皆诠释”。《古新圣经》的注解又是对译文的诠释,因此称得上是“诠释的诠释”或“翻译的翻译”。《古新圣经》的译文是文本,注解是副文本,两者共同建构了《古新圣经》的意义空间。注解是译文的补充与延伸,作为副文本的《古新圣经》注解既诠释译文,使变动的意义空间趋于稳定,同时也丰富译文,令文本的面目更为多彩多姿。贺清泰做注的手法繁复,或沿用教内传统,或另创新诠,或自问自答,或夹叙夹议,在多种方式中尝试实现中西沟通,扩大了文本可能的接受范围与程度。
与译文相比,注解虽位于边缘,但它脱离源文的羁绊,可用更为通
俗易懂的白话写出。贺清泰故而得以面对读者直接发言,并借助语言规训操控文本的意义走向,使《古新圣经》贴合现实语境,在具体的一时(清代中叶)一地(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为传播基督信仰服务。作为边缘文本,注解反而可以因此获得某种权力,伺机颠覆文本系统中原有的秩序等级,成为文本解释权的“幕后”操纵者。由是观之,《古新圣经》的注解不但不可或缺,而且意义非同小可。《圣经》经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若与中国乾嘉时期的语境契合神交,只能依赖注解提供必要的缓冲地带,形成诠释与翻译意义上的渡河津筏。
Annotating the Bible in Mid-Qing China:Poirot's Efforts
Haijuan Zheng
Louis de Poirot,a French Jesuit living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translated the Vulgate Bible into the Gu-xin-sheng-jing,an annotated version in vernacular Chinese.Arguably the earli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in vernacular Chinese,Poirot's Gu-xin-sheng-jing claims a unique status and is of great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cal translation,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it failed to reach a huge audie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About 1,500,000 Chinese characters in total,Gu-xinsheng-jing encompasses a rich assortment of biblical translations as well as annotations,which account for approximately 20 percent of the content.Some of his annotations make sense of the text in light of biblical exegetic and theological conceptions as conceived by ancient and medieval church fathers,while other annotations allude to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Interestingly,Poirot's very practice of annotating the bible paralleled Chinese scholars'prevailing conduct of annot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Qianlong-Jiaqing period.In practice,Poirot innovatively integrated the Chinese social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ime into his annotations,and quite often ventured to attack pagan beliefs such as Buddhism and commonly held superstitions.This paper makes a focal study of Poirot's annotations of the Gu-xin-sheng-jing and,by means of observing Poirot's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annotating,tries to analyze how Wester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ceptions may confront,conflict,or coalesce with Chinese culture.
Gu-xin-sheng-jing,Louis de Poirot,Biblical exegesis
郑海娟,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明清传教士、《圣经》汉译等研究。电子邮箱:zhenghaijuan@126.com。
* 两位匿名评审人针对本文的修改提供了宝贵意见,笔者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