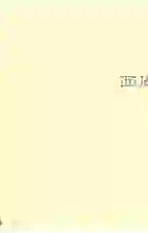珍珍在幸福路
2014-11-13张漫青
张漫青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个废弃多年不用的邮箱。想着密码应该都忘了,但事实是我毫不费力就输入了密码。这个也不难解释:密码并没有失去,而是一直藏在下意识里。我善于给生活细节中的疑问找个无伤大雅的答案,就像丧偶的男人为孩子找个后妈一样理所当然。
打开这个邮箱,竟然有一封未读邮件,时间是五年前的九月份。发件人是陌生的。我打开这封邮件:
小萱,你好。
你一定会很好奇我怎么会写信给你。昨晚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你美丽的倩影。
昨晚见到你,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时刻。你太特别了,我很少这么开心的。至于珍珍,我几乎可以视而不见了。
你昨晚谈到很多有趣的事情,真过瘾啊。当时你还问我有没嫖过娼,你那么直接,那么可爱,完全打动了我的心。
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盼望能再见到你。
等待你的回信。
方志伟
这封邮件让我的脑子短时间内进入了浅回忆。我皱眉眯眼,一副思考状。哦,可能是他,应该是他,他是谁?他是“方志伟”,但方志伟是谁?
我关了邮箱,给小兰拨电话。小兰是我的同学,在老家当个公务员,她是我现在唯一还会偶尔联络的同学。
寒暄之后,我问小兰是否认识一个叫方志伟的人。小兰想了一会儿说,哦,是他呀,就是珍珍的前男友呀。我问,哪个珍珍?小兰说,高珍珍啊,咱们的高中同学啊。我猛地想起来,噢,高珍珍啊,又高又胖的珍珍啊,她现在怎么样?结婚了吗?跟方志伟还是跟别人?
小兰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后说,你真的不知道?
我问,知道什么?
小兰说,高珍珍五年前就死了。
我说,啊……怎么会?发生了什么事?
小兰说,具体我也不知道……听说是心脏病突发,送去医院抢救几个小时没醒过来……
我说,原来她有心脏病啊。
小兰说,不是,原来她并没有心脏病,后来拼命吃减肥药,心脏才受不了的。都怪她那个男朋友,整天嫌她太胖,你知道她好不容易找到个男朋友,为了取悦于他,她花了不少钱去买那个什么减肥药。
我说,唉……女人太傻了。
小兰用气愤的口吻说,珍珍死了没多久,那个男的就又找了一个。
我骂道,妈的!
小兰又问,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讲?
我说,什么事?讲吧!
小兰停顿了一下说,珍珍曾经为了你跟她男朋友,也就是那个方志伟大吵了一架。
我吃惊道,不会吧!我好像只跟方志伟见过一面,我连他长什么样都忘了。
小兰说,具体我也说不清,反正珍珍是那么说的,那阵子她老提到你,她好像在心里跟你较劲,虽说没多久你就离开了老家,但她还是会时不时地跟方志伟聊到你。
我说,噢,这事有点无聊,他们好端端的聊我干嘛呀?说实在的,我跟他们都不算熟……
读初二那年,我第一次喝酒,是跟一个叫珍珍的同学一起在我家楼下的小花圃里。这是另一个珍珍,不是那个胖珍珍,这是一个瘦珍珍。瘦珍珍是我的初中同学,胖珍珍是我的高中同学。
那天晚上,天气死热死热,一点风都没有。忘了是谁提议一人买一瓶啤酒,降降暑。瘦珍珍的头发是天然卷,细条身段,在班级里寡言少语,成绩总是倒数几名。她几乎没有朋友,唯独跟我还能说上几句话。我是一个怪人,所以我吸引了怪人愿意对我掏心掏肺。虽然我并不喜欢看别人的日记,但已经有五六个同学主动拿自己的日记给我看。不过这个珍珍并没有对我掏心掏肺,她没有拿自己的日记给我看,而是在某节体育课之后请我吃根冰糕,或者下课的时候拉我一起上厕所。
第一次喝啤酒,我们模仿大人的样子,举着酒瓶往喉咙里狠命地灌。那时候觉得啤酒很苦,不好喝。其实现在也这么觉得。我们把啤酒灌进肚子里后,头有些晕,但不严重,主要是肚子涨得厉害。我们相视而笑,现在想来并不明白有什么值得去笑。珍珍蹲在一丛灌木边,呆呆地不知在看什么。我坐在旁边的石凳子上,用鞋子在地上胡乱摩擦。我们都不吭声,一方面啤酒占了我们的肚子,另一方面天气热得我们头脑发昏。一片热寂中,珍珍突然问,你知道我家住哪里吗?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嘢。她摇摇头说,其实不重要。
珍珍是转学生,被安排在班上最后一排。没有同桌,孤零零地上了半学期的课,许多同学才发现她的存在。她说我是第一个主动找她讲话的人。我向来喜欢注意孤独的人,觉得他们比热闹的人更有趣。某次下课,珍珍孤零零地趴在课桌上,我坐到她旁边,问她怎么了。她说肚子疼。在我的印象中她的脸色一直黄黄的。我很懂事地没再问什么,陪她一直坐到上课铃响。我在班上不缺朋友,大多数时候我跟他们玩,偶尔才会跑去找珍珍聊几句。珍珍不爱说话,我们聊的东西很有限。我对她一无所知,如果她也把日记给我看,或许我会知道得多一些。我也写日记,但我从来不会给别人看。那些把日记给我看的人,虽然莫名其妙地信任我,但我认为是一种天真。
在花圃里喝着啤酒,珍珍突然站了起来,说,我好像听到了脚步声。我说,有人的地方当然有脚步声。她又摇摇头,卷发一晃一晃的,与身边的树影呼应着,仿佛是植物旁边的动物。沉默了许久,她说,我挺害怕的。我竟然咯咯笑起来,说,珍珍,你太忧郁了,我们还小,不能想那么多。
然后,珍珍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都放假在家。我忙着写作业和喝绿豆汤。星期一到学校,就听到一件事:珍珍割腕自杀了。
我开始为这件事找答案。后来听到一个传言,说珍珍自杀是因为被人搞大了肚子。我不认为这算一个什么答案,但我开始学会琢磨事情,我反复地想,珍珍那天晚上问我“你知道我家住哪里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对她家“住哪里”表示感兴趣,我甚至觉得如果我知道了她家住哪里,她就不会割腕了。
我很顺利地读完初中,顺利地读完高中,然后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北方的大学。在大学里,睡在我下铺的是一个开朗的北方女孩。她头发又短又粗,像刺猬一样可爱。爱吃面条和土豆,成天叽叽喳喳,一笑起来就露出又白又大又整齐的牙齿,并且每次都露出两排,绝无例外。她身材矮胖,眼睛小,加上刺猬头,无论怎么开朗,都让人觉得像一个无辜的小动物。
有一次我感冒了,没去上课,宿舍里只剩我一个。外面下着雨,这使我很空虚,我空虚的时候就会变得脆弱,脆弱的时候会尝试去干莫名其妙的事,比如我跳下床,坐在下铺的碎花床单上,觉得很没意思。就蹲下来,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皮箱子。我打开皮箱,在衣服、公仔、手电筒和旧杂志中找到一个本子。即使不打开,我也知道这是一本日记本。我太熟悉这种属于日记本才有的私密气息了。
令人意外,小动物一样无辜的北方女孩一点也不无辜。她的日记本里有令人心惊肉跳的性幻想,也有阴暗恶毒的谩骂与诅咒。脏话和粗语淅淅沥沥,绵绵不绝,我忍不住朗诵了几句,再配上窗外的嘀嗒雨声,在感冒特有的一种眩晕里,我仿佛遭遇了诗。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开水,看热气在日记本上袅袅如烟,在北方的冬天,这是常有的景象。北方女孩写了她的暴君父亲,写了她善良但不勇敢的母亲,写了企图占她便宜的邻居老头,最后写到了她的表哥,然后是珍珍。
噢,又一个叫“珍珍”的。我不明白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叫“珍珍”的女孩。
北方女孩写珍珍是表哥从烂货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贱人。她在“贱人”后面加了五个感叹号。她写珍珍动不动就坐在表哥的大腿上,怀疑她屁股里装了一个老鼠夹。写表哥为珍珍一颗一颗地剥瓜子壳,把瓜子仁一粒一粒地送进她鲜红的嘴唇里。她写珍珍浑身上下没有一根骨头,眼睛里却长满了刺刺的骨头。
我在自己的笑声里和感冒的昏沉里,一页页地看着日记。北方女孩的日记本充满嫉妒和愤怒,与她平日里所呈现的判若两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很粗疏平常的事,每个人都不是别人可以想象的。但我把眼睛定在了一行字上:
表哥失恋了,喝醉酒跑到那个贱人楼下大喊大叫。表哥在门牌“幸福路32号”底下喊得嗓子都烂了,她也没下来。
我顺利地大学毕业,顺利地回到老家,顺利地失业了。
我的高中同学小兰和胖珍珍(瘦珍珍早已死去)跟我同时大学毕业,但她们都有了去处。胖珍珍被安排在她父亲的单位,一个银行的营业厅。小兰被安排考公务员,笔试过了,正等待面试。我没有被安排在任何单位。珍珍和小兰都有男朋友,我没有。我们三个在一起谈论的是时髦衣服、工作、男朋友和正在放映的电影。偶尔也聊一聊张爱玲,但聊得很粗浅,主要是胖珍珍提起的,她说张爱玲很霸气。我和小兰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
珍珍个子高,小兰说她应该找一个高个子的丈夫。我说,夫妻两个有一个高个子就够了,不能浪费资源。珍珍说她男朋友就是高个子。小兰问,你会跟他结婚吗?珍珍说,你们还没见过他吧,有空大家见个面。
大家都有空。小兰没带男朋友来,她带了一个追求者,男的,她说他很帅。整个晚上气氛怪异,我有点烦,但笑得哈哈的,大家都喝了一点酒,在老家最有情调的一个小酒吧里。
珍珍的男朋友确实很高,也很瘦。珍珍在他旁边更显胖硕。整个晚上我一直坐在一张秋千椅上,双手扶住两边的秋千绳,看着眼前的两对情侣(小兰和追求者之间算不算情侣持保留态度),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秋千椅不稳,坐在上面并不舒服,但我不想站起来。两对情侣显得矜持而愉快,随着杯中酒匀速地被喝进肚子里,他们的话越来越多了,但话题仍陈旧而无聊。
珍珍穿着一件蕾丝边黑色上衣,豆绿色筒裙,裙子底下两条圆圆的粗腿踏实而真实。在我的记忆中,珍珍的腿是那天晚上最真实的存在,可以这么假设,没有珍珍的腿,就没有那个夜晚。
小兰很擅长装扮自己,这也是她总有不少追求者的原因。眉眼精心描画过,口红恰到好处的红。头发烫得很有弹性,一浪一浪地细腻翻滚。墨绿色打底裤把两条腿绷得纤细修长。
那时我还没学会化妆,头发随意披着,穿着显不出体型的宽松暗色上衣。我荡着秋千,荡出一阵歪歪扭扭的哀伤。哀伤的内容,与我对未来的空洞想象有关,是自怜自艾、嫉妒、无聊和玩世不恭的杂交物。
当两对情侣谈起自己的工作单位或将要进入的工作单位时,我想到的却是更加迷茫而深邃的问题:这个聚会为什么是五人,而不是四人或六人呢?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中间会挤进来一个莫名其妙的我?
两个小男人小心翼翼地喝了一点酒后,就开始抽起了烟。两个小男人之间无话可说,两个小女人之间也无话可说,但四人之间却喋喋不休、细细碎碎、呵呵哈哈地说了一个晚上。谁也不知道交谈是如何展开和叠合的。
珍珍几乎每句话都有一个“方志伟”开头,比如她说“方志伟,你觉得怎么样”、“方志伟,这首歌很好听”、“方志伟,洗手间在哪里你知道吗”。
但方志伟从来不用“珍珍”开头。他提到他单位的清闲,家里房子的再装修,以及前女友的小鸟依人。珍珍始终淡淡地笑对方志伟。
方志伟脸色苍白,虽然个子高,坐下或站着都窝着上身,仪态不好看,话不算多,眼珠子骨碌碌转得很勤快。他突然递给我一支烟,我不紧不慢地用食指和中指夹住烟。他把打火机递给我。我吸了一口,吐到天上去。一边说,我不爱烟,不爱抽,不爱抽烟。
在五人的聚会里,小兰的追求者始终面目模糊。珍珍的男朋友方志伟有一张方脸,一个中正的鼻子,眼睛大,眼珠小,眼珠像水里的两粒鹅卵石。小兰的追求者穿白衬衫和黑西装,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男人。方志伟穿黄色衬衫,下摆塞进咖啡色长裤里,显然是一个虽没见过什么世面却渴望去见世面的男人。
方志伟的眼睛是什么时候从鹅卵石变成鱼泡的,我一点都不记得,当然也不在乎,只有那个大鸟一样依偎着他的珍珍才会在乎。但方志伟对珍珍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那个晚上,珍珍的话挺多,她一开口,方志伟就把头歪离她那边。开始珍珍并未感觉到,后来也没感觉到,也许永远都感觉不到。
鱼泡眼是所有眼睛里最不受欢迎的一种,它们长在方志伟的脸上,却有着说不出来的协调感。小兰的追求者喜欢谈论工作的事情,他是一位人民教师,他问方志伟在哪里工作,后者回答得很轻飘,谁也不可能听得到。珍珍替他重说了一遍,她像他的母亲或保姆一样,温柔地说,他呀,他在医院里做内勤。小兰的追求者想知道内勤具体是做什么的,被小兰打断。小兰的鞋跟可真高啊,我一个晚上都在替她的脚担心。
我坚信五人聚会比任何一种聚会都无聊。酒吧放着爵士乐,老外歌手嗓子沙哑含混,像一颗橄榄在喉咙里百转千回了几个世纪。我看着光鲜靓丽的小兰以及她西装革履的追求者,又低头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明显的污垢。我觉得什么都不会发生。
时间不算太晚,两对情侣没有谁提出离开。我认为他们应该有下一场活动,做真正适合情侣的事。我决定说些什么,然后把一切结束掉。
于是我吐了一个不成形的烟圈,问他们中的两个男人,喂,你们,嫖过娼吗?
所有人都笑了。包括酒吧里的陌生人。但他们笑他们的,我们笑我们的。
小兰和珍珍把笑收好,整理皮包准备离开。小兰的追求者像贴身保镖或哈巴狗一样不离小兰左右。只有方志伟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看着我,鱼泡眼睁得很大,填满鼓鼓的求知欲。
我挥挥手说,有空到S城(我上大学的城市),我带你们去嫖娼!
方志伟哈哈哈哈大笑不止。其他人的表情掩没在了夜色里。
大学毕业后我辗转了几个城市,后来有个朋友介绍我到一个南方城市郊区的一家罐头厂上班。这家罐头厂不大,待遇也不算好,我稀罕的是可以包吃包住,要知道我东奔西走那么 久已经受够了租房子这种事。后来发现这家罐头厂周边环境不错,依山傍水的,算是一个惊喜。最惊喜的是,罐头厂员工不多,有多余的房间,这样我就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单人宿舍。
这家罐头厂不但生产人吃的罐头,也生产狗吃的罐头。当然我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不参与罐头的直接制作,只是我注意到狗罐头的包装远远比人罐头的包装漂亮得多。
在罐头厂待了两个月后,我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了,与同事们也相处得比较融洽。每天下班后到厂里食堂吃饭,然后回到宿舍,看看书,洗漱一下,就可以睡觉了。这里的生活总体来讲是平静的,不带一点波澜。
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书,听到隔壁有奇怪的声响。像什么动物被另一个动物摔打的声音,又像有一口痰被憋在喉咙深处郁郁不得志的声音。隔壁住着一个颇有姿色的中年妇女,我们曾经寒暄过几次,听她说她老公孩子都在老家,她自己一个人跑出来打工。她曾经问我一个人住害不害怕。我说,为什么要害怕?她说她刚来的时候很害怕,现在好多了。我说,害怕是一种主观感觉,跟外界没有任何关系。她又问,你是大学生,怎么不到大城市大公司去工作?怎么会跑到这种荒郊野岭的鬼地方来?我说,现在的大学生像饭粒一样平凡而渺小。她愣了一下,可能是对我用“饭粒”这个比喻感到有些陌生吧。
她好像很渴望跟人说话,但是在我面前却欲言又止的。她曾经在下班后请我去她宿舍坐坐。她宿舍里杂物很多,像住了很久很久的样子。我觉得自己被请到别人家做客,就有义务关心别人一下,于是就问,你想你老公和孩子吗?她叹了口气说,怎么不想?然而却没有按一般人的常理那样打开话匣子。
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但脸上还残留着姣好的五官轮廓,皮肤白白的,身材也颇有风韵。我说,你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吧?她笑了笑,摇摇头,又点点头,对我说,我是过来人,给你一个忠告吧。我笑着说好啊。她说,也没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别太自以为是了,毕竟青春是很短暂的,有时候睡一觉第二天醒过来就老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兴奋地说,你这么美,年轻时一定害过人,所以才说这样的话。
她并没有被我的笑声感染,冷冷地说,你猜错了,我没有害人,我是被人害。
我觉得气氛不太融洽,坐了一会儿就找个借口告辞了。之后也很少碰到她。
那天晚上隔壁的声响虽然有些奇怪,但第二天我就忘了。
后来另一个同事跟我聊天,我无意中问起了隔壁女人的事,这个同事就告诉我关于她的一些事。原来她十几年前就在这家罐头厂上班,因为姿色出众,被老板看上了,做了他的情妇。后来老板看上了更年轻的女人,就冷落了她。但她不甘心,一直不离开罐头厂,老板拿她没有办法,即使她没事可做,也得对她管吃管住。
这是一个极其俗套的故事,这个女人除了倔强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个同事还跟我说,老板其实是个好人。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好人?他说,老板爱狗,咱们厂狗罐头的生产量是全市第一,质量也是第一。他又说,老板前几天丢了一条狗,难过得好几天都没来上班。
我突然想到,那天晚上隔壁发出的声响,会不会跟老板的狗有关?
我问同事,老板养了几条狗?
同事说,几条我不知道,反正不少。而且每条狗都有名字,老板经常牵着狗到厂区花园散步,嘴里有时喊“花花”,有时喊“甜甜”,有时喊“娇娇”,哈哈哈,好像都是女人的名字。对了,那只丢掉的狗,名字好像叫,叫什么珍珍的。
珍珍?我大吃一惊。
对,就叫珍珍。同事笃定地说。
上高中的时候,胖珍珍曾跟我说她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后来小兰问我是否知道珍珍的秘密。也就是说,小兰也知道胖珍珍的秘密。
我记得,当初为了得到这个秘密,我到珍珍家里听她唠叨了几个小时。珍珍一直在咳嗽,但我们把脸凑得很近。第二天我开始咳嗽,接着喉咙发炎肿痛了一周。后来我总结,这个秘密确实可怕,且深刻,且带有病毒。
当时珍珍喋喋不休地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胖吗?我说,你其实不算胖。珍珍反复地说,她如何早熟,初中时就有如何多的男生注意她,并且给她写情书。在这样的氛围下我鼓足勇气承认她是个标准的美人。后来我总结,这句恭维是我为了友谊作出的最大牺牲。
我原来可没那么胖。珍珍说,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但你不能告诉别人。我赶紧点头。
于是珍珍告诉了我这个可怕的秘密。这个秘密让我难过了一个晚上。我没想到珍珍是个悲剧人物,我原先一直以为悲剧总发生在美丽的瘦子身上。
后来珍珍说她要减肥,因为只有减了肥才能得到幸福。我不同意,我说幸福跟胖瘦没有必然联系,我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这个论点。但珍珍沉迷在自己对幸福的概念里,而且她是不太懂逻辑的,小兰也不懂逻辑,女人大多数都是感情动物。
我也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从不告诉别人。这个秘密是:我很无聊,且我的无聊绵长而广阔,抵抗无聊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头扎进书堆里。胖珍珍家里有很多书,但她从来不看那些书,她说那些书是她父亲的,她不会碰。我不管那些书是谁的,我想碰就碰。珍珍的父亲从来都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那些书却在珍珍的房间里。我每次借走三四本书,看完再来珍珍家,还上次的书,然后继续挑选这次要借的书。有时候我在珍珍家里听到男人的咳嗽声,是那种苍老的咳嗽声,这让人怜悯。
珍珍也会时不时地显露出对我的怜悯。她说你的工作怎么办?或说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她会喋喋不休地提起这两个问题,也许是因为她需要对朋友表示关心,也许是因为她需要让对方铭记她拥有这两样东西而对方没有,也许是因为对方从来不回答她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对方回答了但她从来不记得。
五年后的这一天,我看到珍珍的男友方志伟在五年前写给我的邮件,就不得不去想珍珍那个可怕的秘密。其实这个秘密无需回忆就轮廓鲜明。除了这个秘密,其他任何回忆都虚假得可怜。珍珍在我的回忆里注定再次遍体鳞伤。珍珍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被自己的父亲,也就是那个拥有苍老咳嗽声的男人强奸了,然后她失眠、吃药,副作用就是发胖。
珍珍认识了方志伟,为他堕过胎,并且为他一次次地减肥,虽然她认为减肥是为了得到幸福,但我不明白为减肥丢了命,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方志伟在珍珍死后,湮没在人群里,结婚生子,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觉得,任何幸福都不该太便宜。比如,五年前的那封邮件,不能总悬在上面,应该有人用石头把它砸下来。比如,五年前的珍珍,应该像个真正的悲剧人物那样,在五年后大放光芒。
我在罐头厂待了半年就辞职了。有人问我是不是觉得没有前途才离开的,我说我对前途并没有什么想法,但对罐头厂生产的罐头渐渐有了想法。但我没有告诉他,自从罐头厂老板丢了那条叫“珍珍”的狗,我每次看到狗罐头就会强迫性地认为珍珍就藏在这罐头里面。
我再次失业,到了另一个城市,因为工作很难找,我租了最便宜的房子,而且是跟三个陌生女孩合租。每天一醒过来就开始在各种报纸的夹缝里寻找招聘信息,打电话,或在网上投简历,等消息,或胡乱穿衣梳洗,搭公交车,然后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地去面试。回到出租屋有时是前半夜,有时是后半夜。无论我回来得多晚,客厅都亮着灯,那三个女孩要么坐在沙发上边嗑瓜子边看电视,要么就坐在卧室床上叽叽喳喳地打牌。等我洗漱完毕准备上床睡觉时,她们才不慌不忙地开始梳妆打扮,用比普通话流利几百倍的家乡话说说笑笑。我听不懂她们的家乡话,每天晚上我只等着她们打扮完赶紧离开这个屋子,这样夜晚才能彻底安静下来,我才能捂上被子睡个好觉。
她们白天睡觉,夜里上班,很显然是干特殊行业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鸡”。跟她们合租房子,我早有心理准备,我们这个片区的房子是全市最廉价的,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赌徒、混混、农民工和鸡。没错,住在这里挺危险。但我很穷,没有工作,而且不愿回老家,所以我配得上这份危险。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上街,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说我命硬,心肠也硬,将来会很麻烦。我记得他头戴一顶破毡帽,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墨镜,神气十足,好像知晓天下事,跟算命先生的形象完全吻合。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活得胸有成竹的人。
合租时间长了,我跟她们渐渐熟了起来。我很难记住她们的名字,一是她们家乡口音太重,二是她们这个行业一般都会用“艺名”。我搞不清她们的名字是真名还是艺名。她们中间有一个留着刘胡兰式的齐耳短发,看起来很朴素,走在街上完全没人会觉得她是干这个的。她说现在流行清纯,她这个样子很受欢迎,有些客人还以为她是大学生。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陈素娟,名字也挺朴素。相比另外两个浓妆艳抹的女孩,我更喜欢陈素娟一点。
有一天晚上陈素娟没有上班,我们买了些啤酒和卤味,边喝边聊。
陈素娟说,你工作怎么还没找到啊?
我说,很难,没准一直都找不到。
她说,早知道你就别读什么大学。
我说,为什么?
她说,读了大学,人就有了傲气,找不到工作,又没法跟我们一样,想低也低不下去。
我说,我可以低下去,我现在已经很低很低了,不然怎么会住在这个鬼地方?
她说,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我说,我连工作都没有,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你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我就好了。
她说,等我存够钱,就不干了,回老家去。
我举杯说,祝你成功!陈素娟!
她说,以后别叫我陈素娟,这个名字太土了。
我说,不土,我喜欢。
她说,但我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珍珍。
我说,珍珍?
她说,珍珍,珍贵的珍。
我赶紧问,你老家有没有一条街叫“幸福路”?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珍珍,我终于找到你了!
她说,你为什么要找我?你以前认识我?
我说,你家是不是在幸福路32号?
她说,不是,我家在农村,幸福路是城市里的路名,而且我听说很多城市都有幸福路。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我沮丧地点点头,是的,我知道,很多女孩都叫珍珍。
收到方志伟五年前的那封邮件后,我做了一个梦。
我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方志伟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问他,这五年,你嫖娼了吗?
方志伟的声音在电话里异常鲜活,仿佛刚刚吃了一颗甜润润的喉糖。
他说,呵呵,没想到,没想到是你。我还以为你早忘了我呢。
我幽幽地说,寒暄的话不必说,我只问你,你嫖娼了没?
方志伟说,呵呵,你还是那么直接,哈哈,我喜欢。
我说,你他妈到底嫖了没有?
方志伟说,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我说,我刚刚才收到这封信。
他大叫,天啊。
我说,我现在就给你回信,听着,我在信上说,你害死了珍珍!你是杀人犯!
不,害死珍珍的人是你。方志伟幽幽地说,那天晚上见到你之后,我就不爱珍珍了。我什么都没说,但她很敏感,她什么都知道。
不关我的事。我说。
珍珍很天真,她以为她瘦了就能变成你。他说。
珍珍是个好姑娘。我说。
珍珍是个好姑娘,但我烦透了。如果我没认识你,我应该会跟她结婚生孩子。他说。
不关我的事。
也不关我的事。
你心里没有珍珍,你是一个嫖客。
我的确嫖了,感觉并不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没有一件事情会比想象中更好,蠢货!
我喜欢你骂我。方志伟幽幽地说。
你现在很幸福吧?
什么是幸福?他继续幽幽地说。
在梦的下半部分,我把妓女珍珍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方志伟。方志伟问珍珍,你叫什么?珍珍说,我叫珍珍啊。方志伟在我的梦里大汗淋漓,如梦方醒……
另一个珍珍,走在幸福路上,走进一家酒吧,喝得烂醉,被两个男人带到酒店,她听到他们的对话,一个说,她怎么喝那么多?另一个说,她真够傻。一个又说,够玩很久了。另一个又说,要玩个痛快。珍珍在心里说,蠢货……第二天醒来,两个男人看到床上有很多血,暗红色的,陈旧的血。珍珍展示着手腕上的疤痕说,对不起,血都流干了……
敲门声响起,打开门,服务生抱着一只小黄狗说,先生,这是您的早餐……
服务生脱下帽子,秀发柔顺飘逸,原来是个女人,她扭头就走,走得很快,快得要飞起来,就要离开所有人的视线了,突然回眸一笑,说,有空去幸福路找我……
我醒了。珍珍没有变成真正的悲剧人物,我也没有。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