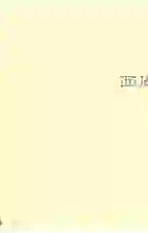当今之中国的理想和现实
2014-11-13郑翔
郑翔
池上这两篇小说的关键词是“艺术”和“理想”。这是两个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词汇。在那个年代,“艺术”作为一种纯洁、崇高的精神理念,和“理想”是紧密相连的,很多人把它当作终身的事业,甚至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语)。那么,在这个广泛使用“拼爹”、“潜规则”等词汇的年代,“艺术”的“理想”将会遭遇怎样的现实呢?这就是池上这两篇小说所关注的。
这两篇小说有着相似的情节框架,但内涵又略有侧重,讲述的是两位以艺术为理想的女性,在理想和爱情方面所遭遇的挫折和应对。《虞美人》中的虞娟娟和《桃花渡》中的阮依琴分别是学舞蹈和越剧的,她们抱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如果没有艺术,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走向了社会,但现实早已发生了改变。正如绍兴舞蹈团的门卫对虞说的:“这年头谁还会看这种正规到无聊透顶的舞蹈呢?”这个存身于锈迹斑驳的大楼的绍兴舞蹈团,也早已只能去下乡演出了。所以,虞娟娟想在“一个充满古老气息的舞台上跳舞”的理想,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她连一个与专业相关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后她看到一个广告,毅然离开老家奔赴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希望为自己获得“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去了之后,她才发现,剧组根本不需要她的舞蹈,只让她跑个龙套,因为女主角是早已内定的。阮依琴离开绍兴去杭州越剧团,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舞台,但剧团同样没人顾及她的嗓音,只让她做做剧务。当然,两个人后来都得到了展示才能的机会,但机会的获得首先并不在于她们的才能,而且她们都付出了自己的身体。虞娟娟获得机会是因为领导想找一个新人压一压那个跋扈的女主角,但为了能保住机会,她忍受了男主角陆帆对她身体的入侵;阮依琴则是被投资方的赵老板看上,而获得了上台当主角的机会。这或许就是当今之中国艺术理想需要面对的“潜规则”。
这两篇小说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爱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艺术理想的追求与对爱情的追求往往具有价值观上的同构性,同样追求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也是虞娟娟开始时的想法。虞娟娟把自己的爱情给了一个有妇之夫,一个不懂潜规则的书法家吴东盛。不过,虞对吴的爱与其说是爱他这个人,不如说是爱他与自己类似遭遇——空有才情却无人欣赏,一种被自己理想化了的献身精神。但现实并不浪漫,吴根本没有勇气接受她的爱情,她的爱情落了空,最后跟一个自己并不爱的老乡回了家。阮依琴为了抓住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没空打理爱情,她拼了命地唱,终于唱得了梅花奖,但也把自己唱成了“资深剩女”,最后随便选了个人草草结婚。对待爱情的态度虽然不同,但结局却很相似。爱情也早已丧失了它的纯洁性和崇高性。
理想和爱情上的失落,使这两篇小说的叙事带有明显的怀旧和感伤气息。在叙事过程中,小说不断地把当下和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作着比较,并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失落。这两篇小说都为女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在乡下驻守自己理想的老师。上一代和这一代,乡下的单纯和城市的复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获得更大的舞台,她们不得不走向城市,因为她们已经看到,商品大潮的冲决而来,已让乡下的驻守难以为继,但城市里又没有她们的理想家园。她们陷入了精神两头无依的窘境。在《虞美人》的末尾,当虞娟娟回到故乡西塘时,她看到:“整座古镇上每家每户门前都挂上一串新的红灯笼……成片成片,红灯笼把这座小镇仅存的那点古韵给弄没了。红灯笼把古镇点成了一片扎眼的血色,肆无忌惮。”它和李煜的《虞美人》一样,都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美好年代的一曲挽歌。
不同时代的比较,让池上的这两篇小说,超越了当下很多小说只是局限于对某人某事的具体叙述和情绪发泄,把一个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涉及时代精神症候和人的灵魂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是具有相当的尖锐性和深刻性的,是一个比较高的起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提供的几个在当今之中国同样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怯懦,具体表现为对理想和尊严的不能坚守。虽然虞和阮都觉得艺术的理想要高于生命,但那其实只是她们没有遭遇现实时的想象,在这一点上,她们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之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那个时代,艺术之所以成为很多人的理想,不但是因为艺术中所有的浪漫情怀,更因为他们把艺术的唯美、崇高看作是一个超越世俗的精神高地,也是人的尊严的象征,所以他们高傲、坚忍、充满激情,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决不妥协。但虞和阮显然更加现实,在她们这里,艺术和理想的内涵实际上都已发生变异,那就是争得演女主角的机会,所以她们对身体的入侵者几乎不做任何反抗,她们的内心实际上也早已默许了“潜规则”。在爱情上也是一样,虞娟娟的追求实际上只是一种不谙世事的冲动,所以,当她遭遇了理想和爱情上的一点挫折,“忽然间惊觉,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她个人的一场华丽赴宴”之后,马上就放弃了一切,跟着自己并不爱的冯朝回了老家。类似的是阮在爱情上的“退而求其次”;还有困惑于家庭生活“怎么就过成了这样”但仍决定忍受的吴东盛;还有高大英俊本该演岳飞却被潜规则为小梁王,被虞娟娟侮辱拒绝,却仍整天带着笑容跟在她身边的冯朝;还有被阮依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没有一丝火气的潘志文。总之,人之为人的追求、坚守、尊严和血性,在他们身上已经几乎看不见了。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概括过中国人性格的两个字——卑怯。在强大的现实法则的制约下,中国人正在日益丧失理想情怀、坚守的品德,以及他们的尊严感和血性。小说对当下中国人这一普遍性格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不过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对这些人物的行为进行批评或谴责,而在一种略带同情的客观呈现中,表达了一点无奈和感伤,这或许是一种比较普遍的“80后”作家面对现实的态度。
这两篇小说在主题、人物性格和设置,甚至结构上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相比而言,《虞美人》故事简单,主题更为单纯集中,所以稍显空灵,具有一定的隐喻性;《桃花渡》更质实,更及物,内容更丰富,涉及人物面对欲望和处境变化时的内心变化和现实应对,以及对不同处世态度的得与失的思考等,但是因此也使小说的线索、主题略显芜杂和不集中,有点为事所拘。
这两篇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语言简洁和准确性方面的提炼,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的建立等。比如,“不算太宽,也不算太窄”的河,“不轻也不重的病”,“一个很撩人的姿势”,都不是具体、准确的表达;比如,“快到家的时候,一场绵长的秋雨悄无声息地降了下来,轻易地就将阮依琴打湿了”,一个即时的时间和“绵长”,“绵长”“悄无声息”和“轻易地打湿”之间,都是存在矛盾的;再比如“绵长”和多处出现的“多年以后……”等别人已使用或模仿多年的陈词滥调,应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