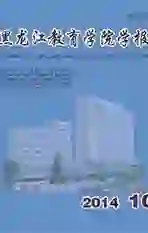《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主题和叙事特征
2014-11-10袁秀萍
袁秀萍
摘要:《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代表了福克纳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福克纳运用现代主义写作手法,通过艾米丽的悲剧人生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南方人矛盾的精神世界,探索人类心灵冲突这一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艾米丽;主题;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10-0121-03
引言
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这段时期,随着欧洲现代哲学文学思潮如精神分析学、象征主义、意识流等相继传入,美国文学在民族文学建立的基础上,迎来了现代美国文学最辉煌的时期。伴随着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同的文学流派应运而生。“南方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被称为“美国南方文学之父”的威廉·福克纳正是生活在美国南方经历深刻社会历史变革的时期,他的思想也由此打下了时代特有的烙印。独立成篇的19部长篇和70部短篇组成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描写他熟知的南方人物、历史与事件,通过反复出现的主题,小说浑然成为一体,集中反映了南方各阶层人物在两百年来社会历史变迁中典型的精神面貌及心理状态,特有的乡土人情观念跃然纸上,堪称描写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史诗,宏伟浩瀚而又荡气回肠。因为对当代美国文学艺术卓越的贡献,1949年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地位卓绝,对他的文学研究仅次于莎士比亚。在福克纳“世系小说”这顶桂冠上,短篇小说可谓是镶嵌在长篇巨著周围的璀璨宝石。“这些短篇小说以虚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感人至深的主题、深邃的道德寓意,以及小说文本与叙述手法的多样性和艺术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1930年发表于《论坛》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是福克纳最负盛名、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以历史的笔触再现了以艾米丽为代表的美国南方妇女的悲剧命运,表现了他对南方社会的反思和对南方妇女的关怀,同时强烈抨击了当时南方盛行的迫害妇女的父权制度和清教主义妇道观。
一、《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主题
文艺作品通过描写人物的心理、行动、言语及相互间的矛盾来表现主题。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内战后的南方作为作品展现叙事主线的特定历史场景,福克纳通过所有叙事铺垫向读者暗示:艾米丽的不幸更多应归因于当时的整个南方社会,而不仅仅是她个人。福克纳通过揭示艾米丽无力摆脱发生在现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如何煎熬影响其内心世界,使其堕落和变态,来展示一代南方人在同样的社会矛盾背景下中相似的人生经历。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艾米丽在父亲死后,就与世隔绝地独自居住在父亲留下的破败大木屋里,只有一个哑巴黑人管家。她中断了与外界的任何接触,拒不理会社会发展变迁:不装信箱,不缴赋税。40年过去了,她孤傲地终老一生,镇民们为她送葬之后,怀着好奇心终于进入一向封闭的大木屋。打开一间幽暗神秘的卧室,一套白色结婚礼服映入“我们”眼帘,一具干腐的男尸骇然躺在床上,旁边的枕头窝还有一撮花白的女人长发,似乎不久前刚有人睡过。原来她一直与被她毒死的情人荷默·伯顿的尸骸同床共眠。父权主义思想传统在南方社会根深蒂固。在她身上,不仅有传统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延续,还有她在传统的桎梏中挣扎的绝望。她是父权主义思想和清教妇道观的牺牲品。“美国南方保守的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也从宗教的角度维护父亲作为家长的统治地位。”[2]艾米丽父亲生前“赶走了所有青年男子”“抢走了她一切”,即便死后仍然左右着艾米丽,她有的只是与世隔绝的孤寂和“父亲的炭笔画像”。这个“神化”的权威剥夺了艾米丽选择生活的自由,她只是家族、财产和荣誉的一部分,代表了无力挣脱男权主宰下的社会中女儿们的悲剧宿命。“父亲”在小说中从未以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出现,但他的影响却贯穿始终,深远而无处不在。在“我们”的印象中,“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父辈手中的马鞭驱走了她的青春,孤零零留下她成了一名老处女。当父亲去世时,她坚持了三天,坚决不许“我们”埋葬死去的父亲。作为南方父权的典型形象,他成功地牢牢控制了女儿的一生。
清教妇道观在艾米丽身上也刻下了烙印。对妇女贞操的崇拜是美国南方清教妇道思想所极力推崇的,妇道观要求女人应该没有激情、没有性欲。上层社会的白人妇女只能成为“冰清玉洁”的淑女,她们的贞操高于一切,背负着历史、家族和传统的荣誉。男人们极力要维护的首先是妇女的贞洁和清白,而不是她们的生命或权利。浓厚的妇道思想使美国南方变成了比新英格兰更为清教化的地区。“淑女风范”旨在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她们没有自我,无力掌控自身命运,几乎谈不上什么自由,只会保持淑女的骄傲和矜持,却无力面对生活。艾米丽与生俱来注定要活在沉重的枷锁下做她姓氏的淑女。她只有过去,面对变革和现在无所适从,只能关紧了大门,傲视拒绝一切新生事物,保持过去拥有的虚幻的辉煌,体现了她对清教教义的无能为力。从始至终艾米丽代表的是传统的化身和义务的象征,更是被关注的对象。代表了杰弗生小镇居民的“我们”一直在叙述艾米丽的故事,对她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倍加关注。当来自北方的工头荷默闯入艾米丽的生活时,“我们”议论纷纷,反响强烈。当沐浴着爱情的他们招摇过市时,“我们”纷纷以忧心如焚的目光关注着他们,“偶像”艾米丽的“堕落”招致了诅咒和不满。表面上艾米丽被人们赋予耀眼的光环,却不被允许有正常女人的需要。而当艾米丽一再和荷默亮相时,人们再也忍不住了,明目张胆地横加干涉,丝毫没有过去的敬畏与忍耐。浸礼会牧师登门劝导,“我们”还联合艾米丽两个傲慢保守的堂姐妹向艾米丽施压,我行我素的艾米丽最终不得不屈服了,不再和荷默公开露面。当伯顿意图离去时,她选择了让他永远躺在自己身边,社会使她异化为非人。“这些人物总是被突如其来或从世代的禁锢中渐渐宣泄遗传下来的传统、环境、情欲,引向悲惨的结局。”[3]艾米丽与荷默的悲剧正是旧南方与新北方,贵族阶级与劳工阶级矛盾深化的象征。几乎没有自己话语权的艾米丽一直是“被看”的对象,由他人即“我们”来描述、确定和批判。如风雨飘摇中的玫瑰的艾米丽的悲剧命运影射出作品深刻的社会内涵和强烈的震撼力量,这正是福克纳思索和苦心营造的主题意义。endprint
二、《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叙事特征
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不一致被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称为“时间倒错”(anachronies)。小说由五个部分构成,福克纳精心构建的故事框架是基于运用五个空间的独特叙述角度和多层次的时间倒错手法,用回忆和闪回来追溯艾米丽神秘的一生,塑造了一位被父权主义和清教妇道观剥夺了一切的女性无力面对现实以至于沉沦变态的形象,反映了新旧南方价值观念冲突的不断激化。福克纳运用意识流、时间倒错、哥特风格、隐喻、象征等手法揭示了作为南方腐朽传统象征的艾米丽的矛盾冲突与她南方古老而辉煌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柏格森直觉主义认为一维性系列(即过去、现在、未来)无法表达人的内心体验,因此这三者之间应相互并列、浸透和倒置[4]。福克纳以艾米丽的去世作为故事的开头,发现伯顿的尸体作为故事的结尾,闪回追叙往事讲述艾米丽及她所代表的旧传统的衰亡,超越于时空的限制自如地安排情节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为一体,极大地激发了读者推敲探究寻求主线的兴趣。相互渗透的意识流、时间倒错和叙述角度变换等现代手法的运用使神秘的气氛贯穿小说始终,读来令人费解难懂,但作者深刻的寓意却尽在其中。第一部分以艾米丽小姐去世了,全镇的人前往送葬开篇;第二部分读者进一步得知三十年前她家宅院曾散发出难闻的臭气以致有人不得不偷偷潜入宅院内去撒石灰粉。艾米丽房子的臭气为荷默的死亡埋下了伏笔,同时也暗喻南方古老传统与道德充满着腐烂和死亡的气息。第三部分则回顾了艾米丽与荷默相爱和艾米丽去药店买砒霜的细节。第四部分叙述荷默失踪了;最后一部分描述艾米丽死后神秘房间内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乔伊斯、伍尔夫和福克纳被公认为意识流大师,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整个事件依照“我们”的记忆、回想去重现,并非按照传统的先后逻辑顺序,可谓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在视角上,全知叙述、内部聚焦和外部聚焦交替使用,运用了“我们”和“他们”作为叙事视角,艾米丽几乎被剥夺了话语权,由他人来解读。讲述者人物和反映者人物“我们”和“他们”交叉回顾叙事,尽管叙述者思绪跳跃不定,但许多时刻通过叙事者内心思维连贯起来,故事发展的准确时间借助文本一些暗示不难推断,这极大地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层次感和真实性。与逝去的南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我们”在讲述的同时也在被读者解读,“他们” 身上折射出来的矛盾寄托了福克纳的南方情结——传统与希望的斗争仍然在持续着。
美国南方传统的哥特式小说可追溯到爱伦·坡。福克纳受其影响,在世系小说如《圣殿》《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中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哥特式手法。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福克纳糅合侦探小说和哥特式小说的特点,借助凶杀、暴力和死亡等刺激的情节和阴森恐怖的气氛来揭示人性深处黑暗的东西。“把人物放到他所创造的特殊环境之中,利用恐惧的特殊力量,打破社会为人铸造的外壳,以便能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揭示人最隐秘的内心世界。”[5]神秘的古老宅院、离奇的女人、死尸、成为墓穴的新屋、消失的哑巴男仆都具有哥特式恐怖小说的特点。艾米丽体面下葬后,“我们”撬开了艾米丽楼上四十年来无人涉足的房间,一片积尘中呈现出褪色的玫瑰色窗帘和灯罩,布置陈设像婚房,细细再看,可见绣着荷默名字的男式睡衣、椅背上的领带、地板上的袜子,最后赫然落入眼帘的是床上的一具骷髅,龇牙咧嘴,惨白可怕,双臂呈拥抱的姿势,阴森恐怖就像一座墓室,这一切生动地揭示了艾米丽隐秘的内心世界和矛盾冲突。“象征”是无形心灵内在生活的外在符号。福克纳借助象征隐喻手法来烘托主题并生动地图解艾米丽的困境。艾米丽的身躯被“我们”看作一尊“偶像”,象征着她行使了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功能并承载着宏大的使命。作为“灯塔守望者”的她很大程度上不能为了自己而存在,她被边缘化了,只能将自己奉献给公众。艾米丽与荷默陷入情网本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艾米丽和其行为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在封闭且等级思想根深蒂固的南方文化里,跨越等级差异的恋情无疑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加之历史的悲情掺杂进了她与荷默的关系中。内战失败的痛苦记忆犹新,人们无法面对南方再次被征服,尤其是他们的“偶像”被征服。艾米丽被强加了太多沉重的象征负荷,她与荷默的交往无疑是在挑战南方社会道德的底线,不仅会动摇老处女的完整性,更是在撼动南方历史、阶级和文化的根基。旧南方赋予艾米丽虚幻的荣耀和真实的漫长悲剧的煎熬。
结语
一度拥有世袭传统和旧经济文化的美国南方先后经历了内战、重建、北方机械文明冲击、种植园经济没落和田园梦破碎,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特征。福克纳以凝练的笔触,独特的叙述结构,将艾米丽这个艺术典型呈现在读者面前,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思索和审视社会历史发展,将特定历史人物置于特定历史时期来再现普遍意义上人类心灵的挣扎与毁灭。用这篇不足五千字的短篇小说成功地表现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主题——美国南方新旧秩序的冲突及南方没落贵族阶级的守旧和衰亡,带给读者深刻而独特的审美体验。福克纳留恋南方的文化传统,割不断与南方的历史渊源;同时揭示南方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罪恶是福克纳永远的主题。“我爱南方,也憎恨它,这里有些东西我根本不喜欢,但是我生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因此我愿意继续维护它,即使是怀有憎恨。”[6]福克纳在代表了短篇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那个夜晚的太阳》、《红叶》和《干旱的九月》中 都表现了对南方深沉含蓄的爱。
参考文献:
[1]H.R.斯通贝克.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序[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614.
[2]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75.
[3]建刚,等.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G].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363.
[4]李常磊.福克纳的时间哲学[J].国外文学,2001,(1):58.
[5]肖明翰.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J].外国文学评论,2001,(2):98.
[6]朱雯.外国文学新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5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