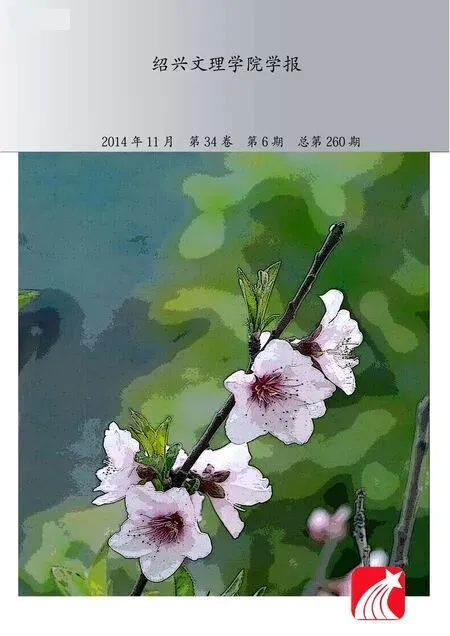“鉴湖文化走廊”论纲
2014-10-26陈民镇
叶 岗 陈民镇
(1.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102400)
“鉴湖文化走廊”论纲
叶 岗1陈民镇2
(1.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102400)
“鉴湖文化走廊”是一道上起六朝下至唐宋、以越文化中心地为中心、立体多维的文化走廊。“鉴湖文化走廊”的发生发展与时代大势息息相关。六朝时期“鉴湖文化走廊”初步繁兴,伴随着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融汇,越地文化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姿、多元互摄的面貌。在唐代,“鉴湖文化走廊”继续发展,并臻于鼎盛。南宋时期鉴湖渐趋堙废,“鉴湖文化走廊”也逐步衰落。
越文化;鉴湖;鉴湖文化走廊
自竺岳兵、邹志方等先生倡导“浙东唐诗之路”以来[1],这一诗歌之路乃至文化之路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我们不妨将时间的幅度拉大,并且不独将视角放在“路线”层面,可以发现,在越文化中心地①的范围内(与“浙东唐诗之路”空间范围有所交叉),在六朝时期已经形成了文化走廊,并延续至唐代以后。故此,我们拈出“鉴湖文化走廊”的概念,指涉这道上起六朝下至唐宋、以越文化中心地为中心、立体多维的文化走廊。之所以以“鉴湖”命名,一是在于东汉马臻围筑鉴湖为这道文化走廊奠定了基础,鉴湖之衰亦与文化走廊之衰同时;二是在于越文化中心地是这道文化走廊的主要范围,鉴湖流域又是越文化中心地的中心;三是鉴湖是越中山水的代表,而这道文化走廊又是以山水为依托的。“鉴湖文化走廊”的发生发展与时代大势息息相关,而越中山水、佛道仙踪、隐逸情结、人文思想的多元汇聚以及本土居民与寓居者的共同创造则是“鉴湖文化走廊”几个基本元素。
一、六朝时期“鉴湖文化走廊”的初步繁兴
在多元文化的互摄与互动之下,六朝时期的越地文化呈现出繁兴的面貌。在此期间,越文化又实现了一次突进,“鉴湖文化走廊”的繁荣是直观体现。东汉筑鉴湖后,“鉴湖文化走廊”逐渐形成。在六朝尤其是“永嘉南渡”之后,“鉴湖文化走廊”初步繁兴。六朝时期越地文化显现出多元互摄的特征,其背后自是六朝文化的多元性使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融汇,越地文化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姿、多元互摄的面貌——这是“鉴湖文化走廊”在本阶段的重要特征。
(一)佛—道—儒—玄的互摄
由于没有定于一尊的理论,六朝处于一个缺乏思想权威的时代,价值观念有待进一步整合,新的思想学术也在孕育之中。“佛—道—儒—玄”的互摄共生成为一条重要线索,不同的思想在摩擦中相互渗透,在冲突中相互融合,开始形成中国思想学术多元激荡的基本格局。这在作为当时思想学术一大中心的会稽,表现尤为明显。东晋时期会稽宗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佛、道两家。在东晋时期,会稽系南方三大佛学中心之一②。当时流行以“诸法空相”为主要义理的般若学,所谓的“六家七宗”[2]除道安的本无宗在北方外,其余六家、六宗均活动于江东,其中有六人在会稽,并以剡东为主要建寺之处。外来的佛教正经历“中国化”的关键阶段,其与北地玄学相交融,并向越地渗透。而道教与越地本土重神信巫的传统信仰有所牵涉,早于东晋就已在越地扎根。至于两汉时期在越地逐渐壮大的儒学思想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由于越地儒学根柢不如中原地区深厚,其他思想也便有了更多的生长空间。
六朝时期儒学虽不如两汉兴盛,但仍有所发展。当时儒学有南、北学之分。与北方儒学固守古文经学不同,南学虽然同样延续郑学,但更多地吸收了老庄思想的精髓。儒家经典的注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贯彻玄学精神的注疏逐渐取代了旧注疏。东晋名士讲求以道释儒,徘徊于“名教”与“自然”之间,道家与儒家思想得到了高度的融合。不过传统的经学虽风光不再,但仍有所发展。三国时期越地的经学较两汉有长足进步,其中首推虞氏,代表人物有虞翻,家传《易》学,曾作《易注》九卷,与荀爽、郑玄并称“易学三家”,时贤孔融因而感叹“乃知东南之美,非徒会稽之竹箭也”[3]。另山阴人阚泽刊约《礼》文及诸注,为刘洪《乾象历》作注,亦为三国越地学人的代表。东晋以后,余姚虞氏、山阴贺氏(先世为庆氏)、山阴孔氏、山阴谢氏等儒学世家又有长足发展。贺循尤擅三礼之学,其后人如南朝的贺瑒、贺革、贺琛、贺德基等亦以治《礼》著称于世;虞喜在研究天学的同时,也涉足《毛诗》《孝经》;孔氏的孔佥、孔子袪等于经学亦有所长。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4],六朝时代尤其是东晋,玄风劲吹。玄学发轫于中原,源自清谈,随着晋室南渡而向江南地区转移,会稽遂成为一大中心。刘宋时期,玄学与儒学、文学、史学一道被列为独立学科。玄学主要依照老庄之学以及《周易》,讨论“道”“无”“有”关系、“本”“末”关系、“自然”“名教”关系等论题。玄学大抵有如下几点特征:追求生命意识的自觉与思想的解放;执着于内在的超越以及对存在意义的本原性追索;呈现出思维的绵密精深。玄学上承道家学说,调和了儒道两家的正面价值,又援佛入玄,使得佛理与玄言相参,有助于佛教的中国化[5]。东晋名士多与高僧交游,而支遁等越地高僧亦精研玄学。玄学与佛学理论上有相契之处,佛经初传多以玄学之术语翻译③,大有佛学玄学化之趋势,而佛理之思辨则进一步刺激了玄学的抽象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玄学是乱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正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所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能、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6]但越地又是乱世的一片净土,会稽山水提供了游心太玄的背景。玄学本身是来自北方的思想学术,但在越地得以更加自如地绽放。它是对传统儒学的反拨,一方面在儒学相对薄弱的越地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越地自王充便已见其端倪的思想批判性与创造力在玄学身上得到了呼应。
(二)山水文化—名士文化—宗教文化的综融
在六朝时期,山水开始真正被赋予审美意涵,成为名士的精神家园,亦为佛教等宗教文化所栖居。越中山水与佛道仙踪一再成为名士心中与笔下的意象,而宗教则影响了山水的改造与名士的心境。
越地山川,钟灵毓秀。刚健如会稽山,婉丽如鉴湖,清奇如天台山,宛转如剡溪,奇崛如天姥山,隐秀如东山,均为中华胜境,吸引六朝名士络绎寻访。王羲之兰亭流觞,支遁剡中放鹤,王徽之雪夜访戴,皆成典故。所谓“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7],“山阴道上”为当时名士心之所系,顾恺之的名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8],实为时人心声。
佛寺多栖名山,越地的佛教圣地亦多依附于秀美山川,如天台山、石城山、沃洲湖等即是。如越地名胜新昌大佛寺,端坐于石城山的峡谷间,初创于东晋永和初年,高僧昙光为领略越地山川,慕名居此。而著名的沃洲,在东晋时期便有竺道潜、支遁等高僧和王羲之、戴逵等名士游憩、栖隐于此,“或游焉,或止焉”[9],为江东佛学中心。道教的目标是“得道成仙”,故多寻觅名山大川。而会稽的山水之美,不仅促成了宗教活动的兴盛和宗教义理的充实拓展,而且还渗透于东晋士人玄学人格的追求与新的山水自然观的建立。越地的不少山水,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若耶溪南旁葛仙翁钓矶据说因葛洪“尝投竿坐憩于此,谢康乐兄弟皆尝游,每至此,酬唱忘归”[10],嶕岘麻溪下的孤潭“上有一栎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11]。他们所游历和寓居的地区,正是会稽山水最美之地,正所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8]。
(三)文学艺术—玄学—山水的会通
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④,主要表现在文学开始从学术中分离、文学审美价值的发现、文体的细化、文学理论的丰富、文学创作与文学集团的活跃等方面。文学之外,其他艺术门类亦得到长足的发展,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也被赋予了独立的品格。伴随着六朝时期的思想解放,士人追求人格之独立,传统经学已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文学艺术成为他们释放玄想的对象。六朝文学艺术的发展,会稽即是重要的策源地。六朝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往往贯注于他们的创作之中,简约玄澹的精神使文学艺术进一步摆脱经学的束缚,确立了独立的品格。
玄风刺激了六朝人对山水的观照,而玄言诗正是玄学与山水相渗透、结合的产物。东晋诗坛以玄言诗为主导,而玄言诗的代表诗人王羲之、孙绰、许询皆寓居会稽。可以说,会稽正是东晋玄言诗的中心,永和兰亭之会产生的诗集《兰亭集》更是玄言诗的一次大结集。兰亭诗或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而抒发玄理,预示着山水诗即将兴起。
山水情结使然,会稽涌现了孙绰《游天台山赋》、谢灵运《山居赋》、支遁《天台山铭序》、王籍《入若耶溪》等山水名篇。与越地结下不解之缘的谢氏为六朝重要的文学世家⑤,涌现出了谢安、谢灵运、谢道韫、谢惠连、谢朓等文学名流。尤其是谢灵运,成为山水诗的鼻祖。至此,山水开始成为文学作品中独立的审美对象。谢灵运《游名山志序》说“山水,性质所适”,他对山水的审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士族身份之上的,这与一般的隐士不同。谢灵运之《山居赋》系用韵文写作的会稽地方志。谢朓则进一步发展了山水诗,是继谢灵运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山水诗人。谢惠连《泛南湖至石帆》对鉴湖的风光作了细致的描绘:
轨息陆途初,枻鼓川路始。
涟漪繁波漾,参差层峰峙。
萧疏野趣生,逶迤白云起。
登陟苦跋涉,瞥盻乐心耳。
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12]
与唐宋文人以鉴湖为主题的诗篇相比,谢惠连的这首诗“字句清峭,兴象华妙,节短韵长,一往清绮”[13],唐宋的“鉴湖诗”也有了上溯的依据。
中国山水画之独立,正在晋末之时。在山水审美意识逐渐加强的背景之下,山水画与理论亦不断成熟,名作、画论迭出。所谓“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6],越地灵秀的山水为山水诗与山水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玄风浸润之下,其时画风高古,追求风神。戴逵、戴颙父子世称“二戴”,长期栖隐于会稽剡县,在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方面皆负盛名,戴逵尤以佛教雕塑著称,《吴中溪山邑居图》系其山水名作。在士人心境转变的背景下,六朝书法得到长足的发展,士人多寄情翰墨,书法理论完善,名家辈出,会稽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尤为典范。王羲之《兰亭集序》被视作“天下第一行书”,这幅书法的创作既体现出当时士人对山水的心仪,同时也透射出他们的复杂心境[14]。名士寓性情于方块字,追求神韵风姿,此时的汉字已远远超越了实用价值,而升华为一门精深的艺术。“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15],这又是文学、艺术内部的互摄现象了。
二、唐代“鉴湖文化走廊”的兴盛期
就人文成就而言,隋唐越地最为绚丽的风景莫过于诗歌的繁荣。在越地绽放的诗篇,是唐诗这一庞大山系中引人注目的峰峦。此前已有不少学者重视“浙东唐诗之路”的现象⑥,我们则认为唐代越地的文化现象与六朝存在一定的呼应,在两宋有一定的延续,殊难将它们割裂开来。我们在前文提出“鉴湖文化走廊”的概念,并强调其有如下几个基本元素:其一,越中山水(以鉴湖为核心);其二,佛道仙踪;其三,隐逸情结;其四,人文思想的多元汇聚;其五,越地人士与寓居越地者的共同创造。唐代“鉴湖文化走廊”的继续演绎,同样合乎上述特点,并臻于鼎盛。以下试作阐论。
首先是越中山水这一载体。自东晋士人“发现越地”以来,“会稽山水,自古绝胜”[16],“越郡佳山水”[17]早已享誉神州。在东汉鉴湖筑就之后,越地“稽山鉴水”的基本自然景观格局确立。会稽山相传是夏禹大会诸侯之地,而鉴湖则如硕大的明镜辉映越地风物。所谓“百里油盆镜湖水,千峰钿朵会稽山”[18],一刚一柔,动静相宜。尤其是鉴湖,经过六朝人的经营,风光愈加秀丽,成为世人心向往之的圣地。“天下风光数会稽”[19],以稽山鉴水为中心,越中山水如无以复制的山水长卷铺展在古越大地。所谓“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9],越中山水多姿而灵动。在东晋士人善于发现美的眼光的烛照下,这方水土被赋予了灵动的生命,号为“山水州”[20]。越中吸引文人骚客的,除了秀甲天下的山水,也有与山水相缠的人文意蕴。在这里,杜甫“枕戈忆句践,渡浙想秦皇”[21],孟浩然“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22],李白感慨句践灭吴之后“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23]。越地深厚的人文积淀,与越中山水实际上已经合而为一。正如王勃所说:“许玄度之清风朗月,时慰相思;王逸少之修竹茂林,屡陪欢宴。加以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或登吴会而听越吟,或下宛委而观禹穴。”[24]李商隐亦云:“越水稽峰,乃天下之胜概……思逸少之兰亭,敢厌桓公之竹马。况去思遗爱,遐布歌谣,酒兴诗情,深留景物。”[25]在唐人的眼中,越中山水是厚重的,也是神秘的,孟浩然在渡钱塘江时发出“何处青山是越中”[26]的疑问,不无倾心与迷惑。
对于唐代诗人而言,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前贤的足迹,回望魏晋的同时,追寻心中的越中山水——这是唐代文人的一种情结。永和九年的那次雅集令唐人心向往之,“遥想兰亭下,清风满竹林”[27],“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乡心万里赊”[28]。“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29],“入剡寻王许”[30],谢灵运等前贤的足迹也为唐人所追寻。可以说,在“鉴湖文化走廊”的背景下,唐人是六朝人的隔代知音。
越中山水如巨大的磁场,令唐代文人流连忘返。杜甫“壮游”越中的经历,使其“欲罢不能忘”: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杜甫《壮游》(《全唐诗》卷二二二)
李白对越中山水也是情有独钟,“遥闻会稽美,且度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32],越中山水一再入诗人的梦境:“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31]在送友人往越中时,李白对越中山水可谓如数家珍,俨然是资深的导游:
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
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
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
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
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
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
——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全唐诗》卷一七五)
面对越中的秋色,李白动情地写下“越水绕碧山,周回数千里。乃是天镜中,分明画相似”[31],在寄情山水的逸兴中,也隐隐透露出消极的意绪。会稽山、鉴湖、剡溪、天姥山、天台山、若耶溪、越台、禹穴等是诗人们笔下的常见意象,也是他们寄托的对象。越中山水是立体的,六朝的世人可以说是最早“发现越地”,令越中山水声名大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唐代则是诗人团体集体性地“感受越地”。
虽然“鉴湖文化走廊”在六朝已经形成,但与鉴湖相关联的文化内涵,在唐代才成熟定型[32]。无论是越地的本土诗人还是入越中游历的骚客,鉴湖始终是人们最热衷描绘的对象: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李白《子夜吴歌·夏歌》(《全唐诗》卷一六五)
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
——李白《越女词五首》(《全唐诗》卷一八三)
三百里鉴湖频频成为诗人们笔下的意象,而唐宋的“鉴湖诗”实际上要追溯到六朝。“犹闻可怜处,更在若邪溪”[33],由鉴湖延伸出的若耶溪等水域同样是人们心仪的风光。这片水域由马臻奠定,诗人在留恋鉴湖风月的同时,也不忘感念马臻的开创之功。“广水遥堤利物功,因思太守惠无穷”,在马臻筑鉴湖之后,越地“长与耕耘致岁丰”[34],不但山水趋于灵秀,社会经济亦得到长足发展。
其次是佛道仙踪,与六朝一样,其仍然是与越中山水相交的维度。

“越中多有前朝寺”[35],唐代越地佛寺众多⑦,“云藏古殿暗,石护小房深”[36]、“野桥连寺月,高竹半楼风”[37]的清幽古寺成为诗人的题咏对象。与六朝时的诗人一样,唐代文人多与僧人交往,灵澈、清江等人即为著名诗僧。如刘长卿送别灵澈上人时不禁感慨“那堪别后长相忆,云木苍苍但闭关”[38],赵嘏则有“自晒诗书经雨后,别留门户为僧开”[39]之句,诸如会稽戒珠寺、云门寺等名寺则是文人习业之所。
唐代道教得到长足发展,唐代文人与道教亦有不解之缘。如孟浩然在越州遇到太乙子时写下“仙穴逢羽人,停舻向前拜”[40],心已神游越中的洞天福地。像越中名士贺知章,晚年归隐乡里时便请为道士。《唐才子传》卷二载:“天宝三年,因病梦游帝居,及寤,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即舍住宅为千秋观。”李白也曾写道:“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41]不过总体而言,越文化中心地的道教并不及佛教兴盛,且缺乏代表人物。
再看隐逸情结。一方面是越中山水的吸引,一方面是宗教思想的感召⑧,不少人流连于越地而生归隐之志,“无名甘老买臣乡”[42],《太平广记》卷二○四便记述了鉴湖畔隐士独孤生的故事。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贺知章、秦系与方干。
越州永兴人贺知章晚年辞官,唐玄宗“诏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43]。贺知章辞官归乡后,写下《回乡偶书二首》,第一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句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第二首同样抒写物是人非的感慨,惟有鉴湖水给他慰藉: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全唐诗》卷一一二)
在另一首诗中,贺知章同样沉醉于鉴湖的风波:
稽山罢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
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
——贺知章《采莲曲》(《全唐诗》卷一一二)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44]。鉴湖是贺知章的精神故园。这里有他钟爱的“钑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45],也有他精神栖息之所。至今越地有贺秘监祠,寄寓了越地人民对贺知章的敬爱。
秦系也是越州人,“安史之乱”后隐居剡中,《新唐书·隐逸》谓其“北都留守薛兼训奏为右卫率府仓曹参军,不就”。有一首《题镜湖野老所居》(《全唐诗》卷二六〇)被视作秦系的作品:
湖里寻君去,樵风往返吹。
树喧巢鸟出,路细葑田移。
沤苎成鱼网,枯根是酒卮。
老年唯自适,生事任群儿。
或云系马戴作品。根据“路细葑田移”的说法,当时鉴湖流域的围垦或已发生,两宋鉴湖堙废的历史或当追溯到唐代。秦系在剡中隐居二十余年,“越部山水,佐其清机,圆冠野服,翛然自放”[46],后又隐居福建泉州。

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54]。秦系“天宝末,避乱剡溪”[55],而在“未必圣明代”[56],方干的隐居自有其苦衷。
其四,与六朝时一样,唐代“鉴湖文化走廊”同样表现出多元立体的文化格局。绘画方面,如陈宏、孙位等,书法方面,如虞世南、徐浩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续有开拓。以贺知章为例,他既是著名的诗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新唐书·贺知章传》说他:“晚节尤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未始刊饬。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旧唐书·贺知章传》所记殆同。有唐一代,越地的文学、艺术趋于繁荣,且呈现出多元交融的面貌。
最后是越地人士与寓居越地者的共同创造。在六朝时期,“鉴湖文化走廊”的主角可以说是迁入越地的北方人士。在唐代“江浙名士如林”[57],虽然“鉴湖文化走廊”与六朝一样是本土人士与外来人士的共同创造,但本时期本土人士的贡献亦较为抢眼。明人胡应麟指出:“唐诗人千数,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兴、骆临海,中唐钱起、秦系、严维、顾况,晚唐孟郊、项斯、罗隐、李频辈,今俱有集行世。一时巨擘,概得十二三,似不在他方下。”[58]但在初唐,越地的诗人并不多,此后有逐步增长的趋势。就全国的走势而言,初、盛唐时期北方诗作者数及诗作量远高于南方,中唐时期南北差距已经缩小不少,晚唐则是南方占有优势地位⑨。据叶持跃先生的分析,越州的主要诗人有初唐的贺知章(甲等)、虞世南(乙等)、万齐融(丁等)、贺朝(丁等),盛唐的严维(乙等)、秦系(丙等)、释清江(丙等),中唐的释灵澈(丙等),晚唐的吴融(甲等)、朱庆余(乙等)[59]。越地本土人士不但在文坛发挥影响,来自越地的王叔文等也一度进入政坛导演“永贞革新”。在唐代以后,随着中国文化重心向东南倾斜,越地人士对于全局的影响无疑更大了。
我们也不能忽视外来人士的影响。在唐诗历史上影响较大、与“浙东唐诗之路”关系较为密切的客居文人有百余位。其中元稹与白居易隔(钱塘)江的酬唱较为典型,“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最多,至今称兰亭绝唱”[60]。在大历年间,还有所谓“浙东唱和”。唐时严维、鲍防所结集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以当时浙东联唱集会为基础,收录了一批浙东客居诗人的作品。鲍防是湖北襄阳人,与谢良弼合称“鲍谢”,当时在越州做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幕府,据记载,他是当时浙东实际决策人物,但这位在唐代诗坛中并无多少影响的诗人,在客居浙东时,却与当地文人严维举办了一次对浙东文化发展有着历史性影响的盛会,而且,还可以发现,浙东联唱中留有姓名的36人中[61],除了严维外,全都不是浙东人。可见,客居文人已经对当时浙东文化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六朝,“鉴湖文化走廊”也是思想交锋的场所,在唐代则似乎少了思想方面的成就。这并不限于越地,就全国而言,唐代在思想上都似乎是乏善可陈的。六朝作为乱世,唐代作为大一统的王朝,不可同日而语。再者,虽然精英层面的思想相对平静,但一般的思想并非一片贫瘠,对此,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已经有所论述[62]。
三、“鉴湖文化走廊”的衰落与回光
南宋时期鉴湖渐趋堙废,鉴湖文化走廊也逐步衰落。这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改变,更多的是社会背景的转向,越文化的“近世化”的趋势加强了。如果说“鉴湖文化走廊”更多的是外来人士与越地土著的共同创造,那么“靖康之难”之后越文化则更加依赖于本土人士,且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信力与创造力,逐渐走向成熟。
东汉开创的水利工程——鉴湖给越地带来的惠利,王十朋《鉴湖说·上》曾作如下总结:
故会稽、山阴无荒废之田,无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汉永和以来,更六朝之有江东,西晋隋唐之有天下,与夫五代钱氏之为国,有而治之,莫敢废也。千有余年之间,民受其利博矣久矣。[63]
然而随着越地人口的增长以及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⑩,与湖争利的现象愈加严重,鉴湖水域渐为淤塞。宋代以来盗湖为田的现象愈演愈烈,曾巩《序越州鉴湖图》载: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64]
盗湖者达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乃至“湖废几尽”——这尚是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的情况。根据曾巩的记述,当时鉴湖仅存“其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坞,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在此之后,盗湖为田的现象益加严重。《越州图经志》载:“岁月浸远,浚治不时,日久湮废,濒湖之民侵耕为田。熙宁中,盗为田九百余顷。尝遣庐州观察推官江衎经度其宜,凡为湖田者两存之,立碑石为界,内者为田,外者为湖。”[65]江衎立碑石,实际上是默认现状的权宜之计。《越州图经志》又载:“政和末,为郡守者务为进奉之计,遂废湖为田,赋输京师。自时奸民私占为田益众,湖之存者亡几矣!绍兴二十九年十月,帝谕枢密院事王纶曰:‘往年宰执常欲尽干鉴湖,云可得十万斛米。朕谓若遇岁旱,无湖水引灌,则所损未必不过之,凡事须远虑可也。’”废湖造田的行为,不但是“奸民”垂涎田地的结果,更成为当地政府增加赋税的公开行径,宋高宗也已开始忧虑废鉴湖的后果。王十朋《鉴湖说·上》也记载,“政和末,有小人为州,内交权幸,专务为应奉之计,遂建议废湖为田,而岁输其所入于京师。自是奸民豪族公侵强据,无复忌惮,所谓鉴湖者,仅存其名,而水旱灾伤之患无岁无之矣”。针对这一短视行为,王十朋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岁得租米六万余石。为官吏者徒见夫六万石之利于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顷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顷之岁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废湖为田其害不止于九千顷而已也”,鉴湖一旦被废“今则无岁无灾伤,盖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岁无之。自废湖而为田,每岁雨稍多,则田已淹没,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矣”。《宋史·吴芾传》载“鉴湖久废,会岁大饥,出常平米募饥民浚治”,吴芾离任之后马上“大姓利于田,湖复废”。在反复的疏浚与填湖的拉锯之中,废湖的势力最终占了上风。乾隆《绍兴府志》存录张惟中的一首《镜湖》诗,作者不但感慨“今日烟波太半无”,还讽刺“唯有一天秋夜月,不随田亩入官租”。正如沈遘《鉴湖》所言:
鉴湖千顷山四连,昔为大泽今平田。
庸夫况可与虑始,万年之利一朝毁。[66]
沈遘尚生活在北宋,南宋时期的陆游也因目睹鉴湖堙废所带来的恶果而痛心疾首:
躬耕蕲一饱,闵闵望有年。
水旱适继作,斗米几千钱!
镜湖浃已久,造祸初非天。
孰能求其故?遗迹犹隐然。
增卑以为高,培薄使之坚。
坐复千载利,名托亡穷传。
民愚不能知,仕者苟目前。
吾言固应弃,悄怆夜不眠。
——《镜湖》(《剑南诗稿》卷三二)
“镜湖浃已久,造祸初非天”已经明确指出之所以“水旱适继作,斗米几千钱”,除了天灾,更多的是人祸。无奈“民愚不能知,仕者苟目前”,一部分官吏和民众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千年水利工程毁于一旦,心系百姓疾苦与家乡风物的放翁“悄怆夜不眠”。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二中便说:“陂泽惟近时最多废。吾乡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除了鉴湖,陆游还历数其他被堙废的湖泽——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南宋时期越地灾害频仍,这与本阶段气候转凉有关。但鉴湖堙废所带来的调节作用的减弱,也可能加剧了天灾的危害。像“积雨仍愁麦不支”[67]“城南积潦入车箱”[68]的场景,一再上演。陆游在《稽山行》中说“镜湖滀众水,自汉无旱蝗”[69],但这一切在陆游的时代却已不复再现。
一方面是鉴湖的萎缩乃至消亡,越地原有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一方面是世风丕变,我们所说的“鉴湖文化走廊”也逐渐走到了尽头。南宋越地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陆游,正是“鉴湖文化走廊”的绝响。论者多重视陆游诗词的文学史地位,而从越地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它又是越文化转型的见证。陆游作品不止于描绘越地近世风貌的风情画,更是寄托放翁山水情结、隐逸情结的风景画,其既反映了时代转向的新现象,也赓续了“鉴湖文化走廊”的旧精神。
人们提及陆游的文学创作,每贴以“爱国诗人”的标签。梁启超便曾说陆游“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70]。世人多重放翁慷慨激昂的一面,却忽视了占陆游作品百分之七八十的写景诗[71]。钱钟书先生便曾指出陆游“高明之性,不耐沉潜,故作诗工于写景叙事”[72]。陆游晚年“早曾寄傲风烟表,晚尚钟情山水间”[73],最令放翁念念不忘的莫过于巴山蜀水与稽山鉴水。陆游对故乡的山水始终怀有深情:“吾州清绝冠三吴,天写云山万幅图。”[74]陆游钟情故乡的会稽山,“平生爱山心,于此可无悔”[75],在《稽山行》这一著名诗篇中,陆游在赞美“稽山何巍巍”的同时,也动情地描绘了越地的风土人情。会稽山的大禹陵是越地的标志性景观,陆游曾写下“会稽多名山,开迹自往古;岂惟颂刻秦,乃有庙祀禹”[76]这样的诗句。在《禹祠》中,陆游不但追忆前贤,更联系当下:“念昔平水土,棋布画九区。岂知千岁后,戎羯居中都。”[77]中州沦陷,始终是陆游心痛之处,无奈恢复中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呐喊。
在陆游的笔下,不乏对前贤在“鉴湖文化走廊”所留下的足迹的向往。如其《兰亭》所云:
兰亭绝境擅吾州,病起身闲得纵游。
曲水流觞千古胜,小山丛桂一年秋。
酒酣起舞风前袖,兴尽回桡月下舟。
江左诸贤嗟未远,感今怀昔使人愁。[78]
东晋时期的永和兰亭之会乃是“千古胜”,“江左诸贤”的风骨引后人神往。陆游所处的时代,与彼时相比已然是另一番世局,不由“感今怀昔”。
陆家自七世祖以来傍鉴水而居,陆游的三山别业、会稽石帆别业均在鉴湖之滨。嘉泰《会稽志·山》载:“三山,在(山阴)县西九里,地理家以为与卧龙冈势相连,今陆氏居之。”陆游曾说“山园三亩镜湖旁”[79]“吾庐镜湖上,傍水开云扃”[80],鉴湖不但是他祖居之地,亦是其精神故乡。陆游自述“五十年来住镜湖”[81],其86年的生涯大约有50年生活在鉴湖之畔[82]。正因为此,鉴湖的意象在他笔下一再出现:
五更欹枕一凄然,梦里扁舟水接天。
红蕖绿芰梅山下,白塔朱楼禹庙边。
——《上巳临川道中》(《剑南诗稿》卷一)
我摇画楫镜湖中,碧水青天两绝奇。
——《雨晴游香山》(《剑南诗稿》卷一七)
“重楼与曲槛,潋滟浮湖光”[69]的鉴湖令陆游魂牵梦萦,即使身在他乡,故乡的鉴湖也一再入梦:“我家山阴道,湖山淡空蒙。小屋如舴艋,出没烟波中。”[83]陆游55岁在建安提举福建常平茶事任上追忆“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84],在夔州任上,陆游写下了《初夏怀故山》:“镜湖四月正清和,白塔红桥小艇过。梅雨晴时插秧鼓,蘋风生处采菱歌。”[85]陆游所寄怀的,不惟鉴湖的风景,亦在于故土的风情。
“鉴湖文化走廊”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隐逸的情怀,陆游最终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隐士,但国仇家恨的压力也令他心生纵情山水的念想。他在《烟艇记》表达了“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86]的愿望,《思故山》也说“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这实际上是对“鉴湖文化走廊”的神往。陆游笔下一再出现的“隐君子”,有学者便认为可能是陆游对自己的另一个形象的设计[87],表现了陆游对隐逸山林的向往。
鉴湖虽在宋代已近堙废,但诗人笔下的鉴湖依然秀丽多姿[88]。除了陆游的诗文,还有其他文人墨客的足迹。王十朋在《会稽风俗赋》中极力描绘鉴湖的壮阔与明净:“其水则浩渺泓澄,散漫迂潆。涨焉而天,风焉而波。净焉如练,莹焉如磨。”[89]在《鉴湖行》中,他又沉醉于“鉴湖春色三百里”,“回首湖山何处是,欸乃声中画图里”[90]。诸如“贺家千顷水云乡,六月荷花风最凉”[91]这样的诗句,南宋不减唐代,似乎鉴湖景观虽然不复当年但并不影响文人对鉴湖的欣赏。但说不曾影响很难合乎实际,日渐萎缩的鉴湖已经成为人们精神避难的港湾,“鉴湖文化走廊”在经历最后一抹亮色后也逐渐走向尽头。在此之后,“鉴湖文化走廊”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不再是主流,而伴随“近世化”而来的务实市民风尚则成为越地的主色调。我们再也难以看到六朝的雅集、唐朝的诗路了。
注释:
①我们所说的“越文化中心地”,即确立于越国时期、定型于五代以后的区域范围,实际上也是南宋以来绍兴府的范围,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县,相当于今天绍兴市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以及杭州市的萧山区、宁波市的余姚市。虽然经历多次变迁,但以上区域始终作为越文化的基本范围存在。本文所说的越地主要指这一范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基本空间背景。
②其它两个中心分别在建康和庐山。
③玄学主张“以无为本”,而佛教主“空”,认为物无自性,全凭因缘而合。当时的佛经翻译就把“空”译为“本无”,故佛学与玄学互相阐发,佛、玄趋于合流。不过,这种翻译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于1920年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说”,随着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阐发而影响深远。当然,中国文学观念的净化及完全独立,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
⑤丁福林先生有专著研究,参见丁氏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⑥参见竺岳兵《剡溪——唐诗之路》,《唐代文学研究》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4-880页。所谓的“浙东唐诗之路”指的是一条始自萧山西陵(今西兴),经浙东运河、古纤道、鉴湖,转入曹娥江,溯剡溪,到天台山华顶峰,经国清寺至新昌为主要路线的唐代诗人往来比较集中的古浙东旅游路线。按竺岳兵等人的考证,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51人,都曾走过这条诗路,占《全唐诗》收载诗人总数2200位的18%多,诗人们所写并留传至今的浙东唐诗有1500多首,参见竺岳兵《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⑦尤其是在五代,与中原佛教衰落不同,吴越时更是兴盛,蔚为“东南佛国”,越州“凡梁开平以后,称造某寺赐某额,皆钱氏割据时为之”,参见嘉泰《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
⑧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参见李红霞《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神仙道教深刻影响着古代文士们隐逸山林的思想和情趣,佛禅思想对诗人们具有以道统的意义来支撑其精神,并帮助他们获得身心的自由超越与心灵之止泊安定的作用,参见卢晓河《求仙与隐逸——神仙道教文化对山林隐逸之士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胡遂、肖圣陶:《论佛教对于隐逸的超越意义——以晚唐诗人为例》,《湖湘论坛》2010年第5期。此外,战乱与隐逸的关系也需要重视,“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的两次动乱与越地隐逸之风有微妙的联系。
⑨尚永亮:《唐五代诗作者之地域分布与北南变化的定量分析》,《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351页。另据景遐东先生的统计,唐代越州共出有30位诗人,存诗808首51句,其中会稽8人,共117首30句,包括孔德绍12首2句、陈允初11首、康造1首、秦系42首、清江21首2句、灵澈17首26句、罗珦1首、罗让2首;山阴5人,共391首14句,包括孔绍安7首、贺敳1首、严维78首12句、澄观1首、吴融304首2句;诸暨3人,共40首,包括陈寡言3首、良价36首、周镛1首;余姚有虞世南32首;剡县2人6首,包括徐浩2首、叶简4首;永兴有贺知章21首3句。此外籍贯不详的有10人,共201首4句,包括万齐融4首、贺朝8首、朱庆余177首、朱可名1首、庄南杰6首、范氏子4句、若耶溪女子1首、诸葛觉1首、遇臻1首、越溪杨女2首。其中较明确的初唐4人,盛唐4人,中唐12人,晚唐8人。初盛唐的江南诗人多出身于江南世家大族,中晚唐大幅减少,普通家族崛起。参见景氏著《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118、133页。
⑩淳熙九年(1182)朱熹奉旨赴绍兴府赈灾时估计,全府除上虞、余姚之外的会稽、山阴、诸暨、嵊县、新昌、萧山6县人口约140万人,耕田约200万亩,参见朱熹《奏救荒事宜状》,《晦庵集》卷一六。人均耕地约1.4亩,要知道大中祥符年间越州田地面积6122952亩,据推算人均有6.5亩。
[1]竺岳兵.剡溪——唐诗之路[M]//唐代文学研究:第6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64-880;邹志方.浙东唐诗之路[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竺岳兵:唐诗之路综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7.
[3]吴书·虞翻传[M]//三国志:卷五七.
[4]谢灵运传[M]//宋书:卷六七.
[5]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130.
[6]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王羲之传[M]//晋书:卷五〇.
[8]言语[M]//世说新语:卷二.
[9]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M]//全唐文:卷六七六.
[10]石[M]//嘉泰会稽志:卷一一.
[11]渐江水[M]//水经注:卷四〇.
[12]谢法曹集[M]//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三册.
[13]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
[14]叶岗.永和兰亭之会对江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J].社会科学战线,2001(6).
[15]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M]//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0.
[16]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M]//全唐文:卷四九三.
[17]权德舆.送上虞丞[M]//全唐诗:卷三二四.
[18]元稹.送王十一郎游剡中[M]//全唐诗:卷四一三.
[19]元稹.寄乐天[M]//全唐诗:卷四一七.
[20]孟郊.越中山水[M]//全唐诗:卷三七五.
[21]杜甫.壮游[M]//全唐诗:卷二二二.
[22]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M]//全唐诗:卷一六〇.
[23]李白.越中览古[M]//全唐诗:卷一八一.
[24]王勃.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M]//全唐文:卷一八一.
[25]李商隐.为荥阳公与浙东大夫启[M]//全唐文:卷七七六.
[26]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M]//全唐诗:卷一六〇.
[27]崔峒.送薛良史往越州谒从叔[M]//全唐诗:卷二九四.
[28]刘长卿.上巳日越中与鲍侍郎泛舟耶溪[M]//全唐诗:卷一五一.
[29]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M]//全唐诗:卷一七四.
[30]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M]//全唐诗:卷一七五.
[31]李白.越中秋怀[M]//全唐诗:卷一八三.
[32]刘亮.唐代诗人与镜湖[M]//陆游与鉴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62.
[33]宋之问.泛镜湖南溪[M]//全唐诗:卷五二.
[34]李频.镜湖夜泊有怀[M]//全唐诗:卷五八七.
[35]姚合.送文著上人游越[M]//全唐诗:卷四九六.
[36]吴融.题越州法华寺[M]//全唐诗:卷六八四.
[37]赵嘏.越中寺居[M]//全唐诗:卷五四九.
[38]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还越中[M]//全唐诗:卷一五一.
[39]赵嘏.越中寺居寄上主人[M]//全唐诗:卷五四九.
[40]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乙子[M]//全唐诗:卷一五九.
[41]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M]//全唐诗:卷一八二.
[42]李频.越中言事二首[M]//全唐诗:卷六五一.
[43]辛文房.贺知章传[M]//唐才子传:卷三.
[44]李白.送贺宾客归越[M]//全唐诗:卷一七六.
[45]贺知章.答朝士[M]//全唐诗:卷一一二.
[46]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M]//全唐文:卷四九〇.
[47]齐己.寄镜湖方干处士[M]//全唐诗:卷八三八.
[48]方干.镜中别业二首[M]//全唐诗:卷六四八.
[49]方干.陪王大夫泛湖[M]//全唐诗:卷六五〇.
[50]方干.鉴湖西岛言事[M]//全唐诗:卷六五〇.
[51]方干.赠会稽张少府[M]//全唐诗:卷六五〇.
[52]贯休.春晚访镜湖方干[M]//全唐诗:卷八三四.
[53]虚中.悼方干处士[M]//全唐诗:卷八四八.
[54]李红霞.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M].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5]秦系传[M]//新唐书:卷一九六.
[56]方干.镜湖西岛言事寄陶校书[M]//全唐诗:卷六五三.
[57]辛文房.朱放传[M]//唐才子传:卷五.
[58]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M]//唐上.
[59]叶持跃.论浙江唐五代时期诗人的籍贯分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1).
[60]元稹传[M]//旧唐书:卷一六六.
[61]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述[J].文学遗产,1989(增刊第18辑).
[6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63]王十朋.鉴湖说[M]//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二三.
[64]曾巩.序越州鉴湖图[M]//元丰类稿:卷一三.
[65]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873-875.
[66]沈遘.鉴湖[M]//西溪集:卷三.
[67]陆游.洊饥之余复苦久雨感叹而作[M]//剑南诗稿:卷一四.
[68]陆游.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镜湖渺然想见湖未废时有感而赋[M]//剑南诗稿:卷八三.
[69]陆游.稽山行[M]//剑南诗稿:卷六五.
[70]梁启超.读陆放翁集:之一[M]//饮冰室文集:卷四五下.
[71]莫砺锋.论陆游写景诗的人文色彩[M]//陆游与鉴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7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0.
[73]陆游.闲适[M]//剑南诗稿:卷七一.
[74]陆游.小雨泛镜湖[M]//剑南诗稿:卷一七.
[75]陆游.稽山[M]//剑南诗稿:卷八一.
[76]陆游.会稽行[M]//剑南诗稿:卷七五.
[77]陆游.禹祠[M]//剑南诗稿:卷七〇.
[78]陆游.兰亭[M]//剑南诗稿:卷二七.
[79]陆游.春晴自云门归三山[M]//剑南诗稿:卷三九.
[80]陆游.吾庐[M]//剑南诗稿:卷一〇.
[81]陆游.秋兴[M]//剑南诗稿:卷八三.
[82]邹志方.陆游的镜湖情缘[M]//浙学、秋瑾、绍兴师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7.
[83]陆游.病中怀故庐[M]//剑南诗稿:卷一一.
[84]陆游.思故山[M]//剑南诗稿:卷一一.
[85]陆游.初夏怀故山[M]//剑南诗稿:卷二.
[86]陆游.烟艇记[M]//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一七.
[87]李建英.陆游的镜湖诗简论[M]//陆游与鉴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44.
[88]渠晓云.试析宋代诗人笔下的鉴湖[M]//陆游与鉴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81.
[89]王十朋.风俗赋[M]//重刻会稽三赋:卷一.
[90]王十朋.鉴湖行[M]//王十朋全集·诗集:卷一二.
[91]张孝祥.鉴湖纳凉[M]//于湖集:卷二.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Corridor of Jianhu Lake
Ye Gang1Chen Minzhen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2.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0)
“The Cultural Corridor of Jianhu Lake” existed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rridor with the areas of Yue as the center. It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n the Six dynasties, “the Cultural Corridor of Jianhu Lake” took its preliminary boom. With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Yue culture has become diversifie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ultural Corridor of Jianhu Lake”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finally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orridor gradually declined with Jianhu Lake silting up.
Yue culture; Jianhu Lake; Cultural Corridor of Jianhu Lake
2014-09-3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越文化发展论”(13FZS037)的阶段性成果。
叶 岗(1965-),男,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陈民镇(1988-),男,浙江苍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G127
A
1008-293X(2014)06-0001-12
(责任编辑张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