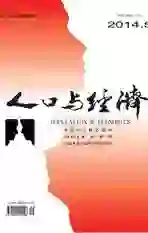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
2014-10-16任栋李新运
任栋 李新运
摘 要:产业部门的发展需要劳动力资源的支撑,文章以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OLS估计法考察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较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将更为迅速,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受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影响更为显著。我国应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区域间转移、深化对外开放、提升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四个方面来应对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劳动力年龄结构;青年劳动力比重;产业结构调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095-09
一、引言
“未富先老”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特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社会积累水平下降,更体现在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上。目前我国“二三一”产业结构转型尚未成功,消化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严峻。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相同步,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引发的系统性困境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格局已经发生深刻转变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从2011年的峰值9.40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9.39亿人和2013年的9.36亿人。,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加速,“延迟退休”、“放开二胎”等政策的制定,将深刻影响我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口抚养比逐渐下降,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稳步升级。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但由于人口基数小(只有4亿),所以第一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增加不多。第二次生育高峰开始于1962年,持续至1973年,10年间人口出生率处于3%~4%之间,全国新出生人口将近2.6亿,这一次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婴儿潮。1986~1990年我国迎来了另一个小生育高峰,主要是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在此期间进入生育年龄,但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此期间出生的婴儿只有1.2亿左右[1]。由于各次生育高峰的出现,使我国人口结构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长达5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2],为实
(中)图题 图1 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注:产业结构高级化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变动率指当年水平较上一年的变化比例。人口出生率的起始年份为1960年。
现高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基础。图1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与人口生育率的变化存在正相关性,其中产业结构变动的正相关性特征更为明显。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变的关键时期,关注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试图回答劳动力年龄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到底存在怎样的影响,在不同产业和地区有何差异。
二、文献回顾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传统研究主要着眼于人力资本或劳动力资源总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特别是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通过将人口统计变量引入经济增长实证模型,验证了1965~1990年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上升促进了东亚经济体人均生产率的提高,并指出随着东亚各国老龄化时期的到来,经济增长率将会承受压力[3]。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以爱尔兰和我国台湾为例,指出近代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转变提高了人均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有利于促进教育投资和提高储蓄水平[4]。有学者将年龄结构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1989~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效率,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储蓄向生产性投资的转移[5]。伯尔施-祖潘(B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评估,并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很可能会压低经合组织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在储蓄减少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增加社会资助支出[6]。伯尔施-祖潘还以德国为例,认为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教育和培训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以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7]。我国对人口结构转变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普遍认为人口红利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要素供给、提高储蓄率、带动公共投资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8];老龄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养老保障与养老保险、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特殊老年群体养老、积极应对老龄化等领域[9]。
刘易斯(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从劳动力转移视角扩展了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逻辑,当“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时,产业结构调整将依赖于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10]。拉尼斯(Ranis)和费景汉(Fei)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拉尼斯-费景汉模型(RanisFei Model)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存在阻力的[11]。沃尔斯(Volz)以2000年以来德国17个部门和两种类型的家庭数据为样本,分析认为劳动力老龄化会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来对产业部门造成影响,并有利于健康和教育部门的发展[12]。安纳比(Annabi)等人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来考察加拿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本国产业和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和均衡失业率下降,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工资水平,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成本上升,劳动附加值低的产业规模会相对扩大;另外,老龄劳动力消费偏好的改变将有利于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13]。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也关注了劳动力年龄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杨道兵等人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的影响入手,讨论了劳动力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14]。朱洵等人运用“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方法,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及产业结构调整方案进行了初步探讨[15]。但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对人口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没有足够重视,尤其缺乏对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理论假说与模型设定
1.理论假说
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供给角度看,人口转变引起年龄结构变化,从而改变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教育水平的提升将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社会负担系数下降能增加社会储蓄;二是从需求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改变总消费、投资、进出口以及国际资本流动[16]。但人口转变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社会储蓄和改变消费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中青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可能对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生育高潮(1946~1964年),该时期出生的人口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0%,并且普遍接受了较好的教育[17]。与之相对应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尽管美国正处于经济滞胀时期,但产业结构依然实现了快速转型。与美国类似,二战后的日本在1947~1949年出现第一次生育高峰,3年内出生婴儿的总数超过800万,20世纪70年代前期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但只持续到1975年;与之相对应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第一产业比重快速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共同上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产业升级进展缓慢,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第三产业比重再次出现加速上升[18]。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历程也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并且总体上是随着劳动力青年人口
联合国曾在一份文件中把14~25岁的人称为“青年人口”,而世界卫生组织将44岁以下的人列为青年。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青年是指十五六岁~30岁左右的人生阶段。从我国目前企业招聘要求来看,一般将35岁作为入职的门槛线。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本文结合人口普查数据的年龄分段,以
15~34岁作为青年人口的年龄区间。相对于中年人口,青年人口的职业固定性较差,转换职业的成本较低。比重的下降,产业结构调整速度逐渐趋缓,见图2。
劳动力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变换工作的概率随着工作资历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年龄和工龄的增长,劳动者变换工作的成本会提高,工作流动性将会下降[19]。这意味着当产业结构需要快速调整时,老化的劳动力结构很难快速转变为与之相适应的就业结构。二是人力资本的向下兼容性[20]使文化水平更高的青年劳动力能够适应更多的就业岗位,职业选择范围的增加提高了青年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可能性,并且青年劳动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力和创新能力更强 [21],更能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这主要是对经济激励和体力、智力能力发生变化的理性反应[22]。多数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在职业生涯初期呈上升趋势,当年龄超过峰值之后(不同研究对生产率峰值年龄的判断存在差异),年龄的增长会导致体能的下降,但在脑力劳动方面会存在差异[23],尽管体能、技能等多种原因导致年龄和劳动生产率在不同部门存在差异,但当控制了这些异质性之后,年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部门间并没有明显差异,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变化呈驼峰形状,在35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4]。四是在我国农民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明显高于城市劳动者[25],而且逐步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学历明显提高,有条件选择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且就业偏好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26],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也充分说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27]。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劳动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产业间流动。相对于中老年劳动力,青年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更高,就业流动性和适应性更强。因此,在同等的发展条件下,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较高的地区更适合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更快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之,劳动力老龄化将抑制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产业结构的僵化。
假说2:从地区差异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所处阶段和发展模式不同,在粗放型发展模式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地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制约程度应当高于集约发展模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占主导的地区。
2.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本文以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作为劳动力年龄结构指标,以产业结构调整量的绝对值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指标,虽然该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但是能够更直观研究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关系,并且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下,产业结构调整量的大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产业升级的速度。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我们构建如下经验模型: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概括:需求方面的相关因素有人均GDP、人均收入水平、出口强度、城镇化水平;供给方面的因素有人口结构、劳动者报酬、人力资本、资源禀赋、投资、FDI、技术进步、地理因素、产业政策等。因此,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负担系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直接利用外资水平、贸易开放度
由于各省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不一致,对数据质量影响较大;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技术进步与教育水平相关度较高,且具有显著的外溢性;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故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并未包含以上变量。。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样本数据包含中国内地的30个省(区、市)[KG-*2](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将四川省和重庆市进行了合并处理),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跨度为1988~2012年。为了与人口普查资料相统一以及考虑变量的数据稳定性,我们将这24年划分为5个区间,即1988~1992年、1993~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7年和2008~2012年,并以1990、1995、2000、2005、2010年作为区间代表年份。变量说明见表1。
被解释变量为每个时期区间内三次产业结构总变动率(ISCR),计算方法为每年各产业占GDP百分比变动量的绝对值之和,主要衡量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第二、三产业比重总变动率(SC、TC)为时期内对应产业占GDP百分比变动量的绝对值之和。
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YLP),即15~3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其中,2010、2000、1990年三个年份的数据可由人口普查资料直接计算获得,2005和1995年数据则是根据2000年和1990年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推算获得,之所以没有采用相应年份的抽样普查数据,是因为1%的抽样调查比例很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而利用总体普查数据推算的结果主要受分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差异的影响,这种误差对年龄结构总体分布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2000年相邻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约为1‰,而55~59岁人口的死亡率与10~14岁人口的死亡率之差仅为8.26‰。,另外忽略迁移人口对地区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我国人口迁移率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于潇等人在2013年的分析,2000~2010年东部地区净人口迁移率由6.721‰变为10.36‰,中部地区由-6.12‰变为-10.07‰,西部地区由-3.59‰变为-5.89‰,具体参见:
于潇、李袁园、雪俊一.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五普”和“六普”的比较\[J\].人口学刊,2013,(3)。
考虑到净人口迁移率占总人口比重依然较小,且无法准确获得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故本文未考虑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人口负担系数(SBC)为代表年份的0~14岁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EDU)为代表年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按照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以上16年进行估算,由于没有1985年的受教育水平调查数据,我们以1982年普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进行替代。人均GDP增长率(PGDPR)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区间年份内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变动率(FI)为区间内历年投资比重变化量绝对值的平均值。直接利用外资占GDP比重(FDI)为区间内各年份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按当年汇率进行折算。出口额占GDP比重(EXP)为区间内历年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平均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全国总体样本的面板回归结果
首先考察全国样本中三次产业结构总体调整量和二、三产业结构调整量与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的关系。其中,对全国总体样本采用的模型分别为混合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二、三产业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中利用聚类稳健标准差对估计结果进行校准,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恰当的模型。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主要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模型并未考虑人口结构的内生性问题。表2报告了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的1~3列数据的分析结果看,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在控制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投资、出口等因素之后,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4~7列数据的分产业检验中,两者的统计关系依然显著,这表明较高的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有利于产业的快速升级,假说1得到验证。进一步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对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影响,说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直接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如果假定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为高级化,则该结果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产业升级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发现的,FDI在中国不同行业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倾斜性,大多数外资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其中又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这就导致当我国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和剩余劳动力较多时,FDI能够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吸纳就业的作用,但是当产业结构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FDI将阻碍产业升级。
在全国分产业样本的分析结果中,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第二、三产业调整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变动与人口负担系数和对外出口显著正相关,即发展第三产业更加符合我国当前老龄化趋势下的就业形势和需求特征,并且加快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模型中产业结构调整变量并没有体现方向性,但是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可以认为第三产业比重是逐渐提高的。。
2.东、中、西部样本的面板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区间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差异,我们分别对东中西部的样本进行检验。表3报告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样本回归结果。
从表3可见,地区间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中部地区二者的相关性更强,而东部地区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不显著。该结果说明,劳动力老龄化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对中西部有较明显的抑制效应,假说2得到验证。
东部地区样本中人口负担系数、人均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出口均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变量中人口负担系数、人均GDP增长率和对外出口均为需求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为投入因素,反映了东部地区产业调整的主要动因是需求和资本的双重推动。相对于东部地区,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主要为人口年龄结构,具体是青年劳动力投入和人口负担系数,其中人口负担系数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有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正向影响。
从东西部发展差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重点倾斜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平衡战略布局,中西部地区在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力资本、进出口总额和引进外资上均远落后于东部地区,1999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地区间经济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从区域产业演变特征来看,在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压力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向邻近的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中部地区正处于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之中,但依靠资源禀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对于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因此,劳动力老龄化对中部地区产业调整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东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并未明显引致中高级制造业的转移[28],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还将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因此,留住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意义重大。相比之下,东部地区作为我国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中心,主要以原材料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为主,劳动生产率较高,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资源的约束。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率先在东部地区集聚,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将成为影响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是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198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得到国家和地区样本回归结果的支持,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正向影响。当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较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将更为迅速;反之,劳动力老龄化将抑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均与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并且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第二、三产业调整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负担系数和对外出口显著正相关,发展第三产业更加符合我国当前老龄化趋势下的就业形势和需求特征,加快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由于区域异质性特征,地区间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对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次之,东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是需求拉动和资本推动;相对于东部地区,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则主要是劳动力供给结构,特别是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劳动力需求特征差异有关。
第四,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依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剧和劳动力青年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产业转型升级将趋于缓慢,应着力转变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劳动力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二是在保证传统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适应老龄化社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三是加快推进产业区域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政策扶持力度,并结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投向加以引导,鼓励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同时应制定配套的人才吸引政策,吸引青年人口在中西部地区落户就业;四是面对“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应从主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入手,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孟令国,李超令.我国二次人口红利的困境摆脱与现实愿景[J].改革,2013,(1).
[2]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9).
[3] Bloom, D. E., J. G.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3).
[4] Bloom,D.E., D.Canning. Global Demographic Change: Dimensions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4.
[5] Wei, Z., R.Hao.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4).
[6] Brsch-Supan, A.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Savings,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OECD Area[R]. 1995.
[7] Brsch-Supan, A.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J]. Labour, 2003, (1).
[8]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9]张晓青.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新动向[J].人口与发展,2009,(3).
[10]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1] Ranis, G., J. C.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4).
[12]Volz, U. B. Aging, Labor Supply and Consumptionsectoral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Germany[R].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Helsinki, Finland, 2008.
[13]Annabi, N., M.Fougère, S. Harvey. Intertemporal and Interindustry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for Canada[J]. Labour, 2009, 23(4).
[14]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6,(1).
[15]朱洵,周彦汐. 劳动力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3,(3).
[16]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人口红利[D].武汉大学,2010.
[17]李银珩,李硕珩.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
[18]关雪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2,(7).
[19]Farber, H. S. The Analysis of Interfirm Worker Mobility[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4, 12(4).
[20]陈晓光.人力资本向下兼容性及其对跨国收入水平核算的意义[J].经济研究,2005,(4).
[21] Frosch, K. H. Workforce Age and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Surv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1, 13(4).
[22]Oster, S. M., D. S. Hamermesh. Aging and Productivity among Economis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1).
[23]Skirbekk, V. Age and Productivity Capacity: Descriptions, Causes and Policy Options[J]. Ageing Horizons, 2008, 8(4).
[24]Gbel C., T.Zwick. Age and Productivity: Sector Differences[J]. De Economist, 2012, 160(1).
[25]Knight, J.Y.Linda. Job Mobility of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32).
[26]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
[27]方行明,韩晓娜.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J].人口学刊,2013,(2).
[28]李娅,伏润民.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J].世界经济, 2010,(8).
[责任编辑 冯 乐]
[7] Brsch-Supan, A.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J]. Labour, 2003, (1).
[8]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9]张晓青.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新动向[J].人口与发展,2009,(3).
[10]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1] Ranis, G., J. C.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4).
[12]Volz, U. B. Aging, Labor Supply and Consumptionsectoral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Germany[R].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Helsinki, Finland, 2008.
[13]Annabi, N., M.Fougère, S. Harvey. Intertemporal and Interindustry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for Canada[J]. Labour, 2009, 23(4).
[14]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6,(1).
[15]朱洵,周彦汐. 劳动力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3,(3).
[16]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人口红利[D].武汉大学,2010.
[17]李银珩,李硕珩.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
[18]关雪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2,(7).
[19]Farber, H. S. The Analysis of Interfirm Worker Mobility[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4, 12(4).
[20]陈晓光.人力资本向下兼容性及其对跨国收入水平核算的意义[J].经济研究,2005,(4).
[21] Frosch, K. H. Workforce Age and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Surv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1, 13(4).
[22]Oster, S. M., D. S. Hamermesh. Aging and Productivity among Economis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1).
[23]Skirbekk, V. Age and Productivity Capacity: Descriptions, Causes and Policy Options[J]. Ageing Horizons, 2008, 8(4).
[24]Gbel C., T.Zwick. Age and Productivity: Sector Differences[J]. De Economist, 2012, 160(1).
[25]Knight, J.Y.Linda. Job Mobility of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32).
[26]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
[27]方行明,韩晓娜.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J].人口学刊,2013,(2).
[28]李娅,伏润民.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J].世界经济, 2010,(8).
[责任编辑 冯 乐]
[7] Brsch-Supan, A.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J]. Labour, 2003, (1).
[8]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9]张晓青.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的新动向[J].人口与发展,2009,(3).
[10]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1] Ranis, G., J. C.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4).
[12]Volz, U. B. Aging, Labor Supply and Consumptionsectoral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in Germany[R].Con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Helsinki, Finland, 2008.
[13]Annabi, N., M.Fougère, S. Harvey. Intertemporal and Interindustry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A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for Canada[J]. Labour, 2009, 23(4).
[14]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6,(1).
[15]朱洵,周彦汐. 劳动力老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年龄-产业”双重结构的定量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3,(3).
[16]李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人口红利[D].武汉大学,2010.
[17]李银珩,李硕珩.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2).
[18]关雪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2,(7).
[19]Farber, H. S. The Analysis of Interfirm Worker Mobility[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4, 12(4).
[20]陈晓光.人力资本向下兼容性及其对跨国收入水平核算的意义[J].经济研究,2005,(4).
[21] Frosch, K. H. Workforce Age and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Surv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1, 13(4).
[22]Oster, S. M., D. S. Hamermesh. Aging and Productivity among Economist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1).
[23]Skirbekk, V. Age and Productivity Capacity: Descriptions, Causes and Policy Options[J]. Ageing Horizons, 2008, 8(4).
[24]Gbel C., T.Zwick. Age and Productivity: Sector Differences[J]. De Economist, 2012, 160(1).
[25]Knight, J.Y.Linda. Job Mobility of Residents and Migrants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32).
[26]白南生,李靖.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8,(7).
[27]方行明,韩晓娜.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J].人口学刊,2013,(2).
[28]李娅,伏润民.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J].世界经济, 2010,(8).
[责任编辑 冯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