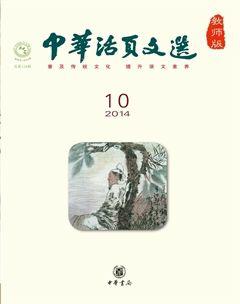悲生悯死与乐天知命
2014-10-15罗献中
罗献中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大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众人熟知的东晋时期的两篇名文佳作。有趣的是,这两篇体裁不同、风格迥异的美文都不约而同地谈及了敏感的生死问题,表达了各自的生死观。不过,两文虽然出自两位同一时代的封建士大夫之手,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认识却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这一点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忽视或误读,值得对其加以比较和辨析。
《兰亭集序》描述的是作者王羲之与众名士们在春暖花开的修禊日里,来到风景优美的山阴兰亭,一起“流觞曲水”、饮酒赋诗、尽情欢乐的盛况,并由此延伸,感叹有生之乐和人生苦短,抒发了对生与死的感慨。《归去来兮辞》描述的是作者陶渊明因向往田园又“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官职(彭泽令),毅然“归园田居”的喜悦和对秀美风光、诗意生活的热爱,进而表达了疏离官场、终老田园的决心以及对名利和生死等问题的看法。
从整体上看,两文在生死观上既有同也有异。不过,比较起来,不是通常的“大同小异”,而是“小同大异”“异大于同”。其中,两者较为相同的观点是生年有限、人生易逝。这个方面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兰亭集序》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归去来兮辞》云:“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面对良辰美景,两文作者都感叹人生苦短,不及自然万物那样生命持久。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关键是以何种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能否正视这个问题。两文生死观的不同点正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迥乎不同,差异甚大,有回避与正视、悲观与达观之分。这一点比较隐晦,需仔细辨别。具体说来,前者的态度是回避的、悲观的,不敢正视死亡的必然性。作者认为人生无常,寿夭由天,生命终归幻灭消失,因而为之无限伤感。例如作者慨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现了在生死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悲伤;他又借“古人”之口感叹“死生亦大矣”,并直接对人生的最终结局发出悲叹,如“岂不痛哉”“悲夫”等。这种感伤情绪在该文的后半部分挥之不去,笼罩着半篇文章,令人产生一定的压抑感。所以,王氏对生死问题的态度可谓是“悲生悯死”“谈死色变”。相对而言,后者的生死观虽然算不上是积极、乐观的,却也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比较达观、开朗的,亦即看得开、敢正视。陶渊明直言道:“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作者认为在有限的、所剩无几的生命中,要顺应自然,随缘自足,恬然自安,安度余生,不可有非分之想。可见,陶氏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不是回避和悲悯,而是直面生死、乐天知命、“视死如归”。
那么,同为东晋时期的士大夫,为何在生死观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应该与他们的个人身份、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不无关系。王羲之出身于晋代名门望族,身世显赫,当时位高权重的士族大官僚王导正是其堂伯父,唐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家即指其家族。然而,当时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十分严重:无力抵御外族入侵,被迫狼狈南迁,残存半壁江山,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且仍受虎视威胁。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内乱频仍(如322年王敦之乱、327年苏峻之乱),导致生灵涂炭。此外,北伐严重失利,大败而还,损兵折将,死伤惨重(如349年褚裒北伐、353年殷浩北伐)。如此等等,不能不令统治阶级中如王羲之之类的爱国恤民之士忧心忡忡,心情沉痛。同时,他们也一定会对生命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感触良深,备感痛惜。另一方面,王羲之所隶属的门阀士族阶级普遍腐朽没落,颓废消极,暮气沉沉,仿佛得了集体“抑郁症”,这同样让人心情压抑。王羲之个人虽然不同凡俗,积极进取,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但他毕竟生活在如此残酷和沉沦的环境里,难免不深受周围士大夫空虚消沉、“贪生怕死”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所以,王羲之虽为成就非凡的书法家,但在文中流露消沉甚至悲观的情调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即为“环境造就人”。只不过,他比同时代同阶层的士大夫们要清醒、理智一些而已,能认识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认为不能将生与死等量齐观,主张有生之年应该做些实事,不宜醉生梦死。这也是这位大书法家的难能可贵之处。但消沉、颓唐、萎靡、堕落,毕竟是他们这个阶层的精神常态,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兰亭集序》在生死问题上出现消极、悲观的论调,不仅是王羲之个人思想情绪的体现,更是他所处的整个士族阶级的思想倾向的体现,是腐朽颓废的统治阶级在政权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时发出的集体悲鸣与哀号。
与此相反,陶渊明就大不相同了。他虽然也出身于官僚家庭,但不属于士族阶级,没有世袭特权,父亲只做过小官又早亡,家境此时已经没落。他个人虽然也曾为官,但官职不大、官位不高,未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后来更是毅然辞官去职,归隐田园,沉入社会最底层,并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整日与下层百姓为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些就是属于他的生活。诚然,身处社会动荡、生命脆弱的时代,陶渊明难免也会受世风的影响而时有思想消极、内心空虚的表现,如认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等。但是,劳作的磨砺和充实,农人的刚强和友善,乡风的淳厚和质朴等,更会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他,让他能够及时摆脱一时的消极和空虚,及时地调整、矫正偶然扭曲的心态,进而能够正视人生的惨淡,正视死亡的归宿。此亦为“环境造就人”。同时,陶渊明又是个闻名于世的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之人,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一般而言,能够参透名利得失的人也通常能够参透生死等问题。所以,陶渊明能用道家顺随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在晚年曾写了“自挽”的《挽歌》和《自祭文》,从正面直接表明了自己豁达的生死观,其中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归去来兮辞》也正和这些诗文一样,较为典型地表现了陶渊明对人生的彻悟和对生死的正视。也正是基于此,他才珍惜现世的生活,并尽力寻求人生的乐趣。例如文中提及和显示的他的各种“快乐生活”:“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等。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由以上粗浅比较可知,王羲之和陶渊明这两位同时代的文化巨人,在生死观的问题上并非“英雄所见略同”,而是二者之间大异其趣。该现象的出现固然令人颇感有趣,但对促使二者差异形成的因素的探讨则更为发人深思,给人启发,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