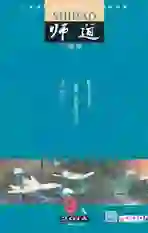一棵树是怎么变绿的
2014-10-10李明海
李明海
总觉得中国大地上的事物变化太过迅速,站在年过不惑的当口,偶尔回首过往时,已经有些不胜踉跄与尴尬了。
我最早教书的小学,记忆里那离开小镇三两里路的两幢白墙灰瓦的校舍,以及环绕校舍的那一湾清浅的荷塘,小竹林,暮鸟投林的大树,那记忆里无数次栖止的地方,于今仅剩三间老房子而已,余外皆成废墟,复归田地,与周围田野并无二致——哪里还能找到我的青葱岁月的影子呢?
但哪怕是仅剩的三间破旧房子,也牵连起许多的记忆。房子据说是村里以前的祠堂,两扇寸余宽的实木板门,不费点气力还推不动呢。我师范毕业刚分来这学校的时候,这相互贯通的三间房有两间是老师办公室,另一间是一个集体宿舍,放了好几张床。那时候村里的小学都还有晚办公,老师们灯下批作业到星夜方散,各自回家(除我之外,都是本村的),我一人留校。来校不久就听说这办公室“闹鬼”,好几个老师都说,曾经夜里办公时,听见厚重的木门吱吱呀呀地打开,却并不见人进来。走出门四下望,没有一丝风,白漂漂的月亮。都觉得有些奇怪,把门重新掩上。过了不久,又听见门吱吱呀呀地响,徐徐打开,壮着胆子再去看时,仍旧没有一丝风,白漂漂的月亮。——我却不怕什么,其后在这屋里住了好几年,也未曾遇到过什么。倒是对同事们口中的“白漂漂的月亮”这一细节,无端地印象深刻。
甚至入夏天热时,我会锁了门,直接把被子铺在门前的乒乓球台上,露宿。学校连围墙也无,校舍后边有几户人家,都早早地安静了。周遭都是田野,无边水稻,荷风送来的香气,静静横过夜空的一只两只白鹭,加上头顶的一天星光,都独独地属于我一个人了,感觉自在地像个王子。学校旁边,两排白杨树底下,有一条灌溉用的水渠,稻子扬花时节,渠水汤汤,终夜不息。睡前可以泡着被白天的烈日晒得温热的渠水一洗工作的疲乏,如沐温泉。夜里周围都静了,只听见虫子的唧唧声和渐渐稀落的蛙鸣,哗哗的流水声就灌满了双耳,直流入梦乡。夜半醒来,耳畔流水声依旧。我有时会在心里温习起白日里背过的唐宋诗词或古文观止的句子,有时就只是听那流水,同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东山魁夷的《听泉》:“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水,日常的烦乱生活,遮蔽了它的声音,当你夜半突然醒来,你会从心灵的深处,听到幽然的鸣声,那正是潺谖的泉水啊!回想走过的道路,多少次在这旷野上迷失了方向。每逢这个时候,当我听到心灵深处的鸣泉,我就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标志。”我也会在朦胧中检视自己的生活,想一想尚不可知的未来。
那时天亮得早,农村的孩子,到校也早。学生来了就读书,全都大声地读,真可谓“书声琅琅”。有学生到校了,我也就进教室,跟班。因为学生早读都是把一本语文书翻来倒去地读,我也没太多好指导的,顺手带上本《唐诗三百首》,学生读学生的,我读我的。穿行在学生当中,走走读读,激昂处朗咏,低徊时悄吟,常常惹得学生窃笑。有时候冷不丁地,学生的读书声渐渐低了、停了,只有我的诵读声在教室里回响。大家哄地一笑,立刻又呜呜啦啦一起捧读。我每读到精彩处,也常招呼学生停下来,把刚读到的诗中的佳句写在黑板上,即兴阐释一番,学生中有的似乎听懂了,有的可还瞪着眼睛。也不必深讲,擦了,继续早读。——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应该也是一种境界吧?一首诗读到可以成诵时,丢下书本,折到教室外边走廊上,看东方既白,残月在天,远村近树薄雾袅袅,在心里把诗意默默体味一番。耳边传来零星的鸡啼,“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或“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之类相干不相干的句子会油然浮上脑海,刹那间会感到一种时空的迷茫。
那时的岁月差不多天天如此。《唐诗三百首》慢慢翻完了,又换上《古文观止》,是小开本,可以很容易握在手里的那种。“一日之计在于晨”,这话真没错。我竟然把整本的《古文观止》一路全背过来了。后来又换了《宋诗三百首》、钱钟书先生编的《宋诗选注》以及《续古文观止》《清文观止》《明清十六家小品文选》等等。
每年落初雪的时候最令人低徊,在心底里都当作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是下课时候,天阴好几日了,干冷。孩子们在教室前疯玩。似乎听见有孩子在隐约叫嚷着下雪了。出去站在廊下,看见漠漠的天空里闪过白白软软的雪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抛洒着,落地即化为虚无,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但孩子们已经小兽一样地要疯狂了,都仰着头伸出手追逐从天而降的片片雪花。转眼就飘得密了,看见近前的一对小姐弟,姐姐望着渐密的雪花,强拉着弟弟要到廊下来避避,拉不动,只好自己躲过来,扑打着身上的雪。弟弟兀自仰头,着了魔似的,还伸出舌头去接那雪片。姐姐呆望了片刻,熬不过,也再次冲进雪里耍去。老师们站着瞧着笑着,也不多管,就连办公室檐下挂着的铁钟,也迟迟没有被敲响。
雪下到晚上,地上已是薄白的一层。同事们陆续离开后,我往厨房去,打开煤油炉——是老校长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怕我一个人生火做饭太麻烦。因为落雪的缘故,心情也无端地好。正当炉子里的白菜开始翻滚的时候,有人闪身进来,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学生,一身雪,手上端着一方嫩嫩的豆腐,说是他爸让送过来的——他家是开豆腐坊的。那一晚,还破天荒地独酌了一回,心里反复地念叨着那首《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边把目光和酒杯迎向虚空。
入夜风定,惟雪片簌簌地扑打窗纸。几回放下书本,掀开窗帘,看雪,无言。甚至披衣出门,站在教室走廊尽头的麦地边,借着隐约的灯光,看雪花箭簇一般密密地斜射着,像天地间一场无声的战斗,悲壮而凄美。睡至夜深,还屡被屋后竹林里大雪压枝的断折声惊扰。
带毕业班,备考气氛浓了,学生被要求住宿,但学校条件所限,于是这原本有隔墙的三间房子被拆了隔断,打通成一整间大屋,当作师生共同的宿舍兼办公室,学生全部打地铺,靠右墙边摆着几张老师的床和桌子。我在挨着学生的这边摆个书案,堆书于前,点一盏昏黄的灯,照旧读书。孩子们上完晚自习回来,黑压压的一片都躺下了,陆续起了酣声,偶尔还会有磨牙声,梦呓,都做了我夜读的背景。时间稍长点,混得更熟了,躺下不久,有孩子低声问:“老师,看啥书呢?”“聊斋哦。”我答。于是又传出另一个声音,“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吧。”立刻引来更多的附和,连原本睡着的孩子也侧过身来了。我就随手找一篇,就着古文随口翻成白话,演绎给他们听。有的孩子说觉得有点怕了,缩进被窝里,我说那就不讲了吧?谁知反对的声音更大更多,敢情是越怕越要听啊。絮絮地讲到后来,又有鼾声起来,才悄悄地住了口,大房子里重又静了下来。
我开始尝试写文章也是在那几年里。小学校只订了省报和市报两种,我最初也就只投给两家报纸的副刊。市报不给寄样报,省报的样报也会来得晚些。倒是学生当中,有几个是镇上单位的,或是村里干部家庭的,常常会从报纸上更早地看到我的名字,上课的时候,有孩子会在桌角上放一份报纸,折成方方的,露在最上面的,正是我新发表的“豆腐块”。我在课堂上走动,经过时拿起来看,近旁几个孩子会偷偷会心地笑起来。这种时候,课本就抛开了,把自己的新文章大声念给学生听。我也常给《散文》杂志投稿,都是把手写的稿子塞进信封,贴好邮票,信封正中写明“散文(收)”的字样,然后交给镇上离邮局近的那个胖胖的男孩子。——后来发生了一件叫我哭笑不得的事情。布置学生给远方的亲友写封信,我收上来查看时,有个孩子也在信封正中写个“散文(大哥收)”,乍看觉得很亲切,细看,觉得更亲切了——这正是那个胖胖的男孩子,我的“专职邮递员”,他定是看了许多我给“散文”寄的信,同时自己也没啥远方的亲友,便自作主张地认下这“散文大哥”了。
一度发表小文章不少,但稿费其实也无几。同时又喜欢上穷游,一个人到处走走。二十岁前后,一个人去过三峡,也走过湘西。小镇本来就小,于是就有不相干的人把两者联系起来,传言说我是用稿费游了大半个中国了,到后来好多年回老家的小镇子上,都还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事。
一家来南方落地生根已经多年。成日里,青山不老,白云悠悠,从伶仃洋上吹来的风时不时地带来一阵太阳雨,人对季节的感知越来越迟钝,在这里,连燕子似乎都成了留鸟。我好多次跟现在学生、跟内地的朋友聊到小时候曾经学过的课文《海滨小城》(也在网上查过,但“海滨小城”确切的出处未知),这里跟那课文中所写的已然十分接近:木棉,三色瑾,凤凰花,桉树,椰子树,街上的凉茶店,乡村各处老的或新的祠堂,街道尽头的大海,等等。却很少能见到秋冬落叶的树木。学校里边似乎只有两种落叶树,今天初春的时候,我给落叶树连续拍了近一个月的照片,从枝头叶苞微露,新芽初绽,新绿溅溅,直至绿叶纷披浓荫匝地。两组照片放在QQ空间里头,取个名儿叫“一棵树是怎么变绿的”。有朋友看了感叹“已很少有人去用心感受自然的变化,因为世俗的浮躁已经遮住了他们明亮的眼睛”,我回说,“主要是南方落叶树很少,看到枯枝新叶是个新鲜事。”
其实在心底里,我也是一再地对当初努力挣扎并不乏享受的那段过程,对曾经的青葱岁月,无限感怀。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三乡镇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