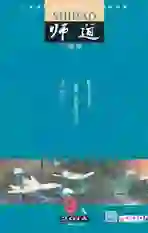我心永恒
2014-10-10朱忠敏
朱忠敏
不知不觉,就要在跌跌宕宕中一头栽进不惑的门槛了,感觉自己恰似一颗秋后漏收的玉米,虽然仍显青翠,却已经不得一夜冷风。不由得怀念起那曾经青葱苍翠的岁月:颗粒尚未饱满,须发也不曾定型,然而却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姿态。
当年大学毕业,恰逢制度改革,原来以为可以吃“国家粮”的捧不上饭碗了。懵懵懂懂中辗转来到了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犹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接待我的是一位长者,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校长。他叫我读了一篇课文,还没读完,就决定录用我了。那时候学校有三幢建筑物:一幢四层共二十四间教室的教学楼,一栋简易棚架结构的食堂,还有一间厕所,中间用墙隔开以区分男女。就在那里,我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老师以青年男女居多,学校并无专门的宿舍,于是抽了教学楼顶楼相邻的两间教室,用作男女老师的宿舍,所有人全住在一块。床是一般寄宿学校学生住的那种上下床。仔细核算下来,大概人均四平米左右,若想有点私人的空间,你就得用床帘把自己的床严严实实围起来,所以我们的宿舍那时候是蔚为壮观的,花花绿绿的床帘围出了众多与床大致相当的长方体的空间。刚开始是一点都不习惯,当你迷迷糊糊想睡的时候,呼噜、梦呓、翻床声奏成的交响曲如影随形而来,让你觉得自己随时会崩溃。我刚去的时候天气尚热,于是经常抱一床凉席,带个小枕头,披一件床单,偷偷地跑到教学楼的天面上去睡。虽然第二天起来时头常会感觉沉痛,但总比睡不着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两月,慢慢地天气渐凉,再也不能露宿,只好硬着头皮回归大宿舍。久而久之,竟也习以为常。后来我睡觉时雷都打不醒的本事,估摸着也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那时还有一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我常有夜半起来方便的习惯,起床后你得先下四楼,然后穿过一个篮球场才能来到对面的厕所。碰上大雨或异常寒冷的时候,常会狼狈不堪。吃过多次苦头后,我一般不敢在入夜后多喝水,临睡前也一定会清空内存。还有,印象中除了办公室会有一点喝的热水外,其它地方是没有热水供应的。于是很多人冲凉就成了问题,我没有关注别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我在那里几年硬是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反正我一年四季冷水浴到底。而且我发现,尤其是冬天,洗了冷水比洗热水感觉被窝暖得更快,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好在得益于那些年农民工兄弟们源源不断涌入城市,学校得到了飞速发展,记忆中好像第二或者第三年就又建了一幢更大的教学楼,并在新教学楼的顶楼给教师们留了一层做宿舍,虽然仍是8个人住一个套间,但里面好歹有了卫生间。
学校大众食堂的伙食是可想而知的,几乎所有人都不习惯。好在出身厨师世家的我有一手还算过得去的厨艺,而且还乐于下厨,于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年轻聚在一起,买一罐煤气、一个小单灶,就算是另起炉灶了。学校地处偏僻,门前刚好就有一大块菜地。那些菜农们也很淳朴,随便给个三瓜俩枣的就能换回一堆时令鲜蔬。那时我们吃得最多的菜恐怕就是爆辣椒、青椒炒肉和香葱煎鸡蛋了。碰上周末,还会搞个小Party什么的,纵论时事新闻,关注社会热点,聊聊新人新书,谈谈风花雪月,倒也乐在其中。
那时我每天的工作基本上是从5∶30开始的,因为学生比较分散,附近几个镇区都有,所以学校接送学生的校车很早就得出发。记得当时我跟的是9号车,应该是路程最远的一趟,因为我常常比别人早出发,常常比别人晚回来。碰上冬天,铁定是天黑出门,天黑归校。跟车确实是一项辛苦而繁琐的工作。学期伊始,你得汇拢所有坐你这趟车的学生名单。一一打电话跟家长确认学生的实际家庭住址,然后合理确定乘车站点,再逐个告知学生和家长具体什么时间到哪里坐车。时间要精确到以分为单位,不然你去早了,学生还没来,去晚了必然惹抱怨。每个站点多少学生上车,你心中一定要一清二楚,人未到,得打电话给家长核实是迟到还是请假。所有的学生上车或者没上车的学生情况核实清楚后你才能返航。而这,还只是开始,因为车上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有,强弱很分明,再加上往往乘的实际人数远超座位数,所以争抢座位的事时有发生。你得随时提高警惕,应付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随时得提醒司机注意车速,提醒学生不要将身体伸出窗外,上下车时不要乱挤。刚开始没经验,总是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后来干脆给每个学生安排好座位,二年级以下的基本每人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大一点的每两人固定一个座位,轮着坐。行车过程中给他们讲讲故事,玩玩脑筋急转弯,或者唱唱歌等等。这样一来,无论是秩序还是出勤时间都得到了保证。乘车学生对我这个跟车老师也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每每在校园内听到车上的学生指着我对他们的同学说:“这就是我的跟车老师”时,心里总会感到莫名的安慰!
当然,那时我大部分最快乐的时光还是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这不是矫情。事实的确如此,那时尚未谈恋爱,再加上吃不好也睡不好,总得给自己找点寄托呗。我的寄托在两方面,一是读书,那时比较钟情于现当代文学。像巴金、茅盾、沈从文、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王安忆、池莉等人的作品,大部分都读过。尤其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更是数次拜读,如果说自己还能写点东西的话,那确实得益于那段时间的海量阅读。另一方面就是我的学生了。我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那时的我刚出道,教学经验尚浅,驾驭课堂也不是那么驾轻就熟,我就经常问自己,你拿什么去吸引你的学生?我知道孩子们都爱听故事,于是每堂课前大约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我会精心准备一个与当堂课内容相关的小故事讲给他们听,这些小故事或激发兴趣,或引人莞尔,或发人深省。比如诚信,我给他们讲成绩相当优异的留德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原因是他在德国有三次地铁逃票记录;比如谦让,我给他们讲“六尺巷”的故事;比如尊老爱幼,我就给他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还有,像UFO、聊斋故事、抗日战争故事等都是他们所喜爱的。记得有一次讲解试卷,这是语文课里比较枯燥的课型。试卷中一道阅读题里出现了痴人说梦这一成语,我就给他们讲了这个成语故事,大意是一个纨绔子弟,一天一大早醒来就把贴身仆人暴打一顿,旁人问其故,曰:“这狗奴才,昨晚我明明在梦中见到他,叫他他居然不答应!”学生爆笑,那堂课效果相当好!甚至于后来“我明明在梦中见到你”这句话一度在班上广为流传!除此之外,学生们在校期间,我基本上跟他们同吃同住。那时学校条件简陋,学生们午休只能趴在自己的课桌上,于是我也就趴在讲台上陪他们。午休结束铃一响,揉揉惺忪的睡眼,站起来伸伸酸麻胀痛的胳膊,师生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许是这四年中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我被另一所学校相中,这里的学生每年光学杂费就要好几万。在这里,我又开启了自己一段全新的历程!这里的学生相对家境优越,见闻更广,自我意识更强。熟悉了农民工子弟的我,突然间面对一群富家子弟,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不管再怎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内心里始终对自己说:“他们只是一群孩子!”我开始用笔在自己的工作日记里记录他们,他们的点滴进步,包括他们的错误都被一一记录,我的做法,我的想法也都随附其后。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将这些打印成册,每个学生及家长送了一份。现在还记得,那本小册子我取名为《我心永恒》,后来,还有家长将其送至了校长的办公桌,给予了我极大的肯定。在那里面,我毫不掩饰地指出了我们的孩子对苦难的感受能力近乎为零,他们过得太顺了,尤其在物质方面。我与几位家长聊天时提到如果有机会想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农村的生活,当时也只是说说,并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家长们反应很积极,很快就有人整合资源并将这件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还年轻,敢想敢做,换成今时今日,我未必敢下那样的决心。就在那个假日,在家长的陪同下,我尝试性带了几位学生去了一趟农村,我一直记得他们在车上看到牛时的那声不约而同的惊呼,看到同龄人穿着露出脚趾头的鞋时的那份惊讶,还有回来时他们一直说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蔬菜。那一次旅行,给孩子们触动很大,也同样给了我很大触动。后来我全力支持一位挚友创办了一家公司,其主营业务之一就是带城市的孩子去体验贫困山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于城市的孩子而言,这实在是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一个极为有益的补充。
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提,我感觉自己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比较华丽的转身。事情是这样的:我以前很喜欢现当代文学,对儿童文学很少接触,读得也很少。但越来越多的人跟我说,想了解孩子,要多读儿童文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一本叫《青铜葵花》的书,作者曹文轩,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听都没听过他的名字。《青铜葵花》应该不是代表曹教授最高水平的作品,但我知道,它给我开启了一扇门。那天晚自修,孩子们在下面写作业,我拿着《青铜葵花》在讲台上看,当看到青铜为了让葵花照一张相,大冬天的把脚下的芦花鞋脱下来卖掉时,无端地,我的眼泪稀里哗啦就流了下来。直到两个懂事点的女生拿着纸巾轻声问我:“老师,你怎么了?”时,我才回过神来自己失态了,抬头一看,所有学生都呆呆地看着我,他们不知道老师到底怎么了。那一刻,我就决定要让他们也读读这本书。那个周末,我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家长,让他们给孩子买这本书,并恳求他们一起读读这本书。后来,我们班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本书,没有一个人没多次读过这本书,据我了解,几乎所有的家长也都读了这本书;再后来,我们班召开了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家长参与的“同读一本书”的读书会,会议空前成功,赚足了眼泪,也赚足了掌声;再再后来,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黑瓦》、《根鸟》、《细米》、《野风车》、《狗牙雨》等作品开始在班上传阅。这件事让我明白,我永远代替不了学生的阅读感受,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不仅要自己喜欢阅读,更要推动学生喜欢阅读。
回忆起熟悉的生活,总感觉没完没了,好在自己还有点东西,能拿来纪念那些曾经青葱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