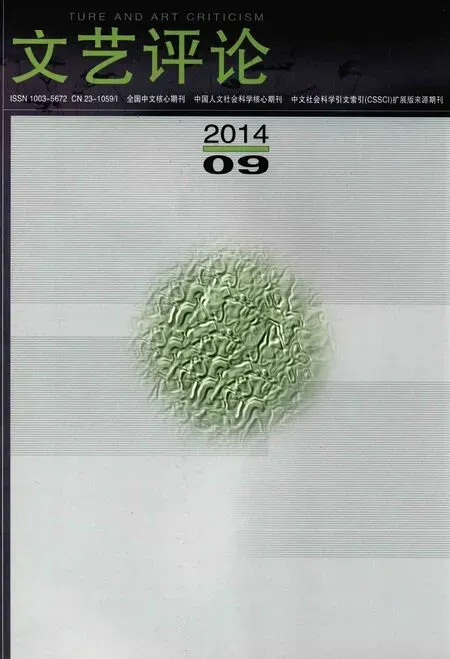这时,灼热的阳光正流连在青朴山上——读鄢然散文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
2014-09-29○邓伟
○邓 伟
在读鄢然若干的小说与戏剧之外,近期又读到她的散文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沈阳出版社2013年版),清晰展现出另一值得关注的文学空间。在此散文集之中有《圣山之恋》一篇,最末一句话——“这时,灼热的阳光正流连在青朴山上”。正是由这一句出发,我们将从整体上审视这一部散文集,并将之作为这篇评论的标题。因为,我们认为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切入到了鄢然散文的某种核心与特质。
这与散文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的内容题材相关,全书分为三辑,分别为“藏行者漫记”、“游戏者杂记”和“阅读者手记”。这样的安排关乎鄢然的生活经历:
我的青春我的好年华都是在西藏度过的,但我人生的最后归宿将是有着天府之国之称的川西平原。我是从成都进藏的,我也早已从西藏回到了当初的出发地。人生就像是画圆。如果说人生是在画圆,圆周的两个一半对应的便是我的两个半圆:四川与西藏。
于是,在西藏与四川的结构性时空转换之中,我们看到“这时,灼热的阳光正流连在青朴山上”——它带给鄢然散文的某种整体的氛围与质地。青朴山——这一西藏圣山——的阳光长久地留在了鄢然的内心,并不断灼烧,成为其包括散文在内的诸多文学样式的内在性构成。可以说,即便是那些与西藏无关的题材,西藏也成为一个明显“缺席的在场”。让我们再细味这一句之中的“这时”一词,说明“灼热的阳光”在此刻仍然地照耀与眷顾鄢然,并不因为时光的荏苒而成为“那时”。虽然,她已经回到、工作与生活在了成都无数年,西藏圣山的阳光仍是在内心普照。亦如鄢然的感慨:“我情思悠悠的藏雪呵,最终都会化在我如今生存的川土上……”
鄢然西藏经历与体验的核心是青春与生命意识。因为青春的充盈,西藏成为她生命的承载,也成为日后不断回眸鲜活明媚而又区别日常生活的空间存在。在《此情悠悠》、《泽当:我生命的驿站》两篇散文之中,我们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初入西藏工作少女的眼睛,打量着这一陌生的世界:有对父辈“老西藏”的沉思,其中无言而博大父爱的弥散;有“师傅父亲和作为徒弟的大头”的故事;有对最初工作地点的牧歌式描绘;有对曾经同事朋友的经历与“趣事”的津津乐道;还有年轻的心对爱情的渴望……在这些并不算十分复杂的往事叙述之中,一种回忆的基调使得曾经的西藏生活具有了生命力,进而显示出特有的魅力。这正是散文的当行本色,现在与过去构成了一种心理时间,并融会无间而随意出入,显示出鄢然散文语言朴实流畅而摇曳多姿。这些散文篇章符合教科书上关于散文哪怕是最为严格的定义,无疑也是散文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之中最为迷人的部分。
我们忘不了在西藏之中,那一个叫“泽当”的小镇。它曾经安慰了最初带着“被放逐”而充满失望心情的少女:
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和父亲就逛完了小镇。小镇实在是太小了。奇怪的是外貌简单的小镇在落日的余晖下弥漫着神奇的气氛,使我产生了进入格林童话世界的感觉。至今我也不明白,那种神奇是来自于小镇上穿藏装的人们,还是在街道两旁嬉戏玩耍的“蓝精灵”。躺卧在群山怀抱中的小镇静静地以她的扑朔迷离迷住了我,不知不觉扫去了我的凄凉,我开始朝着陌生的人们微笑,我的笑容令父亲开心。
或者是泽当镇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铁皮房”:
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单位造房都是用白铁皮代替瓦片盖房顶,用黄土石块建房身。所以造出来的这种铁皮房,既不是藏式的,也不是传统的汉式瓦房。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铁皮房的房顶泛着一片银光,从远处看平地腹心的泽当镇,倒是好不耀目、夺目。
这样的奇情异彩构成了鄢然记忆深处感性西藏的底色,这样的描写自然也有着她西藏生活的基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西藏”何尝不是鄢然心灵的折射与产物,长久地超时空地传流出来,进入文学,为自己的青春与生命镀上炫目的色彩,赋予过去生活以同质的意义。这样,我们看到了一幕——即便是那“破旧不堪荒凉无比的小镇”,也成为了“格林童话世界”,同样是阳光在不断闪耀。所以,当鄢然感慨“旧日的泽当,已被今天要漂亮得多、现代得多的泽当镇取代,因此,我再也不能走进我熟悉的那个小镇了,除非在梦里,在记忆之中”,我们想说的,即便是在过去,可能也并不存在那种“旧日的泽当”,它可能只是鄢然一段青春与生命的弥补性想象,从那一抹阳光开始,在其内心与文学之中存在,并无穷地弥漫,幻生出了若许的奇情异彩,而与现实似无太大的关系。
鄢然与西藏的青春相遇似乎同样也注定她将只是一个西藏的过客——这样的话或许显得比较极端与残酷。同在《泽当:我生命的驿站》之中的一段话,我们想可能更为接近真实:
那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年轻,体会不到泽当镇的魅力,对那些充满着浓郁文化与历史底蕴的民间故事是那样的漫不经心。与我们相反的是,古老的泽当,却总是吸引着拉萨的文化人到此凭吊,寻找西藏文化的根、西藏历史的梦。在泽当镇生活的那两三年里,要不是我跟随着从拉萨来的作家、诗人们爬上了贡布山,参观了猕猴洞,还有雍布拉康和昌珠寺,到今天,我的遗憾会更深,我在小镇的生活,会更平淡无奇。
鄢然的“西藏”,一方面是由民间故事、文化人的凭吊以及日后由概念性的“西藏文化”、“西藏历史”构成,另一方面则是平淡无奇的小镇生活。但是,二者在年轻的心里并不矛盾,在不断重叠,相互映照生辉,都成为了一种时光之中的感性的空间“现实”。
很重要的是,我们还想说明的是“文学”在鄢然西藏生活之中扮演的角色,“文学”带给她西藏体验的意义。我们相信这也是她西藏体验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这也与她后来调到西藏人民出版社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在《有关“麻风村”的零散记忆》一文中,重点谈及的马原的《虚构》,以及自己作责编出版马原的《西海无帆船》一书。在《成长中的记忆》一篇之中,鄢然还以其散文之中较为罕见的郑重笔调写道:“西藏人民出版社作为我西藏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组成了我的人生符号中最神秘最神圣的一个代码,成为我永不消失的西藏情结,是我已经写作并将永远写作下去的动力。”可以说,更多的是在一种精神世界之中,在文学的无限生长之中,与西藏的某种氛围产生了契合与想象——这也是一种较为个人性的体验。
可作旁证的是,当鄢然离开西藏之后,再回到西藏旧日的工作与生活过的地方,就在散文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之中留下了不少的图片,而图片的说明文字多为解释这是在西藏的某地,不少的就自然与其文学创作联系了起来。兹举两例:
站在羊卓雍湖前,一切恍然如梦。三十多年前,我还在西藏山南地委秘书科工作时,曾随地委张副书记、高秘书长等到浪卡子县了解农牧业生产情况,那时在羊湖边上,可没有立这个碑,更没有一辆接一辆的旅游车。而是有许多飞禽在湖边活蹦乱跳,我曾在短篇小说《不仅仅是挽歌》中写到逮小野鸭的情节,可不是虚构,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
这是作者在其短篇小说《白面具中拉姆的情爱之灵》中曾写到的藏王墓所在地的留影。藏王墓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境内,是西藏保存下来规模最大的王陵,吐蕃王朝时期第29代赞普至第40代(末代)赞普、大臣及王妃和赫赫有名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都葬于此。
不管是从西藏的某一地域想到了自己的小说,抑或相反,西藏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鄢然的文学创作之中,纸上与现实之中的西藏相互显现,难以分辨。“西藏”的形象成为了鄢然在现实之中以文字构筑与创造的一个世界,让你无法区分舞与舞者。
在西藏书写之外,散文集《半是藏雪,半是川土》以更多的篇幅展现了鄢然在成都的工作与生活,即是第二辑“游戏者杂言”。散文书写题材的转变,不仅在于地域空间的变化,更表明在心态之上。在告别了青春之后,生活就是生活,无法躲藏。在四川,褪去了昔日的西藏光环,基本上没有了如同西藏那样的奇幻故事,鄢然和我们一样,努力工作,重视家庭,思考着身边的社会,乃至于有暇之中愉快地阅读书籍——一个更为成熟与热爱生活的鄢然向我们走来。大略而言,成都时期的鄢然散文在内容方面有在四川各地采风的感受、对日常生活的咀嚼与感悟、对自己关注的戏剧发展情况的思索、还有作为阅读者畅游西方小说名著的心得。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些就是成都带给鄢然的全部,所面对的世界完全与鄢然没有了距离,一切以文字平实地汇入到了散文,散文就是她生活的本身,于此同时也消失了西藏题材散文的那一种奇情异彩。
接着,让我们追寻鄢然留下的“川土”足迹。如有论者的看法:“个体日常生活的空间,即‘他的空间’只能由他自己个人来经历,不可由其他人来代劳;而且,正是这种空间经历构成他自己的空间。”我们发现,“四川”的空间,或是鄢然面对苍溪县生态庭院建设的示范村的感受:
一种羡慕伴随着惊讶油然而生:但见沃野田畴,农作物长势喜人;错落有致的川北农家小园,翠绿掩映;幽径小道,宛如玉带飘落在铺天盖地的绿色中;庭院内,蝶拂花梢,花红灿烂。放眼看去,苍溪雪梨、猕猴桃新品种红阳果、脆香甜柚等果林环绕四周。一片葱茏,香飘四溢。
或是在成都近郊的洛带古镇的遐想:
老街是陈旧的,青石板铺成的路面坑坑洼洼,留下了时间的皱褶、年轮的印痕。载客的三轮车在路上奔跑着,溅起了一股股酱色的泥水。脚下凹凸不平,我们穿着高跟鞋,深一脚浅一步,感受着细雨中那透着明末清初建筑风格的瓦舍房廊,想象着这个社区家园的建造者和他们的祖先在漫长迁徙路上奔走的情景,便有了一种敬佩和感动。
她仍为自己生活中与“川土”的相遇而感动,思考所面对世界的现实与历史,从中流露出一贯的人文关怀。那么,曾经的西藏呢,“一个密切相关但并不在‘此’的地点(旅游地、冒险地、初恋地、久别的故乡等),它可以用记忆、照片、故事等表象方式在我们生活世界中重复,从而与当下的生存空间形成鲜明对照,但它无法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相衔接,正是这种在别处、不可衔接,或者说某种乌托邦的形式对我们的生活形成了影响。”在此,我们想起了《黄龙溪偶遇的西藏印迹》一篇,当在成都的黄龙溪偶遇“我在西藏工作时家居科委大院内的一个邻居”之时:
我问他现在哪里工作,说自从我们这些邻居从西藏内调回来后,各奔东西,都十六、七年了,一直不曾碰过面,怪想念的。我不好意思地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姓吕,我又自报了姓名,他这才弄清楚了我的身份,想起我们曾家住两隔壁,笑着说他刚才把我当成他的另一个熟人了。
这仿佛就是与西藏关系的一种象征,既熟悉而又陌生,而更多的是遥远,在曲折跌宕之中显得富有张力。鄢然转而融入到了在成都的工作与生活之中,开始了更为无意的为文,更为信笔信手地书写琐细的日常世界了。
在其中,鄢然还写作了不少有关在当下社会之中戏剧存在情形的散文。既有对川剧艺术家崔光丽表演的高度褒扬,也有对川剧在市场经济之下深深的喟叹,更有义愤于在行政指令之下对戏剧发展带来伤害的做法。我们读到鄢然散文之中这样的话:“我们的功夫都还用在了哪里?如果我们把这些财力、人力不是用在让领导的满意上,而是真正用在戏剧改革的刀刃上,情况会怎样?”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愤愤不平的鄢然,与我们在这本散文集之中见到的那个性格温润的好女儿、好妻子、好员工的形象截然不同了,瞬间爆发出来的真性情颇令人瞩目,也是极为可爱的。
在第三辑的“阅读者手记”,我们看到鄢然“阅读一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的感悟与思考”。固然,这些散文篇章是在鄢然不断向文学大师的致敬,同时何尝不是一种对话,或许预示着鄢然散文乃至文学探索新的动向。我们关注着这些阅读带来的散文之中所采用的话语方式,随举两例:
凯尔泰斯的悲观是一种勇敢,这种勇敢能够让他平静地面对从人类伤口里渗出的脓血,为人类的堕落作证。凯尔斯泰的这种勇敢和冷静的悲观主义,还有他为了存在而进行的孤独中的“自杀性思考”,并持之以恒地用文字表述他的这种自杀性的“幸福”,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
霍桑用《红字》讲述了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人类无法避免的悲惨故事,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人的灵魂,人类各色各样的灵魂,而霍桑用人类最强烈的两种情感——爱与恨,讲述人的心灵中有关原罪、信仰、救赎、解脱直至升华的问题,完成了他对灵魂的诉说。
显然,“人类”成为了关键词,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观念超越。由此,我们产生了联想与展望,即是鄢然写作四川生活散文的平实朴素,让人大有原生态的感觉,但在另一方面,在与日常生活的日益趋同之中,鄢然是否应更为积极去追寻精神的向度,开拓出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空间,进而在其散文乃至文学之中展现人类的生存与灵魂——如同她在阅读西方经典小说时的深深体会。最终,我们又想起“这时,灼热的阳光正流连在青朴山上”这一句话来,可以说生命本体的体验与感悟构成了鄢然“藏雪”与“川土”散文写作的全部的出发点,因为无数巨大而闪耀的青朴山正迎面向我们走来,发出声声召唤,在生活的每一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