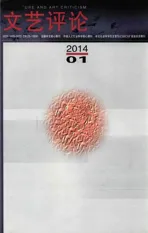新历史叙事的拓展与类型化反思——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则天”题材创作为例
2014-09-29柯丽娜
○韩 伟 柯丽娜
20世纪以来,原生态历史叙事一去不返,它只能借助语言这个特殊媒介转换为具有文本性的遗留态历史,依靠遗留态历史而形成的叙述态历史更不可能获得真实的历史镜像。正是出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作家彻底放弃了对历史真实面目的索求,仅仅执著于综合各种文本折射的历史影像,努力重构出某一时代大致的文化氛围。不仅仅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如此,始终奉历史唯物主义之真为圭臬的历史传记也打破刻板复制历史的原则,多采用小说惯用的故事情节,作品中对话描写、心理描写随处可见,很多历史传记几乎可以和通俗小说划等号。①
诚然,当年如火如荼的新历史潮流已经逐渐淡出我们的理论视野,但其影响仍深深地植根于文学底层。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潮流做一定的回顾,并对当下已经多少发生质变的历史叙事进行反思。因此,本文权以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经典的历史形象武则天作为考察对象,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整理,尽管这种考察存在管中窥豹之嫌。
一、传承与断裂
20世纪90年代的武则天题材小说大都不再被历史典籍束缚,大有天马行空任我行的姿态。武则天的帝王身份也不被有意回避,对素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叙事时间的扭曲、变形都较以前有很大的突破。这一时代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武则天的公共性生活不再被当作小说叙述的核心,而原来处于重大事件点缀地位的私人生活跃居叙事的核心地位。这种质的飞跃无疑使历史向人性化书写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历史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从而获得了更加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不是一个“断裂”性和自足性的空间,它是在过去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也同样是另一个时代和诸多时代的生长点,因而不可能和过去完全地割裂开来,必然表现出和20世纪90年代之前创作的相似之处,并隐约地昭示着未来创作的某些趋势。
首先,对可能性历史的真实性书写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意图。苏童《后宫》(后序)中说自己“没有虚构一个则天大帝的欲望”,其武则天故事“不出人们想象,不出史料典籍半步”。朱兵、张兰亭合著的《武则天》在前言中也宣称读过此书后,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一个较为真实、具体而完整的武则天”。与此同时,为历史人物的“翻案”和“辨诬”的冲动在20世纪90年代也得以延续,包括对武则天政治业绩的肯定:“……武则天的政治业绩有三:任贤纳谏、发展生产、强盛国力等等……这些都功垂青史,名留当代。”②对女皇豁达心胸的赞许:“……女皇叱咤风云五十年,建立了诸多功绩,却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凭褒贬。仅此足可以看出这位不寻常女人的胸襟和气度。”③对武则天历史地位的肯定:“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确为中国女人争了一口气”④等等。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借古讽今的集体主义“醒世特色”有所减弱,更多的是借个人的现代思想意识和人生思考颠覆以往历史叙述。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小说叙事不仅为千年以前的古代历史学家小说家书写的武则天“翻案”,而且也为现代以来包括新时期的小说家创作的武则天形象“翻案”。冉平主张把武则天当作一个“人”来写,“无意塑造一个女英雄,又惟恐把她写成‘小女人’。思来想去,还不如从写一个寻常人入手,以其寻常之处写其不寻常……让一个寻常人的七情六欲在名人伟人的身上显示出不寻常”。⑤而赵玫将这种思想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她借小说叙述人之口指斥前代作者们,不能正视小公主暴死这一历史疑团。“他们仿佛全成了侦探,事过以后他们就都进入到那个出事地点,并跟真的一样掌握了几百年前武曌的犯罪动机和她的犯罪经过”。然而,谁又能进入唐宫重重宫闱之内去证实作者所谓的新生儿的死亡率几乎是总数的一半的事实呢?显然,“翻案”小说中存在着两套叙事话语,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历史话语用于描述层面,现代话语用于阐释层面,两者如何能有机结合,不至于偏离错位,换言之如何解决历史小说中叙述逻辑上的矛盾,不仅是武则天题材小说必须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所有“翻案”类的历史小说必须正视的首要问题。
其次,20世纪90年代虽然已经很少有作家直接批判武则天的“牝鸡司晨”,但一些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认为女性获得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带给大唐王朝不幸的同时,也注定了女性的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罗石贤在《盛唐·四朝真相》中有这样的评价:“……描写了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唐太宗、最好的皇后长孙皇后、最好的宰相魏征,还有一个最坏的皇太后武则天。”⑥在这简短通俗的评价里,可以分析出两点:第一,武则天最后的定位不是皇帝不是皇后,而是皇太后。第二,与唐太宗、魏征、长孙皇后的大贤大德相比,武则天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苏童笔下的武则天是“对李唐皇族的光辉历史的大胆颠覆”,并承认“自古以来红粉之祸都是穿天之石”,言外之意,皇帝的冠冕带到女人的头上就意味着灾难即将降临,而一切的不祥不是源于别的,而是源于女性夺取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牝鸡司晨”就意味着历史人物悲剧性的结局,历史像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一样,不论你怎样挣扎最终都只能走向虚妄无言的结局。在这些作品中,武则天每每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机会而抛弃亲情、利用酷吏、疯狂杀戮、弄权后宫。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家努力使人物生活化、鲜活化,但负面的历史倾向决定了他们难以用积极的笔触演绎主人公的人生,这样悲剧的结局便在所难免。在苏童笔下,武则天临死时紧含在口中的紫檀木球泄露了武则天内心,也印证了作家本人的基本态度。同样,北村笔下的武则天虽是一个聪慧强悍的女子,但更是一个自我精神分裂者,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极度的孤独与恐惧之中,从武则天获得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开始就标志着她进入了孤寂的心灵荒漠,惟有永恒的死亡才能拯救她的灵魂。换句话说,武则天一生的拼搏努力只能最终走向虚无的精神荒漠,在寂静中了此余生。
再次,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叙事出现了情欲化的书写倾向。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世纪90年代可以称为“一切历史都是欲望史”。这一时期的武则天叙事尤为注重武则天与高宗、薛怀义、二张等异性的情爱。武则天与异性的关系变成了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并纯粹是两性交易,很少有两性之间的真实情爱。苏童借太子弘的口表达了自己的道德立场,也是作者的道德评判,“我怀疑我所有疾病都缘于那种不洁的乱伦中的父精母血,我在铜镜中看见我的郁郁寡欢的脸,看见一条罪恶的黑线在我的脸上游弋不定,我甚至经常在恍惚中看见闲置于感业寺的那张淫荡的禅床,孕育于罪恶中的这个生命必将是孱弱而悲伤的,我想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大唐的命运是悲哀而神秘莫测的,“我想一切都是李氏王朝的气数,一切都很神秘而不可逆转”。(苏童《武则天》)从叙述者的陈述不难看出,太子弘孱弱的身体不是缘于疾病而是缘于母亲和父亲不洁的性关系,而母亲无视纲常的放纵行为也必定是大唐难逃的劫数。值得注意的是苏童对唐太宗、唐高宗的评价重心是他们作为普通人所有的弱点和缺陷,但在两性关系方面苏童不置可否。乱伦于男子是天经地义的家事,而于女人就是不能饶恕的罪恶之源。这让人想起了后世作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界定:“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那就该死;女人把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把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更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还污了刀。”格非、北村等人都在作品中表示过类似的思想。
总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对武则天的书写较之以前取得了实质的飞跃,但是在很多的小说中,尤其是男性作家笔下,鞭挞“牝鸡司晨”和“淫秽春宫”的传统儒家思想仍然时有流露。很多论者批判当下是一个媚俗的时代,因而对这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多元文化话语构成的文化时代充满抵触情绪。但是与拒绝相对的是我们必须和世俗人们不断地对话和沟通,对正在发展的大众文化有更明澈而机敏的观察。历史不仅仅是私人化的,而且是欲望化的。历史小说如果缺乏情欲化的书写会削弱小说的情感潜能,但过多的情欲书写又会喧宾夺主湮没小说主题。如何使情欲化书写在历史小说中获得恰当的定位,构筑健康的性文化观,使其成为小说的看点而非败笔,无疑是留给所有小说家的问题之一。
二、权力场与私人场景
事实上,历来对武则天的褒贬不一,对她的攻击和非议主要集中于:一是所谓的“牝鸡司晨”,二是所谓“淫秽春宫”,三就是她的任用酷吏,诛杀宗室重臣。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将宏大叙事与个人书写相结合,权力场和私生活构成了主要的叙事场景。权力与私人情感的缠绕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所有武则天叙事的蔚为壮观的潮流,而这一潮流在当下的宫廷剧、历史剧中仍在延续着。(将在下文谈及)
有论者已经指出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权谋叙事倾向非常明显。⑦许多历史小说家热衷于对权谋权术的叙写,而人物的塑造也被置于激烈尖锐的权力斗争中完成。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叙事中对权谋叙事的描写更是出现了热潮。最有代表性的是葛思绪的《武则天大帝》。在“作者序“中,作者明确地为自己的武则天书写做了一番定位,他说:“惟愿这近百万字的‘大部头’能使读者朋友读后对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阴险、狡诈、毒辣、残忍及玩弄权术,既会抓政权,又会抓兵权的武则天有一个新的认识……”作者先叙述武则天天生的权欲倾向:武则天抓阄时抓皇帝亲赐的玉佩;孩童时说“皇帝轮流做,何日到我家”的话等。其次,又设置一些权欲化的情节,体现其对权力的向往及为攫权而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可以心狠手辣地铲除别人,包括自己的亲子”。野岭伊人也把武则天的权欲写成天生。在曾解道《武则天唯我独尊十二攻心妙计》(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版)中,武则天是善用权谋的“铁血女皇”和放荡不羁的“天下淫妇”。他在书中列举了武则天的十二种手段:
算计——用心思设计人生大目标
驾驭——操纵知人善任
布阵——靠手段调度对手
藏心——越隐秘越奏效
较量——软硬兼施,套住人心
嗜酷——严厉治人显威猛
离合——摆出不同姿态震慑人
用权——一招一式皆有法度
突破——敢于在困境中挺身
纵横——可收可放、心中有数
借力——用第三只手设局
躲闪——善于保护自我的安全
可以说曾解道先生几乎概括了所有武则天权谋叙事的主要内容,在作者的笔下武则天几乎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铁腕女人,武则天辉煌政绩的取得完全是依仗了她无与伦比、屡试不爽的奇谋妙计。由于对权谋的关注成了贯彻作品始终的主线,所以在人情人性的刻画方面几乎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所有的权谋叙事难以克服的弱点。与之类似的还有刘后滨的《巍巍无字碑:武则天治国谋略》、代凯军的《武则天谋政经国的九九方略》、樵子的《石破天惊:武则天统驭方略》等等。
关注了武则天在极端危险的境遇下的“艰难的成长”,蔚为壮观的权谋叙事已经成为近年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普泛性潮流,一方面是因为环环相扣,悬念丛生的权谋叙事更多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另一方面当下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使得人们对如何摆正自身的位置,如何在变幻莫测的复杂人际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成为职场上的杜拉拉充满疑问,而青史留名的众多的帝王将相以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在政治场上游刃有余的表现无疑成为现代人可供参考的典范,现代人急需从他们的身上寻找一种自身所需要的为人智慧,权谋叙事无疑是首选,近两年来充斥电视荧屏的《杜拉拉升职记》、《宫》、《步步惊心》、《甄嬛传》等影视剧的泛滥便是绝好的证据。通过文本的阅读、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与权谋叙事相伴是私人场景叙事。尤其在男作家的笔下武则天政治上的成功更多的得益于她特有的女性身份。
因而在大量的小说叙事中与权力场密不可分的是私人生活场景。从古至今,武则天在政治上的成功始终和她女性独特身份相关,在不同朝代的文学作品中武则天以其美色和无穷的性能力迷惑着高宗,以其心计控制着高宗,武则天是一个让高宗恐惧又不能离开的女人。以须兰的《谁想毒死我》为例,她笔下的武则天被推上了至尊皇位、武则天一直仰慕先帝太宗想做贤君的女性,因而在男权世界里左冲右突。她在政治上的得意风光总是和私人情感生活的悲哀落寞如影随形,须兰没写武则天的政治业绩,也没有过分关注她的私人生活感情,而更多地写了权谋与情感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写她被卷入政治争斗时的复杂心态,那就是用身体交换政治舞台的入场券的辛酸与无奈。而20世纪90年代个人记忆的自由书写的直接结果就是多种个性化、情感化的武则天形象的涌现。如野岭伊人《风流女皇武则天》中淫荡毒辣的武则天形象、葛思绪《武则天大帝》中权欲熏心的武则天形象、赵玫《武则天女皇》中情欲化的武则天形象、冉平《武则天》中寻常女人化的武则天形象以及须兰《武则天》病态疯狂的武则天。不能否认,上世纪90年代本来就是强调个性化和差异性的时代,关注个体,关注差异性是其显著标志。而让历史的差异性以其自身的形态呈现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念。虽然我们不能把历史小说创作个性化、差异化特征的出现仅仅归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不能否认任何实践和创作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彼时众声喧哗的理论思潮的影响。
与展示武则天自身应然的主观因素相关,20世纪90年代的武则天题材的创作在让历史人物“活”起来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将创作主体身上的一些现代意识,包括存在意识、情欲意识等等也投注到人物身上。现代人思想观念的渗透在武则天的创作中并不少见,如格非写武则天在险象环生、阴谋叠加的宫廷依靠权力和智谋,不动声色地排除了威胁自己生存的人,夺取了江山,全身心地投入国事,将大唐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她并没有在功成名就之际找到人生的乐趣,反而品尝到人生的虚幻。格非在文中揭示的不仅是女性更是全人类在历史漩涡中悖论性的生存处境。在北村笔下则着重塑造登上权力巅峰的武则天对生命,对活着意义的探寻。赵玫、须兰又以现代女性的心理去体验、揣摩历史尘埃中非凡女性的生存境遇和被动无奈的选择,写出她被卷入斗争时的孤独与绝望。
三、类型化与反思
与小说创作相比,武则天题材叙事的另一个重要场域则是影视剧本的创作。如果说北村《武则天》、刘连银《武则天传》、葛思绪《武则天大帝》、冉平《武则天》、须兰《武则天》、杨书案《风流武媚娘》、野岭伊人《风流女皇武则天》、赵玫《武则天》、唐浩明《风流女皇“武则天”》等代表的是读书时代对武则天的演绎的话,那么各种电影、电视剧版本的出现则是读图时代下感官和欲望被极大扩展之后的产物,而这也可从另一个侧面透视新历史叙事与消费时代合谋的现实景况。笔者认为在当下穿越剧、戏说剧、女性宫廷剧等题材的影视作品将历史解构得七零八落的大背景下,重新探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武则天题材作品的发展脉络及其质变过程,无疑对更好地审视当下的类型文化乃至类型文学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由于影视语言拥有文学语言所无法比拟的直观性,反而更能彰显新历史叙事带来的形象与情节的全新样态。
可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哪个影视形象像武则天这样被持续关注,并被持续搬上荧屏,每个时代都以乐此不疲的态度宽容地对待着这位历史上的传奇女皇,自从1963年由王月汀作为编剧的电影《武则天》出现之后,50年中不同的编剧根据自己的好恶以及时代的审美风尚已经创作出十余个不同版本的武则天形象,从而完成了武则天形象“人——宫廷女人——普通女人”的三级跳,上世纪80年代冯宝宝版《武则天》、潘迎紫版《一代女皇》实现了对史书生硬而带有脸谱化叙事的反拨,从而使武则天这一历史上的“奸人妒妇”(《新唐书》语)形象重新以“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冯宝宝的倔强与美丽、潘迎紫的大气与豁达将冰冷的历史形象以极为鲜活的样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到了上世纪90年代,相同题材的文学创作则更关注历史真实,其实现途径则带有鲜明的新历史特色,将展示的焦点聚焦于武则天作为“宫廷女人”的独特成长史,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一方面有还原历史真实的冲动,也有展示人物真实的考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小说创作方面本文第二部分已经介绍,在影视作品方面则不能不提到以冉平执笔改编,由刘晓庆主演的大型历史剧《武则天》,剧本第一次演绎了武则天的一生,在尽量尊重历史记载的前提下,侧重展示武则天的宫廷成长史,以女人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人物形象。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叙事由于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往往倾向于将历史文本的深层内容看成是语言学的,诗性的,同时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这一论述事实上拆除了横亘在历史与文学间的那道樊篱,也为当时新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贵的理论依据,使“纪实与虚构”成为新历史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叙事策略。从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题材的创作中不难看到作家在建构一种修辞化的叙述时,往往刻画传达一种更主观化的思想观念,而不只是简单地再现历史事件;作品往往选择那些碎片化的“小历史”作为自己的题材来源,淡化或虚化宏大历史背景和事件,强调叙说与追忆的过程,强调创作主体与历史的对话交流。这当然表明了中国新历史小说与源自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保持着某种精神上同气相求的亲缘性和方法策略上彼此彰显的通约性。
相比于将武则天作为“人”和“宫廷女人”的演绎,当这一形象塑造进化到“普通女人”阶段时则带有鲜明的类型化和媚俗化倾向,或者说是当下类型文学大背景下的副产品。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还是对类型文学概念做一个说明。类型文学不同于文学类型,或者可以称之为大众文学的类型化,它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带有形式和题材的重复性,另一方面是以狂欢化的姿态消解深度阅读。目前充斥于各大文学网站上的盗墓、悬疑、游戏、间谍、职场等小说便是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因此,在这一后现代背景之下,武则天题材的创作必然表现出若干新质,这主要表现在对武则天形象的定位和演绎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题材出现了各种“秘史”版本,如董云卿的《武则天秘史》(北方文艺出版2006年版)、宋晓宇《武则天秘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而2011年由湖南卫视推出的刘晓庆、斯琴高娃、殷桃版《武则天秘史》以及即将推出的范冰冰版《武则天》则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密度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些作品中的武则天无疑承载着更多的文化符码,随着近几年宫廷题材、穿越题材作品的备受推崇,女性相比于传统的男性主人公来说必然会给人全新的欣赏感受,这样各种版本的武则天作品便将女性、宫廷、职场、权谋等类型文学的特点集于一身。武则天的女皇身份演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外在符号,而争锋吃醋、美艳色情、职场弄权等作为“普通女人”甚至是“现代普通女性”的时代特质则成为了基本内核。因此,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突出的是“武媚”形象的话,那么当下更愿意展现“媚娘”身上的“媚”。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则天形象的叙写大约出现了三种局面。第一类是格非、苏童、北村、须兰、赵玫等先锋作家的解构历史作品。他们信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是写作者的心灵史。第二类是冉平、张兰亭、张兵等人的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导的作品,既写武则天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又写出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欲望和情感。第三类是葛思绪的《武则天大帝》、野岭伊人的《风流女皇武则天》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回归古代狭邪演义的消费历史的作品。如果说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大都以反思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和历史的姿态力图走出对历史个性化书写的道路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武则天叙事则明显带有第三类特点,即以感官冲击为主要手段,以带有传奇和情欲的叙事为主要内容。这恰符合当下类型文学的发展态势,近20年以来武则天题材叙事的重要贡献是人物形象变得鲜活而丰满,如果用文学理论术语不妨称之为开始“典型化”。但从另一个方面,即展示方法方面则又重新进入类型化和脸谱化的迷宫。首先,情欲开始定型化。当下的文学叙事已经脱离了新历史叙事的初衷,向野史化与欲望化叙事转型。各种小说、剧本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或达到商业目的都将武则天做了大胆的艳情式处理,因此大量激情桥段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此时的武则天已经与各种肥皂剧中的女主角并无区别,这也从另一层面印证了上文提到的“普通女人”的处理方式;其次,情节变得雷同而乏味。不妨以《武则天秘史》和《甄嬛传》两部热播影视剧为比较对象,武则天与甄嬛故事的展开背景毋庸置疑都是宫廷,加之女性这一特殊的身份便使得故事可以有无限的演绎空间。《武则天秘史》中在宫中处于显贵地位的是王皇后与萧淑妃,《甄嬛传》中的相似角色是宜修皇后和华妃。武则天经历了感业寺最艰难的心理历程,而甄嬛也同样在甘露寺中涅槃成功,并且都是以怀得龙种为重要手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两部剧在精神层面存在遥相呼应的亲缘关系,诚然有《甄嬛传》模仿武则天故事的嫌疑,但近年武则天题材剧作的频繁出现也是对这种潮流的有意迎合。
因此,如果说西方新历史主义带给20世纪80、90年代的是对传统历史观的重新思考,从而使得文学叙事更为接地气的话,那么当这种潮流在后现代的推力推动下,开始肆意为之的时候,便带了新一轮的反思。解构是否应该无所顾忌,当风筝的长线折断之后它将飘往何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必须承认,近20年来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之间的主从关系发生了权利倒转,最初受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文学或文化现象开始变得脱离理论的最初预设,并反过来如脱缰野马一般左突右冲。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文学现象与中国以往的任何时期都不尽相同,原因在于它带有更强的人为性和目的性,是在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乃至后殖民主义等基本理论的直接干预之下而产生的,但当这种理论干预行进到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时候则变得过犹不及,或者说已经脱离了它们的初衷。反思之后如何进行新一轮的重新反思,从而使得历史叙事沿着远离媚俗与雷同的健康路径发展,将是当下理论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