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叛逆到牺牲:论故事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形象
2014-09-29黄世智
黄世智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颂莲是故事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人公,是张艺谋和巩俐合作塑造的重要银幕人物形象之一。颂莲本来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洋学生”,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应该成为旧社会、旧家庭及其婚姻制度的叛逆。但由于思想性格的缺陷和客观环境的影响,她却放弃了反抗,并逐渐蜕变为“老规矩”的奴隶,甚至帮凶,直到最终成为旧社会、旧家庭及其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一、旧社会的叛逆
电影开始时,颂莲是一个旧社会的叛逆形象。她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像当时绝大部分青年学生一样,在婚姻问题上追求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其思想性格与旧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格格不入。但父亲的去世不仅使她无法继续学业,也使她失去了在恋爱婚姻上独立自主的基础。退学回家后,后母劝她嫁人,她并没有同意后母的安排。但后母不断地“劝”她、逼她。最后,在后母不断地催逼下,颂莲只得说:“娘,你不要再说了。你已经跟我说了三天了,我也想明白了,嫁人就嫁人吧!”
娘:“那好!你想嫁个什么人?”
颂莲:“嫁给什么人,能由得了我吗?你一直在提钱,就嫁个有钱人吧!”
娘:“嫁有钱人,可是当小老婆!”
颂莲的眼中涌出泪水:“当小老婆就当小老婆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吗!”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在后母的催逼下,颂莲似乎屈服并放弃了反抗。不仅同意嫁人,而且还同意嫁给有钱人当小老婆。其实她这样做,表面上是对后母逼嫁的屈服,本质上还是对后母逼嫁的继续反抗。她无法说服对方,又没有婚姻自主能力,只有用最彻底的服从来表示自己的反抗。只不过,她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残式的反抗。她想通过伤害自己来证明后母错了。
颂莲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她肯定想嫁一个有新思想并与自己相爱的同龄人。但在后母及其所象征的旧社会及其“老规矩”面前,她无能为力,只得放弃自己的婚姻理想。电影镜头中虽然没有出现后母的形象,但我们从颂莲的表情和二人对话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后母的顽固、冷酷和咄咄逼人。不过,颂莲虽然放弃了自己的婚姻理想,但她并没有完全屈服,而是进行变相的反抗。既然不能嫁一个相爱的人,就干脆嫁一个有钱的人吧,哪怕是当小老婆。她这种宁缺勿乱的态度,在潜意识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爱情纯度。既然不能追求爱情,那就追求钱吧。当然,这种自暴自弃的反抗也暴露出了她思想性格中天真幼稚的一面,预示了她后来悲惨的命运。
虽然同意嫁人,颂莲的叛逆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在去陈府的路上,她拒绝花轿的迎接,坚持步行去陈府。与迎亲队伍背道而驰的镜头成了她叛逆性格的象征与隐喻。到了陈府后,她谢绝管家的帮助,自己拿行李。这说明,她在处处注意保持一个新式女青年的本色,与一切旧的东西保持距离。她也许认为,没有爱情自己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与雁儿初次见面才意味着颂莲开始真正进入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缩影性质的陈府。当雁儿得知眼前这位使用自己洗衣服的水洗手的陌生人就是四太太时,疑惑而不屑地说:“你就是那个四太太啊?”说罢,她一把抢过颂莲面前的脸盆,将脏衣服扔到里面揉了揉。颂莲毫不示弱的说:“对,我就是那个四太太。”她一边展下袖口一边冷笑着看看箱子对雁儿说:“你把箱子给我拧进去。”雁儿虽然极不情愿,但在这个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大家庭里,她只有服从。在拜见陈府人时,三太太推脱不见并遣使丫鬟来说:“三太太说,她今天身体不爽快……说改日再见吧。”颂莲听了,立即表示出不满,并不理会飞谰的礼貌拜见,径直走了。这一方面说明颂莲不知辨别敌友的天真,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了“颂莲注定是一个原有秩序的反叛者。”[1]在陈府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颂莲虽然逐渐被“老规矩”奴化,但她的叛逆性格并没有完全丧失,而且敢直接反抗陈老爷。她带到陈家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父亲”留给她的笛子。当她得知是老爷把笛子“烧了”,就直接对老爷表示不满,顶撞他。
在陈家,没有任何人敢逆着老爷行事,更没有人敢顶撞老爷。颂莲敢这样做,是她的新思想做基础,是她的叛逆性格使然。总之,颂莲嫁到陈府之前是一个旧社会的叛逆,嫁到陈家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思想观念,保持自己的本色个性,拒绝承认一些“老规矩”,敢于反抗周围每一个人,包括具有绝对权力的老爷。这虽然说明了她的天真幼稚,但也说明了她这时仍然是旧社会的叛逆。
二、“老规矩”的反抗者
颂莲是旧社会的叛逆,但却嫁到了作为旧社会缩影的陈府,这就决定了她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自从进入陈府的第一天起,她就不断地对周围压抑自己思想性格的环境进行反抗。对旧社会及其缩影陈府的反抗除了具体表现为反抗周围代表旧势力的人物外,最能表现出颂莲反抗旧社会的思想性格的就是她对旧的社会制度的象征——“老规矩”——的反抗。颂莲刚到陈府不久,陈管家就对她说:“陈家的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往后都马虎不得。”其他人口中也经常提到“老规矩”。“老规矩”其实是旧的社会制度口语化的代名词,是连陈老爷也要遵守的“天理”,没有人敢反抗。就是三太太的反抗也是暗地里反抗,不敢公开反抗。只有颂莲敢多次反抗,甚至公开反抗“老规矩”。
当然,颂莲对“老规矩”的反抗,在嫁到陈府之前就开始了。当后母一再催逼她嫁人时,她最后选择嫁给一个有钱人当小老婆。她说:“当小老婆就当小老婆,女人不就这么回事吗?”在旧社会,婚姻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都是大事,需要明媒正娶,有一整套必须遵守的礼仪程序。这都是“老规矩”。对于婚姻大事的这种态度就是在破坏“老规矩”,就说明颂莲早已开始了对“老规矩”的反抗。出嫁时,她拒绝乘坐迎亲的花轿,独自步行到陈家大院。“她走向陈家宅院之时正好与迎亲的队伍‘背道而驰’,场面调度的这种反向处理,显然暗示着主人公对一种传统婚姻仪式的背弃。”[2]这是对旧社会传统嫁娶“老规矩”的反抗。不过颂莲这时的反抗还停留在张扬个性的层面上,反抗的还是老规矩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她对“老规矩”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嫁到陈府后,她说大太太太老,不情愿跪拜祖宗牌位,对每天站队听宣、吃饭点菜等规矩表示不理解。总之,颂莲不愿遵守陈府的“老规矩”,几乎时时处处有意无意地在反抗“老规矩”。当然,她对老规矩最强烈的反抗是她没有按老规矩处理自己与老爷和大少爷之间的关系。
刚到陈府时,颂莲觉得陈老爷体贴温柔,不管是问捶脚是不是舒服还是问她想吃什么菜都是温声细语。因为一时得宠,颂莲是大院中唯一一个敢于在老爷面前说不的人。但她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老爷用来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在被梅珊请去陪高医生和王先生打牌时,当高医生问她:“听说四太太大学没有念完,为什么?”她说:“念书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老爷身上的一件衣裳,想穿就穿,想脱就脱呗!”既然对自己与陈老爷之间关系的本质已经看清,颂莲就不再是恃宠撒娇似的对老爷说不,而开始真正反抗老爷了。不按“老规矩”处理自己与大少爷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老爷的反抗,也是对“老规矩”的反抗。颂莲知道在“男权宗法制社会里,女人不忠是所有行为中最偏离规范的,受到的惩罚也最严厉。”[3]但她却主动试探大少爷飞浦。颂莲与飞浦是在笛声引导下相互认识的。两人的大胆交流与试探使颂莲的生活中有了一缕阳光。虽然由于飞浦的胆怯懦弱,颂莲并没有象梅珊那样出轨,但颂莲对飞浦的情感暗示实际上表示出她反抗“老规矩”的勇敢。她的试探已经比梅珊还要大胆。
颂莲还敢当面直接反抗老爷。当得知陈老爷拿走并毁掉了她心爱的笛子后,她当面追问笛子的下落。当陈老爷说把笛子烧了时,她虽然不敢直接表达不满,但她惊讶的语气和委屈的眼泪已经说明一切。
陈老爷穿好衣,从背后抱住颂莲的肩膀,亲昵地说:“怎么啦,生气啦?”
对陈老爷的示好,颂莲并不领情,她一甩肩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继续表示不满。
陈老爷说:“好啦好啦,别耍小孩子脾气啦。今天我带你去吃五味坊的小馄炖。你不是说过爱吃吗?”
陈老爷拍拍颂莲的肩膀以示安慰。
但颂莲继续表示不满,她一手推开陈老爷,强忍着的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了下来。
从以上场景可以看出,对于具有绝对权威的陈老爷,颂莲表面上充满自暴自弃的懦弱和无能,她似乎默认了陈老爷对她命运的掌控和逼迫,并且表示顺从,放弃了反抗,但实际上她是在变相地进行反抗。颂莲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句话,但她用语气,用肢体动作,用表情,用眼泪表示反抗。这使得陈老爷破天荒地被迫哄她。这种反抗是其他人绝对不敢做的。因为陈老爷是夫权、族权和其它“老规矩”的代表和执行者,对他的反抗就是对一切“老规矩”的反抗。颂莲对“老规矩”的反抗是自保、自信,更是她的思想个性使然。
颂莲虽然自信坚强,但相对于强大的旧社会势力,她又是弱小的。就如同电影开头的镜头。后母的视觉形象虽然没有出现,但却在注视着颂莲并支配着她的命运。她刚走进陈家大院的时候,虽然眼角全是自尊和不屑。可是镜头中的她被挤压在墙根,又的确太渺小了。她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并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对旧社会及其“老规矩”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不知道同情其他姐妹,团结他们一起反抗“老规矩”。在陈府大院,她也参与了妻妾之间的竞争。她的反抗是无力的,盲目的。所以颂莲的反抗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更严重的压迫和惩罚,也使她一步步地沦为了“老规矩”的奴隶。
三、“老规矩”的奴隶
颂莲从进入陈府到最后发疯是一个不断反抗“老规矩”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被“老规矩”奴化的过程。
从进入陈府开始,颂莲就不断反抗“老规矩”。但如果辩证地看,反抗“老规矩”既是对“老规矩”的否定,也是承认并证明“老规矩”的存在。颂莲虽然想保持自己叛逆的思想个性,但周围环境却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她。因为陈府的人都已经是“老规矩”的奴隶,即使是同样具有叛逆个性和行为的三太太梅珊也经常提醒她注意“老规矩”。周围这些人的态度已经内化成社会无意识的宗法文化,成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老规矩”,也成为颂莲耳濡目染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颂莲也逐渐无意识地接受“老规矩”,并成为了“老规矩”的同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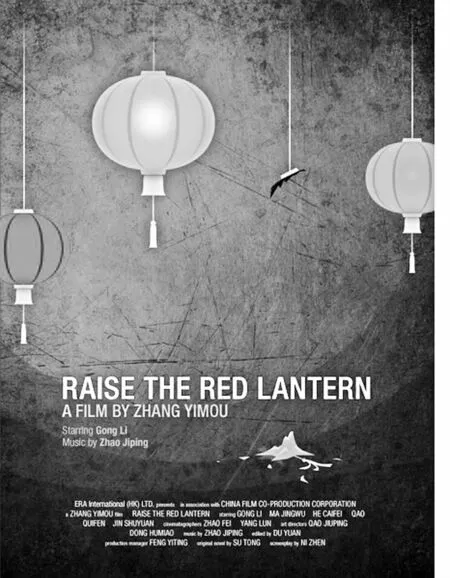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海报
刚到陈府时,她对诸如“锤脚”、“点灯”等怪异的规矩感到不理解,甚至厌恶。但她慢慢发现,当每天的捶脚声音响在大院里的时候,她也开始需要这件东西。于是,陈老爷问:“怎么样,点灯锤脚,到这会儿你觉出点意思来了吧,再过几天,你就更离不了了!”果然,她逐渐发现,不能点灯就吃不到想吃的东西,不能点灯就总是被人欺负。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发现不按“老规矩”行事,不同流合污——承认“老规矩”的绝对权威并参与妻妾之间的争斗——就无法生存。她想凭借自己的聪明机警在争斗中取胜,但聪明机警反而加紧了她身上的“绳索”,与别人争宠也说明她接受了“老规矩”的宗法性地位。
当别人问她为什么大学没有读完的时候,她起初的回答是因为父亲病了供不起。这说明她喜欢读书也看重自己受过大学教育的经历。但后来她逐渐认识到念书没有什么用,自己也像其他太太一样,只不过是老爷身上的一件衣裳而已。而当她发现雁儿住处的布偶上有自己的名字,并且是卓云写的字时,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争斗。她已经不自觉地被男权文化环境同化,并自觉地参与了与周围姐妹的生存竞争。在争斗过程中,她慢慢蜕变,把卓云、雁儿、梅珊等看成自己的敌人。当她得宠时,就让老爷命二太太卓云来给她捶背,在二太太忍气吞声地伺候她时,她还时不时地挑剔二太太的手法说:“二姐,手再轻点。”“对,就这样。”这时的颂莲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张狂模样。她这样做“虽然只是为了使自己更有力地占据陈家的核心地位,但实际上已成为现有秩序更有力的维护者。”[4]完全成了“老规矩”的奴隶和执行者。
从电影讲述与颂莲有直接关系故事内容的叙事语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颂莲的遭遇和思想的变化。在她逐渐被“老规矩”奴化的过程中,镜头的远景也逐渐发生变化。电影开始的大部分镜头都是以颂莲的主观视角来叙事的,但后来逐渐转变成客观视角了。颂莲由起初默认的观看者不自觉转换成了被看的对象。在故事发展进程中,颂莲逐渐成为“老规矩”的奴隶,电影镜头也逐渐把颂莲物化为陈府环境的一部分。
颂莲揭露出雁儿偷点灯笼的事,虽然是她被逼反抗的表现,但同时也说明她被陈府的“老规矩”奴化了。当她发现雁儿房间的许多破旧灯笼时,她对雁儿说:“好哇!你敢偷偷地点灯笼。这灯笼是你一个丫鬟随便点的吗?府上的规矩你知不知道,你还想不想活?”这句话表明陈府“老规矩”已经潜移默化为她的思想意识了。当她假怀孕的骗局被拆穿并被封灯后,她的气势一落千丈。但她对这一切变故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当飞浦说她蠢时,她还反驳说:“我蠢?我不蠢。我早就算计好了,开始是假的,只要老爷天天到我这儿,日子久了不就成真的了?”她认为她的失败在于其他太太对她的算计,她说:“我在算计这事,她们在背后算计着。”因此,这时的颂莲已经完全被“老规矩”奴化了。最可怕的是,颂莲不仅成为“老规矩”的奴隶,她还逐渐成为“老规矩”的帮凶。
四、“老规矩”的帮凶
颂莲对陈府的“老规矩”和老爷的反抗并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她对当时的社会、陈府的“老规矩”及周围的人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她开始过于自信,后来又失去原则,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凭个人性情进行反抗。所以,天长日久,她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规矩”并被周围的环境同化,成为男权的旧社会“老规矩”的奴隶,甚至帮凶。
由于对自己反抗的对象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又往往失去原则,颂莲在反抗“老规矩”和老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享受起主子施与的权欲,与其她妻妾争宠,欺压仆人。这是她成为“老规矩”帮凶的思想基础。当四院点灯,她获得侍寝陈老爷的资格时就摆足了主子的架子。
仆人告诉吃饭时间到:“该吃饭了!四太太的菠菜豆腐豆芽都做好了。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都等着呢。”
颂莲:“我不去,让他们把饭端上来。”
陈老爷:“这不合适吧!还是到前边去吃,省得被她们笑话。”
颂莲:“又是她们,笑话怕什么?我就要在这儿吃!”
陈老爷:“好,好!端过来吃。去,让他们把饭菜端上来。”
这个情节是颂莲堕落为“老规矩”帮凶的开始,也最能说明她最终成为“老规矩”帮凶的原因。她为了争宠首先去讨好老爷,而一旦得宠就由被欺压者变成欺压者。她拒绝按常规到前边吃饭,虽然说明她叛逆的性格仍然存在,但她这样做也说明她在本质上完全接受了自己以前反抗过的老规矩,特别是封建等级思想。
在做人上,颂莲开始坚持不做小人,不做恶人,坚守道德底线。但为了生存下去,她身不由己地做出许多伤害他人的事。不过,即使这样,她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坚守的道德底线,心中仍然保存一份善良。促使颂莲不再坚守做人原则的事件是卓云本质的暴露。当雁儿暗示她是卓云叫自己使用巫术诅咒她,希望她死掉时,她开始不敢相信。因为卓云平日里那么和蔼,对自己又是那么的和善,她怎么会想害死自己呢。所以她又直接问:“是二太太卓云?”雁尔没有回答,但是雁儿的神情肯定了这点。这件事使颂莲的思想感情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也不再相信自己。开始毫无原则,不看对象地伤害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变成了“老规矩”的帮凶。
颂莲变成了“老规矩”的帮凶有一个从间接帮凶到直接帮凶的变化过程。她间接地成为帮凶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三太太之死。梅珊与高医生的私情被她发现。梅珊警告她别乱说,她也没有故意公开梅珊的秘密。但她在自己生日吃酒时无意中出卖了梅珊,导致梅珊最终被送到死人屋处死,成为“老规矩”杀人的帮凶。
雁儿的死是颂莲有意地直接做“老规矩”帮凶的典型事件。为了报复雁儿揭露自己假怀孕,她闯到雁儿房间将雁儿屋里暗藏着的灯笼一个个地扔出来,并骂雁儿说:“一个丫环偷着在屋里点灯笼,这灯笼是你随便点的吗?你眼里都有什么人?你把我们这些当太太的往哪搁?陈府还有没有规矩了。”她的话中特别强调主仆之别和老规矩的不可违抗。自己俨然成了老规矩的执行者和老爷的帮手。当二太太欲为雁儿的过错开脱时,颂莲立即驳斥她说:“封了灯我也是太太,我告诉你,太太就是太太,丫环就是丫环。”她不仅进一步强调封建等级的不可逾越,而且又转而逼问大太太说:“丫环犯了规矩该不该处置,怎么处置?”她强调的仍然是“老规矩”的不可违抗。“通过主人公颂莲,张艺谋清晰地展示了旧中国女性(哪怕是知识女性)自主意识丧失的过程。”[5]“老规矩”曾经是颂莲反抗的对象,她深受其害。现在,“老规矩”已经成为她的杀手锏。此时的颂莲已完全认可了封建大家庭中的等级制度,并且竭力维护这一制度,因此她无法饶恕一个企图越位的丫环,何况这个丫环觊觎已久的又是她“四太太”的位置。她是欲置雁儿于死地而后快的。因此,当三太太劝她不必与一个丫环较真时,她态度坚决地说:“我是杀鸡给猴看。”此时的颂莲已经不如三太太善良了。颂莲知道丫鬟偷点灯笼难逃重责,为了报复封灯的家法惩处和卓云的伎俩,她终于凭借陈府的“老规矩”和“太太就是太太,丫鬟就是丫鬟”的权位等级,以恶制恶地要求严惩雁儿,最后导致雁儿死去。这表明她已经成为“老规矩”和老爷的直接帮凶,最终变成了压迫奴役自己的环境的组成部分,成为自己最憎恨的那些人的同类。
五、旧社会的牺牲
颂莲在被“老规矩”奴化并最终成为老规矩的帮凶,残害别人的同时,她自己也在一步一步地成为旧社会及其“老规矩”的牺牲品。
陈老爷怀疑颂莲的笛子是她“同学”的礼物,暗中拿走并毁掉它。颂莲知道后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并因而失宠。这件事成为她命运转折的前奏。始终不让观众看到真面目的陈老爷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及其宗法制度的象征。在陈府,陈老爷就是“老规矩”。颂莲深知这一点,但她对“老规矩”的“吃人”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为了重新得宠,她假装怀孕,结果被封灯,这是她成为旧社会及其“老规矩”牺牲品的关键一步。她虽然说陈府的“人算个什么东西?像狗、像猫、像耗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她自己也已经变得不像人了。为了报复雁儿,她揭露了雁儿私下点灯的秘密,没有想到导致雁儿死去。雁儿的死使她失去了陈府所有人的好评,她因此更加孤立,精神上也失去了平衡。如果说封灯后她还能平静的生活,那么雁儿死后她就无法过正常的生活了。
当然,颂莲成为牺牲的标志性事件是梅珊之死。她酒后失言导致梅珊与高医生的私情泄露,梅珊最后被送到死人屋处死,而且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使她发疯。梅珊被送往死人屋的情节被处理成整个电影的高潮之一,导演通过主观视点的镜头运用表现颂莲的恐惧,表现她发疯的整个过程。
其实,颂莲发疯是必然的,没有梅珊之死,她也会发疯。她的发疯和她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如果她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她可能就会像其她姨太太那样要么活得有滋有味,要么苟且偷生。但颂莲是个大学生,大学生在那个时代是最先接触现代文明,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成规陋习的变革者,是反封建的战士。颂莲虽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但她毕竟受过启蒙教育,其思想性格还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因此,她是陈府女人中的另类。只有她在不高兴的时候敢给陈佐千脸色看,只有她追求人要有人的活法,而不能像猫像狗。因为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生活理想她都不同于其她太太,这也使她难以与其她太太同谋,与世俗同谋。但环境逼迫她一步一步压抑自己思想性格反抗性的一面,并在言行上竭力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因此,她事实上又成为了“老规矩”和周围人的同谋与帮凶。这种生活状态导致她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甚至人格的急剧分裂。这种分裂在其她几位太太身上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只有颂莲无法长期承受这种生活。因为颂莲虽然在新式教育下有了人的意识,但对她来说这种人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人生体验。她缺乏应对强烈精神矛盾的经验和能力,因此,她的生命意识和自尊意识与自己人不像人的生活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并随着自己思想矛盾逐渐增多,感情痛苦也逐渐加剧,她精神和人格的分裂形成的张力终于在目睹梅珊之死时失去了平衡,促使她发了疯。
六、观众期待视野中的人物形象
作为一个反抗旧社会及其“老规矩”的女斗士,颂莲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叛逆”。她对“老规矩”及周围人的反抗、奴从和最终被害都是她叛逆性格直接或者间接的表现。后来,她虽然被奴化,并堕落成为帮凶,但她最后发疯说明了她的叛逆性格虽然被压抑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发疯也是一种变相的抗争。颂莲的性格发展过程也就是她的“叛逆”导致她成为“牺牲”的过程。她命运的发展方向与她的初衷及其努力的目标截然相反,并最终导致她作为“牺牲”和“帮凶”的双重失败,这是电影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般观众期待视野中的像颂莲这类人物命运的必然结局。因为普通中国观众在“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品中见到过很多这类人物形象(如《家》中的鸣凤和《北京人》中的愫芳等),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知习惯,太独特和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们反而难以理解和接受。
在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前,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主要有《红高粱》和《菊豆》。在《红高粱》和《菊豆》中,张艺谋塑造了九儿和菊豆两个银幕女性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颂莲的性格比九儿和菊豆单一、抽象,也更理性化。作为《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人公,颂莲从进陈府到最后变疯前的性格特征主要是“叛逆”,是一个简单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过程。她的性格不仅缺乏丰富性,也缺乏九儿和菊豆那种性格发展带来的审美张力。这虽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高度风格化、程式化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编导急于表达思想,忙于构思造型,而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不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的形象也因此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需要,是普通观众期待视野中的人物形象。
[1][2][4]贾磊磊.影像语言的感性形式与表达语境——张艺谋影片中的视觉/心理意义[M]//论张艺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7.
[3]柴莹.文化视域中的“张艺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5.
[5]张若雪.读解张艺谋:以工巧营造沉重[J].艺术广角,19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