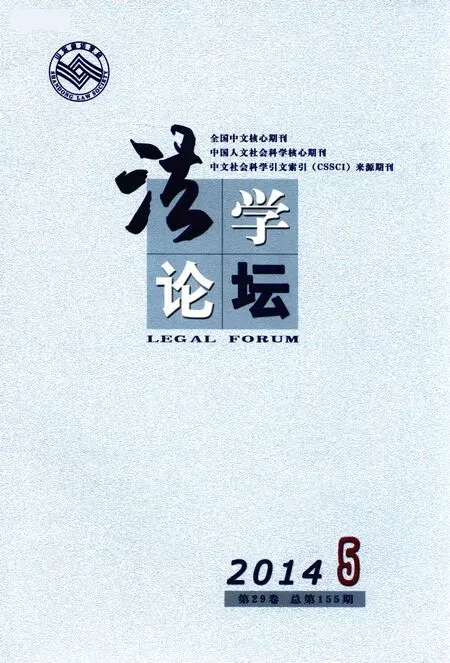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14-09-20胡学军
胡学军
(南昌大学 立法研究中心,江西南昌 330031)
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胡学军
(南昌大学 立法研究中心,江西南昌 330031)
事案阐明义务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前沿理论,在解决现代型案件证明困境问题上发挥了有力作用。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对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基石的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制度形成了挑战,其产生与发展也正是围绕着与辩论主义及证明责任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当今各国阐明义务一般化的趋势比较明朗,这尤其对于传统上注重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我国诉讼制度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目前引进无限制的“事案阐明义务”会使我国司法改革辛苦建构起来的证明责任制度及民事诉讼模式转型前功尽弃。其积极意义只不过在于在特定的案件类型中以此理论可弥补证明责任分配可能的弊端。
事案阐明义务;辩论主义;证明责任;一般化趋势
在民事诉讼中,假如双方当事人就自己所掌握的事实与证据有绝对的提出与否的决定权,那么未能掌握此类事实、证据的一方就很可能得因此负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对不掌握有关事证的当事人来说,此时的举证负担将兑现成现实的证明责任判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传统证明责任主导的理论语境下,由接近事实掌握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对该事实负客观证明责任就成为当然的解决方案,如证据责任分配诸学说中考虑证据所持及举证能力的所谓“危险领域说”或“证明责任倒置”理论。但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败诉风险随证据所持而发生转换并不具有正当性。*参见胡学军:《证明责任倒置理论批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其实,上述前提假设在现代司法中是不成立的。当事人对其所掌握的事实及证据并不应享有绝对的处分权,因为这与当事人对自己享有的实体权利的处分是不一样的。理论上,事实证据本身具有客观性,现代诉讼应当推动双方在这方面做到信息共享,只有如何评价和利用该信息才是双方智慧与策略较量的领域。由于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是任何国家诉讼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理论上任何人均有如实作证的义务,法院有义务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对于证人拒不提供证据或作伪证的,法院可以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或予以惩罚,如果说因为掌握事证之人因其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成为当事人而可豁免作证义务,这种过于放纵当事人的理论就不免有些奇怪。当然,一般来说,有理由让更有动力与激励来关心案件事实揭露的当事人负证据提出责任。不过,由于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的对立性,可能对于特定事实与证据的提出会抱持正好相反的态度:一方希望披露,另一方意欲掩藏。现代型案件的大量出现导致作为原辩论主义建立基础的当事人地位平等与信息对称等实质条件丧失,特别是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传统“谁主张、谁举证”的提供证据责任分配法则难以贯彻,而倒置客观证明责任的作法又往往矫枉过正,因此,在现有证明责任分配理论框架之内寻求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合理调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毕竟,查明事实真相以实现公正无论如何都是诉讼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因此,采取何种制度办法使当事人能够平等方便地接近与取得裁判所需的事实、证据,避免因证据偏在而产生持有证据方不提出证据,从而使事实呈现不应有的真伪不明状态,就成为民事诉讼法上的重要课题。在此情形下,肯认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在无充分根据时提出不特定具体化的证据调查申请的“摸索证明”或赋予不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事案阐明义务”都是解决证据偏在时持有证据方不提供事证而对证明责任方当事人的救济办法,我国学界近期在这两种理论上多有“拿来主义”的观点,*近年关于这两个理论的介绍与初步研究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周成泓:《论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4期;刘显鹏:《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探析》,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4期;魏庆玉:《摸索证明论》,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占善刚:《证据协力义务之比较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柯阳友、严洁:《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初探》,载《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田海鑫:《论协同主义视野下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但多数研究方法比较孤立片面,往往从发现真实的单一目的出发持比较激进的观点,而对理论的复杂背景及其相互关系则缺少深入的探究。
一、事案阐明义务论的发展脉络
当事人的“事案阐明协力义务”概念首先由德国学者提出,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掌握事证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难于对相关事实及证据予以主张与举证时应对法律上重要的事实及对证据手段之存在与否给予答复。我国台湾学者所谓事案阐明义务,主要是指“当事人对于事实厘清负有对于相关有利及不利事实之陈述(说明)义务,及为厘清事实而提出的相关证据资料(文书、勘验物等)或忍受勘验之义务”。*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10页。理论上事案阐明义务应当是双方当事人均应承担的一种义务,而并非针对民事诉讼中某一方当事人。但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下,由于负担证明责任方当事人本就具有提供自己掌握证据的内驱动力, 似乎没有必要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故理论上也多将这一概念称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之事案阐明义务”。*“阐明”或称“解明”,是与“证明”一词涵义有所区别的术语。证明一词显示了证明主体的目的是为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事实主张的存在,而阐明或解明则不具有这种目的性,主体只是提供事件相关信息以呈现事实本来面目。在阐明度或解明度很高而证明度仍未达到证明标准时,即案件事实的真伪不明状态。参见王亚新:《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证明》,载《证据科学》2013年第6期。但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强调阐明义务的双方承担性,这种理论安排一方面贯彻了民事诉讼平等原则,强调积极参与诉讼,协力查明案件事实是每一个诉讼主体都应当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此种界定有利于正确理解设置当事人事案阐明协力义务的目的——澄清案件事实而非欲加重或减轻某一方当事人的负担。如不将诉讼中的证据偏在理解为仅限于主要事实上,则显然应将这一阐明义务扩大适用于所有要证事实。但基于证明责任分配所产生的内在压力会促使应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尽力举证,而无需以事案阐明义务来加以解释与规范,故学者更多的关注点聚集在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身上。但笔者认为最好将阐明义务当作一种解决因事证信息分布不平衡所产生的证明救济措施,是弥补客观证明责任分配弊端的附属制度。
根据证明责任分配法则,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亦负主观抽象证明责任,这种责任分配的单方固定性使一方得独自承担事实与证据提出责任,而对方则可以逸待劳,仅须在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的本证即将奏效时,提出反证即可。承担证明责任方如果不能举证使待证事实在法官心证程度上达到证明标准,则法官将依据证明责任分配判决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败诉。“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如果‘已掌握’或‘能取得’关于待证事实之事证,则使其负事实、证据之提出责任并承担因未充分提出而无法证明事实至证明标准的败诉判决结果,不但具有正当性基础,同时不致产生特别的问题。”*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但在证据偏在的案件类型中,则不掌握事证一方当事人很可能导致败诉后果。对方当事人对于这种对案件事实查明概不协助的作法,显然有违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与实质正义。
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传统的辩论主义理论下发展出的著名论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无义务为对方当事人提供攻击自己的武器”也同样可能导出这种消极结果。在两造对立的结构下,不负举证责任方当事人显然可以对相关事证无动于衷,对方当事人却可能在消耗极大的人力、财力搜集证据仍不能使案件事实明朗化的时候,独吞败诉苦果。尤其在纠纷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产品缺陷、专利侵权、环境污染、医疗纠纷等现代型案件不断涌现,在这些诉讼中,鉴于主体双方地位的固定化,受害方往往无法取得必要的证据资料,势必造成其因无法提出与待证事实相关的必要证据而使诉讼结果显失公平。这种将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完全付诸自由竞争的“诉讼达尔文主义”忽略了一个问题:当事人事实上在证据信息占有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垄断证据信息的一方当事人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这种优势阻碍真实的发现。因此,如何打破证据信息的垄断格局,保障信息方面的弱者利益,使当事人双方平等且经济地接近、取得诉讼所需要的事实和证据,避免由当事人掌握的信息优劣势而决定诉讼成败,就成为现代诉讼的重要课题。因此,课予不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举证负担,使其积极参与到诉讼中协助案件事实的查明,平衡当事人双方取证能力,弥补相互信息落差,就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的解决方案。
事案阐明义务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探索的前沿理论,在解决现代型案件证明困境问题上发挥了有力作用。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对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基石的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制度形成了挑战。因此,可否在坚持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等理论框架的前提下发展这一概念尤需慎重探讨。实际上,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也正是围绕着与辩论主义及证明责任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1939年德国学者冯·希佩尔发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与阐明义务》一文,对“自由主义”的辩论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并尝试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为当事人确定全面的阐明义务的主张。冯氏以阐明义务和真实义务的差别作为其调研的基础,认为真实义务只包含禁止违反诉讼法的行为,而阐明义务涉及在一定程度内要求当事人积极促成“正确观念”的形成。其将阐明义务的性质界定为诉讼法上的义务,并通过塑造诉讼上的案件类型(反面排除)的途径明确规范当事人的阐明义务。这一文章的意义在于首次提出阐明义务这一概念,开启了这一理论的先河。这种理论主张与其产生的特定时代(纳粹时代)观念是相适应的,但这一革命性的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进足够的关注,并在战后重新崇尚自主主义的观念下归于沉寂。
直到1966年,吕德里茨发表《在伸张私人权利时禁止摸索和答复请求权》一文,重新开启这一话题。吕氏主张无证明责任当事人并不必然负阐明义务,但当证明责任人提出一定盖然性程度的陈述时,他就应负阐明义务。并为非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最低阐明要求创建了三个级别的案件类型,分别赋予其应诉责任、转移主张责任及答复请求权的效果。但答复请求权不依赖于特定实体法律关系,而是取决于主张的盖然性程度。关于阐明义务的性质,则主张其来自于实体法律关系上的答复请求权,但如主张具有特别高的盖然性程度则不要求存在实体上的特殊关系,而可基于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同年,另一学者彼得斯也发表了《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一文,他同吕德里茨一样从摸索证明切入阐明义务论题,但反对吕德里茨的分级别作法,认为因为级别划分的方法不具有准确性且缺乏可行性。在摸索证明这一问题上,彼得斯比吕德里茨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其致力于从法律的具体规则中类推出一般性协助义务,并认为这种一般性义务提供了摸索证明合法化的基础。所有这些理论的提出都与当时批判辩论主义的思潮有关。与吕德里茨和后来的施蒂尔纳不同的是,彼得斯明确批判了民事诉讼中辩论主义思想的滥用,认为诉讼的目的是真实和公正,当当事人为阐明事实而向法院提出证据手段而无法进一步明确其主张时,辩论主义的意义也就用尽了,此时,法院应当承担起维护公正的职责,不应禁止摸索证明。*参见[德]彼得·阿伦斯:《民事诉讼中无证明责任当事人的阐明义务》,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其后,1970年魏尔斯也在批判辩论主义时建议为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创设阐明义务。阐明义务理论虽不乏响应者,但此时并未在德国实务界引起太大的波澜。
1976年,施蒂尔纳发表教授资格论文《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阐明义务》,提出任何当事人均有义务在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具有法律上重要意义的、有理由的主张进行阐明时给予协助。并认为阐明义务是以德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为类比的基础所类推出来的,包括不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所有的可能或可期待的阐明义务,尤其是出示书证、接受询问和参与法官对对方证据的审查。*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阐明义务的性质为诉讼法义务,因为实体法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不完整的。在诉讼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时,当事人有义务在可期待范围内保存所有有价值的证据手段。如一方违反阐明义务,法院可将负证明责任方当事人的主张视为已经得到证明。施蒂尔纳所倡导的诉讼上的阐明义务的概念不久即得到亨克尔和施洛瑟的原则性赞同。但罗森贝克的学生施瓦布认为一般性的阐明义务范围过于广泛,只赞同在实践中根据案件类型进行逐项类推这种折衷的观点。莱波尔特虽然也反对阐明义务的一般化主张,但其观点相对温和,认为这一学说的意义在于可能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纠偏的必要,因此承认在可能情况下有必要对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及证明评价进一步逐项进行诉讼上的纠正。但将阐明义务一般化的这种学说遭到了客观证明责任理论的维护者的完全拒绝,作为施瓦布的学生,戈特瓦尔德和普维庭的态度比其老师更加严厉,认为阐明义务一般化等同于否定证明责任理论,会将证明责任理论倡导者所辛苦建构起来的诉讼法理论大厦基础摧毁,因此主张阐明义务严格受实体法约束。彼得·阿伦斯最坚决拥护这种反对观点,并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当了施蒂尔纳的强劲论敌。
二、事案阐明义务论的主要理论论争
首先,关于阐明义务的理论基础。施蒂尔纳认为阐明义务的基础是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宪法上的司法保障请求权即为发现真实的目的提供了保障。德国联邦宪法委员会肯定了全面的真实调查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法治国家程序保障的要素,原则上必须通过对诉讼标的进行全面的事实审查和法律审查使得这种保护变得可能。因此能够从与法治国家原则相联系的实体基本权利中推导出与法治国家、公正的程序保障要求相协调的阐明义务一般化。此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规定的“正当程序”概念越来越被从整体的欧洲的观念上加以完善,被打上了广泛的协助义务的烙印。*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阐明时的当事人义务——兼论证明妨碍理论》,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而阿伦斯认为施蒂尔纳提倡阐明义务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诉讼目的不仅是发现真实,而应是在正当程序下的发现真实。施蒂尔纳从以发现真实为目的的法治国家的程序保障推导出一般阐明义务太牵强了,根本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而是涉及价值评价问题。施蒂尔纳回应承认“从诉讼中发现真实的要求出发,来比较简单武断地导出事案阐明义务”是新理论的一大问题,*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 469页。亦承认在阐明义务问题上涉及价值评价问题,价值评价优先于理论建构。并认为任何的法律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评价问题。但任何新理论的合理性只能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能僵化地固守于原有的绝对理论或者要求从原理中逻辑地推导出来。宪法上的法治国原则毕竟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观念基础,新理论总是基于观念转变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不存在科学的推导公式,理论的更新取决于理论论证基础在特定时代的可接受性。对是否有必要提出阐明义务理论只是观察视角的不同,德国的法律发展实际上已经创设了阐明义务,现在涉及的只是对其进行法律体系上的加工并且使其同成文法体系相协调。
其次,关于阐明义务的前提。施蒂尔纳认为起码应当存在使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关于该事实主张或证据陈述令人信服的依据。他也同吕德里茨一样通过以经验为基准构建案件类型的思路来解决这一问题。认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出一个概括性的陈述就够了,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阐明时的当事人义务——兼论证明妨碍理论》,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阿伦斯批评认为阐明义务的前提条件——“证实”和“摸索”这样的问题过于复杂不易把握,当事人是否正确履行了阐明义务的判断非常困难,施蒂尔纳以经验为基准构建案件类型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对盖然性的审查实际上还是只能交由法院自由裁量。而如果一切都依赖于法院的情境性判断,显然将导致扩大法官的裁量空间。*参见[德]彼得·阿伦斯:《民事诉讼中无证明责任当事人的阐明义务》,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而且阐明义务理论消解了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这一“民事诉讼的脊梁”的意义,将从根本上动摇民事诉讼制度的架构。而施蒂尔纳则指出:法官裁量权问题并非阐明义务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一直以隐蔽的形式困扰着日常的司法实践,而学术界也一直不愿意直面这个普遍性问题,阐明义务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突显和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关于违反阐明义务的判断。施蒂尔纳认为如果无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完全拒绝进行协助,那么明显他就违反了义务。如果不清楚当事人是否掌握了被主张的案件情况,或他是否隐藏了证据手段,那么必须对违反义务进行证据调查。阿伦斯认为这样的证据调查太繁琐,赋予了法官过多的裁量空间。*参见[德]彼得·阿伦斯:《民事诉讼中无证明责任当事人的阐明义务》,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而施蒂尔纳认为这样的证据调查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文书提交及讯问当事人情况下所规定的途径,本就是法律赋予法官裁量权的范围。问题在于这样的调查是否会导致程序过于繁琐而产生节外生枝的质疑?确实,相对于一般案件中的证据判断这会导致产生额外程序的问题,但阐明义务的追究其前提就是证明困境的存在,不能将阐明义务时的这种证据调查与一般证据正常提供情况下的程序作对比,而应当想想通过这一程序可能促进事实的查明是否值得。因此,这种调查无论对当事人还是法院来说,都可能因此而获益,当然唯一的例外是违反阐明义务的当事人,而正是这一程序的真正启动才可能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阐明义务,避免诉讼的迟延。
最后,关于违反阐明义务的后果。之前理论上对于违反阐明义务效果的选择在对违反义务的行为采用自由的证明评价与证明责任倒置之间徘徊不定,而施蒂尔纳提出在这两种办法之外独立拟制一个不利益作为惩罚,即赋予负担风险责任的当事人以有利的阐明结果,除非对方能够通过提出反证来推翻这一拟制。亦即违反阐明义务的后果就是拟制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只要这并不与法官自由心证相矛盾。*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阐明时的当事人义务——兼论证明妨碍理论》,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阿伦斯则批评了这种可反驳的拟制,认为其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法官的自由心证。*参见[德]彼得·阿伦斯:《民事诉讼中无证明责任当事人的阐明义务》,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施蒂尔纳认为这种批判没有能够清楚地理解作为惩罚的拟制与法官的自由证据评价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将德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视为已经得到证明”的表述误解为对自由证据评价基本原则的重复。而实际上,这一表述希望表达的是:法官的心证优先于真实;如果无法证明真实情况,则根据法官的裁量进行拟制。这种可反驳的拟制应当适合于这种案件事实情况,并且可以取代“减轻证明责任直到证明责任倒置”这一不明确的公式。*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阐明时的当事人义务——兼论证明妨碍理论》,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普维庭的同意。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违反阐明义务的后果不会导致义务人比提出事证更加不利的后果,那么当事人就几乎不会履行阐明义务,因为这样一来起码不会发生任何损失,而只会使对方增加风险(对方应主张或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因此即使不能获利,当事人基于与对方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似乎也总是会选择沉默或简单表示不知情。而拟制证据或应证事实为真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提供证据或坦白事实的结果,如果应证事实或证据与这种拟制尚有出入,并非完全不利于阐明义务人,而多少会促使事实掌握人选择披露真相或相应证据,这也就是施蒂尔纳所谓“作为惩罚的拟制”的真意。
三、事案阐明义务一般化趋势及其法律实践
阐明义务虽然是缘自德国诉讼理论上的独有概念,但从比较法上看绝非一种孤立现象。美国民事诉讼相对独立的审前程序,尤其是其发现程序实际上赋予当事人向对方或第三人收集相关证据的权利,从大陆法中的阐明义务理论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包含当事人全面的阐释义务、提交义务和容忍义务的内容,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阐明义务理论的探讨,但这与英美法系的整体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环境有密切的联系。英国诉讼法将“文件出示”、“交叉询问”、“财产的搜查、保全和检查”规定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全面的普遍性义务,并对违反这一义务的行为课以不利事实认定甚至刑罚处罚来作为制裁。英国的这种全面的阐明义务规定也已影响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诉讼法。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也大都在其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文书或勘验标的物的编辑义务及容忍对标的物和身体的检查义务。这与德国通过法院判例推动的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如此看来,欧洲及整个世界在诉讼上的阐明义务问题的发展趋势上均比德国的法典伸展得还要远。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阐明义务理论在当事人信息共享方面仍显得保守。*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阐明时的当事人义务——兼论证明妨碍理论》,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页。
在承认实际中阐明义务基础上的理论又存在“一般的事案阐明义务”和“限定的事案阐明义务”的区别。一般的事案阐明义务论主张:保障当事人“对事实证据的平等接近”可有效提升民事诉讼法公平、公正、效率三大价值目标。原则上应肯定和保障当事人取得相关事证的“证明权”。但在开示事证将侵害当事人隐私权或秘密权时应加以权衡与协调。此说以诉讼法为基点,以美国法为理想代表。而限定的事案阐明义务论则主张:原则上仍按证明责任分配划定当事人各自举证之范围,除非依当事人间的实体法律关系而赋予一方当事人对对方的情报请求权,否则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原则上没有开示对对方有利事证的义务。但在“证据偏在”的情况下,证明责任方没有取得证据的“期待可能性”时,根据公平与诚信原则,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例外地应负事案阐明义务。此说以实体法秩序为思考基点,以德国法为典型。如此看来,就法院可收集证据范围来看,英美法系范围广而大陆法系范围窄,英美更注重发挥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收集证据的职权作用,而大陆法系更注重当事人自由与私权保障?英美法系更注重查明案件真相而大陆法系更注重法定程序规范的保障?这对于我们通常的所谓的“英美法更重程序正义与诉讼形式”的教条可能有一定偏差。
在全球法律渐趋融合与一体化的今天,阐明义务一般化的趋势比较明朗。德国学者施瓦布曾特别反对阐明义务一般化,认为这样的阐明义务过于广泛地干预了证明责任制度(包括客观和主观的证明责任)。在阐明义务一般化的情形下,诉讼中要么是案件事实阐明要么是在违反阐明义务时可以进行否定性拟制,因此阐明义务使真伪不明情形的实际发生日益减少,主观证明责任实际上已被普遍的阐明义务所取代,而真伪不明情形的压缩也即客观证据责任的意义缩小,依证明责任分配来规范诉讼证明行为的理论就没有多大的适用空间,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责任倒置的意义大为降低,也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了证明责任传统理论上依实体法规范蕴含的价值选择作为诉讼风险评价设置的架构与模式。施蒂尔纳则认为阐明义务理论的提出及运行能够使案件事实能够得到更好的揭示,这应当是司法诉讼的福音,理论的更新应为实践提供更好的解释与指导,而不是相反为保护某种理论的正统地位而要求实践向理论靠拢。阐明义务对主观证明责任的干预被过分夸大,没有人会认为成文法上的协助义务或阐明义务会转移证明责任,它只是减轻了举证人的困难。实践上,阐明义务理论从未威胁取代证明责任,而仅是作为证明责任理论的有益补充,证明责任裁判的正当性本应使事实调查达到合理的程度。施瓦布的学生普维庭则认为,施蒂尔纳主张尽量适用法律认可的阐明义务理应得到肯定,但这与作为最后手段的证明责任判决仍有重要区别。阐明义务的依据(从诉讼法严格限制的阐明义务角度看)只能是实体法。在法律主体间分配程序法之外的义务不是诉讼法的任务,相反,诉讼法应当为实现这方面的请求权服务。若诉讼法创设实体法上未规定的阐明义务就等于在真伪不明时彻底改变了法定的风险分配。*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施蒂尔纳在近年庆祝施瓦布90诞辰的学术交流会上试图整合德国关于阐明义务所达成的共识,他赞赏施瓦布赞同对特定案件类型适用类似的阐明义务是“一个诉讼法学家始终保持的平衡思考”,*[德]罗尔夫·施蒂尔纳:《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质阐明》,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而指出在这一问题上不同论者的差异并非不可调和。施瓦布的弟子戈特瓦尔德在续写“罗森贝克—施瓦布”相续编写的主流教科书时也虽然仍坚持认为“不存在一般诉讼阐明义务”,但赞同基于实体法抽象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或诉讼法一般性规定而存在“特殊诉讼阐明义务”,*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页。同施蒂尔纳一样从立法论的角度赞同未来引入普遍阐明义务。*Gottwald, Gutachten 61. DJT, 1996. 转引自周翠:《现代民事诉讼义务体系的构建——以法官与当事人在事实阐明上的责任承担为中心》,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
反对诉讼上的阐明义务的主要论据就是援引实体法即足以解决当事人间的协力问题。阿伦斯将问题狭窄地限制在诉讼上的阐释义务或说答复义务上。但从德国实践中的判例来看,这一命题难以立足。很多判例认可了竞争法领域内存在着扩大了的陈述义务,而这些案件中当事人由于缺乏特殊关系而并不存在实体法上的(诉前)答复请求权。最终得到广泛承认的,除了实体法上的案件类型之外,必然出现更加广泛的诉讼上的协助义务,但这种诉讼上的协助义务不应当被视为基本原则,而是应被视为受个案影响的特殊情况。这就赋予了法官发展法律的基本动因以正当性。对真实与诉讼自由空间之间的关系的敏锐的权衡,以及在诉讼中能比在诉讼外更容易阐明的感觉这两个动因最终决定了判例的发展。*参见[德]罗尔夫·施蒂尔纳:《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阐明时的当事人义务——兼论证明妨碍理论》,载《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应当肯定,从实定法角度来看,《德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创设清楚完整的阐明义务系统,对阐明义务一般化的法理推演在逻辑上是大成问题的。*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在阐明义务作为规则还是例外问题上,德国历史上的立法者采取了捍卫自由主义的立场。在“编辑义务”及诉前证据保全上采取克制的态度,而当时的立法者尚不知晓协助阐明的其他形式(如身体检查),因此历史上的立法者决定选择限制性的协助解决方法并没有太多原则性意义。世纪之交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在很大范围内决定依靠当事人自己的力量来消除风险以及由此尊重对方当事人的自由领域。一方面只对几种阐明手段规定了协助义务(当事人陈述、文书),对其他手段(物证、证人、一般情况下的勘验)则未规定。另一方面,诉讼法的规定与实体法的规定并存,且未统一清楚规定当事人拒绝协助的后果。而判例则利用诉讼法的模糊规定在各个方面大举推进,将原针对竞争案件所归纳的这一基本原则推广到对案件的普遍适用,使处于显著的事实过程之外的、本身负有陈述责任的当事人,可以期待另一方知情的当事人超出简单争辩而进行详细说明。判例有意识地脱离实体法而从诉讼上论证了对地产及物品的勘验检查。判例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关注理论上的争论,德国学者则通过阐明义务学说而从理论上论证法律的发展。协助义务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一再被扩张,也可以找到出现在不同领域内的接受阐明义务学说的裁判。近年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没有明确承认所谓的“一般案件事实解明义务”,但是又承认应当使不负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负有“第二位主张责任”。实际上此概念已经十分接近案件事实解明义务,甚至可以说是无所差别。*参见沈冠伶:《民事证据法与武器平等原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3页。
就事案阐明义务理论本身确实还存在着许多值得详细探讨的地方,无论是德国的施瓦布、施蒂尔纳还是日本的谷口安平、高桥宏志都展望并期待这一理论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谷口安平认为这可以评价为一种有利于实现当事人实质平等之视角的理论。这一争议在逻辑与理论推演上是无法分清胜负的,我们可以以实际效用为评判标准的实用主义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检视。阿伦斯认为通过实体法上的阐释义务就能够解决实践中的法律发展问题,通过实体法上的义务就可令人满意地解决判例中的案件,因此反对阐明义务概念化。而如果将事案阐明义务作为诉讼上当事人的一般义务来予以承认,那么就会与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体系产生矛盾,而且阐明义务前提要件的不明确将造成诸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局面。施蒂尔纳承认事案阐明义务理论确实将引起证明责任与主张责任在实际层面上面临着一些变化,这是当前应当克服的问题。小林秀之也提出这种理论会使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趋于模糊,而且恐怕会使当事人沦落到单纯向法院提供信息者的地位,进而丧失其应有的诉讼主体地位的疑虑。并认为,作为对陷于证明窘境(证据缺乏)当事人的救济手段,可以通过规定实体法上的信息请求权之方式来予以实现。*参见[日]小林秀之《新証拠法(第2版)》,弘文堂1998年版,第127页。但对于上述这一观点,日本学者铃木正裕提出了这样的反疑问,即阿伦斯所言及的实体法上的信息请求权是否真正属实体法性质,如在日本实体法上就几乎不存在信息请求权规范。*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正因此才需要诉讼法上的相应制度来加以弥补。
总之,事案阐明义务理论在不同国家不同整体法律制度环境中应当区别对待,但当今世界关于事案阐明义务的争论已从是否存在阐明义务转变为应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承认事案阐明义务。各国法律的发展也表明阐明义务在实践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关于事案阐明义务,可以从理论上假设一段光谱。在光谱的两端,均不存在事案阐明义务问题:一是在绝对职权探知主义下不需要此概念;一是在传统辩论主义原旨下不允许存在此概念。这两种极端可谓理论上的两种“理想型”,在当今世界司法实践中可能难以找到实例。而在此之间则存在从宽到严的五种情形(当然在理论细分上应不止五种,但作为一种类型化分析方法,五种类型的概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则可在世界不同国家找到基本相对应的现实法例与制度实例。(如下图示)

按中庸的思维习惯,我们可重点分析光谱的中点即第三种情形,基本代表了阐明义务问题上的折衷观点与作法。但这一情形的界定是较模糊的,无论设置前提条件(证明责任方主张已经具体化或虽欠具体化但有相当根据)或排除要件(证明责任方主张未具体化或虽具体化但尚不可信)实际判断起来可能都会很困难。在日本,也有学者通过设定阐明义务存在的条件来界定阐明义务范围的问题,有一种深受德国学说影响的观点主张,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承担事案阐明义务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第一,负证明责任当事人能够提出自己对权利主张具有合理基础的线索;第二,负证明责任当事人与事实隔绝因此客观上处于无法阐明案件事实的状况;第三,要求对方当事人阐明相关案件事实不存在责难可能;四,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具有能易于阐明案件事实的期待可能性。承担阐明义务的当事人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法院可以将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主张拟制为真实。而且,在主张具体事实阶段、证明活动阶段以及诉前收集证据之阶段,都会产生这种事案阐明义务。*参见[日]春日偉知郎:《民事証拠法論: 民事裁判における事案解明》,商事法務2009年版,第46页。
不管上述五种情形还是四个要件的设定与选择其实都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阐明义务理论如何适应实践需要的经验问题,司法实用主义的进路是允许探索和试错,由学术讨论和司法实践的互动来决定事案阐明义务存在的空间。正如德国这一理论的发展所显示的,学者的主张可能超前也可能保守,这种论争不定的状况恰好给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并与理论起到一种积极的互动作用,但归根结蒂,起决定作用的是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司法实践的选择。
四、事案阐明义务论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由于我国传统上注重追求案件客观真实,事案阐明义务理论尤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国实体法规范的粗线条与不完善也更需要这种学理上的诉讼理论支持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我国法律上向来强调任何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当事人作为最了解案情的人自然也不例外。由此看来,事案阐明义务在我国应当具有良好的观念基础。但是否需要引进或建构这一理论取决于我国整体法律制度这种现实环境。何况,在德国这一理论也聚讼纷纭远非完善。我们应该在对这一制度在他国的现实及其实际发展进行深入比较了解的基础上论证其在我国当前的现实可能性。
我国学界关于事案阐明义务这一概念的探讨尚未充分展开,而在司法改革过程中“证据开示义务”则已制度化。我国台湾地区也没有对“事证开示义务”与“事案阐明义务”这两个概念及其内涵加以定义或进行分辨。如前所述,证据开示与事案阐明义务两概念所涉及的诉讼政策的价值选择具有高度共通性,但在具体操作方式及违反义务的效果上存在差异。证据开示制度是指知道事实、持有证据的当事人在经请求的情况下必须说明事实提出证据。与此相联的问题是开示义务的范围如何确定及谁有权提出开示请求,请求开示的手段及违反开示义务的制裁效果是什么?而事案阐明义务侧重于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主动说明事实、提出证据,在未尽此义务时,依违反义务的情形及案件类型课予某种不利益的效果。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证据协力义务”,“诉讼协力义务”。事证开示或事案阐明义务是否存在是实质的证据开示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在广泛的事证开示理论基础上,当事人可充分利用发现程序取得必要证据,证明责任裁判空间会变得很小。
观念上对诉讼的不同定位反映出两种相对立的诉讼政策:第一种主张民事诉讼是为解决私人之间私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必须自行提出有利于己的事实,并仅对此事实加以举证,而不负对对方当事人有利事实与证据的提出责任。在私法自治原则下,掌握对自己不利事证的当事人有选择不提出该事证的权能。而第二种主张民事诉讼不应仅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竞技,而更应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不能因为证据被一方当事人掌握并加以隐藏而获胜。为追求判决公正,双方当事人应对所有纠纷有关事实与证据加以开示。在当今社会,第一种政策为社会公众所难接受,且有违反宪法诉讼权、平等权保障之嫌,两大法系均先后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第一种政策而向第二种政策转变。就当事人已知道的事实及已掌握的证据来说,根据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即产生事证开示义务,以实现诉讼法上公平、公正及效率的价值目标。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与举证妨碍在法理及规范体系上形成完美契合。*有关以事案阐明为功能指向的举证妨碍理论,参见胡学军:《具体举证责任视角下举证妨碍理论与制度的重构》,载《证据科学》2013年第6期。
德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事案阐明义务问题是与摸索证明的实质性问题相伴而生的,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也应“同类项合并”。摸索证明的容许性其实与事案阐明义务的范围与条件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不过事案阐明义务是从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其应负案件事实证据的提出范围问题,而摸索证明是从应负证明责任(但处于事件发生经过之外)的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其可提出推测性事实主张及证据要求的范围问题。二者在规范具体举证责任转换问题上可能是殊途同归的。摸索证明的容许性在于事案阐明义务范围的宽窄,因此,单从这一方面来看,摸索证明的容许性可被事案阐明义务的范围问题完全吸收,而不具有概念独立的必要。由于对事案阐明义务存在与否也没有绝对规范性的尺度,一切均以法院在具体情形下的裁量为标准。摸索证明的“证明”意义即在于其充当了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缓和举证困难的手段与理由。因为一旦提出“摸索”就意味着当事人具体举证责任的卸除而导致提供证据责任的转换,即使法院不准许当事人摸索证明也应在裁判之前向当事人进行阐明,使其有提供其他证据或进一步表达意见的机会。提升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是当今世界司法尤其是我国当前司法所注重追求的功能之一,传统理论往往将法院裁判本身的正确性(包括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当作当事人对法院裁判信任的决定因素,而当代方兴未艾的程序保障理论则认为增进当事人对裁判的信任应当更加注重诉讼程序中主体之间沟通的优化,并发挥以正当程序吸收不满的功能。从这一角度来看,摸索证明对我国更具现实借鉴意义。
总之,当今西方国家在事案阐明义务问题上的法律实践显示出的融合趋势提示我们:既不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绝对的“谁主张、谁举证”,也不存在无条件限制的广泛的证据开示,理论与制度的移植必须考虑特定时期、特定观念背景与整体制度环境。摸索证明与事案阐明义务虽然是我国当前新奇的概念,但绝不是陌生的制度。我们不应健忘: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传统的法院包揽证据调查的职权主义模式下,将当事人仅仅当作证据提供者,“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的弊端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对象。目前重提宽泛的“摸索证明”或无限制的“事案阐明义务”都会使我国司法改革辛苦建构起来的证明责任制度及民事诉讼模式转型前功尽弃。在我国以辩论主义为基石、以证明责任为脊梁的现代对抗式民事诉讼结构基本成型,但改革尚未成功的当前引进西方的这种后现代理论,于我国却是一种倒退。其积极意义只不过在于在特定的案件类型中以此理论可弥补证明责任分配可能的弊端。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Forward or Backward: the Obligations of Clarify the Case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uthor&unit:HU Xuejun
(Legisl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The obligations of clarify the case as frontier theory in civil proceedings law, has played a strong role in addressing the plight of prove in the modern cases. But the concept put forward a challenge to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the Burden of Proof theory which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But the concept proposed formation of a challenge but then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as a cornerstone of modern debate doctrine and burden of proof system.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is also around this issue. In today's world the generalized trend of the obligations of Clarify the case is clearer, this is especially has great temptation for our traditional litigation system which focus on the pursuit of objective truth. But the introduction of unlimited " the obligations of Clarify the case " will make our judicial reform and the model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complete failure. The positive sense of this theory only may be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burden of proof in certain types of cases.
the obligations of clarify the case; adversary system; burden of proof; generalized trend
2014-05-10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民事证据立法问题研究》(JD1346)的阶段性成果。
胡学军(1973-),男,江西修水人,法学博士,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D915.2
:A
:1009-8003(2014)05-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