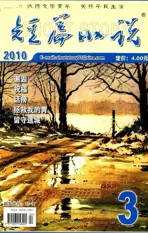有魔力的人
2014-09-20张留留
◎张留留
有魔力的人
◎张留留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要红了。微博粉丝与日俱增,我渐渐开始出门戴墨镜。但这样还不够,我的经纪人说,我的屁股上还欠一脚,把我像射门的足球一样,踢进声名的网里。于是给我找到了他,让他在报纸的重要版面,写篇关于我的深度报道——他那一支笔,据说捧红了很多人,经纪人要我珍惜这次机会。
我牢牢记得去拜访他的那一天。循着经纪人给我的地址,来到一条污水横流的小巷,我踌躇了一下,很后悔穿了新买的鞋。为了准备今天的约会,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置办行头上。我想起了手提包里的包子,那原是我精打细算的午饭。刻不容缓,我吃了包子,把唯一的袋子套在脚上,单脚跳着过了水坑。根据我一贯小心的做法,我特意拉低了帽檐,脱下了西装,排除了任何能让人认出、让我掉粉的可能。有两个孩子一直嘻笑着看着我,我想他们不会认出我的。
我的终点是靠北的一间小屋,在阴雨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破旧、肮脏。此时我心里犯了疑忌——这种地方,会是用一支笔捧红很多人的人住的吗?我的经纪人是否在夸大其辞,或者根本弄错了人?
门没有关,进去后跟外面一样冷。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一把椅子,一无所有——不,还有一点东西,那就是搁在地下、用来接雨水的大大小小的罐子。
“留得破罐听雨声。”这是他见到我第一句自嘲的话。也正是这句话,让我相信他还有两把刷子,是我要找的人。
“文章我已经写好了,你看一下吧。”他大大咧咧地说着,将几张稿纸扔到我面前。
什么?写好了?我吓了一跳。我们此前根本没有见过,经纪人今天是让我来把过去的经历跟他谈谈,然后再讨论写什么的啊!况且,整个屋子里没有见到一张桌子,也没有见到一本书、一张报纸,他是在哪儿写的、又是根据什么写的呢?
让我更大吃一惊的是,这篇名为《记青年创作新锐张小留》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我挽起裤腿、套上塑料袋跨越水沟的事情。要知道这件事刚刚发生,就算他在第一时间于窗口看到了我,可我进屋连十分钟都不到,不要说构思了,就是单单打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进文章,也令人难以置信。难道,他有未卜先知的功能?
也许那水坑存在已久,每一个尚未成名、忐忑不安、野心勃勃的作者,他们羞涩的囊中都有两个用塑料袋套着的包子,遇到水坑时都为了爱惜衣服而挽起裤腿,给新鞋套上袋子。要是我的假设为真,那这文章也没什么稀奇——在我来之前,他可能设想了多种我面对水坑时的表现,写了不止一个版本的文章,再对号入座,专门给我一个下马威。
我可不能让他吓住了,我把稿纸推还给他,“跳水坑的细节固然生动。不过,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我还是希望多谈一些跟读书和写作有关的事。”我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去,把两条腿伸得直直的,尽量摆出一副轻松、随意的姿势。“比如,在我幼年的时候,我曾经受教于一位姓郭的老者,他家里有很多书——”
“一位姓郭的?家里有棵桃树?”
“没错。”听他提到桃树,我心里一紧。
“我在你早期的文章中看过,你跳墙到这位老人家里,是为了偷树上的桃子。他是个盲人,目不识丁,家里并没有书。”
我面红耳赤了。说实话,早些年我从未梦想过自己会大红大紫,所以才会把这些不体面的小事写进文章来凑趣。要是我早有预感,我肯定要写一些“头悬梁、锥刺骨”、“囊萤映雪”、“苦学不辍”的事情,有谁不喜欢拥有高尚、大气、完美的过去呢?不过,发表这些文章的,我记得,可不是什么有名的杂志。其实,还是我掏钱包,这些杂志才肯发表的。现如今,这收费杂志倒闭很多年,大概只有图书馆还存有样刊,普通人根本是看不到的。
我把我的这层意思,除了交钱发文章之外,都告诉了他。
“你先往下看吧。”他挥手打断了我。
我一下子坐直了,端正屁股、并紧双腿、挺直后背,想要展示出一些气场来。可奇怪的是,当我以前面傲慢的姿态坐时,椅子结结实实、不摇也不晃,可当我试图坐正时,椅子咯吱咯吱响起来,屁股下、腰后面,似乎所有的部件都在移位、变形。我赶快跳起来,椅子又寂静无声了。
在这一起一坐之间,我觉得彻底被他打败了。这把椅子,又是他测试人的道具。渐渐地,伸直两脚坐在椅子上,变得不是那么自在和舒适了,因为这不是我自由的选择,而是被迫的结果。只有这样,我才能稳稳当当坐着,不让椅子讨厌地吱吱叫。
他坐在床上,俯视着四脚朝天的我,在他灰色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是厌倦和赶快写完的解脱,仿佛在说写文章跟一个裁缝锁一条裤脚没什么两样,大家谁也别装了不起。
为了掩饰尴尬,我把文章高高地举在头顶——因为那可恶的椅子——快速看了起来。
接下来,谈到了我和梯米尔的交往。他也是一位作家,才气也许有一点,可全被他的财富给拖累了。他终日忙着设宴,救济或招待写作同行,所以,他简直没有时间去安安静静完成一篇作品。但这也无所谓,以他的乐于助人和宾至如归,我们原谅他在作品里的细节瑕疵和逻辑的小小混乱。毕竟,就他的财富而言,他写得已经很好了。但他似乎对此并不满意,老是抱怨金钱、过多的饮宴拖累了他的才华,他不加节制地花钱,我们也不遗余力地帮他。当他千金散去的时候,大家都纷纷向他祝贺,他自己也很高兴,以为一个新的创作高度会到来。
但我们显然没说实话,他也高兴得太早了。在千金散去和创作辉煌之间,还有长长的一段不文一名、穷困潦倒的路要走,这条路不走到头,不体会世界的世态炎凉,休想写出一流的作品来。命运向他显示了自己的残酷:当梯米尔有钱的时候,他尚且能写出一些虽然内容风花雪月,但故事也颇可观,笔调轻松的作品来。起码适合他那个阶层的人,或者想了解富豪生活的人看。他整日为柴米发愁时,他也还是写这些东西,但不免让人觉得他在虚张声势、想入非非了。我不喜欢这样的梯米尔,我有先见之明,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祝贺他散尽家产的人。那时,我正经过作家基金会的推荐,在参加“作家培训大师班”的全封闭训练呢。
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却提到了我出现在梯米尔的酒宴上,毫不起眼地坐在桌子角落里狂吃不辍。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能吃的小胖子有一天会大红大紫。
在这段描写中,唯一合我心意的,可能就是“大红大紫”四个字了。至于梯米尔,想起他现如今的债台高筑、穷困潦倒,且笔风慢慢转向尖酸和刻薄,我想,最好还是不提为妙。如果我真的是“默默无闻”地出现在桌子的角落,那么,是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我的。况且,我也不是奔梯米尔而去的,也许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梯米尔搞错了,我从来没有出现在梯米尔的圈子里。”我字斟句酌,“事实上,我接到过邀请,但我没有去。我在勤奋地写作。”
还是那冷冷的灰眼睛,但我并不去看他,而是在两腿伸直、不能弯腰低头的情况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稿子的旁边加了个重重的“×”号。直到那时,我才觉得胸口舒了口气。
现在回忆起来,让我有胆量这么干的,是一直在叮咚作响的瓦罐。
我又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提到了我的妈妈。哦,妈妈,提到她我就落泪。自打妈妈过世后,我做梦梦到的房子里,都是空的。世界上不会有人比她对我更好,她从不坚持要我工作去养家糊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省吃俭用,把最后一个铜板寄给我。要是她能活到今天,活到我即将大红大紫的黎明,她该是最开心的一个!
自然,也不用说,为了我的成功,她也愿意付出一切。既然如此,那么……
在我沉吟的时候,他看出了苗头。
“又有哪里不对了?”依旧是那充满厌倦的灰眼睛。
“没有什么。”我打消他的疑虑,“一点小问题。您大概把我母亲的过世时间搞错了。”我放下稿子,把两只手叉起来搁在胸口,这样多少能减轻点两脚朝天的不自在,恢复一点自信。“我母亲不是五年前过世的,她是上个月二十八号才走的。”
“什么?!”我和他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他第一次出现了惊讶。
“在这里,我要透露一个秘密。医生早在去年夏天,就判了我母亲死刑。她之所以能活到上个月,是为了读我的新作《月亮从东边升起》。当时,我奔波于书桌和医院,彻夜不眠,伏案写作,为的是第二天好在母亲的床头读给她听。说来也怪,这作品比所有的抗生素都管用,我母亲已经掉光的头发奇迹般地长了出来,脸也恢复了光泽。可以这么说,我母亲的最后一段时间,比其他的病人都要安详、快乐。这大概是文学作品能够给予人的精神力量吧。要知道,那时,我的内心极度痛苦,情感悲痛到了极点,简直是上帝抓着我的手在写作。上帝知道要写什么,而我只是他的传声筒、打字机。大概正因这样,这部作品才获得出版社的青睐,得以在母亲过世后迅速出版——”
“五年前,令堂刚过世的时候,你在博客上写了一系列哀悼文章,难道,这也可以造假吗?”
我早就做好了脸红的准备。在五年前,我曾经想到过发表,可杂志的稿费少得可怜,让我觉得是对母亲的亵渎。我赌气把它们写到博客上,可关注者寥寥,跟我大张旗鼓的哀悼极不相衬。一气之下,我全删了它们——幸亏我删了它们,现在,这些文章可以换个时间重见天日了,一举双得,何乐不为?既然推迟几天或几年,一点也不能改变去世的事实,妈妈一定会很高兴改变一下时间和方式,来方便一下我的。我是她的儿子,我比别人更了解她。不是吗?
“关于我母亲的过世,我想我最有发言权。”我不想多说,在这篇稿子上,又打了个“×”。
“嗤,嗤!”回答我的是两声冷笑。“我的文章一经写好,从来不改!”
我承认有点儿周身发冷、局促不安。可我不会让他压倒我。他知道在面对谁吗?那是我,即将声名鹊起的人物,这是他为我写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我不会再找他的。这阴暗的房间,漏雨的天花板,大大小小的瓦罐,让我深深怀疑起经纪人的举荐——一个能用笔捧红很多人的写手,为什么自己不去大红大紫?被虚荣冲昏头脑,也是为这不能端正坐姿的椅子所气恼,我说出了终生后悔的话:
“以上提到的问题,请您务必按照我的意见去修改。鉴于您的经济状况,酬金先付一部分,其余等改完后再付。”我环视空空的四壁,留下了一个信封。
“我一个字也不会改,一个字也不会改!”是他的声音。我走出房门,重新挽起裤脚时,却发现没有把刚才的塑料袋叠起收好。寻思一阵后,我花了点小钱,雇佣一个孩子搬了几块砖来垫脚。
我深信他会改的。
果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看到了这篇文章——哦,不,混蛋,他竟然一点也没有改!愤怒之下,我拿起电话。
“请仔细看看,这篇文章跟你有关系吗?”他厌倦地说完,便挂了电话。
我这才注意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并不是《记青年新锐作家张小留》,而是《记青年新锐作家梯米尔》。
电话铃声不期而至,是一个朋友。“你知道吗?梯米尔红了!”他兴奋地对我嚷道。
这次是我挂的电话。
梯米尔红了。这个厚脸皮的家伙,竟然连我的母亲都接管了。我跑过去找他理论的时候,他正笑得两眼放光,很高兴地看到他又有回到过去生活的可能。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他冷冷地对我说。
我再次冲进肮脏的小巷,穿着我最昂贵的鞋子涉水而过。当我泥水四溅地跑到他屋子里去时,发现那儿已经人去楼空了。只有瓦罐还摆在地上,等着不知何时会落下的雨水。装了钱的牛皮纸信封,摆在不能让人端坐的椅子上。仿佛他料准了我会来。
经纪人怪我错失良机。“跟你说他有这种魔力,他写谁,谁就能红!”
我始终不明白的就是,他那支笔,捧红了很多人,为什么却无法捧红他自己?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