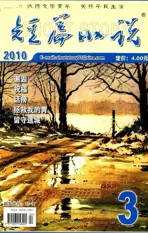捡拾
2014-09-20刘志波
◎刘志波
捡拾
◎刘志波

爹的脚在垃圾箱边碰到我时,觉得软软的,以为是只死猫,借着路灯的光亮细看,才辨出是个同类。爹说我当时的脸紫得像个茄包,手指横我鼻翼下,微微觉出一丝气息,就把我揣怀里抱回家。爹紧着熬了半勺面糊,找根竹筷蘸着抿我嘴里。慢慢,我有气无力地哭起来,爹悬着的心才放下,咧开两片厚嘴唇,脸上绽出灿烂的笑。
爹太奢侈了,第二天不再喂我面糊,而是从小卖部买来奶粉喂我。
我自幼在爹的背上长大。爹用捡来的旧衣,拆了洗净,为我缝一个布兜,每天出门,爹就用布兜把我固定在他身上。爹是留我在家担心,爹说他早年一个同伴,儿时就让老鼠咬掉了一只耳朵。爹这般精心呵护是不想让我落下残疾。爹本身就是残疾人,只有一只胳膊,一条腿比另一条腿还短半截,走路一歪一扭的,背上的我,也随他一歪一扭。爹这毛病,是那场大地震留下的,爹说要不是好心人从废墟里把他挖出来,早就托生了。爹可吃够了身有残疾的苦痛,每次背我系布兜时,都是用牙叼着一条带子,用那只粗糙的手来打结。牙,就是他另一只手。一次爹捡了一三轮车废纸箱,怕滑落,就用绳捆。爹咬着一只绳头,另只手打个结猛力一拽,嘎嘣,就崩掉了一颗牙。真担心,爹一旦牙齿掉光了,岂不等于又断了一只手臂。
爹每天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见了垃圾,喜得像淘金者发现金矿,立马跳下车来,用自制的铁耙子,仔仔细细把垃圾耙一遍,生怕漏掉一张纸片。一股股臭味,冲冲地钻进我鼻腔,熏得我阿嚏阿嚏直打喷嚏。爹的收获,都写在脸上,特别是捡到值钱的废铁烂铜,爹的脸,就不自觉地像菊花一样开放。
爹带我出门就是一天,揣两个馍,便是午间干粮。灌一塑料桶水挂车把上,渴了就咕咚几口。爹宽厚的背像柔软的床,不论多么嘈杂,困了我就趴上面睡。饿了我就哼哼唧唧吭哧,再不理我就咧嘴嚎。爹见我咧嘴,就知我饿了,爹就掰一口馍,放嘴里嚼,然后对着我嘴,用舌尖将嚼碎的馍舔进我嘴里,像燕子妈喂小燕子那样。我吃饱了,就冲爹笑。爹也冲我笑。
慢慢,我会爬会走了。爹出门,不再背我,爹把我放三轮车上,哼着小曲,还时不时回头冲我做个鬼脸,逗我咯咯咯地笑。这时,爹就来了精神,三轮蹬得欢,车座上的屁股上下地扭,有时还大撒把,举起独臂,仰着脖子,狠劲地吼一嗓子。我也学爹吼一嗓子,尖细的声音,像爹的回声。
爹为我起名叫“大猫”。爹说“大猫”是老虎的意思,希望我长得威猛雄壮,虎虎生威。我还真就长得虎头虎脑,虎虎势势。尽管我不如城里孩子吃得好,可我长得比城里孩子还壮实。爹见我白白胖胖,心满意足,很有成就感,常常蹬着三轮,故意去孩子多的地方。一次我往地上一站,一个孩儿妈立刻凑上来,舌尖咂得啧啧响:看人家这孩子长得,这叫一个俊!说着,手就伸进我裤裆里,拽着我的小鸡鸡:嗯,还是个带把儿的,长大了,肯定是个猛男呢!
爹在一旁嘿嘿笑。
笑啥?肯定是。孩儿妈冲爹说:这孩子,反正也是你捡来的,卖我算了。
给多少钱?爹问。
孩儿妈伸出俩手指:两万!两万怎么样?够你捡几年破烂儿的。
爹说:你就是给个金山,俺也不卖!
孩儿妈满脸不悦,扯着嗓儿喊:苗儿再好,栽你那盐碱地,也长不成材!
转眼,我满7岁了。
一天,爹拿出一个捡来的旧书包,灯下,用针把破的窟窿缝好,说:过两天,你就去上学,我给你把名报上了。
我一听,撅起嘴:我不愿上学!
爹瞪圆了眼,问:为啥?
我勾着头,没吱声。反正我不愿上,整天教室里闷着,哪有跟爹捡破烂儿自由,说不定还能捡半瓶汽水喝。
爹一拍大腿,急了:这学你想上也得上,不想上也得上!你小子想接老子班是不?没门!长这大,爹这是头回冲我发火,眼珠子瞪得溜圆,我好怕。
我只好乖乖地去上学。
我家住县城边上,这里原是采煤塌陷区,在一块荒地上,爹用捡来的砖头垒起房子,用树枝夹起院子,院里堆满捡来的破烂儿。从家到学校走二里地。头天上学,爹用三轮车送我,以后爹再不管接送。不管刮风下雨,都是我一人,颠颠儿来回跑。爹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在苦窝里长大,吃苦并不怕,怕的是受人欺。
班里同学不爱和我玩,嫌我脏,嫌我土。最讨厌的是那个叫王一宁的小子,长得猴模猴样,穿着一身名牌,脖上挂个玉张飞,许是仰仗张飞爷保佑撑腰,净干讨嫌的事。见我,不是拍我脑袋,就是踢我屁股。我和他一组搞教室卫生,他从来不干,我不替他搞,他就骂我“野杂种”。开始我没理他,后来他再骂,我就急了,奶奶的,我照他的鼻梁骨狠狠的就是一拳,打得他口鼻蹿血,嗷嗷直叫。
我闯了祸。
那小子他爸是个公安,开着警车找到我家,手指我爹鼻子,凶凶地撂下一句话:以后你家崽子敢再动我儿一指头,看我不把你这两间猪窝平了!
爹盯着我楞了,回过神儿后,挥手给我一个大耳光。打得我天旋地转,眼冒金花。我辩解:是他先骂我的……
爹说你骂不得?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要知道,你爹就是个捡破烂儿的,咱斗得过谁呀!果真咱这两间破屋被人平了,你睡大街去?以后你给老子记住,再惹事生非,看我不敲断你的腿!
我眼里吧嗒吧嗒直落泪。我委屈,我不服!干嘛我非得受人欺负?可我不敢再反驳,我怕爹的大耳光。
爹打完我肯定后悔了,当着我面,竟自己抽自己一个嘴巴。我一头扑上去,抱住爹的腿说:爹,我错了,以后再也不给爹惹事。爹把我揽怀里,说好孩子,听爹的话,啊!爹抚摸着我头,喃喃自语:爹不该打你,爹不该打你……
爹不再单单捡破烂儿了,还收破烂儿。爹说我上学,买书买本的花销大,收破烂儿虽花本钱,但来钱多。收来的废铜烂铁报纸塑料瓶……爹将其分门别类,然后用三轮拉了,交废品站换钱。
爹也干杂活。只要给钱的活,爹都干,不给钱给破烂儿也干。有一家地下室冒水,要爹把里面箱子搬出来。见爹一只胳膊,就摇了头。爹说不能门缝里瞧人,那不把人看扁?让我试试。地下室水里泡着一箱一箱,半屋子,全是酒。爹一猫腰,手抠箱底,腋下一夹,一箱酒就搬出来,不到一小时,完活。主家见爹干活实在,从箱里抽出一瓶酒,塞爹手里:得,工钱顶了。
爹将那瓶酒放屋角捡来的木箱上。爹说等有喜事了,就把这酒打开喝。
可喜事何时到我家?我绞尽脑汁想半天,也未曾想出。
入冬了,野地里田鼠没了踪影,猫进洞,避风寒。
那日放学,天上飘起小雪。寒风呼啸着,刀似的割脸。我手揣进袖筒,缩着脖子,弓背猫腰,一溜儿小跑,哆哆嗦嗦赶回家。
爹破例炒了俩菜,比平时多一个。饭桌上放着那瓶酒,瓶盖已打开,屋里弥漫着醉人的酒香。
爹,有喜事?我心跳加快,想起过去爹说过的话。
有,有,大喜呢!爹兴奋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地进里屋,领出个半大小子:瞧,我给你捡来个弟弟。
我瞥一眼那小子,比我还高半头。问他几岁了,也不答话,抹搭着眼皮,拉着脸子,鼻涕邋遢,带相儿,一看就是个痴呆!
我不解,不无埋怨地说:爹,你咋捡个傻子呀?
不料,这话把爹脸上的喜悦扫得一干二净。爹说话的语气变了调,冲我道:傻子怎么了,傻子就不是人?这大冷天,他蹲马路牙子上,浑身冻得筛糠,过一夜,不得冻死?好歹他也是条性命。从今儿开始,你们就是亲哥们儿,他不灵性,以后你还得谦让着点。
我没敢再说话,我怕爹发火扇我大耳光。
爹先为傻子倒上酒,再为我和自己倒上。未等爹说开场白,那傻子端起酒碗,一仰脖儿,一口倒进嘴。因喝得急,酒劲冲,一时承受不住,噗的一口,就喷射出来。真恶心!这饭没法吃了,我一头扑进里屋。
爱吃不吃,咱爷俩吃!来,儿子,猛劲吃!爹甩出一肚子气话。
像当年待我那样,每天爹出门都带着傻子。爹为傻子起名叫“二猫”。二猫爬上爹的三轮车,爹喊一声“坐稳了”,就欢实地蹬着车,出了门。
傍晚回来,爹不再为我带回饮料或香肠。我敢断定,肯定是爹当时捡了,就顺着二猫嘴,进他的肚里,分享了本该属于我的美食。我既嫉妒又羡慕,星期天,我提出要和爹和二猫一同去。爹不让。爹说你在家写作业,认字比啥都重要。我说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写完了。爹没吱声,我就干脆麻利快,一跃跳上三轮车。
爹吆喝的声音很动听:破烂儿——的——卖——浑厚洪亮,铿锵有力,拖着长长的尾音,像唱歌。我和二猫也学爹的腔调吆喝。爹说二猫比我吆喝得好听。屁!我听二猫那声调,像狗踩疼了尾巴叫。
吱扭一声,一处院门打开,探出张满脸皱褶的老太太脸,瘪嘴一颤,喊:卖破烂儿!老人家牙已脱落,兜不住风,声音有些含糊不清。
爹把三轮停门口。我和二猫随爹进院里。院儿不大,南墙根下,堆一堆破烂儿。老奶奶说:我整天一个人心闷,就出去捡破烂儿,一来散心,二来可换个零花钱。
爹说:你老可是过日子人。
惯了。老奶奶说,干了一辈子,闲着倒难受。唉,说来归去,就是干活的命。
一只黄毛狗凑我面前,不咬不叫,乖乖地摇着尾巴,舔我手指头。
见我和二猫,老奶奶愣怔一下,冲爹说:你可是好命,俩孩子,个个像虎羔子。哎,国家不是只许生一个吗,你咋就多吃多占,生了俩呢?
爹避开我和二猫,凑老奶奶耳根嘀咕了几句。老奶奶讶异地望着爹,说好,好!你是个好人。就冲这,我这破烂儿以后都卖你,什么钱不钱的,你先拉走。
爹说,不给钱可不行,就你老这岁数,便宜我可不能占。
以后爹和二猫又来老奶奶家收过几次破烂儿,我上学,没空来。
一个星期天,我和二猫随爹又来到老奶奶家。门虚掩着,喊了几声,没人应。院里只有黄毛狗疯了似的叫。爹推开门,那狗就蹿上来,叼着爹的裤腿往屋拖。爹好似预感到了什么,紧赶几步进了屋。
老奶奶躺在床上,迷迷瞪瞪,依然昏睡。嘴唇像干涸的河床,裂一道道口子。爹伸手摸一下老奶奶额头,说:烧得厉害,赶紧送医院。
爹把老奶奶抱上三轮车,又拿床被盖身上。爹跨上三轮在前面猛劲儿蹬,我和二猫一溜小跑在后面推。
进了医院,爹背着老奶奶,左拐右转,总算找到急诊室。
戴眼镜的女医生用听诊器给老奶奶前胸后背听了听,走到桌前开张单子,递给爹:你家老太太这病严重,得住院观察,你先去交费吧。
爹问:交多钱?
三千!
爹蒙了。爹身上只有二百块收破烂儿的钱。爹说钱不够,得回家取。
眼镜女医生满脸不高兴:来看病不带钱!你走了,把个病人丢这儿,不回咋办?
爹呆愣愣,不知如何是好。片刻,爹说,这样吧,我把俩儿子押这儿,行吧?
眼镜女医生瞥一眼我和二猫,不知为何,扑哧一声笑了,没再说什么。
爹手提个破布袋,满脸汗水地赶回来,先向我和二猫一人手里塞个馍。并嘱咐我:这一住院,我还说不定在这待几天呢,你带二猫回家吧,要照顾好二猫,上学别迟到。再有,把三轮骑回去,放这要交停车费,死贵的。
爹,我记住了。我点点头,拉起二猫,跑出急诊室。
爹不在,我就是家长。何况爹授权让我照顾二猫。“照顾”和“管”意思有点相近,好像听老师讲过。
我首先为二猫立了一条规矩:不准他走出院门。二猫若真离开家,傻啦吧唧走丢了,我上哪找去?
我对二猫说:你敢走出院门,我就揍你!
二猫不服气,梗着脖子,吭哧憋肚了半天,说:爹……都不打我,你,你敢……打我?
我在二猫眼前挥一下拳头:敢打!不信你就试试。当初我一拳把个骂我的小子打得口鼻蹿血!
二猫蔫了。看得出,二猫是真的怕我了。
二猫果真听话。我放学回来,他一人乖乖待院子里,只是大嘴咧到耳根上,鼻涕眼泪一大把,哇啦哇啦仰天嚎。
我问二猫:谁欺负你了?你哭啥?
我这一问,二猫更觉委屈了:呜呜……俺想爹……
我鼻子也酸了,何止他想呢,其实俺也想俺爹。
爹五天后回家,人瘦了一圈,塌了眼窝,疲惫得也像病过一场。
听爹说,老奶奶的病并没见好,只是烧退了些,每天依然咳嗽不止。医生该给她检查的都查了,不该查的也查了,什么这光那超的,把个老奶奶折腾得差点散了架。花钱多不说,爹一个外人侍候她,老奶奶不落忍,非闹着出院,死活不在医院住了。
爹叹口气:唉,说来这老奶奶也怪可怜的,地震时没了一对儿女,前几年老伴又撒手而去,就剩个孤老婆子。最亲的人,只有一个侄子,可这侄子又是个不务正业的赌棍,把房子赌成了人家的房子,把老婆赌成了别人的老婆。打来电话,要给老奶奶养老送终。老奶奶知他葫芦里卖的啥药,死活不应他来。一个重病的孤寡老人,身边没个人照应,心里该是啥滋味啊,咱再不帮她,谁帮她?
当天傍晚,爹放心不下,就带我和二猫去看老奶奶。见了我们,老奶奶吃力地欠欠身子,接着就是一阵咳嗽,枯井似的眼窝里,竟有一串串泪珠涌出,滑落在枕头上。
爹为老奶奶做了碗挂面汤,里面还卧个鸡子儿。爹端起碗亲手喂老奶奶。强吃了半碗,老奶奶又咳起来。爹给老奶奶捶了捶背,老奶奶方止住咳,说,剩那半碗汤,不吃也糟践了,扔了可惜,还是趁热让孩子吃了吧。二猫听了,也不等爹下令,跨前一步,端过那碗,秃噜秃噜,三口两口吞下肚。
侍候好老奶奶,天不早了,外面的夜黑得像锅底。爹对老奶奶说:我们回去了,明儿早我再来。
不行!老奶奶说,从今儿你们就住我这儿,这就是你们的家。你们爷儿仨住西边那两间,我住这间,挺宽敞,捡来破烂儿放院里,不是挺好?等我好后,我和你们一起捡破烂儿……
爹说:这可不行,孩子们淘气,会惹你老生气。
听我的,不要再说了,再说就外道了。从今儿起,咱们就是一家人。
我心里一阵狂喜,巴不得住这里,房子宽敞干净不说,以后上学,至少少跑一里路。
爹依旧和二猫去收破烂儿,我依旧去上学。爹每天很早就回来,给老奶奶做饭吃。爹还从诊所请来位老中医,为老奶奶把脉,看了舌苔,开了方子。爹取来药,先用水泡了,晚上支起砂锅熬。给老奶奶喂了药,见老奶奶睡下,爹才回屋休息。
约半月光景,老奶奶的病越发重了,一日不如一日,晚上一夜夜地咳嗽。爹就在床前一夜夜地守候。见老奶奶状态不好,爹怕了,爹不顾老奶奶反对,硬生生地把老奶奶又送进医院。我心疼爹,要陪爹去,爹不让,爹说念书比啥都重要。
三天没见爹了,我想爹,也惦着老奶奶。也不知老奶奶的病好些没有?下午放了学,我没进家,背着书包径直去了医院。
找到爹时,爹正在医院太平间前垂泪。不用再问什么了,我忍不住扑到爹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爹弯下腰,为我擦拭泪痕。爹说,老奶奶走时像睡着了一样,很安详。
爹还说,老奶奶上午还清醒,许是回光返照吧,还说了会儿话。
老奶奶说爹,自从认识了你,才懂得人活着不能光为了自个儿,还应该为别人做点啥,可我……还能做什么呢?等死后将我这把老骨头捐了吧,或许还有点用处。临闭眼老奶奶还叫了声:张二狗……好人呐!
张二狗就是我爹。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