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和谁的“社会共谋”
2014-09-10韦星
韦星
天凉了,每天傍晚,我都到楼下的一个酒铺给母亲打一斤黄酒。温好后,再给母亲喝。这是客家黄酒,听说可以活血,不过,一斤15块钱。
习惯了在老家喝一斤2块钱米酒的母亲,认为:这酒很贵。早年拾过牛粪,一向视“粪土如金钱”的我,也认为:这酒确实贵。但我一点不心疼。如果母亲回老家,我还要再三叮嘱她:“千万不要再干重活了!”此外,我还嘱咐家人“做好对母亲的监督工作”。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孝顺,而是我害怕了。
12月10日这天晚上,一个同学在他的QQ空间里,晒出他父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的清单:22天,18万元!
这远没有结束,他父亲目前还在ICU病房里。我本想说一两句安慰的话,但有用吗?这个时候,钱才是最管用的,但我有钱吗?
想到这些,我悄悄退出。
对一个房奴而言,有一两期不发稿子,我就心慌胸闷得厉害。自救尚难,如何他救?所以只好在拼命工作的同时,祈祷父母身体健康。父母健康,就是为子女挣了大钱。我一直无法想象,如果灾难来临,我拿什么去应对?谁有钱借给我?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肯借钱给我?
这些年,这种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我。如今,随着父母年龄增大,我常感到: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我稍微平静的时候,便狠狠掐我的脖子,让我透不过气来!
只在匆忙的时候,我才能在身心的忙碌中,淡忘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焦虑感。
所以,当我从医的朋友、做公务员的同学,每天都在微信圈里抱怨当下社会的戾气如何重,患者如何不理解医生,刁民如何为难政府时,我在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有时,考虑到今后的采访需要,我甚至违心地应和或认可他们的看法,充当他们的出气筒。
但年底了,我不想那么委屈,我想和他们聊聊,想和这个社会谈谈。
客观说,医生收入还不错,就是比较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认为,自己累死累活,适当多拿点也是应该的。我不想在收入上和他们争执。问题在于:看病确实太贵了,大病真看不起。即便挤入了“中产”行列的白领,也都在感叹:病不起!
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不焦虑?
我們很清楚,白领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上班的背后,一旦家中有人生重病,房贷面临断供,他们的整个人生,就会灰头土脸。
对医生个体而言,他们认为:收费高,那是医院的事,挣钱也是医院在挣。医院则认为自己抬高药价、过度检查的理由是:医疗成本很高,仪器很贵,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拨款……
总之,无论是医生个体,还是医院本身,面对社会指责,他们都认为:所有的坏,和自己无关,自己只是在兢兢业业地做事,但社会却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自己头上。针对患者打砸医院,追打医生,他们也学会了拉横幅、表诉求,要求严惩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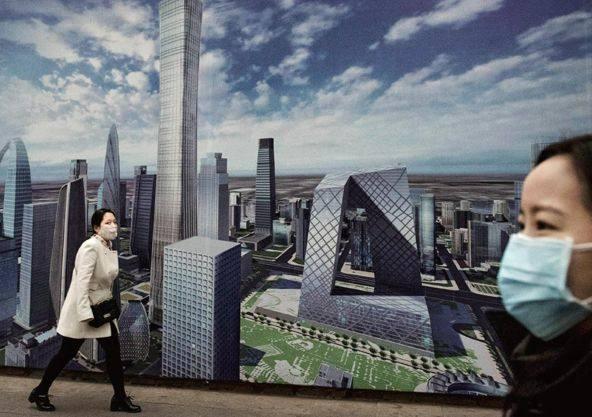
平心而论,我们反对一切的暴力行为。但很多时候,我更多是理解患者的无奈。这种无奈,并不是说这个医生本身有多坏,有多故意地要求患者去做乱七八糟的无关检查——尽管在当下,一旦停电,很多医院的医生就不知道如何看病了。而是说,这根本就是一种共谋!
对患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我这么一点病,就花走我大半生的积蓄!至于我的钱给了医院后,你们如何分配,谁拿大头谁拿小头,那不是患者所关心的。患者没有博弈能力去讲道理,他们只能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医院和为他看病的医生身上。他们认为,医生为医院服务,其实也是既得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他们合作共谋,完成了对患者个体的一次次盘剥—全然不考虑患者的家庭处境,不顾他们是如何砸锅卖铁,如何吃尽苦头,坐尽冷板凳,才讨来了这么一点点的医疗费。
是的,让医院去顾及这些感受也不对,但谁来顾及患者的感受呢?他们的委屈、无奈、苦楚,又能向谁诉说呢?市场化先是将这批人甩到了社会边缘,后来终于有了医保,农村也有合作医疗。
但凡在农村待过的都知道,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一样,早已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被抽到大城市里服务那些非富即贵的阶层和阶层衍生品。所以小病还可在乡镇或县城医院看,稍微重一点的病,只能到市里或省里,甚至是跨省治疗。这样,重病报销的比率,少得可怜。患者的家属,在大病光顾时,就像海边孤立无助的小树,遇到了12级飓风。台风过后,树不是被连根拔起,也是被吹得枝叶散尽,树根折断。
我有个师兄,曾是一家报社教育版的主编,但现在却辞职去给一家民营医院做策划。收入比在报社时好,他向我坦承:“很多门诊,其实都是搞钱的,骗那些民工,小病说成大病,尽量开贵的药,不断重复检查。”这个潜规则,稍有点见识的,其实都知道了—只有民工不知道。
我的好奇在于:师兄,你作为一个曾经的记者,本来是充满正义感的,怎么就去干这种坑蒙拐骗的事?他的回答很坦然:“我只是做策划的,又不是我去骗,骗也是那些医生在骗。”我本来想说,“你的收入从哪里来?”但还是憋住了,这涉及一个共谋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做的环节,没有任何问题,但当这些环节组合起来后,就变成了大家一起合谋干了一件件不光彩的事。
这样,当医患关系出现时,医生要和患者个体去讲道理(当然,医生很忙,没空),但患者已经不想和某个个体讲道理了。患者始终认为:你们怎么分赃,是你们内部的事。总之,你们合谋完成了对我的一次次掠夺,我已一无所有。
其间,孰是孰非,我不想评价,但这就是当下社会矛盾的一个聚合点,是化不开的死结。很多极端事件,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化不开的结,最终演变成一次次全体网民围观和吐槽的冲突事件。
冲突过后,民众的态度还是:同情患者,谩骂医院和医生。所以医生一直认为自己“很受伤”。
其实,包括公安等公务员群体在内,公共事件中,多是遭到公众谩骂的群体。这不是公众不理解,而是当他们和这些权力部门打交道时,都充满了委屈和无奈。即便遇事时隐忍了,也在内心里,种下了满满的愤懑。终于,才在一个感同身受的网络事件中,找到发泄的出口。
从目前看,这些问题无解。它无关民众的素质。因为民众认准的只是,曾经或是不久的将来,“你们曾是或终将是共谋残害我的一分子”。
这种“共谋”的指控,不只医患领域存在,也存在于某些权力者对下层的掠夺事件里。甚至同为下层的弱者,也聚集起来,通过“共谋”实现对更弱者的掠夺—包括对生命的掠夺。
“共谋”的行为和思想广泛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减轻了人们共同作恶的罪恶感。彼此内心都认为:自己只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和结果的恶,完全没关系,即便有关系,自己那也是最轻微的部分。
以《邯郸·系列杀人骗赔事件调查》(见本刊第14期)一文为例,采访前,我一直琢磨:这群杀害和自己有着相同命运境遇的同胞,究竟是怎样一群人?采访后,我发现,21名施害者,都来自社會下层,家境贫寒,生存环境恶劣—有的就住在高山悬崖边。当时我就想,会不会是长期生存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人会产生赌徒的心态,冒险意识也更强一些?
但令人惊讶的是,施害者平时在村里的为人,老实、本分,甚至不和别人吵架。但离开家乡,在黑乎乎的矿井下,他们却疯狂锤杀工友。
他们的疯狂,很大程度上,和分工有关:21个施害者,分别负责招黑工、冒名顶替、矿井踩点、锤杀工友、索赔等环节。这样一来,即便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计划,但都感觉自己的罪孽没那么重。比如:负责招黑工的、冒名顶替、矿井踩点和索赔等环节的人,都认为罪恶的锤杀行为不是自己干的,所以罪恶感没那么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干的是最轻的活。真正锤杀的人,则认为:自己只是负责挥锤的,主谋是别人,自己的行为是受他人指使。主谋则认为,自己只是出了点想法,同时参与索赔,但锤杀、招工、踩点等环节,都是其他人干的。
在这种心理下,每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是最大的恶。但各环节一旦衔接,就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杀人计划。这是下层联手作恶的“共谋”。
另一种共谋,是某些权力者对弱者的剥夺。《贫困农民龙继根之死》(见第22期)一文中,核心事实是:龙继根去镇政府给小孩上户,因缴不起罚款,出现争吵,后来在镇政府跳楼身亡。
事件直接原因可能是争吵引发。镇政府在给龙继根家属几万块钱后,也强调是“救助协议”,谈不上政府的什么责任。但采访中,我发现,龙继根之死,有必然性。
案发当天出现什么意外争执,只是导火索。导致他跳楼身亡的因素,早已贯穿在他不断劳碌奔波,却又无依无靠、备感无奈之中。他的死,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尽管这种合谋杀害,不是权力有意识、主动而为。
龙继根的悲剧,是在遭遇权力冷漠、部门不断推诿后,酿造的。比如,他家很穷,但多年来,低保一直没有他的份。拿到低保的,反而是那些有关系有权有钱的人。
此外,贫寒、窝囊一辈子的他,把家庭乃至宗族命运的改变,全部寄托在聪明的儿女身上。但缴不起罚款,无法入户,小孩上学遇阻,就阻断了孩子的求学路,也阻断了龙继根对未来仅存的一点希望。
龙继根的悲剧,民政、教育、计生等部门,都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政府有规定,我们只是按照规定来。换句话说,相当于表明:龙继根的死,是因为他心理脆弱造成的,和相关部门和学校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这种官僚人格,自己的这种冷漠和不作为,有时候足以把弱者推向死亡。
一切看起来,似乎也是如此。但事件的发生,是有延续性的,是有前因后果的。龙继根的死,肯定和他自身心理脆弱有关,但压垮他的,一定是多个部门长期“共谋”的结果。
还有一种共谋,是无赖者耍泼和政府部门不作为造成的。《一个农民自证清白之死》(见第3期)一文中,吴伟青是个公认的老实人,他因一位83岁的老人指控“骑摩托车撞到了我”而惹上麻烦。事后,交警让吴伟青去交医疗费。吴伟青坚称“没撞到”,但出于好心,他还是出了一些费用。交警一而再、再而三叫他去缴费时,百口莫辩的吴伟青,选择跳塘自尽,以此自证清白。
到底撞没撞?警方事后的结论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事双方发生过碰撞或剐擦”。
但如果处理问题不是为维稳而维稳,可能就不至此。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权力者如果不给吴伟青更多压力,即将的这个春节,吴伟青或许还能和子女好好过过。但这些都永远不可能了。
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离去,让人们感叹:缺乏体制的保护,大家都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因为,社会已经变了,从30多年前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一些人那里变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用“害”字,有些夸张,但不夸张的是:每个人在进入别人操控的领域时,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被剥夺感。比如人们常抱怨:小孩上学要交赞助费;看病要给红包;办事要走关系,得送礼等等。
但我们在抱怨别人领域的同时,别人也在感叹我们的领域:和他们打交道时,同样遭遇种种不快和被剥夺感。
结果就是这样了:各领域之间不断封闭与隔绝自我,我们不愿和其他领域的人交流。我们生活在“指责别的领域胡作,与被别的领域指责为非为”之中。共谋的行为和思想,让我们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任—即便有真诚者的帮助,我们仍然感到担心。
必须打破这样的“共谋”,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