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女性”背后的性别政治
2014-09-10甄静慧
甄静慧
在中国,性工作者一直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除非发生扫黄风暴那样的重大事件,否则,想要媒体乃至主流学术界正儿八经地关注她们,似乎不太可能。即便是,引发的舆论关注点依然逃不开“猎奇”的俗套—灯红酒绿、艳舞女郎、性交易。
然而全民狂欢的舆论盛筵当中,唯独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在政治正确的整肃需求之下,每次都被率先推出台前示众的性工作者,造就她们命运的文化根源又是什么?
性工作者是色情产业利益链条里的弱势群体—这个提法在中国社会尚未得到普遍认同。与之相对的是,有媒体曝光夜总会小姐月收入一两万,大大超出普通白领和基层公务员;某地性交易市场供需两旺,小姐其实去留自如;她们的选择背后,也未必有什么惨绝人寰的故事和家庭背景。这些都是事实。
然而对单一个体的评头品足,并无助于理解整个群体命运形成的社会根源。
事实上,自女权主义兴起,“妓权运动”一直是国际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妓权主义组织,比如中国香港的“紫藤”组织,有的还印发乃至出版了许多相关刊物;然而在中国大陆,妓权运动力量微乎其微,其有限的表现形式仅局限于对“性工作非罪化”的争取,其结果还一直是挫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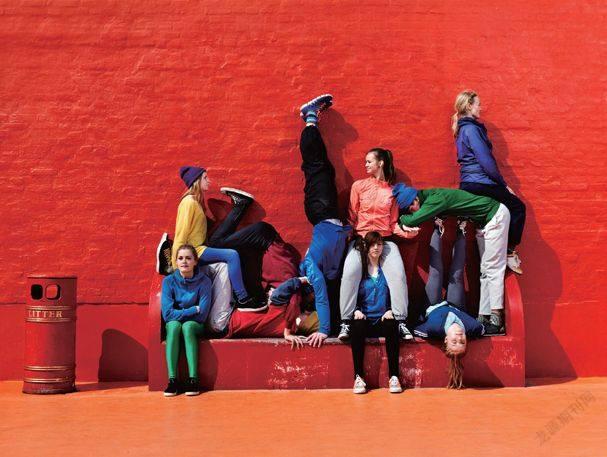
女性如何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平等竞争机会和上升空间?
我们很容易总结出,主流文化对性工作者的贬损及对其权益的取消主要基于两大理由:其一,带有交易/交换性质的性是不道德的;其二,从事性工作意味着好逸恶劳、不劳而获。
然而,女权主义如果单纯就这两个理由进行批判,如过度合理化“身心分离”,简单强调性工作的劳动属性和自由意志,很容易掉进一个逻辑陷阱,即忽略了整个社会文化和性别政治对女性的物化、异化,乃至性工作者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真实处境。
这里要讲一个发生在某一地级市人民广播电台的故事。
岑敏,女,5年前23岁,本科毕业。她曾觉得自己很幸运,一毕业就顺利地从到电台应聘的3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广播新闻记者。然而刚刚兴奋了两个月,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她所在频道的副总监是个50多岁的男人,入职以来对她表现得很是关注,没过多久,竟演变成了露骨的性骚扰。
随后她才得知,副总监的“咸猪手”已是公开秘密,所有女同事都深受其害。但更令她意外的是,当她建议联名举报,维护自己的尊严时,不但得不到任何人支持,还被警告“不要闹事”,“能保住工作不容易”,“又没有把你怎么样”。最后,不愿顺从潜规则的岑敏只好默默辞职。
对职场女性的采访中,这样的故事轻易就能听到很多: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面试后收到人力资源总监派发的自家别墅钥匙;另一位白领,揭发上司强暴未遂后,上级的处理方式仅是让施暴者口头道歉。
大量社会研究和数据证实,拥有同等学力和实习经验的女性,在社会中往往却无法获得和男性同样的平等竞争机会和上升空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研究所针对北京市民的一项调查数据:70%的受访女性受到过职场性骚扰,然而能诉诸法律并得到支持的个案微乎其微。
也就是说,在性别文化基础、教育方式和社会现实压力的多重围剿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都在时刻面临着被要求以身体资本换取社会资源的诱惑、鼓动甚至恐吓。
2011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Roy Baumeister在4月的《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性交市场上的文化多样性:两性平等与更多性行为发生的相关性研究》文章。其理论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男人比女人更喜欢性,所以男人千方百计诱使女人接受金钱补偿并与其发生性关系;其二,一旦女性认同自己需要以性来向男性换取社会资源,基于供求关系,她们会一致同意减少性供给,以抬升性的“价码”。
Roy Baumeister的第一个假设前提,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人们一直相信男人倾向于更多的性交,这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然而现代心理学发展却证明了,造成女性大比例性欲低下以及男女间性需求度不匹配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性别政治和文化压力—比如在强大的守贞文化下,女性被物化,失去对身体和性的自主权,“良家妇女”唯恐被主流社会唾弃,只有主动压抑性欲。
那么,当女性群体无意识地整体屈服于这样的性别处境时,“良妇”和“荡妇”本质上有何区别呢?笔者的中学母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学府,教学质量优良,很多学业优秀的女同学未来的愿望却是把自己打造得越发知性优雅,最后踏足上流社会,嫁个富有的夫婿。
若说这种努力无异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件艺术品找个好买家,可能有点刻薄,然而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批判资产阶级以金钱利益为纽带的婚姻家庭关系相当于“卖淫”,区别只在于“计件出租”还是一次性出卖。近几年“越南新娘”认购市场的兴旺,更是把婚姻的交易性摆上了台面。
性工作者則是另一种女性,她们揭开了包裹在性别政治表层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女性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真实处境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每一个人面前;把充斥社会每个角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交换”演绎成了赤裸裸的交易。
所以她们的“自由”与“尊严”注定为当下社会语境所不容。
社会一边操纵对女性的物化,一边挥舞道德大棒打击“妓女”和“荡妇”,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在以“守贞文化”为代表的性别权力需求下,女性被要求仅在道德文化语境默许的范畴内进行“交换”。而性工作者主动将“性”资源从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中剥离出来,自由进行交易,象征着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主流道德观的操纵,带来一种失控的危险。所以,社会既需要她们来填补情欲低下的“良妇”们所无法满足的欲望,又在道德上狠狠打压她们,不能让她们太得瑟。
“良妇”往往也是讨厌“妓女”的。Roy Baumeister用市场理论去解释这一点:“荡妇”是性供求关系的破坏者,她们以短期交易和价格低廉等方式扰乱市场,打击“良妇”们对贞操和性资源价值的心理预期。
但笔者却更愿意从精神和心理层面去理解。社会和人一样,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对一个无意识地屈从了社会性别文化陷阱的女人而言,如果“良妇”的价值观对应着其内心由社会道德内化而形成的“面具”部分,那么“妓女”的命运则更像是其内心深处被压抑的“阴影”。
看着“阴影”在眼前晃荡,女性自觉的反应是痛苦。除非女性能够觉醒,看到性别文化为其编造的贞洁童话背后的真相,由此她才能理解性工作者作为女性群体的一分子,她们背后有着共同的命运推手。
或许也是基于这些因素,性工作者在备受主流文化贬损的同时,又被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视为性革命和性别解放的先驱—“性工作是工作”尤其成为女权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之一,其强调的不仅是性工作的工作属性,还有女性选择从事性工作的自由。
性工作当然是工作,无论它是否体面、从业者是快乐还是痛苦、屈辱。但对“自由”的理解则需要很谨慎。是争取未来的自由,还是强调现状本身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于后者,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温和的女权主义者持保留意见。
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曾撰文指出:性工作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劳动”。大量心理个案也显示,人若长期沉溺于“身心分离”的性行为,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当然,澄清这些分歧并不影响女权主义者们同心协力为性工作者争取“非罪化”及其他权益。恰恰正因为主流的社会性别文化未曾受到颠覆、女性仍然无法普遍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竞争机会、解放女性身体的观念革命未曾来临,性工作者长期被异化的生存处境更是值得担忧。如何改善它们,成为一个基本而迫切的社会问题。
由此,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性工作从业者,如何改善她们的生存环境,实在是一个很基本的社会问题。
诚然,很多人担心性交易非罪化会令更多女性为庞大的色情組织诱惑和操纵,这大抵是把“性工作者个体”和“色情组织”两个概念混淆了。
无可否认,中国现存的有组织色情业深处存在着不少权钱交易、暴力犯罪,顺藤摸瓜大有可为。而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性工作者的处境,将现实的存在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对真正正本清源的“扫黄”其实是有利无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