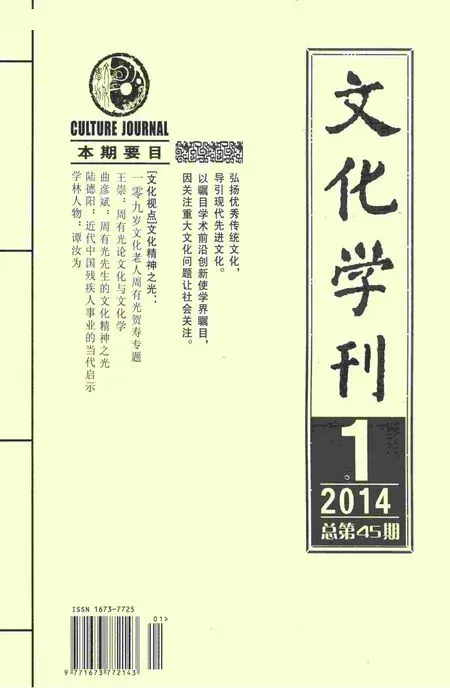认真对待“文化退化”学说——进化博弈论的视角
2014-09-07刘春兴
刘春兴
(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3)
一、引言
“人,诗意地栖居。”这是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一向喜欢引用的名言,它也是现代人心目中普遍渴求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然而,在斯坦利·戴蒙德 (Stanley Diamond)的眼中,现代社会早已失去了“诗意地栖居”的必要条件,如果一定要与这一美轮美奂的理想生活为伴,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到1万多年前人类文化初生之际的原初社会。[1]
在这里,戴蒙德使用了“原初”(primary)这一中性词汇而非“原始”(primitive)这一略带贬义的词汇,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事实上,这种向亘古时代追寻理想状态的怀古幽思在长达数千年的西方思想史中一直绵绵不绝,每当现实社会处于混乱或危机状态之时,人们的这种复古冲动就愈发增长。“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于遥远的文化他者即原始人的关注和想象从柏拉图时代就已拉开了序幕。”[2]
例如,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 (Hesiod)在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详细地描绘了人类文化退化的过程。[3]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没有贫困、没有痛苦、没有忧愁、没有仇恨,所有人都活得称心如意时代,然而,人类随后却堕入了“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 “英雄时代”以及“黑铁时代”。这些时代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在精神上都与“黄金时代”的人大不相同,其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他们渎神、放肆、粗野、纵情、残暴。在完全堕落的“黑铁时代”,人们罔顾公平和正义,到处是杀戮和欺诈,善良者无有回报,作恶者飞黄腾达,强势者鸡犬升天,多数人生活于无穷无尽的苦难和恐惧之中。
无独有偶,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先祖最初生活于伊甸园之中,他们天真无邪、快乐无比,然而,由于他们未能经受住诱惑而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因此犯下了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从此开始日日与苦难为伴,无休无止,并将在最后审判日受到追究。在遥远的东方,思想家老子极为推崇远古的“小国寡民”时代,[4]认为那时的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到了大型的文明社会,却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除以上哲理学思以外,在寻常百姓之中亦不乏渴求回到原始时代的热切声音,当然在许多时候都它们可能是戏谑或牢骚之语,但有时也可能是内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总之,在古今中外的许多心目中,人类文化史就是一部从黄金时代逐步衰败下来的历史。
那么,如此所思所想是不是彻头彻尾的异想天开而不值一提?抑或是可能具有某种科学合理因素而需要人们认真思索一番?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益昌明,在有些人眼中人类的道德水准却不仅未能随之提高,反而日益堕落?本文尝试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论证的起点始自两个重要的科学依据。首先,人类数百万年来一直生活于小型的“狩猎-采集者”社会,直到约1.1万年前的全新世来临之后才开始在大型社会中生活;[5]其次,人类的心理机制是由进化而来,长达数百万年的小型社会生活史塑造了与之相适应的“石器时代心灵”(Stone Age Mind),人类的社会认知能力是有限的。[6]
二、人类社会的合作进化机制
截止目前,进化生物学家们共发现了5种确保社会存续的合作进化机制,包括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选择与群体选择。[7]
(一)亲缘选择
亲缘选择 (kin selection)的概念由史密斯 (Maynard Smith)提出,[8]但其理论体系主要由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构建,[9]它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进化生物学的最重要进展之一。假定群体中合作行为贡献者的成本为c,接受者的收益为b,二者之间的遗传亲缘系数为r。这里的c和b均以进化适合度 (evolutionary fitness)为单位,它是一个用来衡量个体的自身存活以及对未来世代贡献能力的指标,在下文中将不再一一注明。r以个体之间基因组成的相似程度,即任意两个体之间由于具有共同祖先或直系亲属而拥有同源基因的概率来加以度量。例如,父母与子代之间是0.5,全胞兄弟姐妹之间也是0.5,祖孙之间为0.25,叔侄之间为0.125等等。
如果贡献者与接受者之间的遗传亲缘系数大于贡献者成本c与接受者收益b之比,即r>c/b;或者接受者的收益b与贡献者的成本c之比大于亲缘系数r的倒数,即

那么自然选择将有利于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进化出合作行为,从而在他们之间形成相应的社会规范。对式 (1)进行如此的公式变换是为了把已有的5种合作进化机制在数学表达形式上尽可能实现统一,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下文中的类似变换都是基于这一考虑。
亲缘选择理论的逻辑基础在于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个体而是基因,[10]基因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它的绝对自私性既可能导致个体之间的激烈生存竞争,也可能导致亲缘个体之间无私的合作行为。由亲缘选择的力量塑造的利他性行为规范通常镶嵌于个体的本能之中,一般不需要外在的力量予以维持。
(二)直接互惠
在生物界大量存在由非亲缘个体组成的动物社会,个体间也能保持密切合作并能维持社会稳定。亲缘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可由广义适合度的提高而获得进化上的补偿,但如果非亲缘个体通过欺骗行为从其他个体那里获得额外收益但又不必支付对价,其适合度将得以提高,因而欺骗行为很快就会在群体中扩散并最终导致整个群体崩塌。尽管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并非永远不会发生,但为何非亲缘个体密切合作的动物社会同样也很常见?
直接互惠 (direct reciprocity)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由经典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模型可知,[11]对于游戏双方来说单次博弈的纳什均衡 (Nash Equilibrium)是背叛,合作并不是理性的选择。但对于重复博弈来说,假定一局结束再进行下一局的概率为ω,贡献者的成本为c,接受者的收益为b,如果有ω>c/b,或者

则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将会有利于合作行为的保存而不利于背叛行为的入侵。
动物界中广泛存在着由直接互惠而演化出来的动物传统 (animal tradition),其中最典型的是食物分享规范。例如,倘若一种哥斯达黎加吸血蝙蝠 (Desmodus rotundus)个体在夜间未能吸到血,其他吸饱了血的非亲属成员可能反吐出一些给它们,饥饿者们将来也可能投桃报李,从而在个体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2]因直接互惠而演化出的习俗文化更是数不胜数,这一机制即使在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教人向善,自古推崇“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一报恩文化就是直接互惠的生动写照。不过,直接互惠对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有最低限度标准,它要求个体能够精确地识别其他个体并能记住曾经的互动关系,另外它也要求群体的规模不能太大,以确保合作行为贡献者和接受者有足够多的重复相遇次数。
(三)间接互惠
如果甲与乙合作,乙与甲合作,然后甲又与乙合作,那么这是直接互惠的典型形式,但在群体中也可能有另一种形式的互惠,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是通过第三方实现的,即间接互惠 (indirect reciprocity),它以个体在群体中的声誉为基础。
个体之间的相遇是随机的,一个作为潜在的贡献者,另一个作为潜在的受益者。在每轮博弈中,个体采取根据对手的过去表现而相机抉择的条件策略,只与那些声誉分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潜在受益者合作。令个体出生时的分数为零,与其他个体合作时加分,否则就扣分。如果在博弈中个体付出成本c而使得另一个体获得收益b,贡献者就能以概率q了解受益者的声誉分数,如果有q>c/b,或者

群体中基于间接互惠的合作行为就将会在进化博弈过程中得以保留下来。与亲缘选择相比,间接互惠是以个体间的熟悉程度替代了个体间的亲缘程度。
亲缘选择、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构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社会规范进化机制序列,它们在生物进化史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亲缘选择导致的合作形式比较简单,直接互惠也仅要求有足够的智力重复过去的一切,但间接互惠要求群体中的成员能够密切跟踪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其做出评价,因而对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尚未在其他动物群体中发现明确的间接互惠现象。间接互惠是维系人类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机制,并在塑造相应的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好面子,讲名声,甚至发挥到极至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面子文化都是这一机制发生作用的典型例证。
(四)网络选择
上述3种合作进化机制都暗含了一个假定:群体是充分混和的,个体都以相同的概率相遇并进行博弈。但在现实中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可能受制于空间或社会网络因素,基于进化图论模型的网络选择(graph selection)理论描述和解释了这种异质群体的进化博弈问题。
在社会网络图中,以顶点代表个体,顶点之间的连接线代表个体间相互作用。令个体的平均邻居数为k,在每一个连接中合作者的成本为c而受益者的收益为b。假定在初始时刻所有个体均为背叛者,这时产生了一个作为突变的合作者,其初始位置是随机的,如果合作行为的收益成本之比大于平均个体相邻数,即

自然选择将有利于合作战胜背叛,网络选择将会在该群体发挥作用并塑造新的社会规范。
对于具有空间结构的异质种群,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网络选择将能保持合作者种群的存在或促使背叛者种群转变为合作者种群,并且它不依赖于对策复杂性、个体声誉或亲缘关系等其他因素,是独立于亲缘选择、直接互惠与间接互惠的又一种合作进化机制。
(五)群体选择
上述4种合作进化机制都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群体内部,而对外部因素的影响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群体选择 (group selection)理论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早在19世纪达尔文为了解释工蜂或工蚁等膜翅目雌虫的中性不育现象就已提出了初步的群体选择概念,[13]对它的系统阐述主要由爱德伍兹 (Vero.C.Wynne-Edwards)完成但随即遭到威廉斯 (George C.Williams)的痛击而一度销声匿迹,[14]近年来学者们发现群体选择的条件在特定情形下是可以满足的。
假定某一地理区域内存在一个较大的集合种群 (meta-population),它包含m个小群体且m为常数,各小群体成员数量从1到n不等并且只有合作者与背叛者两类,集合种群的大小为T且有m≤T≤nm。令每一个体只与所属小群体的成员互动,贡献者付出成本c并使受益者获益b。如果在全部由背叛者组成的小群体中出现了一个作为突变的合作者,该合作者就必须首先占领其所在的小群体,进而通过合作者小群体占领整个种群。令小群体接纳的外来成员数平均为z,且有m和n远大于1,集合种群的个体总数一直保持不变且N=nm,如果满足

自然选择将会倾向于合作而不利于背叛。
在一个较大的集合种群中,如果小群体的数量足够多,小群体的规模足够小,并且在不同小群体之间个体的迁移也不是特别频繁,群体选择就能成为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进化机制并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演化出能够维护群体自身存在的社会规范。
三、大型社会的合作进化难题
上述5种合作进化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根本前提的。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小型社会中正常发挥作用,而到了大型社会则可能在整体上出现失灵问题,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由式 (1)可知r值越大亲缘选择的作用也就越大,r值越小则亲缘选择的作用也就越小。全新世之前的人类社会是由数个或数十个核心家庭组成的,r值较大,因此亲缘选择作为一股塑造社会规范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两性关系、抚育后代、血亲复仇以及乱伦禁忌等方面的规则都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全新世之后的大型社会主要是由不具有亲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r值越来越小甚至有r→0的趋势,导致其倒数1/r越来越大甚至有 (1/r)→∞,式 (1)成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尽管在大型社会中亲缘选择仍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它已经退缩至家庭、宗族或乡村等微观聚落,其作用就社会整体而言已变得微不足道。
由式 (2)可知ω越大,基于直接互惠的合作行为越容易保留下来,ω越小则直接互惠越难以成立。在小型社会中,博弈双方再次相遇的概率ω是很大的,直接互惠成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举个极端的例子,[15]在小说《鲁宾逊漂流记》描述的无人荒岛上,鲁宾逊和野人“星期五”几乎要天天相遇,对他们来说有ω→1,只要满足b>c,合作就可能永远进行下去。但在大型社会中,博弈双方再次相遇的概率ω很小,依靠直接互惠的力量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塑造相应的社会规范是不太可能的。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商业欺诈文化屡屡发生在火车站等人员流动性大、彼此再次相遇可能性很低的公共场所。
由式 (3)可知间接互惠的进化条件是b/c>1/q,基于概率的数学性质可知0≤q≤1,q越大,其倒数就越小,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q越小,其倒数越大,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小型社会中,由于个体之间长期处于同一个群体中并且互动极为频繁,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哪些人声誉好,哪些人声誉差,也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意味着有q→1,对于任意的b>c,间接互惠就能够在小型社会中成功演化。但在大型社会中,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导致他们能以较大的概率q识别互动密切的亲属、亲友或长期共事者等少数人的声誉,但对于更多的社会交往对象就很难办到了,社会规模过大甚至有可能为沽名钓誉文化盛行而大开方便之门。从社会整体来看,间接互惠只能在小圈子或小团体中发挥作用,对于维持大型社会的合作秩序并塑造相应的社会规范是无能为力的。
式 (4)给出了网络选择的进化条件,它是针对异质种群的合作进化问题而提出来的,k越小,网络选择越容易成立;k越大,网络选择就越难以成立。在小型社会中,任意时刻的个体间互动都可被编织进一个或数个小型互动网络之中,整体的社会互动状态就由少数几个小型互动网络所组成,因而网络选择就能够在小型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大型社会中,任一时刻的整体社会互动状态由极多的小型互动网络所组成,网络选择只能在这种小型互动网络的内部发挥作用,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其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群体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从更大的集合种群视角来观察小型社会的合作进化问题,由式 (5)可知其进化条件是b/c>1+z+n/m。对不等式右侧的解析式而言,n越小,则解析式取值就会越小,因而不等式就越有可能成立;n越大,则解析式取值就会越大,不等式也就越不可能成立。由前文中关于群体选择理论的推导过程可知,如果社会规模n超过一定的限度就需要对它进行技术处理,否则该理论就失去了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因此,群体选择只对小型社会的合作进化才有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这5种合作进化机制均不足以为大型社会提供必要的规范性文化支撑。然而,进入全新世之后的人类社会却逐渐扩大,早在约8,000多年前就在亚洲西南部的古代黎凡特 (Levant)地区诞生了超过3,000人的大型社会,[16]更不用说当代时代拥有上亿人口的那些“庞然大国”了。因此,除了这5种合作进化机制以外,进入全新世以后的大型人类社会必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合作进化机制,对它的详细探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暂时略而不论。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可否认的,在大型社会中,由上述5种合作进化机制支撑的人类文化必定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退化,这就是进化博弈论对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退化现象所给出的解释。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歧义颇多的概念。依照爱德华·泰勒 (E.B.Taylor)的经典定义,[17]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它的外延是非常宽广的,但未能把物质文化涵盖在内,因此奥格本(W.F.Ogburn)等人在对泰勒的定义进行修正时,重点就是把物质文化或实物文化纳入了进来。
一般来说,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或制度文化等次级文化现象。但文化学者们对文化的分类各有不同的做法,常见的有两分法、三分法或四分法等,其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事实上,如果以“规范性”为标准,文化又可以分为规范性文化与非规范性文化。前者主要是指对人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引或强制作用的文化,如习俗、惯例、礼仪、道德、宗教或法律等;后者是指对人的行为没有直接指引或强制作用,但可能具有间接指引或强制作用的文化,如文学、音乐、舞蹈、手工艺或科学技术,以及各类有形的物质文化等。
非规范性文化通常不存在退化问题。如果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如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毁,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以及因环境恶化导致楼兰古国消亡等,那么这类文化多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积累。相对于小型社会,大型社会中的非规范性文化甚至更有可能得到加速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都出现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原因之一。
由于人类的有限社会认知能力,因此在由小型社会向大型社会迈进的过程中,那些由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选择和群体选择这5种合作进化机制所支撑的规范性文化却注定会出现退化现象,这是一个与个体的主观美好愿望无关的客观历史进程。多种多样的规范性文化是社会保持稳定和向前发展的制度基础,它的退化必然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因此,人类社会必定已经演化出了某种新的合作进化机制,具有强制力量的警察、法庭或监狱等形式上的第三方机制或许就位列其中。它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规范性文化的进一步退化,却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消除这一趋势。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现代社会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文化光谱两极化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越来越昌明,文化艺术越来越丰富,公民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这些非规范性文化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都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日益冷漠,道貌岸然的教士最终被证明是猥亵儿童的惯犯,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常常令警察疲于奔命。不仅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急剧的现代化转型,其中一个显著方面就是大量人口开始从乡土村落移居到城镇社会。分别在小型社会和大型社会孕育而成的规范性文化迎头相撞,常常导致激烈的城乡文化冲突,农村“凤凰男”与城市“孔雀女”之间的相互吐槽更是经常在水木社区等高校BBS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口水大战。
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人类已经选择了一条无可回避的大型社会之路。疾驰在这条道路上能让人类领略到无穷无尽的窗外美景,与此同时也就不得不忍受一路上的颠簸之苦。只要人类仍要生活于这颗蔚蓝色的星球,某种程度上的人类文化退化现象就是大型社会赠予我们而我们又不得不接受的伴手礼。
[1]斯坦利·戴蒙德.寻找原始人[M].新泽西:事务出版社,1974.125 -126.
[2]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的“原始情结”——从<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到<原始人的挑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5):97-110.
[3]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M].纽约:佐内出版社,2006.25 -31.
[4][先秦]老子.老子[M].饶尚宽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45 -190.
[5]伯诺瓦·迪布勒伊.强互惠与大型社会的诞生[J].社 会 科 学 哲 学,2008,38(2):192-210.
[6][美]巴斯.进化心理学[M].熊哲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83.
[7]马丁·A.·诺瓦克.合作进化的5条规则[J].科学,2006,314(5805):560 -1563.
[8]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群体选择与亲缘选择[J].自然,1964,201(4924):1145 -1147.
[9]W.D.·汉密尔顿.社会行为的基因遗传(Ⅰ)&(Ⅱ)[J].理论生物学杂志,1964,7(1):1-52.
[10][英]R.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62 -63.
[11]罗伯特·L.·特里弗斯.互惠利他的进化[J].生物学季评,1971,46(1):35 -57.
[12]杰拉尔德·S.·威尔金森.吸血蝙蝠的食物互惠 分 享[J].自 然,1984,308(8):181-184.
[13][英]达尔文.物种起源[M].舒德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4 -157.
[14][美]威廉斯.适应与自然选择[M].陈蓉霞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4-98.
[15][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M].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6]伊恩·库伊特.早期农业村落的居民与空间:探索前陶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日常生活、群体规模与农业[J].人类考古学杂志,2000,19(1):75 -102.
[17][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