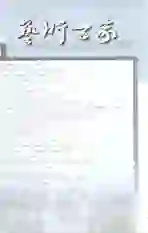《蒙娜丽莎》的研究综述与反思
2014-09-02饶黎
饶黎
摘要:15世纪达·芬奇创作的肖像画《蒙娜丽莎》在五百年的历史中被不断阐释,艺术史学者瓦萨里、佩特、沃尔夫林、弗洛伊德、帕朗第及杜尚等揭示了她优雅、邪恶、荒诞等多个不为人知的面貌。本文通过梳理这些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思考诸多研究之间的联系,期望追本溯源、寻找规律及挖掘出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作品;艺术史学者;图像;传统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Review and Introspection of “Mona Lisa” Study
RAO Li1,2
(1.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17)
15世纪达·芬奇创作的肖像画《蒙娜丽莎》在五百年的历史中被不断阐释,艺术史学者瓦萨里、佩特、沃尔夫林、弗洛伊德、帕朗第及杜尚等揭示了她优雅、邪恶、荒诞等多个不为人知的面貌。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是否截然不同或存在共性,他们的研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以及对研究的追溯,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
从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19世纪之后,艺术领域对这幅画的研究热情普遍高涨。这幅白杨木质板面油画,高77厘米,宽53厘米。创作时间大约从1500年始到1503年止,前后差不多四年时间来完成。从罗斯·金恩的描述,可以推断,这幅举世闻名的画创作于达·芬奇人生的转折点,即从服务了十七年的米兰斯佛扎宫廷回到了久别的佛罗伦斯,画完《蒙》之后,他便投入到了亚诺河改造计划,并赢得了政治家马基维利的支持。很有可能那段时间,他业余从事绘画,军事工程领域才是他真正的理想和兴趣,这方面也影响了他的绘画观念。那么,15世纪的达·芬奇是怎样描绘《蒙》的呢?最早的记载是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及画家瓦萨的《名人传》中的细致描写:“这幅肖像是艺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模仿自然的典范,最灵巧的手能描绘出的一切细节,在这里都充分表现出来了。那双湿润明亮的眼眸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典型,眼睛周围那生动的红色小圈和毛发,不经过最精细的刻画,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眼脸也自然得体,睫毛浓密,每一根都经过细致的描绘,曲折自如,宛如出自皮下,极为逼真。鼻尖上那完美柔嫩的粉色鼻孔真是栩栩如生。嘴唇微翕,从玫瑰红唇到鲜嫩的粉颈,无处不是生动的肌肤而非颜料堆砌。如果人们凝神观看喉头的凹陷之处,仿佛还能感受到脉搏的跳动。的确,我们可以说,这件作品的描绘方式足以让最大胆的艺术家绝望。”
瓦萨里的这段评述大约写于1547年。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幅肖像画,这种描绘基于瓦萨里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模仿”,借用了传统的文学修辞,赞扬了达·芬奇高超的绘画技巧。而这种模仿能激起人的想象力,在脑中产生虚幻的图像。而幻像或错觉基于达·芬奇对解剖、透视、比例及军事工程等科学的普遍的热爱和研究。艺术家运用色彩和线条使平面产生立体真实的错觉,而最终“模仿说”和“理念说”在艺术理论中产生了对立,并影响深远。①在瓦萨里淋漓尽致的描述中,重塑了这幅画的生命力,《蒙》是一首恋人的抒情诗。它和抒情诗之间的比较显然是彼得拉克式的,让人想起了文艺复兴时代诗歌中最著名的绘画《西蒙涅·马尔蒂尼的劳拉肖像》。很有可能瓦萨里有意识地模仿那个传统,他用言情文学和美的意境中的词句来描绘《蒙娜丽莎》。
新柏拉图主义者瓦萨里的描述也显然受那个时代文人影响,如普鲁塔克的《人物传记》一直被瓦萨里奉为楷模。这种描述的传统,直接追溯到古代希腊。在西方美术史中有个来源希腊文的特定的词——ekphrasis,国内译为“艺格敷词”或“造型描述”。使用的目的是为了赞美达·芬奇精湛的绘画技巧以及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刻画。这种描述图像的逼真性和生动性能够刺激欣赏者的创造性想象,引起人从表面和深层解读人物精神面貌的欲望。
艺术史家马丁·坎普说:“它对我们做出了反应,所以我们对它做出了反应。”图像的二重性,一方面使欣赏者产生了想象或幻觉,进一步深入解读图像,从而发现隐藏的内在秘密;另一方面借此描述刺激欣赏者,产生审美快感。《蒙》的肖像画正如彼得拉克《歌集》中的审美体验:“当我有机会看到您那娇媚的面庞,我就把世界上的一切都遗忘,当然,您那甜蜜笑脸漾出的甜蜜酒浆,直到目不转睛地看到您而心情舒畅,……”瓦萨里描述的蒙娜丽莎肖像与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同样让人产生了图像幻觉和审美愉悦,即语言的视觉形象魅力,带给人心理的审美体验。不同的是,瓦萨里不仅再现了达·芬奇高超的绘画本领,还体现“人性的力量”——难以捉摸的微笑、平静和谐的内心。这种表现类似于中国画中的“气韵生动”,对“形和神”完美的表达。很容易就会发现,《蒙》的背景酷似中国式的风景,还像精致的地形工程图,他所使用的“渐隐法”把过于粗糙、生硬的外形柔化,多用于远处或者转折处,这是达·芬奇的发明。按照瓦萨利的说法,这是掌握绘画完美手法的标志。画中的蒙娜丽莎是迷人的,背景也不同于同时代其他画家的处理方式,“渐隐法”让风景画背景就像彼得拉克的诗句一样,更加地诗情画意。
13至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价值观念的发展,源自对基督教统治下中世纪的批判,对古希腊文化的热爱和重新发现。人的观念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莎士比亚、蒙田等的观念里居于核心的地位,无疑,蒙娜丽莎也展现了神性和人性的光辉,肯定了人从自然状态脱离而存在的意义。然而,到了16世纪,宽容的时代结束了。1525年,马丁·路德发表了《论意志的束缚》,认为人是“受束缚的、悲惨的、被俘虏的、有病的和死寂的”。此时权威已经重新确立,开始压制人文主义的精神自由,反对强调人的现世活动。接踵而来的是17世纪宗教的复兴。此后,一批哲人逐次点亮了世界的光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动摇了教会的权威,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打破了理性的秩序,重视感性的力量,直至康德集中于人的经验、意识与想象的创造,连接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endprint
在这样的环境下,18世纪的人们更加仰慕瓦萨里最崇拜的米开朗基罗,还有其他的画家,如拉斐尔、提香、伦勃朗等。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对马基雅利《君主论》里充满谋略世界的重新审视,随之对达·芬奇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俘获了歌德、佩特以及弗洛伊德等精英人士的心。
实际上,《蒙》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变得有名起来。意大利雕塑家鲁伊吉·卡拉马塔制作了《蒙》的铜版画。乔治·桑、肖邦和安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名人慕名拜访,感到迷惑不已:“这颗让人着迷的头颅,隐藏在半明半暗的神秘光线里,显得那么的祥和和骄傲,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挑衅的味道。她那浅浅的微笑,偶尔让人觉得有点邪恶。她那跨越时空而又魅力无比的凝视,对我们充满了诱惑。”
蒙娜丽莎的神话已经流传开来,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诗歌《灯塔》字里行间折射了蒙娜丽莎甜蜜、神秘的微笑。波德莱尔同时代的诗人戈蒂埃笔下的蒙娜丽莎同样的迷人和危险。19世纪,被理想化的女人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角色,对《蒙》的阐释出现了另一条路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19世纪美学理论家沃尔特·佩特说:“比周围的岩石还要古老,她像精灵一样,多次丧生,因而暗知坟墓的秘密……”
佩特对蒙娜丽莎优美的解释,与瓦萨里的描绘相比较,几乎脱离了客观的描绘,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创造性地阐释了一幅肖像画,使一幅画成为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他独辟蹊径,避开了抽象美,以细腻诗意的手法,描述了一个脱俗的蒙娜丽莎。他的思想和拉斐尔前派有联系,罗斯金的观念对他也有影响。其美学观念不受社会或道德观念的制约,与物质无关。
总体上说,佩特对于美的基本观点:是感性、审美化,是主观印象的自我表现,具有浪漫、普遍向上和启蒙的精神。他的批评理论强调必须超越个人印象,进入普遍把握艺术品独特品质的能力,即透过文艺作品本身看到创作者的内部精神世界。他把达·芬奇看做人性的触动者和自然的解释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疑惑不已,发现在达·芬奇的世界里,爱情缺席。他认为,蒙娜丽莎唤醒了达·芬奇对其母亲使人着迷的幸福微笑的记忆。弗洛伊德对此做出一番精彩的精神分析,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现出影响达·芬奇一生心理情感结构及其创作动力的秘密“恋母情结”。
同样的研究热情出现在英国唐纳德·萨松著的《蒙娜丽莎微笑五百年》中,他研究了一个“高雅文化”的产物如何变成大众消费的对象。Donald Capps认为蒙娜丽莎在男人心目中取代了玛利亚的地位,是忧郁信仰的标志性形象,绘画作品能够帮助自然治愈,把忧郁转换为哀伤。Lillian F. Feldmann Schwartz通过计算机技术、对蒙娜丽莎和达·芬奇图像的拼合及历史研究,认为达·芬奇以自己为模型画了蒙娜丽莎这幅画。其他的研究见意大利的学者朱塞佩·帕朗第的著作《蒙娜丽莎——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佛罗伦萨妇女》、《达·芬奇的数字迷宫》等。还有杜尚恶搞的作品尝试反叛传统的文化,摄影师哈尔斯曼夸张篡改了优美的面容等。从20世纪杜尚对经典作品的嘲讽,宣布了一个“图像化”时代的逼近。
综上所述,《蒙》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呈现出了一脉相承的关系,佩特、弗洛伊德、帕朗第、阿塔拉伊以及卡普斯,在继承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延伸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在认识的过程中,似乎我们一直在遵循千年的思维模式演绎和延伸,正如我们根本无法拥有一个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崭新世界,不断地沿袭传统的脉络和把握时代的精神,去发现和寻找新的规律。对传统的重新认识也是人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尊重传统的精髓,是尊重创造力、人和世界的真谛。(责任编辑:贾明哲)
① [美]潘诺夫斯基撰,高士明译《理念:艺术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页。
② [英]唐纳德·萨松著,周元晓、赵永健译《蒙娜丽莎微笑五百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