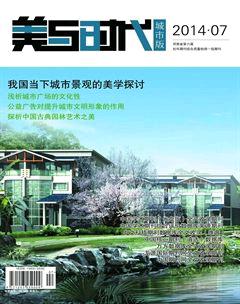族裔散居与异域视野下的“Culture Shock”
2014-08-20李慧研
李慧研
摘要:
影片《撞车》通过多线索叙事,讲述了一系列不同族裔在异域视野下发生文化冲击的故事,通过不同人物身份对本源文化的指代,实现了多种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的对话。
关键词:文化冲击;身份认同;族裔散居
影片《撞车》讲述了一连串由于车祸而引出的故事,影片取名为“Crash”有双关之意的,一方面故事从一场真正的“crash”展开,另一方面,“crash”所代表的“冲撞”之意,是在指代“culture shock”。
影片中的Culture shock,从人物设计和剧情发展角度来说,有几种不同民族的外来客和几组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关系。黑人混混、导演、医生、亚洲司机和偷渡客、拉美裔的锁匠、波斯店主、白人警察法官……这一个个角色与他们不同肤色不同职业下的身份标签,构成了这部影片中的戏剧元素。
文化研究学者陶家俊曾在《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将身份问题归结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以及社会认同[1]。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解析影片,影片中包涵的多种文化身份之间的culture shock,本质上就是社会认同的问题,放置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的特殊环境中,因而带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
影片采取了多线索叙事的方式,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们天然带有的文化冲突成为了影片推进的叙事动力。人在寻求个体认同的时候,会对于非同源文化带有一种排他心理。同源文化的历史积淀为这一民族赋予一种标签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遗留的物质财富共同构成了这一民族独有的文化身份。
这种文化身份逐渐成为一种外化的标签,而这种标签常常伴随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日常的“差异化交往”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或者说“思维偏见”。在影片中,白人警官对黑人夫妇的盘查、白人店主与波斯人的语言冲突等等桥段都有表现,这不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冲突,是一个族裔对另一族裔的思维偏见。就拿片中波斯人一家来说,因为与阿拉伯人容貌相近,让生活在美国的他们处境艰难处处受到不公平待遇,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端引来的私人恩怨,而是911事件后的美国对恐怖主义人人恐慌的影响下,美国人由恐怖主义产生并向阿拉伯人拓展的仇恨情绪。美国人的这种恐惧心理,一方面来自社会紧张局势下地暴力恐惧,另一方面来自文化融合中的未知和排他心理。集体间的文化差异与思维偏见,只能以个体的冲突来表现,影片中选择了几组关于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旨在表现全球化视野内的“culture shock”。
而在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有一个前提不能忽视,即“承认差异”。从多元文化冲击以及文化差异角度解读这两个警察角色,显然小警察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理解文化差异也尊重文化差异的人,但是在内心深处,对于他族文化还是因为未知而缺乏信任感甚至安全感,以至于他虽然邀请了黑人混混搭车,但是却在两人的交谈中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甚至由于精神过度紧张,防卫过当开枪打死了本无意伤害他的黑人混混。他身上所代表的是成长在全球化和多族裔散居背景下的新一代美国人,接受主流推崇的反歧视教育试图从个人开始改变社会对于少数族裔的不公平待遇,而这种行为转变的前提是他在内心中认同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社会阶级,而黑人处于低于白人的下等地位,因此他在内心中,对于黑人是俯视的怜悯视角。而反观青年警察,他是一个不能轻易用好坏界定的人,在影片中,他以一个刁难黑人夫妇的坏警察形象出场,与白人政客的妻子一样,充当着主流社会看向少数族裔的“有色眼镜”,他出言羞辱医院的黑人女职员,认为他们黑人的身份为他们在“反种族歧视”的当下获得了更多的特权,这种特权的本身就是对社会各文化族裔差异性的强调,扩大少数族裔的特权是对社会矛盾的加重。他将对政策的不满对患病父亲的担忧统统发泄到生活中的黑人身上,以求得所谓“是白人占据美国上层社会”的心理平衡,但是当他发现车祸中被困在车内的正是前一晚被他猥亵的黑人妻子的时候,他还是尽其所能冒着生命危险将她救了出来。他的角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种族歧视的情绪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政策面前对给予少数族裔的优待而不满,“羞辱黑人”是对生活中不如意而且不受到主流社会保护时烦躁情绪的发泄,但是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面前,仍然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
罗伯特·麦基在其著作《故事》中写到,“人物真相只有当一个人在压力之下做出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该选择便越真实地表达了人物的本性[2]”。影片中这一对警察搭档的形象对比鲜明,危急关头的不同选择是对原有形象的颠覆,这种颠覆本身揭示的是他们在社会身份之下的真实“自我”。
这两个警察在影片中都经历的这种前后形象变化,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都看到了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只不过一个在通过强化这种差异来表现自己对他族文化的尊重,而另一个却用缩小这种差异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对于没有任何文化标签的“生命”的尊重。
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曾谈到关于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问题,他认为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也是“变化的”,那些隐藏在同一种族文化共同点之下的差异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3]。
站在美国的异域视野下对于不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做历时研究,就是影片中一环扣一环的“culture shock”的来源,其本质就是霍尔所说的那种以同源文化的差异演变形成的“真正的现实的我们”。而站在这种全球化视野的横切面看待多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普世价值观的真善美是任何民族文化经历怎样的演变无法磨灭的精神内核,这种普世价值观可以跨越疆域、国界、肤色,获得不同文化身份的共识。
这种普世价值观,是影片中黑人妇女被白人青年警察救出的时候无声的回望,是黑人母亲看到儿子尸体那一刻撕心裂肺的哭喊。影片在小女孩扑向父亲以小小身躯挡子弹的时刻达到情感高潮,正是因为获得观众情感共鸣的,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亲情。
在影片的最后,白人警察拥抱着年老的父亲,黑人警探安抚着失去小儿子的母亲,父女平安,夫妻和解,虽然失手杀人的白人警察还在彷徨着不知去向何方,但是黑人混混却在金钱利益面前选择了释放一车的东南亚偷渡客。在美国的异域视野下,每天都在发生着“文化冲击”,每天也都在发生着“文化和解”,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因为文化的差异本身就无法通过任何手段去约束或改变。用人性的大爱去包容不同文化身份背后的文化差异,是导演用这样一个复杂的冲撞故事讲给世人的秘密。
【注释】
[1]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3):37-38
[2]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18
[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群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