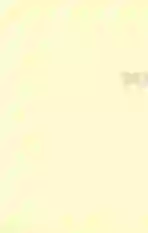先锋、成长经历、现实
2014-08-19刘涛
刘涛
在“70后”作家群体中,魏微出道甚早,我闻魏微之名亦有日也。昔日在复旦读书时,听郜元宝老师课,彼时他热衷于南京作家研究,上课时屡屡评及他们,其中也包括魏微。之后,我来北京工作,某年曾跟张楚、朱文颖等与魏微小聚。
揆诸魏微的作品,计有三个关键词:先锋、成长经历、现实。
一、先锋小说
魏微起步之初曾醉心于先锋文学,小说写得恍兮惚兮,朦朦胧胧。魏微自述读书倾向道:“我的趣味并不高尚,也因此,古典名著的好处我无法领略。很多朋友向我推荐《包法利夫人》,每推荐一次,我就重读一次,技法,结构,白描艺术,人物塑造……我知道它是好的,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好。……我读现代小说,完全是心领神会的。像被人说中了一段隐秘,那里头的弯拐抹脚处,被分析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可怕的,可是可怕之余,也觉得欣喜和放松。我第一次读卡夫卡是在1990年,读的是短篇《判决》。在此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现代小说,我也不知道卡夫卡是谁。我仅是把它当做短篇来读的。读完后,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是惊讶。我于其中发现了小说的另一个空间,广阔的,具有新鲜刺激的质地,就像一道豁口,隐隐露出暧昧的光亮来,然而这光亮是我熟悉的,也让我害怕。” [1] 魏微这段话好像开悟者现身说法,卡夫卡让她看到了光,她从卡夫卡身上获得了“启示”。 [2] 魏微这段话,大致道尽其精神及思想资源。
魏微具有先锋色彩的小说有《在明孝陵乘凉》、《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寻夫记》等。
《在明孝陵乘凉》说的是“那年夏天,小芙和哥哥炯、女友百合去父母的单位明孝陵乘凉”的故事。“那年”是指“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经结束了,全民性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青黄不接的潜伏时期。女人们穿着朴素,看不出是公的还是母的。不多的‘文革时代的标语还残留在豆浆坊和烈士陵园破落的土墙上,在太阳底下打着盹。新时期的片言只字‘张海迪、‘五讲四美充斥于南京的街头巷尾,带着慌张和错落,同样有种不抵实的感觉。”但《在明孝陵乘凉》的重心并不是要呈现新旧交替之际的时代氛围,而在于写少女和少男情感的萌动,写少女成长的经历和性意识。明孝陵乃是丧葬处,阴气充实弥散,但是两个少女、一个少男酷暑之际前去乘凉,为明孝陵带来了生机与生气。历史、人世就是如此,死生,生死,无穷已。小说描写道:“小芙的心里不由得一动,怔怔地站在那儿再也不能够动弹。大约是从走进陵园的那一刻起,她就发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异样。……她开始燥热、心慌,心跳加速。她想那时只有男子会让她安定下来。……百合嘻嘻一笑,像变戏法一样从背后拿出一张妇用卫生纸,不怀好意地问小芙:‘你猜这是什么?小芙当然知道。女厕所常见人用过。……小芙常常艳羡着,它给了她无穷的刺激和想象。她觉得它是女性的、污秽的、妖娆的,代表着她的未来的。她才十二岁,她简直等不及这未来了。”《在明孝陵乘凉》是非常精彩的一篇小说,写出了少女长成的特殊心理,少女情感萌动的娇羞之态;故事背景选在“明孝陵”亦好,小说由此而具历史感与厚重感。《在明孝陵乘凉》采用了先锋文学的手法,譬如作者反复诉说“那个夏天”,叙述时间亦被打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显得支离破碎。其后,魏微逐渐去掉了华而不实的枝叶,以平实的笔调写少女,反而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颇似卡夫卡的《审判》。作者以先锋文学的笔法写“审判”,丝绸商人被误捕入狱,遭严刑逼供,精神、肉体受尽折磨,终于成了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如何炼成”一度是显题,但魏微一反常态,不以现实主义而以先锋文学的笔调写此问题。故事发生在孤岛上,氛围大致如此:“江水浩渺泱泱,看不到尽头,彷佛永远是明天,空气里能闻到雨滴的气味。水草生得极为茂盛,它们相互缠绕,似乎有种疯狂的生命力。”审讯者不知是穷极无聊,抑或是富有使命感……难以判断;“审判”不合常规,极其蹊跷;人物亦恍恍惚惚。
《寻父记》故事情节较少,所写真真假假,或需要读者追寻线索来填充、凭借想象力来完成。“父亲”来路不明,“他是北京人,大学毕业,竟在这个荒僻、落后的小城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们甚至不能怀疑,他是个有档案关系和户籍的人,八十年代中期还补办过身份证”,某日父亲忽然离家出走,“我”和母亲四处找寻,但无果。“父亲”或指现实中的父亲,可能是因家庭矛盾出走,也可能父亲是知青,一旦厌倦,抛弃了“小芳”回城;或有政治含义,“父亲”象征着毛主席;或有“形而上”的含义,“父亲”象征着历史……
魏微处于先锋文学创作的阶段并不太长,之后她逐渐扬弃先锋文学,或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或关注现实问题,如此方倒是显出了她的本色。
二、成长历程
个人的成长经历是文学喜欢的主题:少男少女如何成人;在成长的路上,有多少“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悲伤欢乐、危险和愉悦,以及性的萌动等。
魏微出生于1970年,她幼年处于“文革”时期,之后则处于“新时期”。可是,若希望从她的小说中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则难矣哉。魏微写成长的小说中有人情世事,有起落,有巨变,但都是“琐碎”的,鲜及乎政治与时局。张学东与魏微是同龄人,他亦喜欢以儿童视角写世事,但张学东的小说往往带有“革命时期”的印记,而魏微的小说中则没有。
魏微写成长历程的小说颇多:《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储小宝的婚姻》、《姐姐和弟弟》、《姐姐》、《石头的暑假》以及长篇小说《流年》(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另有一系列散文《爷爷的日常生活》、《青春期轶事》、《妹妹与我》、《小城》、《成长1984》等。这一类小说构成魏微创作的重要部分,读者提及她,一般会想起她这一类的作品。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或有自述传成分。小说很散,围绕着“乡村”、“穷亲戚”和“爱情”这三个关键词展开。小说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写一个关键词。“我们家族”因为爷爷而离开了乡村,进驻城市,“到了我和弟弟这一代,我们已经完全地被改造了。我们开始过上富足的生活,有身份和地位。我们衣着优雅,谈吐精致,性情敏感而害羞。我们惧怕劳动,体质柔弱。”“我”和乡村的联系就是“穷亲戚”,他们时常进城走动,人人有其个性、自尊,通达人情世故,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我”和乡村及“穷亲戚”毕竟有了隔膜,“我”不屑于理他们,厌烦他们进家。“我”的“爱情”亦与乡村和穷亲戚有关。“无数次的恋爱在于我,就像一次恋爱。”因为奶奶去世,“我”回乡村奔丧,再度遇上了穷亲戚陈平子,“我”暧暧昧昧,情不知所起,似乎爱上了他,但也就是止于意念。奶奶丧事甫一结束,“我”就毅然回城,彷佛此前做了一场白日梦。
《储小宝的婚姻》写上世纪7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微湖闸居民的情况,储小宝是其中的一份子。小说通过“我”的眼睛写储小宝的婚姻情况,写一个干净的、纯洁的男子如何因为生活的艰辛一步步走向了落寞,变得邋遢,也写了“我”对他情感的变化。起初“我”是小女孩,储小宝“长得不算难看,干净,明朗,是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青年”,他时常逗我玩,“那时候,我是多么喜欢储小宝啊,我喜欢看他跑步,……我也喜欢听他跑步时,发出的‘啊啊的呼喊声”。储小宝与小吴恋爱,小说以小孩子的视角写他们的交往,真是美好。之后,因为储小宝和小吴做爱无度,引发公愤,被爷爷以整治“风化”之名公开批判。再之后,储小宝结婚,离开了微湖闸。很多年之后,“我”与储小宝再见。这是故事的高潮,颇似鲁迅《故乡》中“我”和闰土的再会。“我”情感大波动,小说写道:“不知为什么,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一下子哭出声来。那是一种丧心病狂的哭泣,伤心,丑陋,自暴自弃。我的鼻涕也淌下来了,它和泪水一起流过了我的嘴角,一直流下去了。我感觉到一种东西,它走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姐姐和弟弟》写姐弟关系。姐姐与弟弟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还是重要主题,但80年代之后因为计划生育,此问题几乎消失。“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因此儿童再也不知道如何为姐姐,如何为弟弟。小说以姐姐为主,写少女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波动,这些皆反映到姐姐与弟弟的关系中。小说写了姐弟相处的美好一面,也写了两人相处中不甚美好的一面:姐姐一度心情纠结,屡屡殴打弟弟。《姐姐》亦写姐弟关系,写少女、少男的成长历程,但过滤掉灰色的一面,侧重于美好的一面。譬如,弟弟作大人状,告诫姐姐“没事不要总趴在绣楼上。走路时不要东张西望。家里来了男客,要懂得回避。……”姐姐谈恋爱时,弟弟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调皮捣蛋,打碎别人家的玻璃……
《流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是魏微写少女成长经历的集大成之作。我以为,这部小说应是魏微的代表作,集中展现了魏微文学创作关注的重心、叙述风格等。
“流年”或取年华如流水之意,小说的主题是追忆似水年华。小说第一句为这部小说定了调:“那时候,我们住在微湖闸,我,爷爷,还有奶奶。我们住在水边,一个机关大院里,过着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流年》中的年华几乎没有时代特色,只写一个小姑娘如何成长,写她周边的人和事,写微湖闸;小说中没有政治风浪、大是大非,都是一些幸福的、枯燥的“日常生活”。微湖闸似乎是一个桃花源,这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代的变与不变似乎没有在此留下痕迹,这里都是日常琐事、家长里短、生老病死。《流年》体现出魏微极大的抱负,她不是要写一代人或某个特定时期,她要写永恒。魏微自述:“它们是日常生活。它们曾经和生命共浮沉,生命消亡了,它们脱离了出来,附身于新的生命,重新开始。远古洪荒,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生活,就止于这些吧。”这是魏微的“世界观”,也是她的“逝者如斯夫”之叹,她的这部《流年》就是要写出“变”中的“不变”。
《流年》“居高临下”,从大处写起;“楔子”颇似《红楼梦》开篇,然后一路往下,交代时代、微湖闸的地理位置、总体环境等,然后写一个一个的人:杨婶、储小宝、叔叔、爷爷、奶奶和“我”……他们各有性格,各有心事,也各有经历,各有不同的命运。“我”是儿童,在微湖闸中,但又似有若无;“我”参与了故事,又置身事外,懵懵懂懂。采用童年的“我”的视角,可以过滤掉很多世故或市侩气,可以看到生命中简单的、根本的、不变的东西。
在《流年》中,魏微的笔触是细碎的,笔调是舒缓的,情感是淡淡的,描述是细腻的,如此行文与“日常故事”极为恰切。随手引述小说中的一段话即能见出魏微的风格:“我还能记得那天清晨,我静静地倚在门边,看着她周围的一切;刚扫完的地,地上洒了清水,空气里有微微的灰尘的气味,清冽又有些刺鼻。我深深地呼吸着,觉得很心满意足了——我喜欢杨婶家里的很多东西,院子里的清晨,院门是洞开的,杨站长下早班了,从门口走进来;我听见了他的咳嗽声,还有沙沙的脚步声。客厅的五斗橱上有一只白瓷鼓,里面盛有我喜欢的糖果,桃酥,还有各种花色的小饼干……”
《流年》没有紧凑的结构、严密的逻辑,章节之间是松散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散淡的;人物都是微湖闸的一分子,他们各自独立,但也有关联。《流年》也没有通常意义上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所以一旦将其中的某些篇章抽离出来,即可单独成篇。《储小宝的婚姻》就是从《流年》中选取出来、略加改写而成,可它依然气足神完,如《流年》一样气足神完。
另外,魏微还有一系列回忆性的散文,也都舒缓如流水,对了解魏微本人的经历、文学志向、创作历程、时代变迁都有裨益。《爷爷的日常生活》写爷爷的革命史、工作史,写爷爷和奶奶的情感;《青春期轶事》写与弟弟、妹妹的相处,写她的童年和成长历程;《小城》写迁居小城的情况以及民风民俗等;《通往文学之路》叙述她的阅读历史、文学趣味、文学志趣等问题,由此可以了解魏微文学创作的大致风格;《1988年的背景音乐》写她在上世纪80年代听音乐、追星等历程;《写给南京》写她对南京的情感、理解……
文学写成长经历固然可以展现出大量有趣的、奇妙的细节,但若止于有趣的细节,还不能成为大作品。《五灯会元》中写高僧大德,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成长、漫游时代,二是为师时代。《五灯会元》写高僧大德的成长经历,摒弃了琐事,主要关注他们的精神成长经历,如此写成长才可能是更大的作品,而不仅仅止于趣味。
三、现实
先锋小说是魏微起步之初的文学资源,成长经历是她的记忆资源,现实题材的小说则是她关注当前、关注现实的结果。魏微对现实的关注范围很广:南京的日常生活、男女关系、家庭的家道兴废、乡村的状况等。魏微这一类小说的数量较多:有《薛家巷》、《大老郑的女人》、《化装》、《家道》、《姊妹》、《沿河村纪事》等。
《薛家巷》与《流年》类似,并非写某人某事,而是有着整体性的抱负,她要写一条南京巷子的总体情况,进而见出南京的日常生活。住在巷子里的是普通市民,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没有惊天动地之事,都是家长里短。想象中,南京乃是六朝古都,几许金粉,多少繁华,秦淮河的流水该有多么温柔……《薛家巷》所描写的南京则与此繁华无关,都是柴米油盐的、琐碎的、尴尬的、忧愁的、欢乐的日常故事。陈三是工厂工人;隔壁姜老太是退休护士,儿孙满堂,生活富足;吴老二是烤鸭店厨师,“生活很是‘得过”……
《大老郑的女人》虽写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风气,但重心在于写伦理问题。大老郑是“我们”家的房客,福建人。故事逐渐出现了变化:“有一天,大老郑带了一个女人回来。”这引起了家人的狐疑、猜测,但是这个女人本分大方,之后大家相处得宜,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故事又起了变化。忽一日,来了一个乡下男人,自称是大老郑女人的男人。于是,事情水落石出,但故事不是在激烈的冲突中结束,而是不了了之。作者也不曾站在捍卫道德的立场上批判大老郑或大老郑的女人,她对故事人物非常体贴,充满了理解与同情。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写相似情节,只是更为惨烈,读罢惟让人感动、慨叹,《大老郑的女人》亦收到了同样的阅读效果。
《姊妹》写三爷有一妻一妾。在今天的法律与伦理中,一妻一妾的情况不被允许,但小说中没有渲染法律和道德问题。《姊妹》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妻妾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爷的反应。两个“三娘”从势不两立、殊死斗争,到可以心平气和,最后乃至于形同“姊妹”。小说写道:“我的两个三娘就这样服从了命运的安排,认领了妻妾的身份,从此消失于街巷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不再剑拔弩张了;战争是需要体力的,从前,她们已消耗了太多,都伤了,怕了,疲惫了。”三爷也经历了从心力憔悴到心平气和。三爷、妻、妾,这样的三角格局竟然维系成功。《化妆》亦写男女关系,但颇似张爱玲的小说,解构了男女之间的美好。小说写嘉丽与其情人的历史与现状。嘉丽一度是丑小鸭,大学毕业前实习,与科长相恋。时过境迁,两人再度相见,嘉丽已腰缠万贯,但却“化妆”成落魄之态,二人之相见遂兴味索然。“化妆”可以通过隐藏真相而见出真相。
《家道》写家道的中落与中兴。父亲在位时声势烜赫,母亲与“我”亦得道升天;父亲一朝入狱,家道中落,如此母亲与“我”方体会到人情之冷暖。母女二人从头做起,历尽千辛万苦,家道中兴。家道兴衰的原因众多,要乎家人戒慎守礼。
《沿河村纪事》通过社会学考察者的眼睛写农村的变迁,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社会学著作如果写得正儿八经,未必能够见出真相,反而是叙述调查“琐事”的著作颇为有趣,譬如《林村的故事》。《沿河村纪事》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冠以社会学调查之名,而其实毕竟是小说。小说写农村教师与学生两代人多次前往沿河村,对其发展了如指掌。小说的重心在于学生一代对沿河村沿革、变迁的了解,而重心中的重心则写的是沿河村“关键时刻”几派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注释:
[1] 魏微:《通往文学之路》,《1988年的背景音乐》,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9页。
[2] 巴金《家》中提及,琴读《新青年》上的《娜拉》时亦曾感受到光,巴金写道:“灯光忽然亮了。”